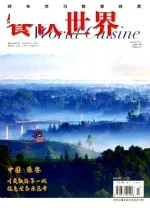京城時尚名廚之楊楊 廚界書生
文/Lucky
楊楊的書卷氣質不僅僅寫在臉上的那副眼鏡上,更多的是鐫刻在他的心里,進而融匯成一種思想,展現在其菜品的創意中。不過他也絕不是一個木訥的書呆子,融會貫通的烹飪知識,加上豐富的烹飪經驗,薈萃而成的是獨具個性的、帶有深刻文化內涵的、采用現代手法呈現的新中式文化主義餐飲。如果說多看、多嘗、多溝通是通往“高廚”道路的試金石,那么對于楊楊來說,多讀書以及貫穿始終的學習態度,則是其迅速找到自己的烹飪特點,并呈現給食客完全不同境界美味的捷徑。
讀書與烹飪不是兩條并行線
上世紀70年代還沒有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初中升高中的競爭也是相當激烈的。從小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的楊楊,在中考過后沒能如愿進入重點高中,“因為普通高中的風氣不是很好,父母給了我幾種選擇,一是‘找關系’進重點高中,二是上職業高中,踏踏實實的學門手藝。學手藝也有兩個選擇:園林和烹飪。當時我對園林根本沒有概念,只有一個思想:寧當雞頭不當鳳尾,所以最后選擇上烹飪學校。入校之前,父親總是有意無意地告訴我,當廚師什么都可以‘先嘗一口’,這就更增加了我對烹飪的向往。”帶著這種比較美好的憧憬,楊楊成了88屆廣安職業烹飪高中的一分子。因為成績出眾,入校后不久,楊楊便在各方面嶄露頭角,并成為班上的學習委員。“雖然當了廚師,我一直認為讀書和烹飪不是兩條并行線。在烹飪學校學習的時候,我都是按照一個正規的高中生的規范處處嚴格要求自己的。”一開始接觸烹飪理論課,楊楊就被那些面點理論知識、刀工理論知識、烹飪技巧、成本核算、原材料知識等深深的吸引,“過去認為烹飪就是做飯,但實際學起來才發現里面的門道有很多,是很博大精深的事情。”以刀工為例,理論課要先學習畫刀,熟悉各種刀型的用法和特點。刀工實操的第一節課是磨刀,學習用刀的不同部位切不同的食材、不同的形狀。“菜墩子要擺在離操作臺邊一拳的位置,人站的位置離操作臺邊也是一拳的距離,兩只手自然成45度角,每個細節要求都是相當嚴格的。”現在想想,楊楊認為,正是有這些看似古板的要求,才為自己日后的標準烹調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翻砂子、切報紙,都是必修課。記得我們課下經常進行的一項比賽就是端鍋,看誰端的時間長,其實也是練習臂力的一種方式。”
烹飪學校的學習帶給楊楊的不僅僅是理論和烹飪技藝,更打開了他的眼界,看到更加神奇的烹飪世界。“記憶最深刻的是李剛老師(現任北京市第103中烹飪職業高中的高級教師,特級廚師)專門來學校為我們上刀工課,他可以在菜墩上墊塊布切肉成泥而布不損,在大腿上墊綢布切肉成絲而綢不斷,看完表演之后,當時真是熱血沸騰,就想有一天能像老師一樣。”為了能像老師一樣出神入化,楊楊總是加緊練習。也正是因為理論基礎打的比較扎實,故而在后來接觸各種菜系、各種烹飪技巧的時候,楊楊比別人更能夠融會貫通。
超強的執行力贏得青睞
結束兩年的學校理論學習之后,楊楊開始了一年的實習期。“直到那時才真算是脫離了學生的身份,以一名廚師的身份走進后廚,同時也真真正正的切實感覺到當廚師的艱辛。”楊楊實習的地點在“歐美同學會”,這是北京飯店的合作單位,很多廚師都來自北京飯店。可能任何一個不起眼的廚師都是身懷絕技。像很多廚師一樣,雖然經過了兩年的理論學習,當楊楊第一天進入后廚,他也迷茫了。“不知道該干什么。師傅們都坐在一邊喝茶,也不管我們,現在想想應該是在悄悄觀察我們。直到現在我還記得特別清楚,旁邊有兩位阿姨在做職工餐,當時他們切的是圓白菜。就覺得自己不能閑著,再加上在學校的時候,老師告訴過我們進了廚房要‘眼里有活兒’,所以我趕緊把兩位阿姨請到一邊,自己干起來。可能就是這個舉動,給廚師長留下了比較好的第一印象。”

在實習的日子里楊楊再次感受到烹飪的千般變化。“在學校的時候,只學過川魯菜,根本不知道還有粵菜、譚家菜等,特別是每到有特別宴請的時候,師傅們就會從北京飯店帶過來一款非常高級的湯底,后來才知道那是譚家菜中的清雞湯。用這道湯做的菜都是些名菜。”雖然像清湯燕菜這種高檔菜楊楊沒有做的機會,但即便僅僅是看看,也是受益匪淺。有了上灶機會之后,師傅開始讓楊楊炒一些簡單菜式,因為基本功扎實,加上他尊師重道,尊重每一位師傅,不拉幫結伙,“每個師傅都知道我是個老實孩子,都愿意多教我一些。像油燜大蝦這種在當時很少見的菜式,還有醬爆肉丁、麻婆豆腐、水煮牛肉等菜肴,師傅都是手把手的教我。等到一年實習期結束,我甚至可以獨自負責一場宴會,烹飪技藝提升很快。”楊楊總結,幫助自己提神的原因有兩個:一是餐廳的活兒不是很多,每道菜都可以仔仔細細的看著師傅做,然后再仔仔細細的自己炒。“正是這種比較寬松的環境以及老師傅的耐心教授,讓我的烹飪技法大增,成了同學中的楷模。”二是楊楊具有極強的執行力。“我的創造力可能不算突出,但我聽話,對于一個實習生來說,企業需要的可能就是超強的執行力。”
無法撼動的頭砧位置
由于楊楊在實習期的突出表現,等到畢業分配的時候,他被優先分配到喜來登旗下的大觀園酒店。“大觀園酒店當時是外資酒店,算是個比較好的工作。剛上班的時候,酒店還沒有建好,崗前培訓了一年。”在這期間,很多廚師之間有分歧,有派別,可楊楊從來不參與他們的任何活動,更沒有加入他們的一次罷工事件。鑒于他在崗前培訓時的優良表現,等到酒店正式開業時,楊楊不僅成為唯一一個留下的學生,更成為后廚的主力和忠誠度很高的員工,成為一個小領導。“后來想想,如果不是有那樣的機遇,也不會有我的今天。”


不過隨后發生的一件事幾乎給了楊楊當頭一棒。“第一次炒菜是做員工餐:番茄雞蛋炒牛肉,即先把肉片滑油,然后炒西紅柿雞蛋,再加肉片。前面炒得都很順利,就在我要加肉片的時候,香港的廚師長對我說‘楊楊,加點糖醋下去’。我也不知道為什么,心想可能是香港人的飲食習慣,就拿了個小勺舀了點糖,問他‘夠嗎?’他點頭,然后我又問‘加什么醋啊?白醋、米醋?’他還說‘加一點糖醋。’我心想‘糖醋?我不是加糖了么再加醋就行了。’他這時就有點急了,‘要糖醋,不要醋。’后來我才知道,他要加的是做古老肉用的糖醋汁。但是他普通話不是很好,加上這些粵菜的汁水雖然都講過,但運用并不熟練,就因為這件事,我這‘炒鍋’一個菜都沒炒完,就給分回了砧板。”雖然心里不服,楊楊還是很聽話,兢兢業業地干自己的“第五砧”。但因為基礎好,條理性也好,沒到一個月楊楊就到了“頭砧”,粵菜的各種醬汁、料頭更是熟于心諳。“后來才知道,酒店的砧板特別是頭砧對于酒店餐廳的把控力度是非常大的,是極其重要的崗位。”就這樣,楊楊在大觀園酒店做了四年頭砧。這期間,不論是香港主廚,還是一般的炒鍋師傅,只有楊楊和當時的中方廚師長沒有變動。
從未停止的學習態度
離開大觀園酒店之后,楊楊南下去過浙江,到過安徽,又回到北京。做過頭砧,也做過主廚、行政總廚、店經理。從酒店后廚,到行政機關廚房,再到社會餐廳,楊楊的經歷可謂頗豐。楊楊在北京餐飲圈開始嶄露頭角,但突然有一天,楊楊認識的一個朋友去了東方君悅的長安一號當涼菜廚師,從他嘴里楊楊發現酒店的經營、出品已經有非常成熟的思想,遠遠超出了自己的理解范圍,這時楊楊毅然決然地辭去了原本店總的職位,去了銀泰柏悅酒店。“進酒店我不圖任何頭銜,薪金是4500元,這對于當時的我來說是非常低的。但在那里,我學習到很多非常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烹飪理念。如果我沒有把以前的成績全部放掉,就不會有現在小小的成績。”回顧過去的日子,楊楊覺得每一步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自己。
正是有了再次在酒店的歷練,到了九朝會之后,楊楊很快的就開始做產品調整,做了很多、很豐富的活動。“現代人講究吃出文化,可什么是文化?過去,皇帝用完膳會吃一塊玫瑰餅,目的是長時間保持口齒留香。但這并所有人都知道這點,所以我們現在幫客人點餐的時候就會建議他們最后點一道玫瑰餅,然后告訴他們為什么要吃以及玫瑰餅的制作工藝。其實這就是文化。怎么吃才健康?就是用合理的烹調方式保持住食材的營養和能量。先把食物做好,然后用含有中式情懷的國際化手法呈現。”
楊楊說,直到現在,他也一直保持著一種學習的狀態,因為不學習就不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