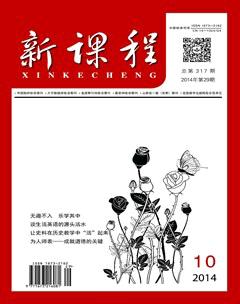由內而外,從內容到形式
莊麗蓁
摘 要:對于以母語交流的學生來說,他們已基本具備了運用語文的交際能力,那么語文課堂還能給他們什么呢?構建高效的語文課堂是所有語文教師的追求,但也是多年來語文課飽受詬病的地方。那么,什么才是高效的語文課堂呢?真正有效的課堂應該是以能力為導向而展開的師生、生生、讀者與作者、讀者與文本的真誠的對話。而想要讓這種對話有效、高效,便必須由內而外,從內容到形式,在掌握學生的已知與未知,找到師生共同提升的地方的同時,努力建構一種低耗、明快、簡潔、便捷的課堂教學結構,全力打造一種直擊靶心的有效教學模式。
關鍵詞:能力導向;有效性;核心知識與能力;課堂模式
構建高效的語文課堂是所有語文教師的追求,但也是多年來
語文課飽受詬病的地方。那么,什么才是高效的語文課堂呢?真正有效的課堂應該是以能力為導向而展開的師生、生生、讀者與作者、讀者與文本的真誠的對話。而想要讓這種對話有效、高效,便必須由內而外,從內容到形式,在掌握學生的已知與未知,找到師生共同提升的地方的同時,努力建構一種低耗、明快、簡潔、便捷的課堂教學結構,全力打造一種直擊靶心的有效教學模式。
福師大余文森教授曾提到“有效教學”,有效的內容表現在能力的變化、提升和發展上,而不是簡單的知識獲得和掌握;同時,這種有效的教學是憑借能力獲得的有效,即教學不僅培養學生的能力,而且依靠學生能力的發揮來理解、掌握、建構、創新知識。
一、由已知到未知,從低效到高效
美國著名教育心理學家奧蘇泊爾說過:“假如讓我把全部教育心理學僅僅歸納為一條原理的話,那么,我將一言以蔽之:影響學習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學生已經知道了什么,要探明這一點,并且據此進行教學。”
因此,弄清楚學生的已知與未知是備好一堂課的前提。已知的可以少教,甚至不教;同時使已知成為通向未知的通道;而未知的則為我們提供了引導學生不斷提升能力的可能。
《奧斯維辛沒有新聞》一課選自必修一第四單元——新聞和報告文學,怎樣才能上好這堂課呢?
關于新聞的教學,初中六冊和八年級都有選入篇目,學生對新聞的基本知識,包括新聞的結構、新聞的基本特點等已經有所了
解。而高中新聞教學則要求“客觀敘述與主觀評價,……把握作者的情感傾向,學子敘事寫人的技巧,培養關注社會的意識。”這才是學生初中涉及的未知領域。
因此,教學這篇課文時,我把教學的重心放在感受文本突破零度寫作的敘述方式,以及細節描寫上。
文中的許多描寫為我們提供了極好的素材,例如,“雛菊怒放”這一細節,很少人能關注到前文中的“對于每一個參觀者”“對有的人來說”與“對另外一些人來說”的區別,這正是學生所未知的。教師及時的點撥為文本的深入理解創造了可能。
另外,關于描寫“雛菊”的意圖,課堂上有相當一部分學生認為,雛菊象征著希望與生命。這與語文教學參考書上的解讀不謀而合。但是,實際上從上下文,以及本文的主題來看,這種理解是不準確的,文章在此更側重于體現法西斯的殘忍冷酷。在這里的適時點撥可以讓學生增強閱讀時的文本意識,學會尊重文本,深入文本,從而更準確地把握作者的寫作意圖,而不是隨心所欲,想當然。
這樣的教學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學科知識的積累與學科能力的提升。
二、精彩切入,巧妙構思
所有擔任語文教學的教師都知道,語文學習的規律有二:一是不斷重復,二是能力呈螺旋上升趨勢。
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語文學科的核心知識與核心能力在不同學段,要求是不同的;同時,即便同樣的教學內容,呈現的方式也應該是千變萬化的。語文教師決不能讓語文課變成了簡單的重復。而簡潔明快的課堂模式自然成了實現課堂有效性的一個重要因素。
《荊軻刺秦王》是一篇傳統的文言篇目,當我們習慣于或從情節切入,圍繞開端、發展、高潮、結局步步展開;或從場面描寫切入,賞析易水辭訣與廷刺秦王兩個場面的教學模式時,不難發現看似
重點突出、自然流暢的課堂,學生卻提不起聽課的興致,更談不上閃耀出師生之間思維碰撞的火花。
有一次,我換了一種方式去上這一課,才體會到另辟蹊徑的快樂。
《荊軻刺秦王》選自必修一《戰國策》,我用一節課的時間解決文言基礎知識。而把重點放在了第二節課文本的解讀鑒賞上,并著重抓住了兩個要點:一個是課堂切入,一個是課堂主線。
荊軻刺秦的行為原本就有爭議,這也是課堂思維火花碰撞的導火索。因此,如何開啟學生對俠義行為的思考,如何創造一種奇妙迷離、引人入勝的課堂境界,成了我選擇課堂切入點的衡量依據。于是,我選擇了2006年人教版《教師用書》課文備課資料后面名家評價荊軻的經典言論。果然,這些名家評議很好地激發了學生的興趣,調動了他們參與課堂的積極性。
而在課堂設計上,我選擇了以性格為綱、以情節為目的課堂構架,并由此設計出一條環環相扣的問題鏈。先由“荊軻刺秦王的準備工作設計完備體現在幾個方面”,引出“待吾客與俱”;接著提出“既然明知條件尚缺,為何荊軻還要去”,引出荊軻性格上的缺陷;進而提出“荊軻對刺秦結果有沒有預感”,引出易水訣別一幕的賞析;最后提出“既然已預感結果并不樂觀,為什么還‘預生劫之”,引出“劍術疏”以及其性格缺陷。最后,我拋出了一個問題:站在現在這個時代,應怎樣看待荊軻刺秦的行為?學生展開了一番唇槍舌劍式的辯論。大家從韓非子在《五蠹》中所說的“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談到了現在的報復社會走極端的行為,以及恐怖主義的反人類行為。
在這一個個問題的激發引領下,學生在課堂上展開了積極的思考,并積極地提出了各自的見解。既深入了文本,又超越了文本。
20年的教學,有朝一日,卻突然驚覺,一貫引以為豪的經驗有時竟成了約束自我的一種枷鎖。而學生也與語文課漸行漸遠,逐漸疏離。怎樣讓學生重新愛上語文課,值得語文教師深思。
參考文獻:
劉草金.行動導向教學法在教學中的應用[J].成才之路,2011(34).
?誗編輯 董慧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