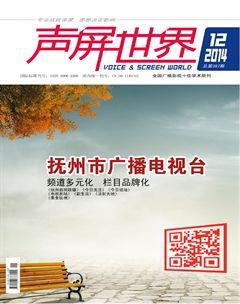法治視野下的傳媒輿論監(jiān)督三原則
庹繼光+張晁賓
【內(nèi)容摘要】:當(dāng)代社會(huì),媒體輿論監(jiān)督是輿論監(jiān)督的核心部分。在我國(guó)全面推進(jìn)依法治國(guó)的進(jìn)程中,傳媒輿論監(jiān)督理應(yīng)遵循三個(gè)基本原則:第一,守土有責(zé),既守住陣地,監(jiān)督到位,不缺席、不失語(yǔ),又守住邊界,不借輿論監(jiān)督開(kāi)展“權(quán)力尋租”;第二,介入有據(jù),只對(duì)已然發(fā)生、證據(jù)確實(shí)的事實(shí)展開(kāi)監(jiān)督,只對(duì)行為的濫用乃至違法進(jìn)行監(jiān)督;第三,嚴(yán)肅對(duì)待輿論監(jiān)督,遵循適度原則,不夸大、不枝蔓,不能將其娛樂(lè)化。
【關(guān)鍵詞】:依法治國(guó) 法治 傳媒 輿論監(jiān)督 權(quán)利 娛樂(lè)化
輿論監(jiān)督是社會(huì)民主監(jiān)督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它是指公眾在充分獲取信息的基礎(chǔ)上,借助一定的組織形式和傳播媒介披露信息、發(fā)表意見(jiàn),在觀點(diǎn)爭(zhēng)論和沉淀的基礎(chǔ)上形成輿論,并利用輿論的力量對(duì)監(jiān)督對(duì)象實(shí)施監(jiān)督。在當(dāng)代社會(huì),輿論監(jiān)督主要通過(guò)新聞媒體的監(jiān)督來(lái)實(shí)現(xiàn),媒體輿論監(jiān)督由此成為輿論監(jiān)督的核心部分,媒體輿論監(jiān)督通常是指媒體接受公眾的委托,運(yùn)用自身?yè)碛械呢S富傳媒資源,通過(guò)披露事實(shí)、傳播信息、表達(dá)意見(jiàn)的方式形成新聞?shì)浾摚_(dá)到針砭時(shí)弊、抨擊不公、遏制腐敗等效果,并促使其改正或完善。
鑒于輿論監(jiān)督特別是媒體輿論監(jiān)督在社會(huì)發(fā)展和進(jìn)步進(jìn)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huì)審議通過(guò)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推進(jìn)依法治國(guó)若干重大問(wèn)題的決定》中,對(duì)于傳媒在依法治國(guó)中的輿論監(jiān)督職能發(fā)揮提出了明確要求,主要體現(xiàn)在下面兩段話中——
其一,“加強(qiáng)黨內(nèi)監(jiān)督、人大監(jiān)督、民主監(jiān)督、行政監(jiān)督、司法監(jiān)督、審計(jì)監(jiān)督、社會(huì)監(jiān)督、輿論監(jiān)督制度建設(shè),努力形成科學(xué)有效的權(quán)力運(yùn)行制約和監(jiān)督體系,增強(qiáng)監(jiān)督合力和實(shí)效。”
其二,“規(guī)范媒體對(duì)案件的報(bào)道,防止輿論影響司法公正。”
當(dāng)下,我國(guó)實(shí)施依法治國(guó)方略,全面推進(jìn)依法治國(guó),傳媒的輿論監(jiān)督活動(dòng)無(wú)疑也應(yīng)納入法治的框架內(nèi),為此,筆者認(rèn)為,傳媒輿論監(jiān)督理應(yīng)嚴(yán)格遵循以下三個(gè)基本原則,確保自身的輿論監(jiān)督行為符合法治規(guī)范,既能充分應(yīng)有的社會(huì)職責(zé),也不僭越邊界,干預(yù)其他權(quán)利或權(quán)力的正常行使。
基本使命:守土有責(zé)
傳媒在輿論監(jiān)督活動(dòng)中要真正做到守土有責(zé),應(yīng)該堅(jiān)持兩個(gè)基本準(zhǔn)則:第一,守住陣地,積極履行應(yīng)有的社會(huì)職責(zé),監(jiān)督到位,不缺席、不失語(yǔ);第二,守住邊界,不利用輿論監(jiān)督的使命牟取個(gè)人私利和小集團(tuán)利益,不借輿論監(jiān)督開(kāi)展“權(quán)力尋租”,不因輿論監(jiān)督損害他人權(quán)利或妨礙公共權(quán)力的正常行使。
傳媒要牢固守住輿論監(jiān)督的陣地,基于一個(gè)最基本的原理,在輿論監(jiān)督的進(jìn)程中,公民是授權(quán)者,而傳媒是公民的委托才得以行使此項(xiàng)權(quán)利:“輿論監(jiān)督應(yīng)該是人民群眾意志的體現(xiàn)。人民群眾授權(quán)給新聞媒體,新聞媒體從人民利益出發(fā),掌握?qǐng)?bào)道對(duì)象的采訪權(quán)、報(bào)道內(nèi)容的選擇權(quán)、報(bào)道力度的控制權(quán)。新聞媒體對(duì)輿論監(jiān)督主體的代表性,體現(xiàn)于新聞媒體的性質(zhì)以及它在監(jiān)督過(guò)程中與作為輿論監(jiān)督主體的人民群眾的聯(lián)系。”①其他學(xué)者也作出了類(lèi)似的闡述:“現(xiàn)代民主政治對(duì)權(quán)力運(yùn)作的要求是公共權(quán)力要具有公共性和透明度。人民以其知情權(quán)和言論自由權(quán)參與國(guó)家政治活動(dòng),并監(jiān)督公共權(quán)力的運(yùn)作,而把二者結(jié)合起來(lái),靠的就是公眾傳媒,靠的就是輿論監(jiān)督。”②
由于傳媒是接受公眾委托才得以開(kāi)展輿論監(jiān)督,因而輿論監(jiān)督對(duì)于傳媒來(lái)說(shuō)不僅是權(quán)利,更體現(xiàn)為一種責(zé)任和使命,因?yàn)樗鼈冇新氊?zé)幫助公眾切實(shí)實(shí)現(xiàn)監(jiān)督權(quán)利,對(duì)于這一點(diǎn),法學(xué)和新聞學(xué)領(lǐng)域的專(zhuān)家都作過(guò)專(zhuān)門(mén)的論述。法學(xué)專(zhuān)家從權(quán)利配置的維度分析道:“社會(huì)之所以將初始權(quán)利配置給了他們,并不是由于他們個(gè)人有什么天然的優(yōu)越,而是社會(huì)為了避免一種更大的傷害;他們應(yīng)珍惜這種自由和理解自身的責(zé)任,應(yīng)當(dāng)格外注重職業(yè)道德和道德自律,這并不是要限制他們的權(quán)利,而恰恰是為了更好地行使這種自由權(quán)。”③新聞學(xué)專(zhuān)家則從傳媒輿論監(jiān)督與司法公開(kāi)的角度進(jìn)行了一番邏輯梳理:“如果說(shuō),司法公開(kāi)對(duì)司法機(jī)構(gòu)來(lái)說(shuō)是一種義務(wù)性規(guī)范的話,那么對(duì)新聞媒體來(lái)說(shuō),就是一種授權(quán)性規(guī)范,即國(guó)家將對(duì)司法工作情況的采訪報(bào)道權(quán)利授予新聞媒體,讓它們代群眾了解并公開(kāi)報(bào)道司法工作信息,行使對(duì)司法工作的知情權(quán)利。”④
應(yīng)該說(shuō),《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推進(jìn)依法治國(guó)若干重大問(wèn)題的決定》進(jìn)一步明確了傳媒開(kāi)展輿論監(jiān)督的使命感,決定中指出:“有法不依、執(zhí)法不嚴(yán)、違法不究現(xiàn)象比較嚴(yán)重,執(zhí)法體制權(quán)責(zé)脫節(jié)、多頭執(zhí)法、選擇性執(zhí)法現(xiàn)象仍然存在,執(zhí)法司法不規(guī)范、不嚴(yán)格、不透明、不文明現(xiàn)象較為突出,群眾對(duì)執(zhí)法司法不公和腐敗問(wèn)題反映強(qiáng)烈;部分社會(huì)成員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維權(quán)意識(shí)不強(qiáng),一些國(guó)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lǐng)導(dǎo)干部依法辦事觀念不強(qiáng)、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quán)壓法、徇私枉法現(xiàn)象依然存在。”對(duì)于這些妨害社會(huì)公正實(shí)現(xiàn)、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傳媒無(wú)疑應(yīng)自覺(jué)肩負(fù)其輿論監(jiān)督的職責(zé),傳統(tǒng)主流媒體尤其是極具強(qiáng)勢(shì)地位的黨報(bào)、電臺(tái)、電視臺(tái)更要始終充當(dāng)輿論監(jiān)督的領(lǐng)頭羊。
守住陣地意味著傳媒特別是傳統(tǒng)主流媒體要在重大輿情事件面前敢于發(fā)聲,及時(shí)發(fā)聲,牢固占領(lǐng)輿論監(jiān)督的主陣地,掌握輿論引導(dǎo)的制高點(diǎn),而不能輕易放棄輿論監(jiān)督和輿論引導(dǎo)的責(zé)任。目前,我國(guó)進(jìn)入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各種社會(huì)矛盾逐步凸顯出來(lái),面對(duì)如此情勢(shì),許多傳統(tǒng)主流媒體采取了保守、求穩(wěn)的思路,在一些重大社會(huì)事件上跟進(jìn)不及時(shí),有時(shí)甚至集體“缺位”“失聲”。而近年來(lái)新媒體發(fā)展迅猛,迅速形成了強(qiáng)大的輿論監(jiān)督力量,甚至在某些事件中擔(dān)當(dāng)了輿論監(jiān)督中堅(jiān)力量的角色,公眾通過(guò)社交媒體發(fā)布信息,在網(wǎng)絡(luò)上展開(kāi)觀點(diǎn)碰撞和匯集,進(jìn)而形成輿論,而傳統(tǒng)主流媒體卻失去了輿論監(jiān)督進(jìn)程中應(yīng)有的主導(dǎo)地位。它們被新媒體拋在身后,謹(jǐn)慎地?fù)?dān)當(dāng)著跟隨者的角色,亦步亦趨地跟隨著新媒體輿論監(jiān)督的腳步,不僅未能充分發(fā)揮獨(dú)立的輿論監(jiān)督功能,更遑論輿論引導(dǎo)了。此外,一些傳統(tǒng)主流媒體一味“求穩(wěn)”,對(duì)于涉及本地的重大輿情不敢及時(shí)反映,而是強(qiáng)調(diào)與當(dāng)?shù)毓俜降牟秸{(diào)嚴(yán)格保持一致,某些問(wèn)題若官方不作回應(yīng),這些傳統(tǒng)主流媒體便采取“鴕鳥(niǎo)政策”,面對(duì)網(wǎng)絡(luò)上已然沸騰的輿論仍置之不理、視而不見(jiàn),錯(cuò)失輿論監(jiān)督和引導(dǎo)的良機(jī),更引起公眾的不滿。在《決定》出臺(tái)的大背景下,傳媒特別是傳統(tǒng)主流媒體應(yīng)當(dāng)強(qiáng)化輿論監(jiān)督的責(zé)任感和使命感,主動(dòng)加強(qiáng)輿論監(jiān)督工作,占領(lǐng)輿論監(jiān)督的主陣地。
守土有責(zé),同時(shí)要求傳媒準(zhǔn)確厘清輿論監(jiān)督的邊界,不逾越邊界。如前所述,輿論監(jiān)督是公眾委托傳媒開(kāi)展的行為,這一前提決定了傳媒在輿論監(jiān)督進(jìn)程中不能公器私用,利用輿論監(jiān)督牟取個(gè)人和小團(tuán)體的私利,但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個(gè)別媒體將輿論監(jiān)督權(quán)利異化為“權(quán)力尋祖”,打著“輿論監(jiān)督”的幌子,行新聞勒索之實(shí),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這種行為必須堅(jiān)決制止。實(shí)際上,正當(dāng)?shù)妮浾摫O(jiān)督與新聞勒索有明確的界限,只要傳媒機(jī)構(gòu)和新聞從業(yè)者個(gè)人沒(méi)有私心,在輿論監(jiān)督過(guò)程中不謀求私利或小團(tuán)體利益,“權(quán)力尋租”的情形便不會(huì)發(fā)生。此外,法治框架下的輿論監(jiān)督過(guò)程也要充分尊重其他公民、組織和機(jī)關(guān)的合法權(quán)益,不能因?yàn)檩浾摫O(jiān)督出于正當(dāng)目的,便在實(shí)施過(guò)程中隨意損害其他公民、組織和機(jī)關(guān)的合法權(quán)益,這也是一個(gè)重要的邊界。
邏輯起點(diǎn):介入有據(jù)
傳媒輿論監(jiān)督作為一種強(qiáng)有力的社會(huì)監(jiān)督,必須追求自身的合法性、正當(dāng)性,因而傳媒在輿論監(jiān)督介入方面必然要堅(jiān)守嚴(yán)格的邏輯起點(diǎn),確保自身行為擁有充足的法理依據(jù)。筆者認(rèn)為,傳媒輿論監(jiān)督介入的邏輯起點(diǎn)至少應(yīng)遵循兩點(diǎn):第一,只對(duì)已然發(fā)生、證據(jù)確實(shí)的事實(shí)展開(kāi)監(jiān)督,不因想象或猜測(cè)而進(jìn)行監(jiān)督;第二,不對(duì)合法的權(quán)利或權(quán)力行為實(shí)施監(jiān)督,只對(duì)行為的濫用乃至違法進(jìn)行監(jiān)督。
第一個(gè)原則,根源于輿論監(jiān)督權(quán)利的“防衛(wèi)”本質(zhì)。對(duì)于這一點(diǎn),法學(xué)家作過(guò)明確的判定:所有公民權(quán)——政治自由,無(wú)論消極的還是積極的自由,都可以歸入防衛(wèi)權(quán)范疇。防衛(wèi)權(quán)可以分為兩類(lèi):一類(lèi)是事先的防衛(wèi),另一類(lèi)是事后的救濟(jì)。在政府已發(fā)生濫權(quán)或侵權(quán)行為時(shí),公民和社會(huì)組織有各種權(quán)利和救濟(jì)渠道,來(lái)抵抗、制止政府的侵權(quán)行為和貪腐行為,補(bǔ)償或賠償公民和社會(huì)組織的損失。從公民的政治權(quán)利角度來(lái)說(shuō),實(shí)現(xiàn)權(quán)利救濟(jì)的主要方式是:運(yùn)用公民的拒絕權(quán)或抵抗權(quán),抵制政府的惡法或不法行政行為;運(yùn)用公民和媒體(包括互聯(lián)網(wǎng))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權(quán)利,形成強(qiáng)大的社會(huì)輿論,促使或迫使政府接受公眾正當(dāng)合理的訴求;運(yùn)用憲法確認(rèn)的公民批評(píng)、控訴和申訴的權(quán)利,通過(guò)上訪、訴愿、向司法機(jī)關(guān)投訴,向人大反映,通過(guò)社會(huì)組織提起公益訴訟,直到依法組織集會(huì)游行示威,以制止、糾正政府的不法行為。⑤新聞傳播學(xué)者也作過(guò)類(lèi)似的闡述:媒體的輿論監(jiān)督既然是為公眾立言、代公眾參政,那媒體與公眾之間似乎也存在某種契約關(guān)系,公眾將參政的權(quán)利部分委托給媒體,媒體的輿論監(jiān)督就是此種權(quán)利的運(yùn)作,而且此種權(quán)利是一種防衛(wèi)性的,并非是進(jìn)攻性的權(quán)力。⑥
正因?yàn)檩浾摫O(jiān)督是事后的防衛(wèi)性權(quán)利,注定它不能憑想象或猜測(cè)而產(chǎn)生,而必然依附于一定的事實(shí)或根據(jù)。換言之,公民不能因?yàn)樽约旱纳暾?qǐng)可能得不到合理的處理而對(duì)行政執(zhí)法機(jī)關(guān)展開(kāi)輿論監(jiān)督,也不能臆斷自己提起的訴訟可能無(wú)法得到公正審理而對(duì)法院提出輿論監(jiān)督的要求,因?yàn)椤翱赡堋笔莻€(gè)人基于想象或猜測(cè)的一種判斷,而非事實(shí),既然對(duì)方還沒(méi)有作出有損公民合法權(quán)益、損害社會(huì)公平正義的行為,公眾自然不能開(kāi)展輿論監(jiān)督,對(duì)尚不存在的行為進(jìn)行抨擊和披露。
其實(shí),這個(gè)原則也是反擊“輿論審判”或者“媒體審判”最直接、最充分的理由。我國(guó)知名新聞傳播法學(xué)專(zhuān)家魏永征教授認(rèn)為,媒體審判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搶先對(duì)案情作出判斷,對(duì)涉案人員作出定性、定罪、量刑以及勝訴或敗訴等結(jié)論。”⑦由于我國(guó)法院獨(dú)立行使審判權(quán),在法院依法作出判決前,案件的定性、定罪、量刑以及勝訴或敗訴都處于不可知的階段,傳媒僅憑自身或他人的個(gè)人判斷、乃至個(gè)人好惡就對(duì)此下定論,甚至以此為依據(jù)展開(kāi)輿論監(jiān)督,完全是一種主管臆斷,沒(méi)有任何確切的根據(jù)。
為此,傳媒對(duì)于司法活動(dòng)的監(jiān)督應(yīng)堅(jiān)持事后監(jiān)督,其優(yōu)勢(shì)很明顯:此刻審判活動(dòng)已經(jīng)完結(jié),相關(guān)信息大多已清晰地呈現(xiàn)在大眾面前,容易為人們所感知,記者前往調(diào)查,自然很容易獲得這些材料,為自己的介入式報(bào)道提供有力的支撐,某些案例已經(jīng)形成了具有法律效力的結(jié)論,更能為傳媒的報(bào)道“撐腰”。有了這些充分的支持,傳媒可以在報(bào)道時(shí)有的放矢,增強(qiáng)介入式報(bào)道的針對(duì)性,使之產(chǎn)生更好的社會(huì)效果。此外,事后監(jiān)督在報(bào)道時(shí)效方面要求較低,記者、編輯和主管領(lǐng)導(dǎo)等往往有充足的時(shí)間對(duì)報(bào)道、言論所涉及的事實(shí),乃至言辭、用語(yǔ)等反復(fù)斟酌,進(jìn)一步提高報(bào)道的準(zhǔn)確性。另一方面,對(duì)于這種事后監(jiān)督,許多法學(xué)專(zhuān)家也持肯定的態(tài)度,如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何家弘教授便說(shuō)過(guò):“傳媒對(duì)審判活動(dòng)的監(jiān)督應(yīng)該以‘事后監(jiān)督為主。……司法腐敗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令人深?lèi)和唇^的。‘暗箱操作是產(chǎn)生腐敗的重要原因,而‘陽(yáng)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這些都已經(jīng)成為人們的共識(shí)。因此讓大眾傳媒的‘陽(yáng)光照亮審判活動(dòng)的過(guò)程應(yīng)該是防止司法腐敗的一劑良藥。”⑧
有人或許要反問(wèn):在法院正式開(kāi)庭前,傳媒對(duì)個(gè)別審判人員未能遵循“回避”原則展開(kāi)輿論監(jiān)督,也違背上述原則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yàn)檫@些人員與案件中的某些參與者存在利害關(guān)系,已經(jīng)是一個(gè)事實(shí),他們?cè)摶乇芏鴽](méi)有主動(dòng)回避,傳媒自然可以進(jìn)行輿論監(jiān)督。
另一個(gè)原則是“不對(duì)合法的權(quán)利或權(quán)力行為實(shí)施監(jiān)督,只對(duì)行為的濫用乃至違法進(jìn)行監(jiān)督”,理由也頗為明確,監(jiān)督本身即意味著糾偏,如果事情本身已經(jīng)處于正常軌跡,或者通過(guò)行政、司法等手段納入了恰當(dāng)?shù)慕鉀Q途徑,輿論監(jiān)督便沒(méi)有必要介入。國(guó)內(nèi)有學(xué)者曾作過(guò)如此解讀:媒介是作為國(guó)家的一種抑制力量存在的,它的主要功能是全方位監(jiān)視國(guó)家公共機(jī)構(gòu)的活動(dòng),揭露和批判權(quán)力的濫用。⑨這段話,更彰顯了傳媒在輿論監(jiān)督中的糾偏作用。不過(guò),在日常報(bào)道尤其是涉及司法活動(dòng)的報(bào)道中,傳媒不時(shí)出現(xiàn)干預(yù)權(quán)利的情形,或者將被告人合法行使辯護(hù)權(quán)說(shuō)成“狡辯”“鼓舌如簧”,或者將被告人上訴稱(chēng)為“意外”“抓最后的救命稻草”,實(shí)際上都是不合適的。
分寸把握:報(bào)道有度
輿論監(jiān)督是推動(dòng)社會(huì)主義民主政治建設(shè)的重要途徑,傳媒輿論監(jiān)督更因其特殊地位而發(fā)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輿論監(jiān)督應(yīng)當(dāng)以嚴(yán)肅的態(tài)度開(kāi)展,遵循適度原則,不夸大、不枝蔓,也不能將其娛樂(lè)化。
任何一個(gè)具體的輿論監(jiān)督過(guò)程,都是圍繞著特定的人物(機(jī)構(gòu))和特定事件而展開(kāi)的,在這個(gè)意義上其內(nèi)涵是很清晰的;但是,事物是普遍聯(lián)系的,這些人物、機(jī)構(gòu)和事件總會(huì)跟其他事物產(chǎn)生聯(lián)系,這又使得其外延變得捉摸不定。在此背景下,傳媒開(kāi)展輿論監(jiān)督時(shí),有必要認(rèn)真把握尺度,既不要任意壓縮范圍,消解輿論監(jiān)督的價(jià)值和力量,也不能肆意擴(kuò)大范圍,橫枝旁出,反倒沖淡了輿論監(jiān)督的效果。
實(shí)際上,傳媒要處理好這一點(diǎn)并不困難,切實(shí)做到遵循兩點(diǎn)就足夠了,一個(gè)是“公益相關(guān)”原則,一個(gè)是“無(wú)害隱私”原則。前一個(gè)原則使得傳媒的輿論監(jiān)督行為具備充足的正當(dāng)性,后一個(gè)原則避免傳媒的舉動(dòng)陷入“以暴制暴”、以違法糾正違法的尷尬境地。
“公益相關(guān)”原則要求傳媒在開(kāi)展輿論監(jiān)督時(shí),只曝光與公益有直接關(guān)系的信息,對(duì)其中涉及侵害公益的行為進(jìn)行抨擊和揭露,而不干預(yù)與之無(wú)關(guān)的其他內(nèi)容。“無(wú)害隱私”原則則強(qiáng)調(diào)在輿論監(jiān)督進(jìn)程中,最大限度保護(hù)相關(guān)人員、機(jī)構(gòu)的個(gè)人隱私、商業(yè)機(jī)密等,但直接損害公益的行為不在此列,例如官員的婚外性行為、企業(yè)的商業(yè)賄賂等。
嚴(yán)肅的傳媒輿論監(jiān)督還應(yīng)該自覺(jué)疏離低俗的“娛樂(lè)化”內(nèi)容。在一些輿論監(jiān)督性質(zhì)的報(bào)道中,媒體為了提升受眾的閱讀、收看欲望,吸引眼球,不惜炒作似是而非的“情婦”“緋聞”等。這些信息內(nèi)容往往缺乏扎實(shí)、充分的事實(shí)依據(jù),固然能滿足部分受眾的窺私欲望,卻背離了輿論監(jiān)督的嚴(yán)肅主題。作為傳統(tǒng)媒體、特別是傳統(tǒng)主流媒體,理應(yīng)堅(jiān)決克服輿論監(jiān)督中的“娛樂(lè)化”,避免嚴(yán)肅與低俗同爐,損害了輿論監(jiān)督的效果。
社會(huì)輿論在某種程度上存在非理性,公眾輿論也時(shí)常出現(xiàn)“一窩蜂”的情形,內(nèi)容混雜、觀點(diǎn)偏激。這時(shí)要求傳媒以更理智、更嚴(yán)謹(jǐn)?shù)膽B(tài)度對(duì)待輿論,把握好輿論監(jiān)督的分寸,既為合理的輿論監(jiān)督行為提供有力支援,也自覺(jué)對(duì)缺乏理?yè)?jù)、僅僅充斥著個(gè)人情感的觀點(diǎn)和議論采取離逸姿態(tài),與之隔絕,避免這些言論借助傳媒的傳播迅速擴(kuò)散,形成強(qiáng)大的社會(huì)輿論,侵害他人的合法權(quán)益,直接影響行政執(zhí)法活動(dòng)或司法活動(dòng)的正常運(yùn)行。
總之,傳媒輿論監(jiān)督的社會(huì)影響力日漸擴(kuò)大,這使得媒體從業(yè)者必然要肩負(fù)起更加重大的社會(huì)責(zé)任,作為新聞工作者應(yīng)當(dāng)恪守職業(yè)道德,嚴(yán)格遵循法律規(guī)范,正當(dāng)行使權(quán)利,自覺(jué)履行職責(zé),在法治框架內(nèi)認(rèn)真做好輿論監(jiān)督工作,使其在依法治國(guó)進(jìn)程中發(fā)揮出更重要的貢獻(xiàn)和作用。
(作者單位:,四川師范大學(xué))
欄目責(zé)編:邵滿春
注釋?zhuān)孩偬锎髴棧骸缎侣勢(shì)浾摫O(jiān)督研究》,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頁(yè)。
②覃理愛(ài),蘇鵬程:《輿論監(jiān)督在反腐敗中的作用》,《中國(guó)廣播電視學(xué)刊》,2005(5)。
③朱蘇力:《<秋菊打官司>案、邱氏鼠藥案和言論自由》,《法學(xué)研究》,1996(3)。
④鄭保衛(wèi):《論傳媒與司法的良性互動(dòng)》,《當(dāng)代傳播》,2008(6)。
⑤郭道暉:《公民的政治參與權(quán)與政治防衛(wèi)權(quán)》,《廣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8(5)。
⑥陳相雨:《媒體輿論監(jiān)督和公眾政治參與》,《西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9(7)。
⑦魏永征:《新聞傳播法教程》,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頁(yè)。
⑧何家弘:《監(jiān)督,還是介入?──論大眾傳媒對(duì)司法公正的影響》,《中國(guó)司法》,1999(9)。
⑨郭 晴:《媒介輿論:在各種權(quán)力與公眾之間》,《新聞界》,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