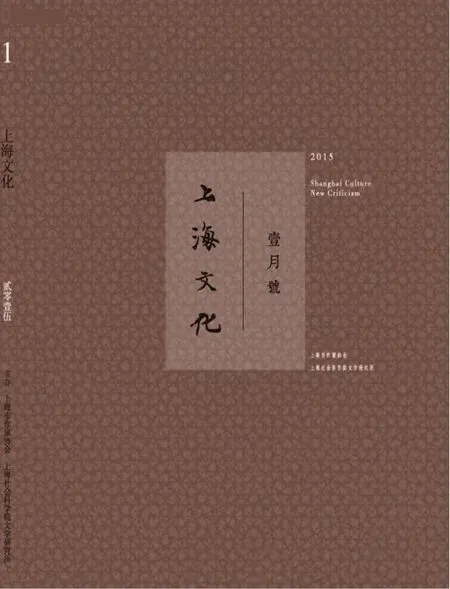長不大的孩子和他的欲望郭敬明解析(上)
霍艷
長不大的孩子和他的欲望郭敬明解析(上)
霍艷
詞語、意象的析解與拼裝
郭敬明坦言,他最喜歡自己的散文作品,并把散文寫作的過程比喻為,“站在一片山崖上,然后看著匍匐在自己腳下的一幅一幅奢侈的明亮的青春,淚流滿面”。2013年末,郭敬明出版了三卷散文集,其中《愿風裁塵》收錄了郭敬明從2004—2013年間全部散文作品。《懷石逾沙》收錄了郭敬明作品集《左手倒影,右手年華》的部分文章,以及他于《最小說》前期的專欄,同時亦收錄了他為旗下部分作者所作的新書序言。《守歲白駒》則以他的第一部作品《愛與痛的邊緣》的文章為主,并加以增補。
三卷散文集的名字都是四個字,但并非成語,是郭敬明從不同渠道化用而來。“愿風裁塵”許是出自“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風、塵兩個意象組合在一起略顯混亂,但郭敬明將其擴展成一段文案,詞語變得具象了:“愿風裁取每一粒微塵,愿靈魂抵達記憶的盡頭,愿一切浩瀚都歸于渺小,愿每身孤獨都擁抱共鳴。愿衣襟帶花,愿歲月風平。”“懷石逾沙”中“逾沙”二字,取自成語“逾沙軼漠”,形容跋涉了長遠路途,經歷了很多事情;而沒有出處的“懷石”,則被解釋為雖然這段歲月的跋涉非常沉重,但依然艱難前行。仔細分析,“石”與“沙”輕重相對,與逾沙軼漠中“沙”與“漠”二字包含的渺遠意象違背,新的組合抹掉了原意中的明朗。但經過郭敬明的解釋,這個生造的新詞語造成了一種陌生化效果,也衍生了新的意義。“守歲白駒”意指留下這本書,化成一匹白馬,守望曾經的歲月。這個詞語從“白駒過隙”化來,源自《莊子·知北游》,本義指白色的駿馬在縫隙前越過,比喻時間過得很快,光陰易逝。郭敬明把形容光陰飛快的意思暗中轉換,體現了他對語言的拆解能力,但同時把一個意象明晰的動態詞語,變得非常含混。“守歲”和“白駒”都有時間感,但在感受上一緩一急,組合在一起顯得混亂。三本書題目艱澀,但這三個編造的詞語一旦成為書名,并輔以解釋,很快就因其陌生感成為青少年間的流行詞匯。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謂:“經過數次感受過的事物,人們便開始用認知來接受:事物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知道它,但對它視而不見……使事物擺脫知覺的機械性,在藝術中是通過各種方法實現的。”把這段話中的“事物”替換為“詞語”,同樣可以適用。不妨說,郭敬明書名中詞語使用的陌生化,在積極意義上,也算得上使詞語擺脫知覺機械性的一種有益嘗試。
郭敬明書名中詞語使用的陌生化,在積極意義上,也算得上使詞語擺脫知覺機械性的一種有益嘗試
另有一些郭敬明的書名,是根本無法領會其意思的。如《陳舊光墨與寒冷冰原》,“光墨”是畫家何寶森提出的繪畫概念,與郭敬明的文章并無聯系,更不能用“陳舊”來修飾。通過閱讀才發現,作者是把光線與墨水這兩個意象強扭并置在一起,組成了“光墨”這個詞語。郭敬明像是喜歡“墨”這個意象,2011年又創造了不明所指的“荒墨”一詞。另如《繪日行》這個題目,在讀完全文以后,依然無法揣摩出作者的用意。還有《霧時之森》、《翅影成詩》、《浪名前少年嬉戲》,都是讓人不知所云的書名。除此以外,他還常把兩個意象并列作為書名,如《虛構的雨水與世界盡頭》、《灰蒙地域與螢火之國》、《荒蕪盡頭與流金地域》等。雖然這些作品最初刊登在《最小說》等青年時尚閱讀雜志上,需配備插圖,對題目有畫面感的要求,但作者不顧合理性,把完全不相干的詞強行組合在一起,可以理解為詞句的生硬嫁接。
對比郭敬明散文的原版與修訂版,他除了對篇章進行選擇,并沒有修改內容,卻有意改寫了幾個書名。《斷夏》原名《某年某個春末夏初》,《七日左右》原名《七天里的左右手》,這兩個改動是將原本啰嗦的書名精煉。《計月器》原名《四季歌》,《小圍城》原名《圍城紀事》,《楊花》原名《揚花》,這三個改動是將原本動態的書名名詞化,加深了對月份、圍城、楊花這些意象的強調。這些都足以看出郭敬明對意象的敏感,甚至可以說,他的散文有很多從意象出發的,這在他后來開設在《島》、《最小說》的專欄里尤其明顯。這些專欄,題目多選取一個意象,如《人間森林》、《光之芒》、《靜流的云層》、《投影儀》、《冬絨》,文章是這些意象的展開與想象。寫法上的共同特征是,開篇描摹一個意象,展開一段不及物的抒情,把“我”嵌入到意象鋪陳的情境之中,最后在自我抒發中照應主題。
如《冬絨》這篇千字文,先描繪了冬天的意象,“冬天的天空很硬,像一整塊櫥窗。白云偶爾緊貼天壁,一動不動。睫毛上凝結的霜花,是眼淚帶來的告別。時間像被水草纏住的錨,它抓緊海底,不肯告別”。接著是不及物的抒情,“記憶也抓緊我,不肯告別。無數過去的日夜仿佛數百個冰冷的靈魂,等待著被點燃,被溫暖,被漆上美麗的顏色”。接下來他將歲月、氣味等抽象化的意象具象化,“歲月像是飽滿的海”,“你留下的氣味像插在森林里的削尖后的木樁”,然后“我”出現,“我前幾天的夢里,有夢見你”。最后再抒發對冬日的感嘆,并在意象落實中結束,“大雪可以把一切都裝點得干凈而原始。仿佛這個世界上所有悲慘的命運、凄涼的糾葛、不甘的纏綿都不曾存在過。它把一切都溫柔地包裹進一朵小小的絨花。它開放在最遠最遠的山泉邊上。就像你別在領口上的那枚冬天”。
對意象的看重,使得郭敬明對描寫對象永遠近距離取景,將所取的景直接占據整個畫框,把細節和微不足道的事物無限放大。這乍看似有日本“浮世繪”的特點,“我愛浮世繪。苦海十年為親賣身的游女的繪姿使我泣。憑倚竹窗茫然看著流水的藝妓的姿態使我喜。賣宵夜面的紙燈寂寞地停留著的河邊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鵑,陣雨中散落的秋天樹葉,落花飄風的鐘聲,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無常,無告,無望的,使人無端嗟嘆此世只是一夢的,這樣的一切東西,于我都是可親,于我都是可懷”。仔細分析起來,卻覺得缺少浮世繪里要傳達的婉轉的人間之情,不關注所寫對象真實的具體,只是將細節一味夸大。作者直奔某個生活主題,使讀者發覺,原來生活中每一個事物都可以引發如此多的感嘆,至于感嘆的深度和廣度,不是作者追求的。這種風格有它存在的理由,當前輩作家思考宏大的歷史主題和寬廣的歷史場景時,發現他們思索的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郭敬明則轉而投向細節,把審美的意境、歷史、時間都集中在一束小花、一個被賦予生命的茶杯上面,用細節承載情感。不是說不能用細節承載情感,只是在郭敬明這里,情感泛濫到了讓人厭棄的程度。
不再任性的彼得·潘
郭敬明早期的散文,是從人物的狀態出發,這個人物就是作者本人,他的散文無一例外是“我”的講述,其他人物的出現也都圍繞著“我”這個中心。《愛與痛的邊緣》是他的處女作,不厭其煩地描寫著校園生活和他珍愛的文藝生活。《我上高二了》、《三月,我流離失所的生活》、《2000,我的泱泱四季》,從題目就可以看出是描繪“我”的生活狀態。
在這些文章里,郭敬明不斷強調,自己是個孩子。他的標志性段落:“我是一個在感到寂寞的時候就會仰望天空的小孩,望著那個大太陽,望著那個大月亮,望到脖子酸痛,望到眼中噙滿淚水。這是真的,好孩子不說假話。而我筆下的那些東西,那些看上去像是開放在水中的幻覺一樣的東西,它們也是真的。”文章中不停地強調,“一個永遠也不肯長大的孩子也許永遠值得原諒”,“但我是個任性的孩子,從小就是”,“而我是個很寂寞的孩子”,“我是個容易受傷的孩子”,“孤獨的孩子悄悄地在風中長大了”,“我是個會在陰天里仰望天空的好孩子,我真的是個好孩子”,“我就是這樣一個孩子,我誠實,我不說謊”,不停指認、強化的,是他“孩子”的身份。
有一段關于自己是“孩子”的描述,已經到了矯情的地步:
很多很多的人告訴我我應該長大應該成熟應該開始培養一個男生最終要成為男人的理智,可是我還是任性地把自己叫做孩子,我不想長大,就像彼得·潘一樣,永遠當一個小孩子,這樣我就可以沿著時光腳印退回來,抱著膝蓋蹲下來小聲唱歌。我是個小孩子,大家不要欺負我哦。
郭敬明不斷強調,自己是個孩子
他從《彼得·潘》里尋找作為“孩子”的合理性,“彼得·潘是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他永遠也長不大。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我想我是嫉妒他的”。朋友說,“彼得·潘是個落拓的孩子,他太任性了。可你和他一樣”。盡管作者表示,自己不喜歡“這個長不大的小怪物”,可“我”還是接受了自己是個讓人傷心的孩子這種說法。他一面指責彼得·潘的驕傲和任性,沒有愛過別人,是個可憐的孩子,一面享受著在幸福里長大,有父母的疼愛,不想繼續長大,不想讓人失望,希望和愛的人永遠在一起的“孩子”狀態。他認為作為孩子沒有錯,而錯的是彼得·潘的任性和固執地不想長大。他接受人不斷成長這個現實,并且辯白,他對身邊人的傷害是“有意想讓別人快樂一點”。
這個邏輯對于一直追隨著郭敬明的讀者是成立的,因為在散文里,他不斷強化著普通人只有靠這種金錢、奮斗換來高人一等的邏輯
郭敬明在不斷強化孩子身份的同時,也剖析阻礙自己繼續作“孩子”的阻力,一是他矛盾的性格,二是現實社會的殘酷。
郭敬明形容自己是一個白天明媚、晚上憂傷的孩子,解釋其原因是他是雙子星座,這特性與生俱來。“我出生在六月六日,神話中魔鬼之子降生的日子,雙子星座……我是個矛盾的人,雙子星的兩個頑皮的孩子在我的身體里面鬧別扭,把我朝兩個方向拉。”“我一直迷路的原因恐怕得歸結于我是個雙子座的人,有著雙重性格……一句‘我是雙子座的,就可以解釋很多事情,但‘很多’不是‘全部’……星座書上說:雙子座的人永遠不安分,渴望扮演不同角色。”
星座原本屬于占星術的一種,仔細分析起來很復雜,涉及人理性的局限和對未知的迷狂。郭敬明沒有對星座深思的興趣,他只是要用這個趁手的工具來應對自己性格中的矛盾。這種輕易的應對方式,沖淡了他對現實生活的敏感。這種沖淡并未讓郭敬明消除作品中對生活的虛擬不滿,在兩套生活準則里游刃有余——他一面抱怨社會殘酷,一面深諳其運行規則。他一直是大家心目中的好孩子、好學生,而非叛逆者。與此同時,他又流露出一種自負情緒,一是對于自己才智的自負,二是對于自己文化品位的自負,這種自負往往帶有一種不經意流露的俗氣:“我很喜歡《麥田守望者》那本書,所以當我在音像架上看到‘麥田守望者’這個樂隊時我就開始冷笑,我想:一支蹩腳的九流樂隊”。
這種自負,在郭敬明后來的作品里則轉化為一種巧妙的混合體。他時常帶著自卑口吻回憶過去:“我也經歷過第一次參加時尚雜志的拍攝,提著一大包自己喜歡的衣服去攝影棚,然后被雜志的造型師翻著白眼,在我的紙袋里翻來翻去,找不到一件她看得上的衣服的時刻。攝影師在旁邊不耐煩地催促著,造型師更加不耐煩地說:‘催什么催!你覺得他這個樣子能拍么!’”過去時的自卑是為現在時的自負賦予合理性,郭敬明持有的邏輯是:正因為過去遭受了冷漠的對待,如今對生活的享受才是理所應當,是“我”奮斗來的結果。而這個邏輯在《小時代》里被發揮得淋漓盡致,作品里一切對上海奢靡生活的展現,對品牌著迷與高消費生活方式的享受,都是合乎邏輯的。這個邏輯對于一直追隨著郭敬明的讀者是成立的,因為在散文里,他不斷強化著普通人只有靠這種金錢、奮斗換來高人一等的邏輯。而對于只看《小時代》的讀者,這種撲面而來的銅臭氣息,這種對于資本的夸張抒情和諂媚,讓他們難以接受。
在《投影儀》里,郭敬明對《小時代》主人公林蕭有一段告白:
我經歷過和你一樣的屈辱——當我穿著廉價的球鞋走進高級酒店時,服務員用那種眼光對我打量;出席某一些高級Show的時候,被負責宣傳企劃的人毫不客氣地對著身上已經精心準備好的衣服問:“我帶你去更衣室吧,你把便服換下來,我們這個是正式場合,你帶來的禮服呢?”
我經歷過第一次逛名牌店的時候,店員眼睛都不轉過來看我的情景。我鼓起勇氣問了一下其中的一件衣服,詢問是否可以拿下來試穿,店員依然沒有回過頭來,她對著空氣里不知一個什么地方,冷冰冰地說:“你不適合那件衣服。”
真的,那個時候我看著那些衣服上的標簽,我一直都覺得他們的價格是不是多打了一個零。
這段寫給林蕭的話,也是郭敬明對于自己當時處境的真實寫照,但他將這一切歸結為社會環境:
這個世界像是突然被翻轉了180度一樣,露出了你完全不認識的一面。
物質沖擊著人類的情感,只有真正被這些滔天巨浪所包圍的人,才有資格談論起所謂的理想和庸俗。就像沒有真正從戰場上回來過的士兵,沒有資格談論戰爭的偉大或者殘酷一樣。
我和你一樣,也對生活有著巨大的沮喪。無論你付出了多少努力,別人不會看到,他們只會永遠死死抓緊你跌到的時刻,時刻期望你摔倒,期待著你的生活突然間變成一團亂麻,突然就變得破敗襤褸。
是社會的物化,是同伴的別有用心,讓林蕭處處受挫,才“抓緊了顧里的手”,認同了這個物質女王的資本邏輯。同樣,也是上海對一個來自四川自貢少年的嘲諷,才讓他付出比常人加倍的努力,來換取對于物質的享受。“出人頭地,改變生活境遇”是一個催眠性的邏輯,郭敬明的作品所以具有廣泛的受眾,正是這個邏輯與諸多國人的心理契合。這個邏輯在過去的文學作品里,一直受到了國家、歷史等宏大價值體系的遮蔽,個體欲望得不到張揚。當文學的崇高地位被消解,宏大敘事不再發揮作用以后,對資本的認同則因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變成一種共鳴。郭敬明是“80后”第一個勇于表達對資本認同的,他在散文里直接表示對錢的熱愛:“我和錢的關系比較曖昧。我們是情人,我愛她,她也愛我……我愛錢,這沒什么好掩飾的。”這背后,折射出個體對于獨立的標準的變化,過去的獨立是人所擁有的美德與真摯情感,而如今獨立僅僅意味著經濟自由。按照一種傳統的評價標準,迎合快樂或者煽動人放縱的文學作品,必然導致欲望、尤其是性欲望和物質欲望的統治,這種煽動性欲望和物質欲望的作品,應該被放逐。如今時代變了,或許在我們這個奇特的共同體,已經可以溫和地接受這一切。
刻意為之的矛盾修飾
迎合快樂或者煽動人放縱的文學作品,必然導致欲望、尤其是性欲望和物質欲望的統治,這種煽動性欲望和物質欲望的作品,應該被放逐
郭敬明早期作品更著迷的是一個矛盾的主題——就像“青春是道明媚的憂傷”。青春跟憂傷都是抽象名詞,在這里做主賓結構;“道”多是用來形容疤痕的量詞,卻用來量化憂傷;修飾語明媚既符合青春的特征,又與憂傷相反,映照出青春的美,卻消解了疤痕的殘酷,實際上是拒絕對青春可能出現的問題的反省。“矛盾”是理解郭敬明作品的一個關鍵點,他不斷強化著自己天生矛盾的性格,在作品中善于抓住矛盾對比書寫,并且運用一種矛盾修辭法。
郭敬明有很多散文直接將矛盾作為主題,他用了一個分身的框架,設置不同軌跡的A、B角色,賦予他們截然相反的性格或境遇。在2001年的第四屆新概念獲獎作文《劇本》里,他設置了一個叫左岸的男人,“左岸是個搖滾樂手,也是個很有靈性的詩人。他有一頭很有光澤的頭發,明亮的眼鏡和薄薄的嘴唇。左岸之所以叫左岸而不叫右岸,是因為他偏激、憤怒、沖動、自負。左得很。就像曾經的我”。他以右岸作為對比,“右岸是個老實的男人。如果這個世界上有按照最讓人放心最不會讓人害怕的條件打造出來的男人,那么右岸就是這樣的人。右岸之所以叫右岸而不叫左岸是因為他的溫文爾雅他的逆來順受。右得很。右岸留一頭簡單純色的短頭發,穿合乎場合的服裝,有恰如其分的微笑,用平和清淡的古龍水。就像現在的我”。如果說一個人存在著兩面性,這個兩面可能是同一時刻存在的,也可能是不同時刻存在的,但都顯露出人本身的復雜性,郭敬明把這種復雜性做了簡化處理,分置在不同的人身上,刻意凸顯他們的差異。作為社會中的人,其心靈世界是復雜且豐富的,不可能是單一面向,高爾基曾說:“人們是形形色色的,沒有整個是黑的,也沒有整個是白的。好的壞的在他們身上攪在一起了。”刻意把人物性格單一化,可能是寫作者有意倦怠,抑或出于某種目的地迎合。
優秀的小說會呈現人性的復雜,但郭敬明卻把復雜簡化,把人物的單面特質無限放大
在《愛與痛的邊緣》里,多次出現了小A這個人物,他既是“我”的補充,也是“我”的對應。小A果斷地選擇了“我”割舍不下的文科,將“我”的猶豫襯托得格外醒目。小A是個天才且話語幽默,“我”卻為成績苦惱感到憂傷。小A臉上的笑容安靜而穩定,是“我”難過時第一個想到的傾訴對象,用自己天生的快樂映襯了“我”的憂傷。郭敬明在《回首又見它》一文里回憶道:“小A不知道我有多么地羨慕他,一個人可以活得那么安靜恬淡與世無爭。”但郭敬明的朋友后來回憶,并沒有小A這個人物,并且,郭敬明的事業上了軌道以后,也不再提及小A,使得我們不得不懷疑,這個人物其實只是作者虛構出來的一個分身。
2006年創作的《二重身》里,他使用了當下的自己與過去的自己對話的模式,這時性格的差異變成了境遇的差異。一個是在上海享受榮耀的“我”,一個是高三在四川上晚自習的“我”,現在的“我”一面羨慕過去“我”的青春和真實,一面告誡“我”殘酷的社會法則。郭敬明把這種自我的對話,以疾病的理由賦予合理性:“二重身是心理學上的一種現象,指在現實生活中自己看見自己。出現二重身的人,往往有很嚴重的心理疾病,都會以死亡告終。”他拋開人性的復雜,而給予了精神分裂的病因。在之后更多作品里,他把“我”呈現的復雜性,歸因于過去VS現在,四川VS上海,純真VS殘酷的對立,也就是說,他總是給人物尋找一個外因,而非內部開掘,或者僅僅把內因歸于雙子座的天生矛盾。
傅雷說:“了解人是一門高深的技術,便是最偉大的哲人、詩人、宗教家、小說家、政治家、醫生、律師都只能掌握一些原則,不能說對某些具體的實例——一個人——有徹底的了解。人真是矛盾百出,復雜萬分,神秘到極點的動物。”優秀的小說會呈現人性的復雜,但郭敬明卻把復雜簡化,把人物的單面特質無限放大。這種一根筋似的人物在他小說里時常出現,《小時代》里顧里對金錢的追求,林蕭的懦弱,唐宛如的滑稽,南湘的猶豫,都是簡化后的結果。簡化的好處是容易構成戲劇沖突,追求故事的曲折,放棄人物的復雜。這種寫作其實是一種倒退,甚至比最為傳統的小說在人物上還缺乏一些彈性。
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里提出“扁平人物”,也稱作“類型人物”或“漫畫人物”,“他們最單純的形式,就是按照一個簡單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創造出來。扁平人物的一大長處是容易辨認,他一出場就被讀者那富于情感的眼睛看出來……第二個長處是他們事后容易為讀者所記憶。由于他們不受環境影響,所以始終留在讀者心中。他們隨著環境而變動,這更顯出其性格是令人放心的。即使他們所在的那本小說會銷聲匪跡,但他們仍然不被人遺忘。”扁平人物在性格呈現上,不如圓形人物,但在戲劇效果上卻大有用場,這就是郭敬明作品里總會出現讓人捧腹的段落,這種幽默感是犧牲了人物復雜性營造出來的。
郭敬明在作品里過多地運用了“小說家筆觸”,實則對常人內心深處的復雜性缺乏了解。“它為了文學的目的,只從男性或女性中選出兩三種最引人注目的,因而也是十分有用的特性成分,而將其余的成分放置一旁。任何與選取的特性成分不合的東西都給刪掉,務必刪掉,因為不這樣做,就站不住腳。要充分占有材料,然后將一切與所需材料不合的東西扔掉。這樣做,他們有個似是而非的為‘小說家筆觸’辯解的借口:它只取其所好,而棄其所不好而已。事實上,他們這么做,也許是對的,但選取得太少了。作家所說的也許是事實,但并不是人生的真象。”在福斯特強調的扁平人物和小說家筆觸里,不用說將扁平人物變成圓形人物的潛質,就連刻寫的生動和準確,都無法在郭敬明的作品里索求。
也許郭敬明并不能準確地把自己的寫作手法定義為矛盾修辭,但當他看見同齡作家周嘉寧的文章《明媚角落》時,大加稱贊:“周嘉寧用簡單的四個字就制造了一場感覺上的風暴,我佩服得很。‘明媚’和‘角落’很格格不入,因為后者不會具有前者的性質而前者不會出現在后者身上。因此它獨特。因此我喜歡。小A說很多時候兩樣不相容的東西混在一起之后就會變得誘人。”他是一個天生對文字敏感的人,當他學會這種矛盾性的詞語超常搭配以后,就大量地運用到自己的作品中,而這種強烈的修辭效果,正給他濃郁的抒情增添了魅力。
如:
我眼前總是浮現這樣的畫面:一個裹著黑色風衣的人站在大雪的中央,夜色在四周發出錦緞般撕裂的聲音,那個人回首,早已是淚流滿面,我知道他的憂傷無比巨大,可是他已經哭不出聲音了。
夜色是視覺,聲音是聽覺,兩者嫁接在一起,使得孤獨感聲態俱現。作者進一步用錦緞撕裂的華麗音效,來形容孤獨,使得孤獨具有了一種排山倒海的氣勢。
再如:
寫字的人會生病,寂寞會逐漸從皮膚滲透進來,直到填滿每道骨頭的裂縫,直到落進所有的血液里。這是一場華麗的放逐。
不用說將扁平人物變成圓形人物的潛質,就連刻寫的生動和準確,都無法在郭敬明的作品里索求
寂寞是抽象名詞,作者將它具象化,像液體一樣可以滲透,可以填滿縫隙,顯示出人被寂寞渾身包圍的狀態。同時,安妮寶貝的“生命不就是一場華麗的放逐”被郭敬明改裝為“寂寞是一場華麗的放逐”,并不合乎邏輯,“放逐”指古時候把被判罪的人流放到邊遠地方,如果說人的生命可以遭到流放,那寂寞作為狀態,是無法被流放的,它是與人緊密纏繞的感覺,一旦人的主體消失,感覺也就自然消失,不能脫離主體而單純談論感覺。
因此我們需要警惕的是,這種變異修辭有時能產生張力和特殊的審美情趣,但隨意組合,故意違反語法規則,人為制造陌生化效果,而非從上下文情境出發,為了怪異而怪異,則會變成一種文字游戲,僅僅顯示作者對語言的賣弄。郭敬明被指責語言華麗而空洞,跟這種賣弄不無關系。
隨意組合,故意違反語法規則,人為制造陌生化效果,而非從上下文情境出發,為了怪異而怪異,則會變成一種文字游戲,僅僅顯示作者對語言的賣弄
單薄的語言游戲
除了超常搭配,郭敬明還營造一種泥沙俱下的氣勢,濫用復雜句和排比句。這種寫法,在他2004年創辦《島》以后,愈演愈烈。是因為《愛與痛的邊緣》、《左手倒影右手年華》主要以描寫高中生活為主體,抒情只是在高中情景還原中的調劑,而郭敬明在《島》、《最小說》上開設的專欄,文字甚至成為了插圖的附庸,僅僅一個普通意象就能引發的大段的抒情,不加克制。
如:
就像我再也不會講,我很難過。
如同我早已習慣講,你去死吧。
我再也不是當初那個會躺在被窩里用筆寫下每天煩惱的高中男生。
你也再不是當初那個因為黃昏起風的操場空無一人就會感到傷心的女生。
我再也不是當初那個穿著白襯衣獨自騎車上學放學的男生。
你也再不是當初那個會在下雨天淋著雨獨自練習投籃的男生。
我再也不是當初那個喜歡在學校頂樓折紙飛機的男生。
你也再不是當初那個偷偷在課桌下面為男朋友生日織圍巾的女生。
我再也不是當初那個戴著耳機在凌晨的臺燈下面用最平靜的表情聽最激烈的搖滾樂的男生。
你也再不是當初那個因為不小心看到前排女生露出的肩帶而突然脖子和臉都變得通紅的男生。
男生啊男生啊我們。
女生啊女生啊你們。
排比是一種加強抒情、敘事或描寫效果的修辭,仿佛某種能夠重復言辭的擴音設備。但在郭敬明的排比句里,這些效果并沒有達到,而只是簡單的意象、句式羅列,目的是凸顯畫面感,
你說要陪我周游世界卻比誰都走得更遠。
你說過要好好地生活卻在電話里哭得一塌糊涂。
你說過下次鳳凰花開的時候我們都要回來,站在學校大門口重新穿起笨重的校服重新拍那張你不小心閉了眼的畢業照片。
你說過那些詛咒我們侮辱我們的人只是因為我們過得比他們更好,所以我們永遠不要低下頭。
你說過我們承受的那些不白之冤那些莫名的責難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總有一天別人會看到我們揮動著翅膀認真而努力地在飛翔,我們所唯一需要覺得遺憾的事情只是說要證明這一切要證明我們自己需要的僅僅是一個漫長的時間。我們可以等,不知道別人能不能等。
你說過就算被大雨淋濕了頭,我們也不能哭。就算被人打落了牙齒,我們也要用力地把那口血吐回到那個人的臉上去。
在這個排比句里,還套了一個復雜句,“你說過我們承受的那些不白之冤那些莫名的責難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總有一天別人會看到我們揮動著翅膀認真而努力地在飛翔,我們所唯一需要覺得遺憾的事情只是說要證明這一切要證明我們自己需要的僅僅是一個漫長的時間”,這個長句是作者人為制造的閱讀障礙,目的僅僅是炫耀語言才華。
由于失去了事件的依托,感情缺乏承載,郭敬明有幾篇專欄只是段落的并列組合,如2009年《愛是琥珀》,他選取了獨占欲、手機、思念、海潮、小雪等關鍵詞,每個詞下面用三到五個短句組成段落,相互勾連并不緊密的段落連成篇章。2011年的《你在世界盡頭》,全文共有三個段落,七句話,沒有一個標點符號。
01
世界盡頭的雨水云層奔跑的倉皇和絕望
我想與你分享的世界和開滿我心房的白色繁花
我把對你的思念用云層包裹成一個漫長的句點
02
你笑容里的天地有黃昏里起風的悲傷
我沒有在你的房間里看過天亮我沒有為你拉亮盞燈
所以你也沒有為我等
03
我們說遙遠的世界背面地殼中心月亮坑洞深峽谷都有愛的存在
我只要你的心里又對我的愛的存在
這種寫作方式使得讀者不加思考,患上思維的懶惰癥,缺乏全景意識,陷入夸大感官體驗的泥沼中
這已經不再是文學寫作,而是詞句的羅列,就算有圖片作為視覺輔助,我們也很難理解作者要表達的意思。如果說前輩作家寫作的出發點是對社會、歷史的宏觀價值思考,用一個故事來承載這個思考,到了郭敬明這里,則是從一個細節出發,可能是一個意象,也可能是一個狀態,往往用一個詞語就能概括出來。郭敬明用文字把這個細節描摹成一段文字,然后加上情感的抒發和個人經歷的印證,組成文章的段落,最后拼接成一篇文章,是一種從小到大的組裝式寫作。
這種組合方式的好處是,語言精致,細部精彩,尤其是句子和段落,常有神來之筆,這使得郭敬明的不少語段成為年輕讀者的模仿對象,甚至成為金句名言。這個現象的原因就在于一代人將關注的重點不斷微觀,聚焦在個體、物的身上,不再關心邏輯與宏觀價值。同時網絡社交媒介的發展,使得語句代替篇章,成為他們彰顯個性的手段,誰能說出一段漂亮的話,誰就能吸引大家的注意,而篇章所要求的更高層次的謀篇布局,則容易被缺乏耐心的讀者忽視掉。但這種寫作方式存在著巨大的隱患,一代人的閱讀變得碎片化,使得讀者不加思考,患上思維的懶惰癥,缺乏全景意識,陷入夸大感官體驗的泥沼中。年輕一代更容易變得情感泛濫,以自我表達為中心,追求純粹的精神世界,關注瞬間的感受,將過去與未來、現在與未來,濃縮在碎片式的意象之中,字里行間彌漫著的泛濫情感,消解了縝密的邏輯,專注于構建內心世界來自我欣賞,無法對現實社會進行有效的探索和發現。
就算把郭敬明作品里的所謂精致的詞語,單個來看,也有很大問題。他不光從傳統詩詞、日本名物里化用詞語,還生造詞語。如他喜歡用的“柢步”,第一次出現在郭敬明主編的《島》書系,作為整本書的名字《島·柢步》,作者給予它的意思是:“柢步”是英語Debut的音譯,意思是首場演出,同時也取“第一步”連讀的諧音。從英文音譯為中文,是郭敬明造詞的一個手段,《島》系列的六部:《島·柢步》、《島·陸眼》、《島·錦年》、《島·普瑞爾》、《島·埃澤爾》、《島·澤塔》、《島·瑞雷克》,所謂的島嶼名稱均是作者英譯自外文,相對應為:
過去與未來、現在與未來,濃縮在碎片式的意象之中,字里行間彌漫著的泛濫情感,消解了縝密的邏輯
柢步:Debut(首場演出)
陸眼:Eyeland(陸地之眼)
錦年:Silkage(錦色年華)
普瑞爾:Prayer(祈禱者)
埃澤爾:Ether(蒼穹)
澤塔:Zeta(希臘語的第六個字母)
瑞雷克:Relic(遺跡)
詞語應該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具有廣泛認知的文學元素,但到了郭敬明這里,已經變成了東西方文化混合的雜交,變成了可隨意拆解的碎片。這些碎片肆意地在郭敬明作品的上空浮動,卻很少落到現實的土地上。
混亂的時間,隨意的結構
翻看郭敬明的創作譜系,發現他很少涉及中短篇小說,幾篇帶有習作性質的收錄在《愛與痛的邊緣》、《左右倒影、右手年華》兩本散文集里。他的短篇小說和散文相類似,以“我”為主角,講述“我”在成長中的孤獨和與周圍人關系。結構簡單,經常用不同敘述者反復敘述同一事情。注重抒情,主要是描繪一種“青春流逝,逐漸長大”的感傷狀態。除了“我”,他人都顯得面具化,情節也似曾相識。
《1995—2005夏至末至》是郭敬明2005年推出的青春小說,故事發生在虛構的淺川高中里,高中生立夏和傅小司,以及他們的好友陸之昂、程七七、遇見上演了愛恨離愁,既有對夢想的追逐,也有對愛情的守候。在故事的后三分之一處,情節突然翻轉,緩慢而安靜的敘述,被不停的變故推動加快,幾個人進入社會各自奮斗,卻遭遇了世俗的殘酷,友情也分崩離析。隨著時間的流逝,原本溫馨的友情因世俗沾染而走向破裂。
郭敬明小說里非常強調時間的流逝感,從這部作品的篇章名就可以看出:
chapter·01 1995夏至·香樟·未知地
chapter·02 1996夏至·顏色·北極星
chapter·03 1997夏至·遇見·燕尾蝶
chapter·04 1998夏至·暖霧·破陣子
chapter·05 1998夏至·柢步·艷陽天
chapter·07 2002夏至·沉水·浮世繪
chapter·08 2002夏至·流嵐·櫻花祭
chapter·09 2003夏至·漩渦·末日光
chapter·10 2003夏至·蘆葦·短松岡
chapter·11 2005夏至·尾聲
篇章以時間命名,選取了1995至2005年十年間的夏至。題名有東西方不同的文化來源,既有“破陣子”這樣的詞牌名,也有柢步這樣的英譯名,給人混同古今中外的感覺。更多的,是作者選取的某種意象,如浮云、暖霧、漩渦、蘆葦。郭敬明刻意制造的時間感,淹沒在這些浮泛的意象里,混混沌沌,有種時間停滯在青春時期的感覺。以意象來概括主人公成長里的某種狀態,就難以避免地依靠大段抒情來營造氛圍。如“那些高大的香樟像是從小在自己的夢中反復出現反復描繪的顏色,帶了懵懂的沖撞在眼睛里洋溢了華麗的轉身。立夏覺得淺川應該是沒有夏至的,無論太陽是否升到最高,這個城市永遠有一半溫柔地躲藏在香樟高大的陰影下面,隔絕了塵世般閉著眼睛安然呼吸”。作者想營造一種淺川世外桃源的氛圍,把時間徹底粘連在一個特殊的時空里,但“帶了懵懂的沖撞在眼睛里洋溢了華麗的轉身”這樣的句子對時空的營造毫無用處,并且很可能是個病句。
可以說,在《1995—2005夏至末至》里,郭敬明刻意為之的時間感已經影響了敘事的進程,除了以“立夏日記”的形式隨意插入倒敘,故事的前后兩部分敘事節奏嚴重脫節。作者肯在前半段用幾百字進行一段景物描寫,在后半段卻吝惜把劇情交代清楚,人物性格的轉變也不具備合理性,熱愛文藝的程七七一下子變成了心機惡人,高材生陸之昂則突然失去了理智,為好友傷人,傅小司從事業的高峰跌落谷底,源于被競爭對手的陷害。不難看出,這正是當時郭敬明陷入抄襲風波的寫照。他把作家“郭小四”變成了畫家“傅小司”,在小說里為自己辯白。不管這里面的本事如何,時間在這本小說里幾乎不再是一個設定著世界也改變著世界(即便這世界是虛構的)的物理量,而成了作者予取予求的趁手工具,可以按他的方式輕易塑造。
與隨意為之的時間感一致的,是作品的敘事視角隨意切換,立夏、傅小司、陸之昂、遇見都作為敘述主體,中間還用黑體字穿插著主人公多年以后的回顧,把作品僅有的留白之處填滿。在陸之昂母親突然得癌癥去世的段落,面對死亡本應使得少年們突然長大,作者應該給予更多的感受空間,但郭敬明卻用文字全部填滿。敘事視角通過一個手機鈴聲的牽引,先是從傅小司跳到了陸之昂:
小司從口袋里掏出手機,看到是立夏。接起來剛剛說完兩句話,那邊就突兀地斷掉了。掛掉電話傅小司朝陸之昂看過去,正好迎上陸之昂抬頭的目光。
陸之昂聽到了和自己一模一樣的手機鈴聲于是抬起頭,他知道是傅小司。站在自己面前的小司一身黑色的衣服,佇立在漸漸低沉的暮色里,像是悲憫的牧師一般目光閃耀,而除了他明亮的眼睛之外,他整個人都像是要融進身后的夜色里去一樣。陸之昂胸口有點發緊,在呼吸的空隙里覺得全世界像是滔天洪水決堤前的瞬間一樣,異常洶涌。這樣的情緒甚至讓他來不及去想為什么傅小司永遠模糊的眼睛會再一次清晰明亮如同燦爛的北極星。
緊接著,作者又插入一段傅小司為敘述主體的第一人稱獨白: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陸之昂那天抬起頭時看我的目光,在開靈師一聲一聲的鑼鼓聲里,陸之昂大顆大顆滾燙的眼淚順著臉龐往下滑。我可以看得出他想控制自己的情緒,可是嘴角依然像極了他小時候被欺負時向下拉的那種表情。我記得在幼兒園的時候我幾乎每天都看他這么哭,為了阿姨的責罵,為了爭不到的糖果,為了和我搶旋轉木馬,為了尿褲子,為了我把玻璃珠給了一個漂亮女生而沒有給他……而長大之后的之昂,永遠都有著陽光一樣燦爛的笑容,談話的時候是表情生動的臉,快樂的時候是笑容燦爛的臉,悲傷的時候……沒有悲傷的時候,他長大后就再也沒有在我面前有過悲傷的時刻,我都以為自己淡忘了他悲傷的臉,可是事隔這么久之后再被我重新看到,那種震撼力突然放大十倍,一瞬間將我變成空虛的殼,像是掛在風里的殘破的旗幟。
在濃重的夜色里,在周圍嘈雜的人群里,他像一個純白而安靜的悲傷牧童。我很想走過去幫他理順那些在風里亂糟糟的長頭發,我也很想若無其事地陪他在發燙的地面上坐下來對他說,哎,哪天一起去剪頭發咯。可是腳下生長出龐大的根系將我釘在地上無法動彈。因為我怕我走過去,他就會看到我臉上一塌糊涂的淚水。我不想他看到我哭,因為長大之后,我再也沒有在他面前哭過。
陸之昂,媽媽一定會去天國。你要相信我。
——1996年·傅小司
在以往的大部分作品里,男性之間總是充滿爭斗與陽剛之氣的兄弟義氣,但郭敬明作品里則細致地體味著男性之間微妙的友情
這是一段極富感受力的青春敘事。作者以漫畫的筆法把陸之昂描述成了一個天使般的人物,“在濃重的夜色里,在周圍嘈雜的人群里,他像一個純白而安靜的悲傷牧童”。濃重的夜色,嘈雜的人群,反襯悲傷牧童的孤獨感,他們本來都在衣食無憂的環境中成長,是現實的殘酷和死亡的陡然而至將他們的快樂擊破,把他們推到人群中間。作者很好地尋找到了一個青春與現實的交接點,并把年輕人站在這個點上的錯愕描摹了出來:“在開靈師一聲一聲的鑼鼓聲里,陸之昂大顆大顆滾燙的眼淚順著臉龐往下滑。我可以看得出他想控制自己的情緒,可是嘴角依然像極了他小時候被欺負時向下拉的那種表情。”在描摹當下的同時,作者迅速用閃回鏡頭,來回憶過去的快樂:“我記得在幼兒園的時候我幾乎每天都看他這么哭,為了阿姨的責罵,為了爭不到的糖果,為了和我搶旋轉木馬,為了尿褲子,為了我把玻璃珠給了一個漂亮女生而沒有給他……”現在與過去的對比,更將成長里的殘酷襯托出來。作者在這段文字里,運用了自己擅長的比喻,“一瞬間將我變成空虛的殼,像是掛在風里的殘破的旗幟”。文字強行制造了一種人被抽空的狀態,顯出現實的殘酷對人的毀滅。盡管情節設置漫不經心,但這種過渡狀態卻寫得如此淋漓盡致,吸引為數眾多的年輕讀者也就不足為奇。
讓人好奇的是,在這個混亂的時間設置里,人物如何成長?與一般青春小說不同的是,郭敬明作品里的青春不光是男女之戀,更是同性的情誼,尤其是男性之間的友誼。在以往的大部分作品里,男性之間總是充滿爭斗與陽剛之氣的兄弟義氣,但郭敬明作品里則細致地體味著男性之間微妙的友情。《1995—2005夏至末至》里傅小司與陸之昂的關系,延續了郭敬明散文里“我”與小A的關系,甚至陸之昂去日本的選擇也和現實中的小A一樣,而傅小司則是作者本人的化身。傅小司是一個性格有點自閉、為人低調、不善交際卻富有藝術才華的人,而陸之昂性格外向、樂于交往、學習優秀、善良直率。兩個人家境優越,從小一起長大,盡管性格迥異,他們卻相互陪伴鼓勵。陸之昂母親去世后,他變得沉默,安靜溫和,成熟穩重,懂得照顧人。直到結尾,陸之昂為了傅小司名譽的清白,用啤酒瓶砸碎競爭對手的頭,逃亡過程中淪落為乞丐,最后被捕。
在兩個人的成長過程中,陸之昂對傅小司有多次告白:
他說:小司,你知道么?其實這二十年來我過的很快樂。因為有你在我的身邊。
因為你,我很努力的學習很努力的畫畫,從以前那個每天只知道淘氣頑皮的傻小子變成了好學生。
因為你,我終于從失去母親的劇痛中掙扎著站了起來,不再頹廢不再自暴自棄,只為了實現母親和自己的理想,只為了你干凈的沒有憂慮的笑容。
小司,一直沒有說出口的話是,那些和你在一起的時光,那些穿著白色襯衣的日子,那些躺在草坪上看天空的日子,那些我們笑的沒心沒肺的日子,因為有了你,都像是天國的日子。
小司,我是多么的想回到過去。
小司,我的夢境里無數次的出現那樣一個場景:我們站在香樟樹下,仰起頭大口大口的喝掉手中的可樂,喉結不斷的翻上翻下。
小司。我很好。我只是,很想念你。
傅小司也對好朋友幾番評價:“他最清楚,陸之昂整天笑瞇瞇地對誰都很客氣,這個人是從來不會把別人的事情放在心上的,這點跟自己一樣,只不過自己表現的比較直接而已。”這種男性情誼的養成,事件并不是主要的助推力,而是兩個人之間的相互感受加深。傅小司將陸之昂放在與立夏同等重要的位置,形容與二人的關系是:“那個男孩,教會我成長,那個女孩,教會我愛,他們曾經出現在我的生命里,然后又消失不見,可是我不相信他們是天使,他們是世間最普通的男孩和女孩,所以我就一直這么站在香樟樹下等待著,因為我相信他們總有一天會回來,回來找我,教會我更多的事情。”作為郭敬明作品的主要目標群體的獨生子女一代,或許更能從他的作品里感受到一點不同于以往的對情誼的描繪,并從中感到溫暖。
《1995—2005夏至末至》是郭敬明作品里時間感最強烈的作品,小說以時間點作為章節,描述了幾個少年的十年成長歷程,不斷出現和時間有關的段落。對時間,郭敬明做了以下幾種處理:一、將時間作為情感標記,如全書第一句:這是1998年的夏天。7月9日。晴。沒有云。一朵也沒有。二、描寫時間的流逝感:于是歲月就這么轟隆隆地碾過了一年又一年。三、拉長時間的幅度:第一秒鐘笑容凝固在臉上。荒草蔓延著覆蓋上荒蕪的山坡。第二秒鐘笑容換了弧度。憂傷覆蓋上面容,潮水嘩嘩地涌動。第三秒鐘淚水如破堤的潮汛漫上了整張臉。夏日如洪水從記憶里席卷而過。第四秒鐘立夏知道自己哭了。在成長中,作者不是以人物的變化作為線索,而是以時光的流逝為線索,這是因為郭敬明并不關注人物,而是關注人物所承載的青春的狀態,是時光將青春消磨的痛楚,是不得不進入成人世界的冷酷無情,成長里的喜怒哀樂最后被簡化為只是青春逝去的感傷。
郭敬明并不關注人物,而是關注人物所承載的青春的狀態,是時光將青春消磨的痛楚,是不得不進入成人世界的冷酷無情
從這點來看,郭敬明的作品里突出的是青春,而非成長。巴赫金說:“大部分小說只掌握定型的主人公形象……除了這一占統治地位的、數量眾多的小說類型之外,還存在著另一種鮮為人見的小說類型,它塑造的是成長中的人物形象。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靜態的統一體,而是動態的統一體。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這一小說的公式中成了變數。主人公本身的變化具有了情節意義;與此相關,小說的情節也從根本上得到了再認識、再構建。時間進入內部,進入人物形象本身,極大地改變了人物命運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義。這一小說類型從普遍涵義上說,可以稱為人的成長小說。”郭敬明作品里的人物不是變化的,而是定型的,甚至是臉譜化的,他們被作者賦予了一種與生俱來的氣質,哪怕是發生改變,也是極端的翻轉,而非在成長中的逐漸變化,因而即便主人公的形象看起來是變化的,仍是一個靜態的統一體。同時,郭敬明作品里的時間是在人物之外的,它只能給予主人公一種青春流逝的感傷,并不能對人物本身造成改變,這使得時間只是作品里的一個刻度、一個裝飾性的背景,而非鐫刻在人物內心深處。
郭敬明作品里的時間是在人物之外的,它只能給予主人公一種青春流逝的感傷,并不能對人物本身造成改變,這使得時間只是作品里的一個刻度、一個裝飾性的背景,而非鐫刻在人物內心深處
在《1995—2005夏至末至》里,盡管不停地提到時間,我們卻很難理出一條清晰的時間線索。書名是1995—2005,但作品引子的起點是1998年的夏天高中畢業,在正文的部分才回到1995年高中入學。引子部分是一段預敘,事先講述或者提及以后事件的敘述活動。但預敘的作用是將懸念提前,在接下來的敘述中逐步推進懸念的過程,而這部作品并非營造懸念,因此這個預敘并沒發揮出作用,只是一種裝飾性設置。小說的第一章,時間開始在1995年夏天,高中開學第一天,立夏到淺川的第三天,小說本來可以沿著這個時間線索發展下去,但“立夏日記”的出現又將時間提前到立夏來淺川的第一天,以幾千字的篇幅巨細靡遺地講述了來淺川頭三天發生的事情,緊接著才是又一段順敘。第二章題目名為“1996夏至·顏色·北極星”,但只有兩千字左右的篇幅講述1996年,而前面近兩萬字依然停留在1995年,這就使得題目和行文出現了不符的情況。
從第三章開始,文章中出現了黑體字的插敘,盡管題目是“1997年夏至·遇見·燕尾蝶”,但時間依然錯位在1996年,第一個插敘則是“小司,如果那個時候你停下一秒鐘,也許我的問題就能出口了。你……是祭司么?是我一直喜歡了兩年的……那個獨一無二的人么?——1998年立夏”。也就是說,在1997年作為標題的章節里,順敘發展在1996年的故事里插入了1998年的追憶,如果說倒敘是根據表達的需要,把事件的結局或某個最重要、最突出的片段提到文章的前邊,然后再從事件的開頭按事情先后敘述,那這段話應該是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可實際上這句話只是作者的一時起意,臨時穿插,因為很快又出現了第二段倒敘:“立夏,你知道么,那個時候我在淺川一中沒有朋友,在認識你之前,我從小到大都沒有朋友,所以,有人關心的感覺第一次讓我覺得很溫暖,那是像夕陽一樣的熱度。你相信么,即使很多年之后的現在,我依然這么認為——2002年遇見。”這段倒敘則是來自小說的第二女主角遇見,而接下來的第三段倒敘來自1996年的遇見,至此,整個線性敘事全被打亂。黑色方框里的倒敘,其實并無對情節有實質性的推動作用,只是一段抒發,如“遇見,拉著你的手,無論是哪里,我都感覺像是朝天堂奔跑,你相信么?1999立夏”。作者不惜打亂時間線索,在不同的時間點上跳來跳去,只為了肆意抒發感情,顯示出他在結構上的隨意。小說除了是語言的藝術,情感的表達,也是一件精巧的裝置,而結構作為小說的基本要素,體現出一個作者的謀篇布局能力,如何將材料、人物、事件按照主次均勻組織和安排是一門藝術,而郭敬明在這方面明顯是漫不經心的。
?郭敬明:《左手倒影右手年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2頁。
?郭敬明:《愿風裁塵》封底,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
?郭敬明:《懷石逾沙》內容簡介,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
?郭敬明:《守歲白駒》內容簡介,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
?[俄]什克洛夫斯基等著,方珊等譯:《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版,7頁。
???郭敬明:《愿風裁塵》,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121頁;122頁。
?周作人:《苦口甘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85頁。
















編輯/黃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