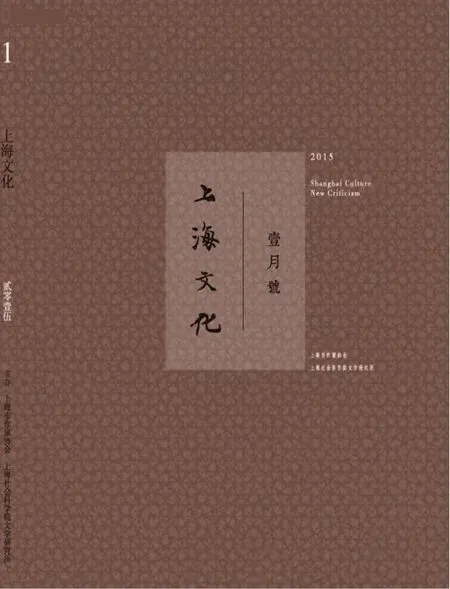作為故事的集體記憶與集體書寫對文革小說的一種反思
鄧金明
作為故事的集體記憶與集體書寫對文革小說的一種反思
鄧金明
文革小說,或者說小說形式的“文革敘述”,在當(dāng)前的文革研究中,處在一個微妙的位置上。一般說來,文革小說作為“小說家言”,不大會被嚴(yán)肅的史學(xué)研究所采信。在重實證的史學(xué)家看來,文革小說與其他關(guān)于文革的影視、舊物收藏、消遣娛樂一樣,只是一種關(guān)于文革的“通俗記憶”,而不是建立在歷史資料文獻(xiàn)基礎(chǔ)上的“嚴(yán)肅記憶”或者說“實錄記憶”,因此有其局限性。但另一方面,在現(xiàn)行體制下,文革小說又是國人談?wù)摗⑹鑫母锏闹饕緩胶头绞健S腥司驼J(rèn)為,“所有這些小說形式的‘文革敘述’,不僅已成為當(dāng)代文學(xué)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學(xué)現(xiàn)象之一,而且也是以現(xiàn)代漢語書寫的讀者最多、影響最大的一種‘文革敘述’”。如有些學(xué)者所言,由于嚴(yán)肅文革記憶空間遭到某種限制,通俗形式對于維持文革記憶的作用就特別重要。
但是,文革小說并不是用來維持文革記憶的一個無奈的替代品,它能引起我們更深入地思考記憶與書寫相關(guān)的一些本質(zhì)問題,比如真實性問題。文革小說不被史家采信,究其緣由,是其真實性可疑。可這種質(zhì)疑的產(chǎn)生,很大方面是因為我們過去對文革敘述的評判往往只取一種“真實”標(biāo)準(zhǔn),即“事實性真實”標(biāo)準(zhǔn),而忽視了“情感性真實”標(biāo)準(zhǔn)。實際上,文革小說與那些歷史文獻(xiàn)資料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它能提供一種心理、感受、情感的“真實”,這種“真實”對于理解文革歷史同樣重要,而這正是文革心態(tài)史亟待研究的。
如果我們承認(rèn)文革小說是“以現(xiàn)代漢語書寫的讀者最多、影響最大的一種‘文革敘述’”,那么我們就無法忽視文革小說所具有的認(rèn)同性,而這又是如何與“文革小說”作為一種文學(xué)所必然具有的差異性結(jié)合在一起的呢?或者說,我們到底該如何理解文革小說所具有的集體性與個體性這兩面?二者的關(guān)系又如何?這些問題正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另外需要加以說明的是,許子?xùn)|的專著《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50篇文革小說》(以下簡稱為《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將是本文一個重要的參照與反思對象。這不僅因為它是目前大陸出版的唯一一部研究文革小說的著作,更重要的是,它作為文革小說研究的開山之作,將文革小說定性為“集體書寫”,將其書寫的“文革記憶”定性為“集體記憶”,影響很大,因此本文對文革小說的研究,必然要從反思這部著作開始。
方革小說是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與“集體書寫”是《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一書的關(guān)鍵詞,尤其是前者。先來看該書是如何理解“集體書寫”的:
“集體書寫”在本書中有兩層意思,第一是指作家、作品之間的對話關(guān)系:每一位敘說者都希望自己的文革故事與眾不同,而且能夠更深刻地理解文革。每部文革小說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對其他文革故事的修改、補充或重寫。第二,“集體書寫”也意味著讀者需求、詮釋群體及意識形態(tài)機器對文革敘述的介入——通過印數(shù)銷量,通過評獎或選本,通過爭議或批判……所以在獲獎小說或暢銷作品里大量出現(xiàn)的情節(jié)和敘述策略,便同時體現(xiàn)著故事敘說者們的集體選擇與讀者群體的公眾需求(以及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某種制約)。
我們可以看到,所謂書寫的“集體性”,在第一層意思中,被理解為作者/作品之間的一種“對話”關(guān)系,即彼此間的“修改、補充與重寫”,也就是說,單個的文革書寫之間形成了一種“互文”。但是在第二層意思中,卻馬上背離了這種書寫的“對話”性質(zhì),走向了集約。所謂的“故事敘說者們的集體選擇與讀者群體的公眾需求(以及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某種制約)”,無不在說明,單個的書寫——無論是創(chuàng)作、閱讀還是闡釋、批評——之間不再是一種多元的對話關(guān)系,而是服從于一種集體性(更確切地說應(yīng)該稱為“同一性”)。這種集體性表層上體現(xiàn)為敘事的模式化上,而深層上則體現(xiàn)為一種共同的社會文化心理。
《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一書的基本思路是,通過分析1977年以來的在中國大陸上寫作與發(fā)表的五十篇文革小說的敘事模式以及這些文革小說中的主要角色及其敘事功能,從而歸納出四種包含不同意義結(jié)構(gòu)的敘事類型:契合大眾通俗文學(xué)趣味的“災(zāi)難故事”(十二篇)、體現(xiàn)知識分子與干部憂國情懷的“歷史反省”(八篇)、先鋒派小說對文革的“荒誕敘述”(十七篇)以及“紅衛(wèi)兵—知青”角度的“文革記憶”(十三篇)。通過這四種類型,文革或者被描述成一場“少數(shù)壞人迫害好人”的災(zāi)難故事,或者被總結(jié)成一個“壞事最終變成好事”的歷史教訓(xùn),或者被解析為一個“很多好人合作而成的荒謬壞事”,或者被記錄為一種“充滿錯誤卻又不肯懺悔”的青春回憶。四種敘事模式本身就是文革記憶集體性的體現(xiàn),而更重要的是,這四種敘事模式的形成,又共同受制于一種作為“主導(dǎo)傾向”的“文化心理狀態(tài)”:
所謂“賦予”各種關(guān)系系統(tǒng)“以結(jié)構(gòu)的主導(dǎo)傾向”,在“文革敘述”中主要就是“逃避文革”、“忘卻文革”的傾向。當(dāng)然,這種“逃避”文革影響、“忘卻”文革歷史的“主導(dǎo)傾向”,相當(dāng)程度上是以集體無意識的形式制約著各種“文革敘述”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而且是以“因禍得福”、“壞事變成好事”、“不可解釋”或“青春無悔”等不同方式,使得“文革敘述”的制作者與接收者們可以求得放心與釋懷。
當(dāng)小說家用文學(xué)形式將他們個人的文革經(jīng)驗變成大眾論述時,他們實際上有意無意地參與了有關(guān)文革的“集體記憶”的創(chuàng)造過程。這種有關(guān)文革的“集體記憶”,與其說“記憶”了歷史中的文革,不如說更能體現(xiàn)記憶者群體在文革后想以“忘卻”來“治療”文革心創(chuàng),想以“敘述”來“逃避”文革影響的特殊文化心理狀態(tài)。
簡單說,《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一書通過分析五十篇文革小說,得出的最終結(jié)論是,這些文革小說的共同目的并不是記憶文革,反而是忘卻文革,也即該書書名所示,是一種“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
關(guān)于《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一書的論述思路,首先,是敘事學(xué)在小說研究中的效用問題。《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一書主要采用的理論模式是普洛普的故事形態(tài)學(xué)理論。可問題是,普洛普的故事形態(tài)學(xué)是建立在民間故事基礎(chǔ)上的,民間故事是一種繼承性遠(yuǎn)遠(yuǎn)大于發(fā)揮性的“敘述”,它與文人小說存在差異。故事形態(tài)學(xué)對故事情節(jié)與人物角色作了高度的概括和提煉,放棄了故事的細(xì)節(jié),這在民間故事流傳中并無大礙,而對文人小說來說,卻是致命的。說到底,文革小說講述的“文革故事”體現(xiàn)的是一種個人性、獨特性、錯綜性的文革經(jīng)驗,這種經(jīng)驗的價值往往就在于它無法概括、無法通約。當(dāng)然,無法否認(rèn)不同的文革經(jīng)驗?zāi)苷业侥撤N同一性,可問題是,經(jīng)過高度概括而來的這種同一性還能代表原本錯綜復(fù)雜的文本本身嗎?說到底,《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一書對文革小說在文革敘述中的特殊性還遠(yuǎn)遠(yuǎn)不夠重視。所謂的“要從小說模式來考察‘集體記憶’的建構(gòu)方法,則必須透過(有時甚至忽略)藝術(shù)趣味匠心特色的差異變化,以尋找敘述策略風(fēng)格選擇后面的歷史規(guī)定與情節(jié)設(shè)計敘事規(guī)范的文化邏輯”,這種解讀小說的思路,筆者認(rèn)為是本末倒置。文革小說本質(zhì)上是文學(xué),與其他文革敘述相比,“藝術(shù)趣味匠心特色的差異變化”揭示出的意涵,往往是根本性的,文學(xué)性越強的小說越是如此。實際上,《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一書提到的四種敘事模式中,第三種即先鋒派小說對文革的“荒誕敘述”,其概括是最為牽強的。究其根源,就是因為先鋒小說的文學(xué)性最強、最難概括。而這類小說在五十篇小說中有十七篇,又是數(shù)量最多的,這就不能不讓人質(zhì)疑這種從敘事學(xué)出發(fā)的模式化分析,其效用性到底有多大。
《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一書通過分析五十篇文革小說,得出的最終結(jié)論是,這些文革小說的共同目的并不是記憶文革,反而是忘卻文革
其次,敘事模式之間的差異問題。《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一書也承認(rèn),在文革敘述中,“每個敘述者都以青春、傷勢,甚至死者的名義擔(dān)保他們的故事的真實,但讀者卻分明在不同的故事中看到不同的文革歷史。這些互相矛盾甚至截然相反的‘文革圖景’及其對歷史文革的解說當(dāng)然聯(lián)系著文革后不同‘詮釋群體’(Interpretive Community)、不同意識形態(tài)力量之間的妥協(xié)與斗爭”。正因如此,才會產(chǎn)生不同的敘述模式。“敘述模式之間的差異,則顯示著各種文化力量對‘文革集體記憶’書寫過程的不同制約。”但是,到底是何種“詮釋群體”、“意識形態(tài)力量”或“文化力量”又是如何在制約著敘述模式的差異及矛盾,《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一書卻語焉不詳。書中只是簡單提到了文革小說的作者和讀者的社會身份對其敘述的影響。但是,不同力量制約下的不同的文革敘事模式為何會最終都導(dǎo)向?qū)ξ母锏耐鼌s呢?這個問題,是《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一書永遠(yuǎn)都無法回答的。按照書中的論述,如果被精挑細(xì)選出來的五十篇具有代表性的文革小說無論其歸屬于何種敘事模式,都是對文革的一種忘卻,那么我們就會得到一個荒唐的結(jié)論:所有的中國當(dāng)代文革小說都在遺忘文革。這就好比說,面對文革,敘述只不過是在遺忘,沉默反倒是在銘記了。當(dāng)然,作者可能是認(rèn)為:所有辯解性的文革敘述都是在忘卻,只有懺悔性的、控訴性的文革敘述才是記憶。可惜的是,五十篇小說中并沒有這類小說。但是,與其說是當(dāng)代中國沒這樣的小說,不如說,“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只不過是作者強加的一個結(jié)論。比如,無論先鋒派把文革敘述成“很多好人合作而成的荒謬壞事”還是認(rèn)為“無法解釋”,都難逃在逃避、忘卻文革的指責(zé),但是《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一書又認(rèn)為,在四種敘事模式中,“第一和第二類型,為了忘卻的敘述結(jié)構(gòu)比較明顯。第三類則是對這一結(jié)構(gòu)形式的挑戰(zhàn)與修改”。此種矛盾抵牾,只能說明作者無視敘事模式之間的差異性,強行將其統(tǒng)一納入“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的牽強。
面對文革,敘述只不過是在遺忘,沉默反倒是在銘記了
最后,“集體記憶”的運用問題。“集體記憶”是《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一書最核心的概念,但是全書并沒有對其加以任何界定和闡述,只是在“導(dǎo)論”第15頁注釋[18]中,簡單交待了一下:“本書在使用‘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這個概念時,參考了Michael Billing,‘Collective Memory,Ideology and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David Middleton&Derek Edwards ed:Collective Remembering,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0.p.60.”《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一書,是通過“新歷史主義”的觀點引入“集體記憶”的。“新歷史主義”認(rèn)為,“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刻,各種關(guān)系系統(tǒng)都是同一種賦予它們以結(jié)構(gòu)的主導(dǎo)傾向……相聯(lián)系而發(fā)生作用的。無論是在過去還是在對過去的詮釋中,歷史都遵循一種模式或結(jié)構(gòu),按照這種模式或結(jié)構(gòu),某種事件比其他事件具有更大的意義。在這一意義上,結(jié)構(gòu)制約著文本的寫作和閱讀”。在《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一書看來,在文革小說中,敘事模式就是“結(jié)構(gòu)”,而產(chǎn)生這種“結(jié)構(gòu)”的“主導(dǎo)原則”,則是一種逃避文革、忘卻文革的集體無意識,或可稱作集體反記憶、集體忘卻。既然這種集體無意識是先發(fā)的,在敘述或書寫之前就有了,那么就有一個問題了,這種集體無意識從何而來?它是先天俱有的還是后天生成的?它是民族健忘癥的體現(xiàn)還是人類逃避痛苦的天性使然?所有這些問題,《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一書都沒有回答。因此,把文革小說當(dāng)中概括出的種種敘述模式,最后歸結(jié)到某種神秘的集體記憶、集體無意識,不僅無助于廓清問題,反而使問題更加含混。說到底,這與集體記憶理論本身的局限性不無關(guān)系。
“集體記憶”的危機
文革記憶往往被冠以“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稱號,比如用作本文反思對象的《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50篇文革小說》,但是“集體記憶”的這個提法其實是值得好好辨析的。“集體記憶”是法國社會學(xué)家哈布瓦赫(M.Halbwachs)提出的一種觀念。他認(rèn)為“人們通常正是在社會之中才獲得了他們的記憶的。也正是在社會中,他們才能進(jìn)行回憶、識別和對記憶加以定位”,“存在著一個所謂的集體記憶和記憶的社會框架;從而,我們的個體思想將自身置于這些框架內(nèi),并匯入到能夠進(jìn)行回憶的記憶中去”。“記憶的集體框架也不是依循個體記憶的簡單加總原則而建構(gòu)起來的;它們不是一個空洞的形式,由來自別處的記憶填充進(jìn)去。相反,集體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體記憶可以用以重建關(guān)于過去的意象,在每一個時代,這個意象都是與社會的主導(dǎo)思想相一致的。”“正像人們可以同時是許多不同群體的成員一樣,對同一事實的記憶也可以被置于多個框架之中,而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體記憶的產(chǎn)物。”“這些數(shù)目龐大的框架實際上彼此交錯、部分重疊,當(dāng)回憶在這些數(shù)目龐大的框架的結(jié)合點上再現(xiàn)時,回憶就會變得更加豐富多彩。遺忘可以由這些框架或其中一部分的消失加以解釋……但是,某種記憶的遺忘或者變形,也可以由這些框架在不同時期的變遷來解釋。依靠環(huán)境和時點,社會以不同的方式再現(xiàn)它的過去:移風(fēng)易俗。由于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接受了這些習(xí)俗,所以,他們會在與集體記憶演變相同的方向上,使他們的回憶發(fā)生屈折變化。”
有論者據(jù)此認(rèn)定,文革記憶是一種集體記憶,其理由為:第一,“文革”是一個集體性的政治運動;第二,“記憶”文革這一行為具有集體性;第三,支持記憶者對“文革”進(jìn)行記憶的往往不是個人原因,而是集體原因;第四,社會文化決定了我們對“文革”的理解;第五,我們社會的“文革記憶”是社會傳播的產(chǎn)物,而社會傳播是受到社會政治文化控制的。這恐怕代表了大多數(shù)以“集體記憶”來指稱文革記憶的人的看法。我并不想完全否認(rèn)文革記憶集體性的一面,但是請注意哈布瓦赫“集體記憶”概念本身的局限性,以及這種局限性又是如何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我們對文革記憶的認(rèn)識。
劉易斯·科瑟在為哈布瓦赫的《論集體記憶》所作的“導(dǎo)論”里,曾指出哈布瓦赫關(guān)于“集體記憶”的論述,是建立在“現(xiàn)在中心觀”(presentist)基礎(chǔ)上的。“對哈布瓦赫來說,過去是一種社會建構(gòu),這種社會建構(gòu),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現(xiàn)在的關(guān)注所形塑的。”“這樣一來,歷史就成了一組在不同時間拍攝的、表達(dá)著各種不同觀點的快照。”但是這種觀點受到了美國社會學(xué)家巴里·施瓦茨的質(zhì)疑,后者認(rèn)為“歷史不是一組不連續(xù)的快照組成的,而是一部連續(xù)的電影”,“如果把現(xiàn)在中心觀的方法推至極端,就會讓人感到歷史中完全沒有連續(xù)性”。“過去總是一個持續(xù)與變遷、連續(xù)與更新的復(fù)合體。集體歷史記憶還是具有累積和持續(xù)性的一面的。在根據(jù)現(xiàn)在對過去所做的新的讀解之外,也至少顯示出部分的連續(xù)性。一個社會當(dāng)前所感知到的需要,可能會驅(qū)使它將過去翻新,但是,即使是處于當(dāng)代的改造之中,通過一套共有的符碼和一套共有的象征規(guī)則,各個前后相繼的時代也會保持生命力。”施瓦茨的觀點提醒我們,文革記憶具有持續(xù)性,這種持續(xù)性使我們不能把文革簡單排斥在現(xiàn)在之外而被形塑。這一點聯(lián)系現(xiàn)實其實很好理解。雖然作為歷史的文革已經(jīng)結(jié)束了,但是在文革中形成的那一套思維、話語、關(guān)系、心態(tài),作為一種文革記憶仍然在當(dāng)代存在著。我們并不能很容易就與過去的“文革”劃清立場。這是每一個文革親歷者甚至非親歷者都要警醒的。
文革記憶具有持續(xù)性,這種持續(xù)性使我們不能把文革簡單排斥在現(xiàn)在之外而被形塑
其次,哈布瓦赫認(rèn)定不同的記憶框架決定了不同的集體記憶,但是他忽略了不同的記憶框架之間并非和諧共處而更多是針鋒相對的。正如有論者指出的,哈布瓦赫“關(guān)注的是一種和諧統(tǒng)一的集體,在這樣的集體中,人們分享同一的記憶。但實際社會環(huán)境中的記憶并不總是同類同質(zhì)的。恰恰相反,記憶是社會中不同人群爭奪的對象,也是他們之間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指標(biāo)。主流文化往往控制記憶資源,而對異文化采取壓制態(tài)度,因而異文化抗?fàn)幍闹匾侄伪闶潜4嬉环N相對于主流文化記憶的它類記憶或者福柯所說的‘反記憶’(Counter-Memory)”。記憶的分歧,不僅存在于不同記憶框架之間,甚至存在于同一記憶框架之下。因此,當(dāng)我們用“集體記憶”指稱文革記憶時,不能望文生義,誤認(rèn)為“集體記憶”就是記憶的認(rèn)同與統(tǒng)一,只有正視文革記憶中存在的種種分歧,不回避差異,才能真正達(dá)成認(rèn)同。
實際上,集體記憶與個體記憶的關(guān)系,并非前者支配后者的關(guān)系,而是后者交流、分享形成前者的關(guān)系
最后,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有社會決定論之嫌,在集體記憶/個體記憶的二元結(jié)構(gòu),集體記憶處于絕對強勢的支配地位。這種過分強調(diào)集體記憶的思路在《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中表現(xiàn)無遺:“再特殊的感性材料,再隱秘的私人記憶,在文革書寫中又總是要以歷史‘大敘述’的面目出現(xiàn),總是伴隨著對災(zāi)難起因、起源、后果、教訓(xùn)的解釋與總結(jié)。換言之,有關(guān)文革的私人記憶必須要以公眾記憶的語法才能被書寫被閱讀。”實際上,集體記憶與個體記憶的關(guān)系,并非前者支配后者的關(guān)系,而是后者交流、分享形成前者的關(guān)系。倫理哲學(xué)家馬格利特就提出了一種“分享記憶”(shared memory)的說法。他認(rèn)為:“分享記憶不是一種個人記憶的簡單聚合。它需要交流。分享的記憶融合和標(biāo)定事件記憶者的不同角度。比如廣場上人群的記憶,雖然每個人都只是從自己的特殊一角經(jīng)歷了事件的一個碎片,但卻可以融合成一個整體事件。其他沒有親身經(jīng)歷的人也可以通過敘述的途徑而不是直接的經(jīng)驗分享他們的記憶。分享的記憶是以現(xiàn)代社會記憶分工為基礎(chǔ)的。”這就好比“盲人摸象”,如果人人摸的都是相同的位置,那無論如何都無法拼湊出大象的整體形象來,只有人人摸的部位不同,彼此交流匯總,最后才能得出大象的完整形象。因此,形成集體記憶的前提是保證個人記憶的獨特性。
因此,將文革小說書寫的文革記憶定位為集體記憶,實際上會產(chǎn)生很多誤區(qū)。尤其是,這種對集體記憶的強調(diào),會阻礙“文革記憶”在個體生存論上的積極意義。
“記憶現(xiàn)象學(xué)的”開新
首先我們要看到,對記憶的研究,其實存在兩種面向:“一方面是隨主體意識的現(xiàn)象學(xué)而來的記憶現(xiàn)象學(xué),另一方面是記憶自始就在公眾領(lǐng)域為之發(fā)揮作用的記憶社會學(xué)。”毫無疑問,在以往的“文革記憶”研究中,以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為代表的記憶社會學(xué)一直占據(jù)著統(tǒng)治地位。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集體記憶”理論在國內(nèi)的應(yīng)用方面,“題材豐富,著述頗多,但大多集中于對文革時期發(fā)生的重大事件進(jìn)行分析”。而本質(zhì)上是一種個人記憶研究的記憶現(xiàn)象學(xué)卻一直不受重視,這值得深思。
實際上,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反對的只是記憶生物學(xué),“哈布瓦赫決定性地否棄了關(guān)于記憶的生物學(xué)理論(它支配了上個世紀(jì)開始以來的爭論),轉(zhuǎn)而選擇了一種文化的闡釋框架,認(rèn)為我們的記憶是社會地建構(gòu)的。雖然神經(jīng)心理過程無疑是我們的接受和保持信息的必要條件,但光是對于這些過程的分析不能令人滿意地解釋特定知識領(lǐng)域和記憶領(lǐng)域的構(gòu)成”。在個體記憶/集體記憶的二元結(jié)構(gòu)中,兩者并不截然相對,哈布瓦赫自己也承認(rèn),“人們可以說,個體通過把自己置于群體的位置來進(jìn)行回憶,但也可以確信,群體的記憶是通過個體記憶來實現(xiàn)的,并且在個體記憶之中體現(xiàn)自身”。既然集體記憶只能通過個體記憶來實現(xiàn),那么個體記憶就具有優(yōu)先性。個體記憶(當(dāng)然不是生物學(xué)意義上的)并不必然走向集體記憶,接受集體記憶的支配,正如個體意識也并不必然接受意識形態(tài)的支配一樣。這種對支配和宰制的抵抗,正是社會文化保持活力的體現(xiàn)。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真正能依賴的只有個人記憶,如果記憶是連接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的橋梁的話,那么這個由記憶引發(fā)的行動只能首先由個人來完成,是先發(fā)性的,而個人記憶進(jìn)入公共領(lǐng)域,交流共享而成所謂的集體記憶,則始終是后發(fā)的。
以文革記憶來說,文革記憶是什么?我們當(dāng)然不能簡單理解為“關(guān)于文革的記憶”,正如文革也不能簡單理解為一般的歷史事件。一般認(rèn)為,文革記憶本質(zhì)上是一種“苦難記憶”或者說“創(chuàng)傷記憶”。“苦難”與“創(chuàng)傷”,自然是凸顯文革記憶的受難性質(zhì),以對應(yīng)于文革的浩劫。但文革問題的復(fù)雜之處在于,以所謂的集體記憶引發(fā)的單純的政治討伐和道義譴責(zé),并不能道盡文革記憶的復(fù)雜意涵。如果記憶僅僅作為苦難見證(即把記憶視為對過去的一種信息保存)的面目出現(xiàn),那我們會說,我們降格了文革記憶在歷史中的效能,特別是在我們付出如此慘痛代價的情況下。說到底,建立在苦難與創(chuàng)傷基礎(chǔ)上的文革記憶,是一次我們審視自身精神和意識的難得契機,盡管這個契機是如此讓人苦澀。也正是在這里,我們迫切需要從記憶現(xiàn)象學(xué)的角度來重新審視苦難記憶和創(chuàng)傷記憶。
與記憶社會學(xué)把苦難記憶視為一種苦難見證不同,記憶現(xiàn)象學(xué)把苦難記憶視為一種主體的“精神品質(zhì)”和“歷史意識”:“苦難記憶既是一種主體精神的品質(zhì),亦是一種歷史意識。作為歷史意識,苦難記憶拒絕認(rèn)可歷史中的成功者和現(xiàn)存者的勝利必然是有意義的,拒絕認(rèn)可自然的歷史法則。苦難記憶相信歷史的終極時間的意義,因此它敢于透視歷史的深淵,敢于記住毀滅和災(zāi)難,不認(rèn)可所謂社會進(jìn)步能解除無辜死者所蒙受的不幸和不義。苦難記憶指明,歷史永遠(yuǎn)是負(fù)疚的、有罪的。作為主體精神的價值質(zhì)素,苦難記憶不容將歷史中的苦難置入一個與主體無關(guān)的客觀秩序之中,拒絕認(rèn)可所謂歷史的必然進(jìn)程能賦予歷史中的苦難以某種客觀意義,拒絕認(rèn)可所謂歷史發(fā)展之二律背反具有其正當(dāng)性。苦難記憶要求每一個體的存在把歷史的苦難主體意識化,不把過去的苦難視為與自己的個體存在無關(guān)的歷史,在個人的生存中不聽任過去無辜者的苦難之無意義。苦難記憶因而向人性品質(zh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說到底,建立在苦難與創(chuàng)傷基礎(chǔ)上的文革記憶,是一次我們審視自身精神和意識的難得契機
張志揚在《創(chuàng)傷記憶:中國現(xiàn)代哲學(xué)的門檻》一書中,更是把文革記憶還原為“創(chuàng)傷記憶”。此“創(chuàng)傷記憶”并非指向?qū)嚯y與創(chuàng)傷的見證與指控,而是被描述為“不幸經(jīng)歷的嵌入所造成的‘意義中心’的瓦解”,這個“意義中心”包括“傳統(tǒng)性”與“意識形態(tài)性”。因此,這里的“創(chuàng)傷記憶”就不單指“文革”,而是20世紀(jì)以來國人所遭受的家國變亂。但在張志揚看來,正因如此,“創(chuàng)傷記憶”反而具有一種“開新”能力。如果說“傳統(tǒng)性”的崩潰導(dǎo)致了現(xiàn)代國家的誕生,那么以“文革”體現(xiàn)出來的“意識形態(tài)性”的崩潰,則具有導(dǎo)致現(xiàn)代個人誕生的可能。只有從中國“傳統(tǒng)”的倫理價值、中國“意識形態(tài)”的真理價值以及知識分子的無意識“超我”觀中完全剝離和獨立出來,才能避免“創(chuàng)傷記憶”淪為“同謀記憶”,在自身“創(chuàng)傷記憶”中清除同謀與自欺的遮蔽而敞開純思的意向能力。這有兩個前提,“一是存在從價值中剝離出來而呈現(xiàn)的能再生價值的原初經(jīng)驗;一是個人從社會中剝離出來而呈現(xiàn)的能重組社會的獨立個人”。但是這種“原初經(jīng)驗”和“獨立個人”如何落實呢?書寫者及其書寫就是答案。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書寫,都是對“原初經(jīng)驗”的書寫,在書寫中,才能實現(xiàn)價值的再生。而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書寫者,也必定是從社會中剝離出來的“獨立個人”,因為書寫者的書寫,自動與社會現(xiàn)實劃界了,這與書寫是虛構(gòu)性的還是紀(jì)實性的無關(guān)。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文革的記憶現(xiàn)象學(xué)必然轉(zhuǎn)向記憶詩學(xué)。
“記憶詩學(xué)”中的“文革”
記憶現(xiàn)象學(xué)只是為文革記憶奠定了一個基礎(chǔ),文革小說所書寫的文革記憶,只能在記憶詩學(xué)中才能得到展開。什么是“記憶詩學(xué)”?喬安娜·林德布萊德(Johanna Lindbladh)在《后極權(quán)敘事中的記憶詩學(xué)》一書的“導(dǎo)言”中曾指出,“將詩學(xué)加諸記憶,并非是為了迎合我們那種將過去詩意化的懷舊想法,而是與如下事實相關(guān),即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是神秘的、碎片化的,與我們的意識和感受有著個人性的聯(lián)系,因此有必要有一種不同的認(rèn)識論,以挑戰(zhàn)關(guān)于知識與真實的傳統(tǒng)定義”。因此,“記憶詩學(xué)”的對象并非所有記憶,而只是“文學(xué)性記憶”(literary memory)或者說“詩性記憶”(poetic memory)。文學(xué)性記憶具有如下特點:首先是個人性,文學(xué)性記憶首先是一種個人記憶;其次是情感性,文學(xué)性記憶是一種情感記憶,它與個人的情緒、感受密切相關(guān);再次是非認(rèn)知性,文學(xué)性記憶不是一種認(rèn)知記憶,它的真實不是來自頭腦而是來自心靈;最后是非線性,文學(xué)性記憶是片斷的、非邏輯的、無法推理的。
文革小說所書寫的記憶,只能是一種文學(xué)性記憶,說到底,它并不是關(guān)于過去的信息的儲存,而是在講一個“故事”,一個過去發(fā)生的事。這個“故事”的價值不在于講了什么,也不在于怎么講,而就在于講本身,即在講與聽這個行為過程中,達(dá)到一種經(jīng)驗的交流和分享。講故事者的意圖并不是把“故事”的意義強加給聽者,而聽故事者的目的也不是為了無條件接受“故事”的意義,這個意義并不是故事本身所包含的,而是講與聽的互動行為過程所賦予的。因此從文革敘述、文革書寫中強行歸納出某種集體記憶,實際上是強行為這些“文革故事”賦予一種同一性的意義,也就是強行將過去信息化了。但事實上,作為文學(xué)性記憶的文革記憶,其個人性、情感性、非認(rèn)知性以及非線性的特點,決定了它并不能簡單歸納為某種集體記憶、某種“信息”。
文學(xué)性記憶的反信息化,很大方面表現(xiàn)在它的難以訴說、瑣碎、隱晦、破碎,甚至沉默。有論者形象地稱之為“記憶的微光”:“首先,它與‘記憶的強光’相對,記憶的強光是容易顯露出來的,或是被現(xiàn)行的制度贊許的,甚至歌頌的,是一種強勢存在,如知青的‘青春無悔’記憶模式;或者是明確被現(xiàn)實打壓的,而頑強力挺的存在,如柬埔寨、智利民眾關(guān)于過去傷痕的記憶。其次,它與‘記憶的黑暗’既有一定的關(guān)聯(lián),也有一定的區(qū)別。記憶的黑暗是完全的遺忘,而且其往往因為權(quán)力關(guān)系等,是被打壓或是主體有意遺漏的那一種聲音,如很多知青在講述自身經(jīng)歷的時候有意忽略的紅衛(wèi)兵記憶。而記憶的微光卻類似于躍躍欲試的心態(tài),或是‘欲說還休’的狀態(tài),其可能非常細(xì)小,甚至構(gòu)不成權(quán)力打壓的對象,權(quán)力允許它若隱若現(xiàn),甚至它根本不存在權(quán)力線索中,它游離在權(quán)力之外,如普魯斯特的小點心茶回憶。”正因如此,文革小說作為一種文學(xué)敘述,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來看待“文革”的。無論如何,這種方式顯然不是觀念性的。試圖尋找為什么會被這樣或那樣敘述背后的心理與動機,實質(zhì)上也還是一種觀念性的思路,盡管這種觀念性不是通過內(nèi)容體現(xiàn)出來的。而文學(xué)敘述在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文革時,往往并不是采取一種理性的形式(因此那種將形式理性化并試圖去歸納的做法注定是徒勞的),它甚至?xí)谛问降拿堋⑵扑椤⒖p隙、錯綜之處,在形式的潛意識和非理性中,表達(dá)出自己的意思。
文學(xué)性記憶往往是一種感官記憶,比如味道、聲音、色彩、氣味等。詩人北島就自己最近的回憶性作品《城門開》接受訪談時就提到:“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細(xì)節(jié)的時代……意識形態(tài)化、商業(yè)化和娛樂化正從人們的生活中刪除細(xì)節(jié),沒有細(xì)節(jié)就沒有記憶,而細(xì)節(jié)是非常個人化的,是與人的感官緊密相連的。正是屬于個人的可感性細(xì)節(jié),才會構(gòu)成我們所說的歷史的質(zhì)感。如果說寫作是喚醒記憶的過程,那么首先要喚醒的是人的各種感官。”這一點,我們可以以作家莫言的文革小說《透明的紅蘿卜》為例予以說明。按照《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一書的標(biāo)準(zhǔn)來看,《透明的紅蘿卜》幾乎算不上文革小說,因為當(dāng)中很難概括出什么文革情節(jié)模式出來,整部小說與文革的創(chuàng)傷記憶和苦難書寫幾乎沒有任何關(guān)系,它與其說是在描寫文革記憶,不如說是在描寫一個孩子在文革年代里的感官記憶,而這個記憶全維系在那個“透明的紅蘿卜”上:“黑孩的眼睛原本大而亮,這時更變得如同電光源。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麗的圖畫:光滑的鐵砧子。泛著青幽幽藍(lán)幽幽的光。泛著青藍(lán)幽幽光的鐵砧子上,有一個金色的紅蘿卜。紅蘿卜的形狀和大小都像一個大個陽梨,還拖著一條長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須須象金色的羊毛。紅蘿卜晶瑩透明,玲瓏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殼里苞孕著活潑的銀色液體。紅蘿卜的線條流暢優(yōu)美,從美麗的弧線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長有短,長的如麥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因此《透明的紅蘿卜》中的“文革”是透明的“文革”,其中關(guān)于文革的“記憶”也是一種透明的“記憶”。這種“透明性”是對那種生硬的文革詮釋的一種拒絕。
當(dāng)然,記憶詩學(xué)視野下的文革,并不是要徹底否定文革記憶集體性的一面。實際上,由于“文革小說”是歷史、記憶與敘述三者的綜合,而文革歷史所具有的公共性,已經(jīng)決定了“文革小說”不可能是純粹意義上的個人書寫。但是,筆者還是認(rèn)為,忽視文革小說在文革敘述中的特殊性,過分強調(diào)文革小說中集體性的一面,是十分危險的。因為在當(dāng)前的形勢下,保持文革記憶及書寫的多元性和對話性,遠(yuǎn)比強調(diào)文革記憶及書寫的同一性和獨斷性要來得重要,因為我們都知道,在面對文革這樣的歷史事件上,所謂的集體記憶與集體書寫,是很容易被外界力量所左右和利用的,這是我們不得不警惕的。
正是屬于個人的可感性細(xì)節(jié),才會構(gòu)成我們所說的歷史的質(zhì)感。如果說寫作是喚醒記憶的過程,那么首先要喚醒的是人的各種感官
?參見徐賁《變化中的文革記憶》,《二十一世紀(jì)》,2006年2月號,第93期。
?參見許子?xùn)|《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50篇文革小說》,“導(dǎo)論”第2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0年。許子?xùn)|的這個結(jié)論主要來自理論分析和形勢估判,并非嚴(yán)格的計量統(tǒng)計的結(jié)果,“影響最大”且不說,“讀者最多”也無任何數(shù)據(jù)上的佐證。目前關(guān)于文革的出版物研究、閱讀史研究,實際上還付諸闕如。
?目前大陸歷年來關(guān)于“文革小說”的碩博士論文無數(shù),但能出版者則寥寥。


?這種“牽強”的一個例證是,先鋒派到底是認(rèn)為文革是“很多好人合作而成的荒謬壞事”還是認(rèn)為“無法解釋”,書中前后抵牾。


















編輯/黃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