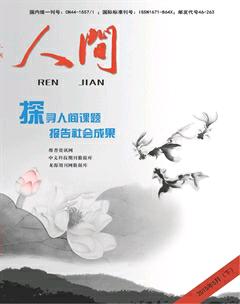論同情在個(gè)體道德養(yǎng)成中的動(dòng)力功能
馬麗娟 章文科
(江南大學(xué),江蘇 無錫 214122)
論同情在個(gè)體道德養(yǎng)成中的動(dòng)力功能
馬麗娟 章文科
(江南大學(xué),江蘇 無錫 214122)
情感主義哲學(xué)家所講的“同情”指的是人的一種能夠體會(huì)自身之外的他者情緒體驗(yàn)的心理機(jī)制,它為個(gè)體的道德養(yǎng)成提供了前提和條件,同時(shí)在個(gè)體的道德修養(yǎng)中發(fā)揮著引導(dǎo)和驅(qū)動(dòng)功能。
同情;道德;驅(qū)動(dòng)功能
日常生活中所說的“同情”是指對(duì)他人的不幸遭遇在情感上發(fā)生共鳴,并給予道義上支持或物質(zhì)上幫助的態(tài)度和行為。作為人類道德形成的前提性心理機(jī)制的“同情”與日常語言中的“同情”很相像,都對(duì)外在于自認(rèn)的他者產(chǎn)生了一種情感上的共鳴,但兩者又不盡相同。這里講的“同情”更多意義上是指人類的一種心理機(jī)制,是個(gè)體能夠理解、體會(huì)處在不同情境的他者,并能產(chǎn)生與他者相近情緒體驗(yàn)的一種能力。這個(gè)“同情”被休謨稱之為“Fellow-feeling”,意為感受到身旁同伴的情緒體驗(yàn);孟子所講的“惻隱之心”、“不忍人之心”也與這里所說的“同情”異曲同工。
一、同情在個(gè)體道德養(yǎng)成中的基礎(chǔ)性功能
休謨是情感主義倫理學(xué)的代表人物,他將道德行為的決定因素歸結(jié)為“道德感”,并且將這種道德感具體化為同情心,主張人類道德的產(chǎn)生根源于同情。休謨所用的同情一詞是由sym(with)和pathy(passion)兩部分組成,意思是指“與……有同感。”同情雖總是一定伴隨著情感,但本身并不是情感,因此不能與憐憫、或仁慈相混淆。在休謨看來,同情是人類天生的一種不可避免的自然本性,是個(gè)體與他者之間情緒的傳遞者。道德行為的產(chǎn)生離不開個(gè)體積極或消極的情感體驗(yàn),但這種情感體驗(yàn)是通過同情來傳遞的。一個(gè)人的情緒體驗(yàn)通過同情就可以變成他者乃至所有人的情緒體驗(yàn),這樣,普遍的道德傾向成為可能。在此,同情也從根源上回應(yīng)了個(gè)體的道德理由問題。
亞當(dāng)·斯密同樣將道德起源歸之于人的一種本能、原始的情感,即同情感。在他看來,不論一個(gè)人有多么自私,在他的本性中都明顯的存在著某種關(guān)心別人命運(yùn)和幸福的情感沖動(dòng),這是人的一種自然本性,它不是由神啟發(fā),亦非源自理性。他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指出,同情是一種基于想象的視他人痛苦為自己痛苦的高級(jí)情感,這種情感是一切道德行為產(chǎn)生的前提,也是人的本性所生來具有的。他說“無論人們會(huì)認(rèn)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gè)人在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guān)心別人的命運(yùn),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的幸福而感到高興外,一無所得。這種本性就是憐憫或同情,就是當(dāng)我們看到或者逼真的想象到他人的不興時(shí)所產(chǎn)生的感情”。[1]正因?yàn)橛腥伺c人之間的情感共鳴,才可能有人們的道德上的交往以及道德關(guān)系的產(chǎn)生。
二、同情在個(gè)體道德養(yǎng)成中的指引性功能
“同情”的心理機(jī)制使得個(gè)體能夠感受到自己與周圍所進(jìn)行的情感交流,在這一基礎(chǔ)上選擇接受道德的指引。休謨首先看到了道德判斷是一種價(jià)值判斷,與事實(shí)判斷不同。休謨認(rèn)為,事實(shí)判斷通常是用“是”與“不是”等系詞來連接,只是判斷事物的真?zhèn)危痪哂猩茞盒再|(zhì)。道德判斷是用“應(yīng)該”與“不應(yīng)該”來連接的,這表明了在道德判斷中有“一種新的關(guān)系或肯定”。這種關(guān)系是價(jià)值關(guān)系,代表了判斷主體有益或無益的傾向,而不僅僅是單純的對(duì)象性關(guān)系,這種肯定代表了一種心理態(tài)勢。所以,善與惡的區(qū)別不是單單建立在對(duì)象關(guān)系上,也不是被理性察知的,而是靠人的情感體驗(yàn)。斯密根據(jù)情感共鳴理論,認(rèn)為“同情”是道德判斷的核心。評(píng)價(jià)自身行為的原則和評(píng)價(jià)別人行為的原則是一樣的。評(píng)價(jià)別人的行為所依據(jù)的,是設(shè)身處地體會(huì)別人的處境時(shí)所感到的,能否與支配行為的情感和動(dòng)機(jī)完全產(chǎn)生共鳴。同樣,我們是否贊成我們自身的行為,也是依據(jù)這種感覺。斯密甚至把同情置于利益之上,強(qiáng)調(diào)法律懲罰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是同情而不是公共利益。
不僅道德判斷的內(nèi)容與對(duì)象摻雜著一定的情感傾向,從而使我們對(duì)這種判斷的理解有了任意性,而且道德判斷的語境每每為情感所渲染。同時(shí),如果道德判斷象杜威等自然主義者所理解的那樣僅僅是對(duì)事實(shí)的描述,把道德命題歸結(jié)為經(jīng)驗(yàn)科學(xué)命題,道德判斷與人的情感無關(guān),那么,這種道德判斷就無法引起人們的共鳴,就不能觸動(dòng)人心,洗刷精神。“道德之所以有勸導(dǎo)和示范作用,正是因?yàn)樗陉愂鍪聦?shí)時(shí)表達(dá)了一種情感和愿望,表達(dá)了判斷者的態(tài)度和信念,否則,它就是一個(gè)冷冰冰的、無法激起他人情感的語句。”
三、同情在個(gè)體道德養(yǎng)成中的“強(qiáng)制”性功能
叔本華也考察了道德的起源問題,并把“采取或不采取某一行動(dòng),純粹是為了另一個(gè)人的利益”這樣一個(gè)動(dòng)機(jī)的考察當(dāng)做道德行為評(píng)價(jià)的標(biāo)桿,由此他將人類道德行為起源問題陳述為“另一個(gè)人的福與禍,怎么可能直接影響我的意志?”這是因?yàn)椋粋€(gè)人能深切體會(huì)另一個(gè)人的痛苦與不幸,正如自己所感受到的那樣,因而急切地希望他(她)能幸福正如這個(gè)人在某種情況下希望自己能幸福一樣。這種同情是“一切自發(fā)的公正和一切真正仁愛”的唯一真正基礎(chǔ)。人的一切行為總有其動(dòng)機(jī),而道德動(dòng)機(jī)及其后的道德意志產(chǎn)生的源泉便在于這種“同情”。
《孟子·公孫丑上》有段話:“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nèi)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yù)于鄉(xiāng)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這里所講的事例也說明了“同情”在個(gè)體道德養(yǎng)成中的“強(qiáng)制”性功能:當(dāng)個(gè)體見到小孩子快要落入井中,“自然地”想要去搭救,但這種行為最初的發(fā)生并不是因?yàn)樵撔袨橹黧w認(rèn)識(shí)孩子父母或者想要得到他人的贊譽(yù)。從這種“自然的行為”中我們恰恰看到了“惻隱之心”(即同情)所具有的強(qiáng)制性力量。
[1](英)亞當(dāng)·斯密,《道德情操論》[M].蔣自強(qiáng)譯,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97:5.
[2](英)休謨,《人性論》[M].關(guān)文運(yùn)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3.
[3](德)叔本華,《倫理學(xué)的兩個(gè)基本問題》[M].任立、孟慶時(shí)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3.
[4]《孟子》[M].萬麗華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B82
A
1671-864X(2015)05-0126-01
馬麗娟(1989—),女,云南昆明人,江南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研究。章文科(1991—),女,江蘇無錫人,江南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