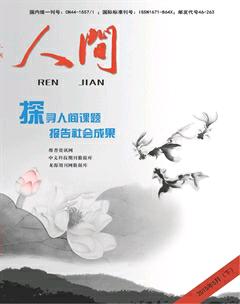現(xiàn)代性詞義追溯
周津
(武警警官學(xué)院,四川 成都 610213)
現(xiàn)代性詞義追溯
周津
(武警警官學(xué)院,四川 成都 610213)
現(xiàn)代性一詞在十七世紀(jì)英語(yǔ)中開(kāi)始流行,十八世紀(jì)后期霍勒斯·沃波爾將它運(yùn)用到美學(xué)語(yǔ)境。馬泰·卡林內(nèi)斯庫(kù)在《現(xiàn)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詳細(xì)梳理了“現(xiàn)代”的發(fā)展淵源,本文試圖在前人的基礎(chǔ)上追溯與梳理現(xiàn)代性詞義的發(fā)展變遷。
現(xiàn)代性;五副面孔
馬泰·卡林內(nèi)斯庫(kù)在《現(xiàn)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曾經(jīng)詳細(xì)地?cái)⑹觥艾F(xiàn)代”概念的起源,②他認(rèn)為“現(xiàn)代”概念首先是在與古代、中世紀(jì)的比照與區(qū)分中呈現(xiàn)自己的意義的。在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現(xiàn)代概念經(jīng)常與古代概念匹配使用,在十八世紀(jì),這個(gè)概念經(jīng)常指建筑、服飾和語(yǔ)言的流行時(shí)尚,基本上在不屑一顧的口氣中被提及。直到十九世紀(jì)、特別是二十世紀(jì),這一概念的意義才開(kāi)始發(fā)生變化。
現(xiàn)代性就廣義意義而言,即成為現(xiàn)代,適應(yīng)現(xiàn)時(shí)及其無(wú)可置疑的“新穎性”。現(xiàn)代性一詞在十七世紀(jì)英語(yǔ)中開(kāi)始流行,十八世紀(jì)后期霍勒斯·沃波爾將它運(yùn)用到美學(xué)語(yǔ)境。在法國(guó),“現(xiàn)代性”只是在十九世紀(jì)前半期才被使用。要精確地表明一個(gè)概念出現(xiàn)的時(shí)間總是很艱難的,像“現(xiàn)代性”這樣極富爭(zhēng)議和錯(cuò)綜復(fù)雜的概念更是如此。但有一點(diǎn)是非常明確的:只有在一種特定的時(shí)間意識(shí)框架中,即線性不可逆轉(zhuǎn)、不可阻止地流逝的歷史時(shí)間意識(shí)的框架中,現(xiàn)代性這個(gè)概念才能被構(gòu)想出來(lái)。馬泰·卡林內(nèi)斯庫(kù)認(rèn)為現(xiàn)代性的觀念雖然與歐洲歷史中的世俗化過(guò)程有關(guān),但這個(gè)概念卻起源于基督教的末世教義世界觀,因?yàn)檫@種世界觀所隱含的時(shí)間意識(shí)具有不可重復(fù)的特點(diǎn)。現(xiàn)代性的概念在異教的古代世界觀中顯然不存在,它產(chǎn)生于基督教的中世紀(jì)。
他還認(rèn)為,在西方文明史上存在兩種現(xiàn)代性:一種是西方文明史的現(xiàn)代性,另一種則是美學(xué)概念的現(xiàn)代性。并且在十九世紀(jì)前半期的某個(gè)時(shí)刻,這兩種現(xiàn)代性發(fā)生了無(wú)法彌合的分裂。我們關(guān)注的是西方文明史的現(xiàn)代性概念。表面看來(lái),似乎沒(méi)有什么比現(xiàn)代性概念更遠(yuǎn)離宗教。似乎“現(xiàn)代人”都是不信教者或“自由思想者”。現(xiàn)代性與世俗世界觀的聯(lián)系仿佛也是理所當(dāng)然的。但是,當(dāng)我們將現(xiàn)代性放在一種歷史視野下就會(huì)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性與世俗世界的關(guān)系比起現(xiàn)代性與基督教的關(guān)系來(lái)顯得微乎其微。馬泰·卡林內(nèi)斯庫(kù)把現(xiàn)代性與基督教的關(guān)系區(qū)分為四個(gè)階段:
第一階段,中世紀(jì)的人對(duì)“現(xiàn)代人”這一名稱的使用是相對(duì)于“古代人”的名稱而言的。前者是指當(dāng)時(shí)的人,新來(lái)者,而后者指任何一個(gè)其名字從過(guò)去流傳下來(lái)并為敬意所包圍的人,不管他生活在基督之前還是基督之后,也不管他是基督徒與否。這反映了“古代人”傳統(tǒng)的本質(zhì)的一致性,其連續(xù)性沒(méi)有被基督的到來(lái)而打斷。
第二階段,從文藝復(fù)興延伸至整個(gè)啟蒙時(shí)期,其特征表現(xiàn)為現(xiàn)代性逐漸與基督教分離。作為文藝復(fù)興的結(jié)果,“古代人”這個(gè)名稱經(jīng)歷了重要的語(yǔ)義變化,它不再是一個(gè)不加區(qū)分的過(guò)去,而是指過(guò)去得天獨(dú)厚,足資垂范的部分——那些異教的古典時(shí)代和希臘羅馬作家。現(xiàn)代人應(yīng)該模仿古代人,然后趕超他們,直到現(xiàn)代人宣稱他們優(yōu)于古代人。這一時(shí)期,權(quán)威原則僅在宗教之外受到挑戰(zhàn),傳統(tǒng)仍然是神學(xué)的基石,但是即使如此,現(xiàn)代批判精神也已經(jīng)導(dǎo)致了區(qū)分啟示式的、歪曲的、虛假的傳統(tǒng)和真正的傳統(tǒng)的努力,對(duì)廣為接受的基督教傳統(tǒng)所做的各種各樣非正統(tǒng)的解釋背后,也有著現(xiàn)代批判精神的存在。到了十七、十八世紀(jì),即使堅(jiān)定的現(xiàn)代人中的好的基督徒也覺(jué)得宗教觀點(diǎn)對(duì)于他們來(lái)說(shuō)太過(guò)非時(shí)間性,從而使自己只限于使用出自理性與進(jìn)步哲學(xué)的世俗概念。在啟蒙的理性主義和經(jīng)驗(yàn)主義時(shí)期趨近尾聲之時(shí),現(xiàn)代性的概念已經(jīng)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先前的中立性。它同宗教的沖突最終變得正面化,做一個(gè)現(xiàn)代人基本上就是做一個(gè)“自由思想者”。
第三個(gè)階段,覆蓋浪漫主義時(shí)期,十八世紀(jì)后期文學(xué)上的宗教復(fù)興,對(duì)于情感和直覺(jué)的新的強(qiáng)調(diào),對(duì)原創(chuàng)性和想象的崇拜。這一切同對(duì)哥特風(fēng)格和整個(gè)中世紀(jì)文明的普遍狂熱相結(jié)合,構(gòu)成一場(chǎng)更大,有些混亂復(fù)雜的運(yùn)動(dòng)的一部分。這就是反對(duì)啟蒙時(shí)期干癟的理性主義及其在美學(xué)上的對(duì)應(yīng)物新古典主義的運(yùn)動(dòng)。浪漫派把“現(xiàn)代天才”等同于“基督教天才”,并認(rèn)為有兩種自律的,被不可跨越的鴻溝所分隔的美:一種是異教的,一種是基督教的。啟蒙時(shí)期謹(jǐn)慎的相對(duì)主義式的哲學(xué)現(xiàn)在被一種宿命論式的歷史主義取代,后者強(qiáng)調(diào)文化周期之間的總體不連續(xù)性。生活在基督教周期即將結(jié)束之時(shí),生活在一種既廣闊又狹隘、既崇高又富有悲劇性的現(xiàn)代性中,我們想象他們擁有的意識(shí):一種基督教正在死亡的新的現(xiàn)代性情感。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浪漫派首先想到“上帝之死”,并于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的預(yù)言教義中給予“上帝之死”以中心地位之前很久,就將這個(gè)本質(zhì)上現(xiàn)代的主題納入了他們的作品。奧克塔維奧·帕斯在論現(xiàn)代詩(shī)歌的著作中,以驚人的洞見(jiàn)指出“上帝之死”這個(gè)浪漫派神話的矛盾內(nèi)涵。他所寫(xiě)的著作名為《沼澤的孩子》,論文的基本觀點(diǎn)之一就是,現(xiàn)代性是一個(gè)“純粹的西方概念”,而且它與基督教不能分離。“上帝之死”的神話實(shí)際上不過(guò)是基督教否定循環(huán)時(shí)間而贊成一種線性不可逆時(shí)間的結(jié)果,作為歷史的軸心,這種線性不可逆時(shí)間導(dǎo)向永恒性。他寫(xiě)到:“上帝之死是個(gè)浪漫派主題。它不是哲學(xué)上的,而是宗教的:就理性而言,上帝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如果他存在,他就不可能死;如果他不存在,一個(gè)從不存在的人又怎么可能死呢?但只有從一神教和西方直線不可逆時(shí)間的觀點(diǎn)看,這種推理才是有效的。……如果有人說(shuō):‘上帝死了,他是在宣告一個(gè)不可重復(fù)的事實(shí):上帝永遠(yuǎn)地死了。在作為一個(gè)線性不可逆進(jìn)程的時(shí)間概念中,上帝之死是無(wú)法想象的,因?yàn)樯系壑莱ㄩ_(kāi)了偶然性和無(wú)理性的大門(mén)。對(duì)此有雙重回答:反諷,幽默,理智悖論;還有詩(shī)學(xué)悖論,形象。這兩者都出現(xiàn)在浪漫派中……盡管每一種態(tài)度的源泉都是宗教上的,但這是一種奇怪而矛盾的宗教,因?yàn)樗俗诮棠颂摽盏囊庾R(shí)。浪漫派的宗教性是非宗教的、反諷的:浪漫派的非宗教是宗教的、痛苦的。”①
第四階段,始于將近十九世紀(jì)中期,這個(gè)階段重新肯定了“上帝之死”,它主要關(guān)心的是上帝死亡所帶來(lái)的后果。現(xiàn)代性和基督教之間的分裂似乎是徹底的,但如果想想眾多被我們歸入“現(xiàn)代”的最杰出作家要么離開(kāi)了猶太—基督教傳統(tǒng)就無(wú)法理解(無(wú)論如何離經(jīng)叛道,他們都繼續(xù)代表著這個(gè)傳統(tǒng)),要么奉行了一種有著無(wú)可置疑的激進(jìn)無(wú)神論,我們就會(huì)質(zhì)疑現(xiàn)代性和基督教之間的徹底分裂的真實(shí)性了。“上帝之死”似乎開(kāi)啟了宗教求索的一個(gè)新紀(jì)元。現(xiàn)代性似乎理所當(dāng)然地接受了“上帝之死”這個(gè)詩(shī)學(xué)悖論。但是,正是在這一宗教求索的新紀(jì)元中,誕生了像克爾凱郭爾、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頭撞開(kāi)理性石墻,反對(duì)自明真理,敢于面對(duì)絕望和瀕臨現(xiàn)代性深淵的絕境。并在絕望中到《圣經(jīng)》中尋求啟示,以積極主動(dòng)的姿態(tài)反抗自明真理。
注釋:
①參見(jiàn)馬泰·卡林內(nèi)斯庫(kù).《現(xiàn)代性的五副面孔—現(xiàn)代注意、先鋒派、頹廢、媚俗藝術(shù)、后現(xiàn)代主義》[M].周憲、許鈞主編.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2年
②出自?shī)W克塔維奧·帕斯.《沼澤的孩子》.參馬泰·卡林內(nèi)斯庫(kù),《現(xiàn)代性的五副面孔—現(xiàn)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藝術(shù)、后現(xiàn)代主義》[M].周憲、許鈞主編.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2年
B26
A
1671-864X(2015)05-0204-01
周津(1982.06-),女,漢族,四川隆昌,講師,碩士,武警警官學(xué)院,文藝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