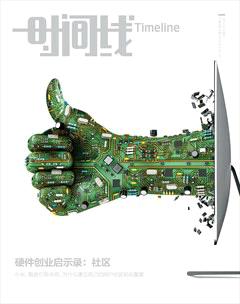Uber是誰?
徐赫
2月13日,總部位于美國舊金山的汽車租賃平臺服務商Uber,宣布正式進軍中國市場,并啟用中文名“優步”。近期,其業務已出現在上海、深圳等地,未來還會拓展到北京。
Uber最早提供豪華私家車的租賃服務,以解決用戶各類的用車問題。而它最終的理想,則是打造一整套便捷的交通信息網絡。
用戶只需安裝一個APP,就可以訂車或租車。與出租車不同的是,Uber的司機和車輛均來自于非官方的租車登記機構,他屬于一家與Uber合作的汽車租賃公司。也就是說,Uber不直接經營汽車租賃,其打造的是一個汽車租賃的信息平臺。用戶、公司和司機個人都可以通過這個平臺注冊、尋找用戶。
這樣全新的商業模式,讓Uber備受投資界追捧。去年8月23日,Uber得到美國私募巨頭TPG和Google Ventures等機構的C輪融資,總計2.5億美元。這使得其估值高達35億美元—要知道,一年前這個數字還不超過10億美元。
當然,風頭正勁的Uber,野心絕不會止步于汽車租賃市場。Uber CEO Travis Kalanick曾表示,“Uber的未來是利用交通的信息數據一站式解決人們的出行問題。”
汽車租賃只是第一步,公司接下來會為用戶提供多種基于交通信息的出行服務。事實上,信息與數據才是他最喜歡談及的話題。
目前,Uber的公司業務已擴展到18個國家42個城市和地區,年收入超過1億美元。現在,它又即將進入交通問題同樣嚴峻的中國。
然而,Uber進入中國的時機卻正值中國本土孵化的嘀嘀打車、快的打車等打車APP激戰正酣之時。Uber 主打的私家車叫車服務業務,雖然表面上不會與這些叫車軟件同市場競爭,但這場戰爭已讓用戶嘗到了用低價體驗不錯服務的甜頭,勢必也會影響到Uber這樣的高端叫車服務的市場接受度。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對租車公司的牌照有嚴格限制,且保護主義嚴重。在接受《財富》采訪時,Kalanick曾表示,他們最初要解決打車難這樣一個“小”問題,但后來卻發現,其實這背后卻牽扯了眾多復雜的深層次問題。
Uber背后的人
Uber的一切,都離不開他的創造者Travis Kalanick。
Kalanick誕生于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六年級的時候,他就開始第一次“創業”—挨家挨戶推銷菜刀。18歲那年,他取得了SAT(美國高考)1580的高分(滿分是1600),和鄰家大叔一同開了一家SAT培訓班,命名為“1500分+”,賺了不少外快。
雖然憑借優異成績進入了有工程師搖籃之稱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但和很多知名的硅谷創業者一樣,1999年,他也選擇了退學。
P2P 檔案交換搜索引擎Scour是Kalanick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創業項目,早期員工只有他和5位同學。該引擎因開創了文檔的免費分享模式而流量迅速攀升,但他同時觸犯了出版公司的利益。2000年,Scour被全球29大媒體發行商聯合控告,追償 2500億美金。兩年后,Scour敗訴,并宣布破產。、
盡管這次經歷讓Kalanick在金錢上遭受了“巨大損失”,但“我從Scour的失敗上獲得的最多的是勇氣。”Kalanick說。“我看到的是一位精明的商人,而不是一個只有20歲的年輕人。”
2007年,Kalanick的第二個創業項目Red Swoosh以1500萬美元的價格賣給了全球最大的CDN服務商Akamai,賺取了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桶金”。得到豐碩資金的Kalanick在舊金山地區買了一套豪宅,不時邀請一些創業者來做客,并向他們提供一些天使投資。
賺取千萬美金并成為天使投資人—Kalanick30歲時就獲得了財務自由。不過,他依然向往創業帶給他的快感。
但Kalanick并不急于繼續創業,因為他還在尋找合適的合作伙伴,以及可以“鉆空子”的領域—Uber的出現,讓我們看到,這個領域就是由大公司甚至是政府機構把控的租車市場。
破壞者
作為硅谷精英及反權威主義者,Kalanick主張打破常規。這種做法可想而知會給他帶來重重困難,但他發現,朋友總比敵人多。
Uber的成立得益于Kalanick有一位與他觀念非常相似的朋友Garrett Camp,后者是一家名為StumbleUpon社交頁面推薦引擎的創始人。2007年,Ebay收購了這家公司。之后,Garrett被迫進入了一種大公司職員的生活狀態,這與他的個人性格非常不吻合。“他過得糟透了,我得去和他找點新的事情做。”Kalanick說。
2008年冬的一天,兩人相聚在巴黎一家酒吧。“我們做點事吧,解決該死的舊金山出租車問題。”第二天酒醒后,Garrett對Kalanick嘟囔著,“ 我們自己找司機和車供人們租用。”
在Kalanick眼中,Garrett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小而美”追求者,他喜歡舒適、便捷的生活方式,這與他追求的商業創新思維非常吻合。同時,舊金山的打車難問題非常突出,需要有一家公司能打破出租車公司的壟斷,給用戶提供更多的方便。
Kalanick聽到這個想法后欣喜若狂。當天,兩位酒醒的中年男人確定了出資金額和方向—買一輛奔馳S級轎車和一個地下停車位,再請一個司機,二人共同負擔司機的工資。
2009年,Garrett順利履行完出售StumbleUpon公司時綁定的合同,著手準備豪華車分時租賃的叫車軟件。公司花費一年的時間招人、確定架構、制作軟件。2010年,Kalanick、Garrett以及工程師Oscar Salazar,在紐約的大街上第一次通過叫車軟件體驗了Uber的叫車服務—雇傭的司機開著公司僅有的那輛奔馳S如約到達。
2011年下半年,Uber進行了一輪3700萬美元的融資,彼時,公司在兩人的領導下已經將業務拓展到世界35個城市。Uber的在線用戶突破了千萬的注冊,其高端車租賃項目成為了用戶追捧的出行選擇。
但這些好消息并未掩蓋其所遭遇的眾多問題。
首先是來自對手的競爭。同樣起步于舊金山的叫車軟件Lyft也在當時將業務拓展到6個城市,并得到了新一輪的融資。后者雖然沒有Uber的發展速度快,但其穩扎穩打的風格搶走了Uber不少的客戶,其成為Uber在美國本土的第一競爭對手。
而最棘手的問題是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汽車租賃服務限制問題。在2011年到2013年的時間中,Uber與出租車公司、行業協會以及各地政府進行了一場持續三年的非官方戰爭。
Kalanick身兼“創業家”和“壞小子”之名。
美國華盛頓地區出租車協會曾以Uber不具備汽車租賃牌照為由,起訴Uber非法運營,“好戰”的Kalanick召集用戶向該協會代表的郵箱發了5萬封郵件和37000條Twitter信息。
英國劍橋政府也曾試圖關閉Uber在當地的辦公室,Kalanick當天就發布了一條Twitter稱,“劍橋市政府陳舊迂腐的法律條文和哈佛、MIT一樣出名。”
Kalanick沒有統計過他究竟收到過多少份要求Uber停止在當地運營的信件,但他沒有退縮。“你只需要告訴Kalanick戰爭開始了,他就會帶給你勝利。”曾經投資過Kalanick第一家公司的好萊塢第一經紀人Michael Ovitz說。
但是,Uber不能僅僅只有敢于挑戰權威的勇氣。宣稱將要進入中國上海和深圳,且會和當地租車公司合作的Uber,最近就遭到了兩地交通部門的質疑。“深圳微博發布廳”的新浪微博認證帳號就曾發布消息稱,Uber與租車公司之間不僅提供車輛還提供司機服務的合作,屬于沒有牌照情況下提供的出租車服務,是擾亂出租車營運秩序的非法運營。
可想而知,Kalanick在復雜的中國市場又會面臨一場硬仗!
目前,Uber已在舊金山成立政策研究部門,專門研究世界各地汽車租賃市場的政策、法規。Uber新一輪融資也將主要用于抗擊保護主義、反競爭。
未來:數據
Uber目前的境況并不樂觀。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政策、法規以及出租車協會都在不停地打壓Uber,因為他們認為,Uber在不停蠶食其賴以生存了數十年的“鐵飯碗”。
Kalanick顯然不會成為坐以待斃的困獸。雖然身處輿論漩渦之中,但他經常抽身去給華爾街的投資者們“布道”。兼具技術和商業頭腦的Kalanick已經想好了Uber未來的藍圖—基于交通信息做更便捷的出行解決方案。
Kalanick的構想并非不切實際。技術出身的他熱衷于數據整合,一直致力于高端汽車租賃業務的Uber,今年1月中旬,進一步下調了其廉價汽車租賃服務“UberX”在美國多個城市的價格,其最終目標是使其服務成為市面上最便宜的出租車服務。而此前,Uber也宣布在上海的租車服務定價下調30%。無疑,門檻降低后的Uber會擁有更為廣泛的汽車租賃和行駛信息。
在Kalanick看來,Uber不是簡單的出行助手這樣簡單的代步車租賃公司,而是在迅速擴張的同時,加大自有平臺上的信息數據量,最終希望能做到個性化的數據歸類,做一站式交通工具解決方案。
在接受《財富》雜志采訪時,Kalanick表示,Uber未來的業務是“用戶需要的時候,Uber馬上滿足他們的愿望”,而且采取的方式是多樣化的。他舉例說,“未來如果你想快遞包裹給住在另一區的朋友,同樣可以呼叫空閑的Uber司機。”
2013年,Uber已經做過用冰激凌車給預定的人送冰激凌,在情人節遞送玫瑰花,提供租賃直升飛機服務,或是在德克薩斯提供燒烤等服務了。不過,這些目前依然是試驗性,其主要任務依然是擴張。
但不可否認的是,Uber正在通過自己的信息交換平臺,召集包括像冰淇淋車、直升飛機、冷凍車這樣的各類商用交通工具提供商,意圖為人們提供包括快遞、出行信息甚至策劃等服務。
簡單來說,未來Uber打算用“租”的理念改變人們對于各類商業交通工具的運用理念,它提供了一整套的租賃解決方案,提高人們出行的效率。
或許未來會出現這樣一種景象:一位用戶要在同一時間去商場購物、送公司文件或者接送親友。而他解決“分身”問題的辦法只需用手機打開Uber的APP,然后接受賬單就可以了。
Kalanick曾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提到,Uber未來的競爭對手絕不會是出租車公司,而是互聯網公司,尤其是以數據分析為主的公司。
那么,中國的相關互聯網公司,你準備好Uber的入侵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