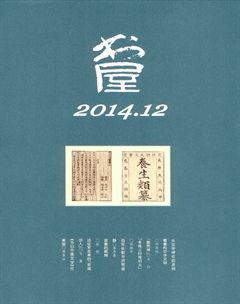遠(yuǎn)征軍走來的“玫瑰詩人”
飛翼
一
“用血從荊棘上換取玫瑰,有靈犀自花唇上聽得花叫。”這是詩人趙國泰對“玫瑰詩人”彭邦楨的評介。
彭邦楨祖籍湖北黃陂,1919年生于漢口,黃埔十六期畢業(yè)。他,青年投筆從戎,中年負(fù)笈去臺,以“彭老大”蜚聲詩壇;壯年中西合璧,與美國“黑珍珠”共掌世界詩壇“帥印”,并以一首《月之故鄉(xiāng)》詩歌風(fēng)行世界!他與中國遠(yuǎn)征軍的淵源,先得從中國抗戰(zhàn)的生命線——滇緬公路說起。
“盧溝橋事變”后,日軍相繼占領(lǐng)了中國主要大城市與百分之九十五的工業(yè),中國沿海幾乎所有的港口都落入敵手。戰(zhàn)爭變成了消耗戰(zhàn),對于中國來說,物資供應(yīng)問題此時顯得異常嚴(yán)峻起來。旅居海外的華僑紛紛捐款捐物,籌集了大批國內(nèi)急需的藥品、棉紗、汽車等物資,支援國內(nèi)抗戰(zhàn)。國民政府也拿出極有限的外匯從西方購買了一批汽車、石油、軍火等。這些物資需要緊急運(yùn)回國內(nèi),中國急需一條安全的國際運(yùn)輸通道。為此,中國政府于1938年開始組織三十個縣的勞工約二十萬人修建滇緬公路。
當(dāng)獲悉滇緬公路急需大量汽車司機(jī)和修理工,著名愛國僑領(lǐng)陳嘉庚于1939年2月8日發(fā)表了《南僑總會第六號通告》,號召華僑中的年輕司機(jī)和技工回國服務(wù),與祖國同胞并肩抗戰(zhàn)。這個通告很快就傳遍了東南亞各地,共有三千一百九十二名華僑司機(jī)和修理工紛紛回國服務(wù),他們被稱為“南僑機(jī)工歸國服務(wù)團(tuán)”。
1940年,彭邦楨畢業(yè)于成都中央軍校(黃埔)十六期三總隊步科,分發(fā)重慶某部任少尉排長。次年,他與西南聯(lián)合大學(xué)的同學(xué)們組成了一個戲劇隊,專門到滇緬公路前線作巡回慰問演出。途中,他向國民革命軍新建第五軍報到,繼續(xù)為抗戰(zhàn)義演。
彭邦楨在慰問期間了解到,隨著日軍侵占越南,滇越鐵路中斷,滇緬公路竣工不久就成為了中國與外部世界聯(lián)系的惟一的運(yùn)輸通道。抗戰(zhàn)初期,幾百萬軍隊所需要的武器裝備;維持經(jīng)濟(jì)運(yùn)轉(zhuǎn)所需要的各種物資;無數(shù)內(nèi)遷到大后方的人們所需要的基本消費(fèi)品等物資,都依賴這條生命線運(yùn)進(jìn)大后方。而自1940年10月起的六個月期間,日軍共出動飛機(jī)四百多架次,重點(diǎn)轟炸這里的橋梁。每次轟炸之后,駐守在橋邊的工程搶修隊就及時對大橋進(jìn)行搶修。這些負(fù)責(zé)搶修橋梁的人很多都是當(dāng)年建橋的工程技術(shù)人員。有時炸彈仍然在爆炸、空襲還沒有結(jié)束,他們就開始搶修工作。
于是,彭邦楨與西南聯(lián)大的同仁一道,深入到民工、工程技術(shù)人員與將士中間,搜集到大量的第一手素材,然后自編自演一批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跡的短平快節(jié)目,大受前線勇士歡迎,極大地鼓舞了將士們的士氣。彭邦楨因此被第五軍晉升為上尉參謀。
當(dāng)彭邦楨自畹町演出回到昆明之后,中國遠(yuǎn)征軍第五軍所屬部隊卻在緬甸被日軍擊潰。“在野人山的一個月里,我們一天的食物是一包壓縮餅干。”一位戰(zhàn)友特地給彭邦楨講述了戴安瀾將軍死難的慘景——
那是1942年春,中國遠(yuǎn)征軍為協(xié)助駐緬甸英軍及保護(hù)我國惟一的對外通道——滇緬公路,派遣遠(yuǎn)征軍第五軍、第六軍及第九十六軍進(jìn)入緬甸。這是我國第一次配合盟軍作戰(zhàn),因英軍擅自后撤,使我國軍的側(cè)翼暴露,陷入被包圍的危機(jī),于是便不得不后撤,但日軍早已占領(lǐng)了臘戌,截斷了我國軍的歸路。可是,第五軍是我最精銳的機(jī)械化部隊,也曾是我國軍的總預(yù)備隊。遠(yuǎn)征軍除第三十八師由師長孫立人將軍率領(lǐng)安全撤入印度外,第二○○師長戴安瀾將軍在突圍的途中遭到猝擊而殉職,于是第五軍軍長杜聿明將軍便決心向北撤退,繞道回國,最后竟進(jìn)退維谷,進(jìn)入絕境的野人山,有不少戰(zhàn)士因?yàn)轲囸I和勞累,倒斃在森林里,被螞蟻啃得只剩下一堆堆白骨,真的是“一將成名萬骨枯”!
此時此刻,彭邦楨不禁想起戴將軍出征前作詞譜寫的歌曲《戰(zhàn)場行》,以及他遠(yuǎn)征途中寫下的一首氣壯山河的《七絕·遠(yuǎn)征》。詩云:“萬里旌旗耀眼開,/王師出境島夷摧。/揚(yáng)鞭遙指花如許,/諸葛前身今又來。//策馬奔車走八荒,/遠(yuǎn)征功業(yè)邁秦皇。/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長弓射夕陽。”
彭邦楨還噙著熱淚口占詩一首,詩祭以身殉國的戴將軍及其死難將士英魂。其中有一節(jié)詩云:“而今啊!您已遠(yuǎn)離。/尸骨變成泥土,/靈魂化作空氣。/您離開了我的身邊,/你離開了我的眼睛,/但,您離不開我的心里!”
二
一個偶然的機(jī)會,彭邦楨得知:在中國人民抗戰(zhàn)的關(guān)鍵時刻,美國援華抗日的美國志愿航空隊——“飛虎隊”來到了昆明。“飛虎隊”的全稱為“中國空軍美國志愿援華航空隊”,創(chuàng)始人是美國退役飛行教官陳納德。1941年夏秋,他在羅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以私人機(jī)構(gòu)名義重金招募兩百多名美軍飛行員和機(jī)械師,來華對日作戰(zhàn)。
當(dāng)時倭寇控制了中國的港口和運(yùn)輸系統(tǒng),幾乎使國民政府與外界隔絕。這一小隊空戰(zhàn)人員駕駛著破舊的老式飛機(jī),盡管經(jīng)常面臨燃料、零件和飛行員的不足,但他們不斷譜寫傳奇,多次戰(zhàn)勝遠(yuǎn)比它們規(guī)模大、裝備好的日本空軍。“飛虎隊”開辟空中走廊,給抗戰(zhàn)前線空運(yùn)給養(yǎng),在緬甸公路提供空中掩護(hù),并在中國的上空與日本侵略者進(jìn)行了殊死的搏斗。
為“飛虎隊”的精神所動,彭邦楨主動請纓為美軍“飛虎隊”服務(wù),他因此被任命為云南驛空軍招待所文書股股長。
云南驛是中原文化傳入云南的橋頭堡,也是西南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驛站。云南驛站雖然早已荒廢,但仍然保存了不少作為驛站時期的歷史遺跡和人文景觀:由民居、商鋪、旅店、馬廄等組成的古樸城鎮(zhèn)風(fēng)貌,古代絲綢茶馬驛道的道路遺跡等仍歷歷在目。
云南驛招待所位于滇緬公路線上。招待所除有主任、副主任外,另設(shè)文書、總務(wù)、會計和招待四股,為“飛虎隊”提供食宿、理發(fā)和洗衣等系列服務(wù),招聘的服務(wù)員都是會講英語的知識青年。
彭邦楨走馬上任后,“飛虎隊”給他的印象是:一個個生龍活虎,人人頭戴船形帽,身著飛行皮夾克,標(biāo)致極了!每個飛行員的皮夾克背面均繡有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其下另繡有“來華作戰(zhàn)洋人,軍民一體救護(hù)”二行金字。
盡管戰(zhàn)時物資奇缺,但招待所對美軍的生活安排得十分周到,“飛虎隊”享受著當(dāng)時中國最高生活標(biāo)準(zhǔn)。“飛虎隊”員們兩人住一間房,早餐是三個雞蛋、兩塊煎餅、兩片云南火腿,另加洋芋片、吐司,餐桌上還擺滿黃油、果醬、糖油、白糖、胡椒、牛奶等。endprint
由于中美飲食習(xí)慣的不同,在彭邦楨看來,“飛虎隊”隊員也有雞蛋里挑骨頭的時候。有一天總務(wù)股長對彭邦楨說,正為買不到雞發(fā)愁。彭邦楨告訴他:可以到山那邊買烏雞作替補(bǔ),一樣有營養(yǎng)。
哪知,待總務(wù)人員翻山越嶺買回烏雞煨成雞湯招待“飛虎隊”時,隊員們一見雞肉皮是烏的,認(rèn)為招待所是在用病雞來應(yīng)付他們。不論招待所長怎樣解釋烏雞營養(yǎng)價值高,全體隊員就是不依不饒。直至把烏雞湯全部倒掉,他們才肯進(jìn)餐。
有一次,彭邦楨還親眼目睹了“飛虎隊”與日軍浴血奮戰(zhàn)的悲壯場面。由于云南驛地處前線,日軍經(jīng)常來犯。飛虎隊員駕駛著P—40戰(zhàn)機(jī)沉著應(yīng)戰(zhàn),頃刻間,一個機(jī)尾掉過去,另一個機(jī)頭掉過來,對準(zhǔn)日機(jī)猛烈開火,很快日機(jī)像流星一樣墜毀在山野。
彭邦楨從統(tǒng)計資料中得知:自1941年底到1942年7月,“飛虎隊”在華作戰(zhàn)期間共擊落日機(jī)近三百架,但他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有二十四人在戰(zhàn)斗中犧牲或失蹤。
當(dāng)時修機(jī)場沒有機(jī)械設(shè)備來平整土地,聰明的中國人在附近的石山上將炸出的石頭一劈兩半,打造成了一種圓柱體的石碾,百余人拉著石碾子碾壓機(jī)場的地基,修成了一個個簡易機(jī)場。
有一天,三百余名工人正在機(jī)場搶修跑道,忽然日機(jī)突然襲擊,美軍飛行員不是來不及起飛、就是在緊急起飛過程中,機(jī)毀人亡。此次突襲造成幾十架飛機(jī)被毀和三百余名飛行員、工人傷亡。
當(dāng)時,在戰(zhàn)壕里親眼目睹了這一慘狀的彭邦楨不禁失聲痛哭。晚上,他夜不能寐,辭以情發(fā),一組戰(zhàn)地詩歌《詩玫瑰的花圈》躍然紙上。其中一首云:“而今啊!你已遠(yuǎn)離;/尸骨變成泥土,/靈魂化作空氣。//流水的音波上,/白云的翅膀上,/我仿佛聽到又看到:/你的聲音,你的形象,/仍是那么優(yōu)美,/仍是那么嫵媚!”
三
1942年3月,根據(jù)簽訂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緬路協(xié)定》及英方請求,中國派出三個軍十個師共十萬遠(yuǎn)征軍進(jìn)入緬甸境內(nèi)作戰(zhàn)。戰(zhàn)爭是殘酷的。在沉重打擊日寇的同時,中國駐印軍和遠(yuǎn)征軍傷亡也十分嚴(yán)重,到了1943年下半年,缺員補(bǔ)員成為迫在眉睫的頭等問題。為彌補(bǔ)兵源不足狀況,改善兵源質(zhì)量,國民黨中央執(zhí)委會決定:開展知識青年從軍運(yùn)動。
一天,彭邦楨在羊街空軍招待所,看到了《大公報》一條通欄大標(biāo)題《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社論。文章說:國家在此緊急戰(zhàn)時關(guān)頭,而抗日隊伍中增加一個知識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個普通士兵。
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激勵下,彭邦楨少校與心上人在機(jī)場舉行了既無婚書、又未合巹的“機(jī)場婚禮”后,就率一支青年軍直飛印度藍(lán)姆伽參加美式訓(xùn)練。
藍(lán)姆伽位于印度東北部比哈爾邦,面積二十幾平方公里,有幾條瀝青公路通往市鎮(zhèn)。在印度語里,藍(lán)姆伽意為“神的住所”,一戰(zhàn)時,在印度殖民的英國人在此建立了一個戰(zhàn)俘營,關(guān)押近兩萬名意大利戰(zhàn)俘。1942年初,走出國門的十萬中國遠(yuǎn)征軍被日軍擊潰,最終只有四萬殘軍退至印度邊陲。史迪威決定在藍(lán)姆伽對中國軍隊按照美國步兵訓(xùn)練大綱,進(jìn)行現(xiàn)代化的軍事訓(xùn)練,伺機(jī)反攻。
彭邦楨到了蘭姆伽后被編入駐印軍炮兵第十五團(tuán),這個團(tuán)的士兵中除了中學(xué)生外,還有不少北大、東北大學(xué)的流亡學(xué)生。他們開始訓(xùn)練的科目包括兵器、戰(zhàn)術(shù)、學(xué)科、術(shù)科及思想等方面。新兵短訓(xùn)結(jié)束后,彭邦楨所在部隊正式納入正規(guī)軍編制,又進(jìn)行了專業(yè)訓(xùn)練半年。
訓(xùn)練期間,彭邦楨同這些學(xué)生兵一樣,每天上午進(jìn)行隊列、射擊和體操訓(xùn)練,下午進(jìn)行野外訓(xùn)練和叢林作戰(zhàn)訓(xùn)練。還有游泳、駕船、攀登等項目。
彭邦楨在國內(nèi)陸軍服役過,這里的裝備與國內(nèi)的部隊相比,其待遇用奢侈來形容毫不為過。
彭邦楨所在部隊配備的新式武器,除擁有155毫米口徑榴彈大炮、射速每分鐘七百發(fā)的湯姆森沖鋒槍、謝爾曼坦克、斯圖亞特坦克外,還有三十式步槍、六十式步槍和火箭筒等。一次,美國教官向彭邦楨介紹重達(dá)三十二噸的M4A2-謝爾曼中型坦克時說,日軍的95和97坦克與“謝爾曼”相比,僅僅比玩具強(qiáng)一點(diǎn)。而總指揮部的戰(zhàn)車第二營裝備的M3A3-斯圖亞特輕型坦克,也不是好惹的。日軍最好的97式中型坦克必須要接近到三百米才有可能將之擊毀,而它卻足以在五百米外直接點(diǎn)燃97式坦克。至于汽車的數(shù)量之大,那就更是不足為奇了。
同時,彭邦楨所在的青年軍每人配備了戰(zhàn)斗服、訓(xùn)練服、鋼盔、夾克、急救背包、野戰(zhàn)水壺等,一應(yīng)俱全。他們可以吃到雪白的美國大米和各種美味的罐頭食品。這里營房寬敞,還有游泳池、電影院、俱樂部等娛樂設(shè)施,對于九死一生的中國士兵來說,這時簡直就是人間天堂。
彭邦楨所部除全副美式裝備外,津貼發(fā)的是美金,抽的香煙是美國駱駝牌,吃的是印度咖喱,喝的是印度烈性燒酒。彭邦楨的抽煙和喝酒的不良嗜好,就是從此時開始養(yǎng)成的。
由于彭邦楨率領(lǐng)的受訓(xùn)人員,都是中學(xué)生和大學(xué)生,素質(zhì)相對比較高,按照教官的嚴(yán)格要求,整個訓(xùn)練進(jìn)行得比較順利。接下來,這些受訓(xùn)的官兵,為抗日戰(zhàn)爭的全面勝利奉獻(xiàn)了自己的生命和智慧。
四
1944年夏秋之際,在中日戰(zhàn)爭的緬北滇西戰(zhàn)役中,彭邦楨隨中國駐印軍參加了在緬甸北部密支那地區(qū)對日軍精銳之師的進(jìn)攻戰(zhàn)。
彭邦楨得知,這支日軍就是臭名昭著的九州兵團(tuán)最精銳的第十八師團(tuán),它在中國戰(zhàn)場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難書,多次獲得日本天皇獎賞。該師團(tuán)上海淞滬會戰(zhàn)、杭州灣登陸、南京大屠殺、武漢會戰(zhàn)、廣州戰(zhàn)役等侵華各大戰(zhàn)役無役不與,著名的盧溝橋事變就是由該師團(tuán)發(fā)動的。在1942年新加坡戰(zhàn)役中,該師團(tuán)以三萬兵力俘獲八萬英軍,只損失了一百人,震動英倫三島,因此號稱是新加坡的征服者。
彭邦楨每當(dāng)想起這些沾滿了中國人的鮮血的劊子手,頓時摩拳擦掌,怒火在胸中燃燒,恨不得立即將日寇殲滅于密支那。
密支那為緬北重鎮(zhèn),交通便利,地勢險要。1944年3月上旬,日軍第十八師團(tuán)在得到第五十六師團(tuán)一部增援后,以一個聯(lián)隊主力守衛(wèi)密支那,以另一部在瑞里、雷邦對孟拱方向警戒。endprint
中國駐印遠(yuǎn)征軍新編第三十師、第五十師各一個團(tuán)與美軍第5307支隊(兩個營)編成中美混合突擊支隊,于4月下旬由胡康河谷的大克里出發(fā),分兩個縱隊向密支那挺進(jìn),在擊破日軍警戒部隊后,于5月12日進(jìn)逼丁克路高以西地區(qū)。
中國駐印軍第一縱隊與日軍遭遇后,激戰(zhàn)至晚間,美軍一個營被日軍圍困。次日晨,中國駐印軍一部與被圍美軍里應(yīng)外合,才將日軍擊潰,并乘勝攻占了密支那以北的遮巴德。
中國駐印軍第二縱隊則進(jìn)抵升尼,并在該處開辟小型機(jī)場后到達(dá)密支那機(jī)場以西之南圭河西岸;英軍喀欽族部隊三百余人亦在該地以北地區(qū)活動。5月17日,第二縱隊經(jīng)過幾小時進(jìn)攻,占領(lǐng)密支那西機(jī)場。第一縱隊與日軍機(jī)場守備部隊在密支那北側(cè)對峙。此時,中國新編第三十師和第十四師各一部先后到達(dá)戰(zhàn)場。
狡猾的日軍憑借有利地形負(fù)隅頑抗,而我駐印軍指揮系統(tǒng)紊亂,連續(xù)幾天攻擊毫無進(jìn)展。于是,駐印軍總部將中美混合突擊隊解散,重新調(diào)整部署。
到了5月下旬至7月上旬,彭邦楨部隨中國駐印軍在空軍支援下,對日軍展開了新一輪攻擊。此時的日寇十八師團(tuán)盤踞在野人山,日軍憑借天然屏障與堅固的工事孤注一擲,雙方呈膠著狀態(tài)達(dá)四十余天。在熱帶雨林里,不僅要時刻注意躲藏在密林深處的敵人,還要留心成群結(jié)隊的螞蟥的襲擊,一不小心,被叮咬后就面臨生命危險。日軍為擺脫困境,立即從八莫及滇西抽調(diào)兩個大隊增援。
緬甸八莫距云南畹町很近,八莫是日寇入侵滇西的戰(zhàn)略要地,關(guān)系到緬北及滇西全局。所以,中國駐印軍乘勢以工兵作業(yè)法逐步推進(jìn),同時彭邦楨指揮炮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用155毫米口徑重炮轟炸,幾乎將八莫夷為平地。
1944年7月7日,先由第三十八師打先鋒,勢如破竹,隨后中國駐印軍各部向日軍發(fā)起猛烈攻擊。13日,彭邦楨隨駐印軍共四個團(tuán)和美第5307支隊(兩個營)的兵力,在優(yōu)勢空軍支援下向日軍再次發(fā)動進(jìn)攻,經(jīng)過艱苦戰(zhàn)斗,到16日晚,攻擊部隊迫近市區(qū)。
18日,中國遠(yuǎn)征軍以雷霆萬鈞之力又對日軍發(fā)動了新一輪攻勢。剛開始,彭邦楨部等重炮兵群集中所有火力支援一個方向,爾后轉(zhuǎn)移支援其他方向,使日軍陣地變成一片火海。步兵隨炮兵延伸射擊,開展激烈的巷戰(zhàn)。直至26日,方接近密支那市區(qū)中心,駐印軍又有兩個團(tuán)的兵力到達(dá)戰(zhàn)場。由孟拱敗退的日軍兩個大隊也向密支那增援,被駐印軍第四師一部所阻。27日,駐印軍各部繼續(xù)向預(yù)定目標(biāo)攻擊。戰(zhàn)至8月5日,密支那市區(qū)的日軍大部被殲,僅四五百人用竹筏及泅水渡過伊洛瓦底江,向八莫方向潰退,密支那完全被駐印軍攻占。
此役,中國駐印軍共擊斃日軍二千余人,俘七十余人。遠(yuǎn)征軍重創(chuàng)日軍的消息不脛而走,極大地鼓舞了抗日將士的士氣。
1945年1月27日,滇西緬北的最后一面日軍旗被拔除,兇惡的日寇第三十三軍宣告覆滅,中印公路全線打通,中國遠(yuǎn)征軍與駐印軍于中緬界河的畹町(傣語意為“太陽當(dāng)頂?shù)牡胤健保└浇拿⒂褎倮麜煛4稳眨戆顦E見證了中國遠(yuǎn)征軍、駐印軍和盟軍于畹町舉行了隆重的會師典禮。
典禮臺頂張蓋著鵝黃色的降落傘,前臺兩側(cè)是一副對聯(lián):“歡迎X部隊反攻緬北凱旋回國”;“祝賀Y部隊進(jìn)軍滇西馬到成功”。正中央橫幅白底紅字,赫然寫著一個斗大的“V”。這里的“X部隊”,是指史迪威將軍在印度建設(shè)的一支完全由美國人訓(xùn)練的全美械中國部隊,指揮官為鄭洞國,用于反攻緬北;所謂“Y部隊”,是指在中國云南昆明基地建設(shè)主要由美國人訓(xùn)練的美械部隊,總司令為衛(wèi)立煌,用于反攻怒江;“V”則是“戰(zhàn)勝”的英譯Victory的首個字母。
在嘹亮的軍樂聲中,指揮官鄭洞國與總司令衛(wèi)立煌上臺,兩人緊握雙手,熱情擁抱……首批五百輛軍車滿載美援物資緩緩駛過國門畹町橋頭,這些軍車從印度啟程,穿過野人山,穿過密支那八莫南坎,沿著中國官兵用血肉鋪成的中印公路輾轉(zhuǎn)而來,駛向昆明,駛向重慶。
從中國軍隊入緬作戰(zhàn)起,中緬印大戰(zhàn)歷時三年零三個月,中國投入兵力總計四十萬人,傷亡接近二十萬人;第二次入緬作戰(zhàn),中國遠(yuǎn)征軍傷亡四萬余人,中國駐印軍傷亡一萬七千七百一十一人,日軍傷亡四萬八千五百人。
中國遠(yuǎn)征軍用鮮血和生命書寫了抗戰(zhàn)史上極為悲壯的一筆,彭邦楨則用自己的鮮血和汗水為英烈編織詩玫瑰花圈。有一詩云:“我有一個生原則/也有一個死的意義/我熱情地/為愛活著/我活著/為愛而死//愛人的愛/愛吾國家的愛/愛吾民族的愛/為愛我擬出一個方案/為死者錄下聲音/為生者留住記憶……”
“這是詩人彭邦楨的詩觀,或者說是詩人彭邦楨詩的宣言。”著名詩人謝克強(qiáng)如是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