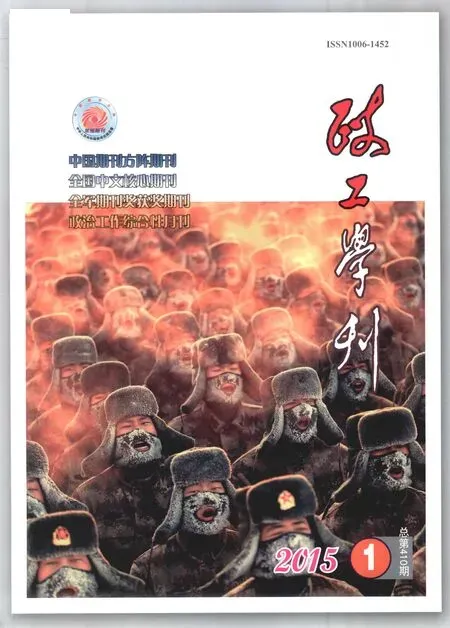想娘親
☉楊大會
想娘親
☉楊大會
2014年10月1日是我43歲生日。往年過生日,不論是在單位,還是在漂泊的大海上,首先撥通的肯定是山東老家母親的電話,“媽,今天是我的生日,孩的生日娘的苦日,記得買點好吃的,我在執行任務不能回去看您了。”然而現在,這個電話竟成了莫大的奢望,手拿電話,悵然若失,心像被掏空了一樣,母親已走了兩年了。
父親去世的時候,母親也是43歲,家里一貧如洗,房子是借來的,五個孩子只有大姐剛出嫁。在以后的歲月里,母親怕我們受委屈,始終沒有改嫁,含辛茹苦地拉扯我們長大,默默履行著對爸爸臨終前許下的諾言:放心吧,孩他爸,我一定把兒女們培養成人,不讓他們受半點委屈。那時我才九歲,不知多少次放學回家,看到母親獨自一人躲在角落里哭泣,見我回來又裝作若無其事到田里干活。生活給了母親太多的苦水,她始終一個人默默承受著、隱忍著、吞咽著……
初中畢業那一年,家里實在是揭不開鍋了,我只能輟學打工。第一份工作是玻璃廠的搬運工,在600多度高溫的炙烤下,30多斤的鐵模子每天要搬運三千多趟,我一干就是四年。至今還清晰記得,當我興奮地拿著第一個月的工資(每天1塊2毛5分,共計37塊5),一分不差地交到母親手里時,母親看著我滿手的血泡和稚嫩的臉龐,一把把我摟在懷里,號啕大哭起來:“苦命的兒啊,媽對不起你,這么點年紀,去遭那么多罪……”我與母親相擁而泣。為了維持全家的生計,母親幾乎什么苦活、累活、臟活都干過。給生產隊淘糞挑糞、在醫院做清潔工、在糧站賣早點、在食品廠攤煎餅、為陶瓷廠加工陶坯,有的工作既危險又辛苦,強度之大甚至連壯年男子都吃不消。記得母親在糧站打工時,每天凌晨三點就要趕過去,一年四季,天天如此。炸油條、煎油傘、蒸米糕、攤煎餅,母親樣樣做得有模有樣。下班后,母親經人同意帶回家的“邊角余料”,總是先緊著我們解饞,自己卻從來不舍得吃一口。
淄博是中國北方的陶瓷之鄉,家家戶戶的生活基本上都與陶瓷有關。為了多掙點錢,貼補家用,母親在醫院做清潔工的同時,自己挑泥漿加工陶坯。泥漿是用家鄉的青石塊磨制而成,因為摻了水,比青石還要沉,兩桶泥漿就有250多斤,母親用她90多斤的單薄身體和1米58的個子,挑起泥漿要走40多分鐘才能到家。每次到家,母親渾身上下的汗像水澆了一樣,衣服褲子都貼在身上,兩邊的肩膀透著殷紅的血印。加工一個陶坯二厘錢,五個才掙一分錢。每一個都要經過沁、倒、削、刻、磨、曬等七八道工序,然后再把加工好的陶坯挑到陶瓷廠,一個星期下來最多能掙到10塊錢,這份活計共持續了五年。那時放學回家,我經常幫母親打下手,一輪做下來,累得腰都直不起來。
有時我們娘倆也苦中作樂,聽聽收音機,哼哼小曲。母親雖然不識字,但特別喜歡聽戲唱戲,京劇、豫劇、呂劇、越劇、黃梅戲,母親都愛聽,樣板戲《紅燈記》《杜鵑山》《智取威虎山》《沙家浜》里的精彩唱段,她樣樣都能哼幾句。我對歌唱藝術的喜愛,就是在那段艱苦難忘的日子里慢慢養成的。后來,為了學會一首喜愛的歌曲或唱段,竟然著了魔似的到同學家、鄰居家去學,有時甚至跑到縣城的百貨大樓去聽,母親從來不攔我。我學會的每一首新歌的第一個聽眾肯定是母親,每次聽完,她總是夸我:學誰像誰,唱得跟收音機里的一樣,將來我兒子準能成為歌唱家。后來,我考上了解放軍藝術學院,還上了中央電視臺,可每學會一首新歌,依然渴望先唱給母親聽,母親始終是我心中最信賴最忠實的聽眾。
家里日子過得再艱苦,在孝敬老人的事情上,母親從來不打折扣。父親在世時,每月給奶奶的生活費是10塊錢,父親去世后,奶奶主動減到了5塊錢。別看這5塊錢,常常壓得母親透不過氣來,但母親就是四處去借也從不拖欠。輪到我們家贍養奶奶時,母親要拿出家中最好的米面,攤好煎餅,蒸好饅頭,和我一起給奶奶送去。怕奶奶記性不好,母親會細心地把錢塞到奶奶貼身大襟褂的兜里。有一次,母親實在沒轍了,打起了我的儲錢罐的主意。那是我辛辛苦苦攢了近一年的零花錢,共六毛一,全是一分兩分的硬幣。看著母親期許的眼神,我含著淚“慷慨”地砸開了儲錢罐——一個殘破的陶瓷茶壺,把錢交到母親手里。母親用她的仁慈和善良侍奉著老人,也用質樸溫良的言行深深地影響著我和哥哥姐姐。
好不容易熬到姐姐哥哥都結婚成家,我也考上了軍校,母親的身體卻每況愈下,胃潰瘍、冠心病、糖尿病一起向她襲來。用醫生的話說,年輕時太拼命了,體力透支得厲害,把身體都累垮了。
考入軍校后,每次回家,母親總央求我一件事——著裝整齊,陪她趕集。每隔五天,家鄉都有一次集市,是街坊四鄰、十里八村的鄉親們自發形成的。海軍軍裝要么一身藍,要么一身白,雖說漂亮,但我總覺得太顯眼,不自在。可母親已近乎偏執地把我和這身軍裝當成了她一生的驕傲。當兵24年來,由于我的演唱特長和工作需要,跟隨部隊出訪了20多個國家和地區。無論我在哪里,只要母親知道了,首先看那里的天氣預報,她無時無刻不在牽掛著我的衣食冷暖。
2007年春節剛過,我把母親從山東接到大連。由于孩子小、房間擠,單位任務又多,母親覺得太煩勞兒媳,住了半年就回了山東。回家沒兩個月,母親就大病一場,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我當時在海島執行任務,軍艦靠岸后,連夜趕赴山東。第二天下午四點到醫院時,母親已昏迷20個小時。醫生說,如果36個小時內,病人有反應,就有救;如果沒有反應,就準備后事吧。可憐的母親,臉腫得連眼睛都看不到了,手腳冰涼,渾身插滿了各種輸液管,孤獨地躺在重癥監護室里。我讓哥哥姐姐們先回家休息,自己守護著母親。母親在大連的半年時間里,我連續創作了十幾首歌曲,發表在《解放軍報》《海軍文藝》和《音樂周報》上,有幾首還錄制成了CD。每次放給母親聽的時候,她都嘖嘖稱贊:我以為我兒子只會唱歌呢,沒成想還會寫歌呢,每首歌曲的調調,好聽得直往人心里鉆!
從晚上八點到凌晨三點,我不停地在母親耳邊哼唱她喜歡的幾首歌。三點半左右,恍惚間發現,母親額頭上的皺紋微微地往上一挑,母親終于有反應了!我的眼淚奔涌而出,飛一般地沖到護士站。在醫院的全力搶救下,母親在重癥監護室躺了七天,總算逃過了一劫。出院后,母親的記憶力急劇衰退,一下子變得少言寡語起來,要說也是翻來覆去地嘮叨那幾件事和幾句話。醫生說是小腦萎縮的緣故。
從2009年開始,我連續執行國慶大閱兵和軍艦出訪任務,回家看望母親的機會越來越少。2012年回家過春節,給母親洗腳剪指甲的時候,她微笑著問我:“媽有日子不出門了,也沒洗腳,你這大軍官不嫌我臟啊!”我笑著回答:“嫌你臟,我就當不了軍官嘍!”怕母親心里悶得慌,我給她穿上羽絨服,裹上頭巾,攙扶她來到街口的集市上。在街口,母親竟然像孩子一樣央求我給她買點瓜子,我擔心她的糖尿病,又怕她咳嗽,只買了半斤。回來的路上,母親還嗔怪著買少了。可我做夢也沒想到,這竟是我和母親趕的最后一次集。
2012年4月,我隨艦參加環球航行任務。7月19日,當軍艦行至南美洲的厄瓜多爾時,母親竟撒手西去。母親去世兩個月后,我才回到祖國。最不可思議的是在母親去世前的半個月里,我竟然連續做夢,夢里母親說自己要走,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我接連從夢中哭醒,最后一次夢境依然清晰記得:母親在村口等我放學,一遍遍喚我的乳名。當天,我拼命往家打電話,家人怕我失控,以謊言搪塞。現在回頭查看自己的海上日記,時間竟然奇跡般的吻合。遠隔千山萬水,怎么會接二連三地做那樣的夢呢?怎么會有如此強烈的感應呢?母子連心啊!
母親去世后的兩年里,我不知有多少次從夢中哭醒,夢見在母親的呵護下一起勞動,一起趕集。因為沒有見到母親最后一面,總覺得母親沒有走,老人家依然活著。正如詩人所說:我相信故去的親人,會變成星星,守望著我們,直到永遠……
秋風乍起,秋雨瀟瀟,今天是我43歲的生日,孩的生日娘的苦日,仰望蒼穹,淚眼婆娑。媽,兒想您啊……
【作者系海軍大連艦艇學院教員,
本文作于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