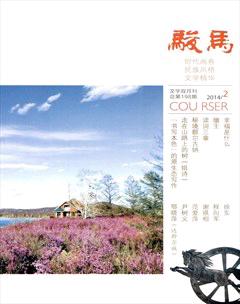沉默的草原
武雁萍
原河北省張家口市人,后遷入內蒙古錫林郭勒盟。2007年開始寫作,作品發于《詩選刊》《星星》《草原》《張家口晚報》《錫林郭勒日報》《錫林郭勒晚報》等。隨筆收入《2012中國隨筆年度佳作》(耿立主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作家協會會員。
一
如果用一首詩歌詮釋一個地方代表一種向往表達一片深情的話,那么這首詩歌非《敕勒歌》莫屬。提到草原,幾乎所有的聲帶都用相同的氣流振動:“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如果不乏想象,在陰山逶迤雄渾的背景下,一個名叫敕勒川的地方,猶如電影慢鏡頭由小而大由遠而近推入你的腦海,天空徐徐張開帳篷空闊而巨大,在蒼茫遼遠處與草原相接,這時,鴻雁高飛風吹草低,綠波之中牛羊若隱若現。如果再深切一點,長調便會從曠野中飄移過來,像霧,一縷一縷爬上你的胸口,蒼涼沉悶了你的孤獨和憂傷,而你,必定趕著羊群在馬背上漂泊向天邊游蕩……
這,便有了草原。
接著,草兒亮了野花艷了,馬駒撒歡羊羔咩咩。在潔白的氈房跟前,美麗的蒙古族姑娘像一團燃燒的云霞,熱烈了篝火熱情了牧歌。酒是一定不能少的,金杯銀杯舉過頭頂,喝得酣暢淋漓不醉不歸。
曾經我想象過這些,那時我在草原之外。我還跟著勒勒車轍找尋盛開的金蓮花,用威武的套馬桿親近過奔騰的駿馬。我讓黎明的露珠掛上飄香的奶茶,還讓牧歸的夕陽捧出肥美的手把肉。更多時候我則學唱草原歌曲,隨性放逐我的歌聲,讓它們穿越千山萬水,用優美動人的旋律一遍一遍撫摸著草原。
當我的歌聲唱出向往唱出淚水的時候,我來到草原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草原人。可是我感覺我的草原之夢破碎了,在我深入草原內部在無數次奔波探尋無數次驗證之后。我沉默了,眼中的淚水變得又咸又澀。我沒有找到敕勒川,沒有看到“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場景。
一千五百多年了,北朝人創造的歌聲已經越過草原深入大江南北,但敕勒川卻一小再小最終失了蹤跡,沉沒在時間的海里。曾經讀過百度呼和浩特市貼吧的帖子,有位朋友稱自己出生在這片土地,讀著《敕勒歌》的詩歌長大,但他從來沒有見過家鄉有過草原。是的,他看不到草原,因為敕勒川早已被土默川所代替,成為了內蒙古的“米糧川”。曾經水草豐美的草場散落的再不是牛羊再不是牧歌,而是翻滾的麥浪垂著胡須的玉米海洋般的胡麻。
一首歌可以穿越時空經久不衰,但它無法阻隔滄桑巨變。敕勒川作為草原的代言和標簽早已名不副實,而《敕勒歌》所描繪的草原景象也越來越難以尋找,變成熱愛草原的人們胸中一個難以平復的心結。敕勒川則被當成一個善意的謊言,沒有人愿意揭穿。
二
或許我會揭穿這個謊言。不過我是熱愛草原的,那種來自心底的深沉和真摯早已深入草原,長成了我的骨頭,支撐著我被草原填滿的身體。
我的這堆骨頭是從太仆寺旗長出來的。
太仆寺旗,我的第二故鄉,一個與馬有著深刻淵源的地方。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說:“太仆,秦官,掌輿馬,有兩丞。”由此可見,“太仆”是一個官職,配有左、右兩位屬官,掌管皇帝用的車輦并主管馬政。“太仆寺”則是衙門名,太仆寺的長官叫“太仆卿”,太仆卿所在的官衙叫太仆寺。縱觀中國古代史,太仆寺旗所在地一直是北方少數民族,包括匈奴、鮮卑、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或部落游牧生活的地方,馬一直伴隨這些少數民族在這里生存。但從清朝初期開始,才有詳細的歷史記載并與馬真正結緣。當時清政府在這里設立太仆寺左右翼牧群,專門為皇家提供軍馬和畜產品。《清史稿·馬政》上說,到了乾隆五年(1740年),兩翼牧場共有騾馬一百六十群,騸馬十六群,一共四萬七千匹。最鼎盛的時候,太仆寺旗畜養過七萬多匹騾馬。
我之所以固執枯燥地介紹這些數字,目的是想醞釀氛圍突出一種對比一個反差。據有關資料統計,到1948年,這個曾經輝煌兩百多年的皇家御馬苑只有五百六十二匹馬!
歷史煙波浩渺般地前行蕩滌了一切,曾經鮮活的宏大的綿延的都漸漸淪為塵埃,被時間不知疲倦地沖走。月亮依然朦朧,太陽依然升起,而草原上曾經萬馬奔騰的磅礴場面則縮小成為幾行泛黃的小楷,隱藏在線裝書里,成為捧書閱讀之人的悲涼和哀嘆。馬以及育馬、馴馬、賽馬、打馬鬃、烙馬印等色彩紛呈的馬文化正一點一點退出草原,淡出我們的視線。蒙古人曾經在馬背上的馳騁呼嘯,也成為這片土地上的神話和傳奇,留給草原去珍存去懷念。但,永遠不可復制。
我要去找馬!
那是一個下午,我在辦公室凝望窗外,毫無來由地,我的心中突然躥出一股熱望,似乎草原在遠方呼喚著我,讓我刻不容緩投入她的懷抱。拿車鑰匙、下樓、發動車子、起步出發。一連串動作仿佛都是下意識完成,我的心中只剩下急切,我的腦海只留有草原。馬,我要去貢寶拉格草原找馬。
六月初,草原終于結束了與風沙展開的曠日持久的戰爭,新綠初染萬象更新。那天,陽光溫暖而柔和,草原安詳而平靜,貢寶拉格草原在一片微茫中漸入我的視野。貢寶拉格草原,位于錫林郭勒大草原南端,地處陰山山脈東段低山丘陵區,是清朝太仆寺左翼牧群的牧場。其總管府設在喀喇尼墩井,在現在貢寶拉格蘇木的五旗敖包附近。
高速公路還未正式通車,車輛很少,我幾乎未踩油門讓車子緩慢行進。這樣,我可以讓眼波翻過側窗盡情打探草原新綠初染的消息。由北往南三十公里的路程,我找到了三群馬,每群二三十匹的樣子。相對于牛羊而言馬太少了!它們抖著馬鬃甩著尾巴,只顧啃食前面的青草,一副無憂無慮的樣子。一時間,我似乎看到龍馬精神、千軍萬馬、策馬揚鞭、單槍匹馬、馬到成功等等與馬有關的詞語都在草原上失神落寞,它們站在馬的身邊卻離馬很遠很遠。馬的歷史已經被時代改寫,馬的輝煌只是馬蹄留給草原的深深的記憶。
恍惚中我看到了馬,很多很多的馬從天邊翻滾過來,它們一路飛奔,它們高聲嘶叫,它們沖向我,它們包圍我,它們淹沒我。這,就是我找到的馬,穿越二百多年的馬,驍勇善戰勇猛無比的馬。
站在皇家軍馬場想馬,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很慶幸我看到了三群馬,否則我的想象不會如此生動地展現太仆寺左翼馬群耀眼的光輝。太仆寺旗有馬,皇家御馬苑有馬。我為我的發現激動著。
激動過后,我不得不為馬而擔憂了。現在的馬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它耕田不如農機,肉食不比牛羊,奔跑不敵汽車,放牧不勝摩托,在當今的經濟社會已經失去經濟價值,那達慕大會賽馬御馬節馬術表演、旅游景點游客騎馬,不能改變馬減少的趨勢,馬今后的命運越來越多舛了。
不知道,馬背上的民族沒有馬該如何悲哀。不知道,失去馬的草原還是不是草原。
三
此刻,萬籟寂靜燈火恍惚,我在遠離草原的一座城市想著草原。距離可以喚醒理性,我感覺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懂得草原。我想草原一定跟人一樣,喜歡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拉開回憶的閘門,讓那些深刻的記憶像水一樣漫過時間堤壩一一再現在眼前。太多的歲月輪回太多的世事變遷,我無法切入,我只有從寥寥幾筆的歷史描述中去感知草原體悟草原。
不必從幾千年前開始追溯,一百多年前草原的疆域遠比現在遼闊。草原一直在被迫“瘦身”,而蠶食它們的正是我們自己。歲月倒轉,在二十世紀初正大光明殿,一群身著官服背后拖著長辮子的男人們激烈爭吵。爭吵過后,漢人拖家帶口大批涌入草原,草原立刻沸騰起來。鎬頭、鐵鍬、犁等鐵器,從四面八方包抄過來,先是察哈爾、烏蘭察布等西部草原,后是昭烏達、哲里木等東部草原被顛覆了。如果時間還能繼續往前,到了我一定可以親眼目睹霓裳羽衣舞的時代。那時國泰民安大興屯田,河套和鄂爾多斯地區被開墾。再往前就該輪到黃土高原了,那是漢武帝的杰作,七十萬移民將種子撒入高原,草原從此變成農田。翻閱歷史,這些段落不知道草原會不會忘記,我想,歲月只能模糊她曾經擁有的疆域,但那些切膚之傷應該是不會忘記的。
新中國成立以后,在“大躍進”“以糧為綱”“牧民不吃虧心糧”等口號聲中,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直至九十年代,草原又承受了三次大規模的切膚之痛。生產建設兵團、部隊、機關、學校、廠礦企業單位紛紛涌入草原亂占牧場。這期間,草原面積大幅度減小,由上世紀六十年代的8667萬公頃下降到九十年代末的7370萬公頃,三十多年中凈減少1297萬公頃。
我很想知道,敕勒川是什么時候被什么人掠奪并改寫了歷史的;我更想知道,我的第二故鄉皇家御馬苑所在地,唯一的貢寶拉格草原是如何保存下來的,而周圍其他牧區是什么時候改變的。這些,我想草原肯定記得相當清楚,只是,她不愿意告訴我。
草原一直沉默著。
當鄂爾多斯地區的沙丘初露端倪的時候,我們不覺得什么;當庫布齊沙漠初具規模的時候,我們也不覺得什么;當巴丹吉林沙漠、騰格里沙漠、烏蘭布和沙漠、毛烏素沙地、渾善達克沙地、科爾沁沙地、呼倫貝爾沙地風起云涌的時候,我們還不覺得什么。當鋪天蓋地的沙塵暴揭竿而起,向著首都北京浩浩蕩蕩進軍的時候,我們似乎才有所警覺。我們買單的時間到了,為我們的前輩和我們自己買單。
我熱愛的貢寶拉格草原,漢語譯為深深的泉水,可是我走遍所有的草場也未看到泉水在她懷中流淌。曾經水草豐美的皇家牧場,現在卻是地瘦草荒飛沙走石。太仆寺旗所轄四鎮一鄉一蘇木,除貢寶拉格草原外全部變成農區。其相鄰草場,屬河北管轄的壩上四縣也全部開墾種糧。這些農區十年九旱全部靠天吃飯,如果不打井根本沒有收成。
草原是寬厚的無私的,盡管人類對她很不友好,但她依然捧出所有供養投奔她來的人們,可是我們人卻不盡如人意。我們的盲目,我們的愚昧,我們的熱衷,讓多少開墾出來的耕地撂荒?草原干旱少雨多風且風大,被開墾的土壤表層極易隨風而逝,而剩下的土質顆粒粗大保水保肥能力差打不出多少糧食,被迫丟棄淪為撂荒地。狂風大作,撂荒地揚起塵埃形成大規模的沙塵暴。可是,還有很多人把環境惡劣、草場退化的首要原因歸罪于過度放牧,羊,成了真正的“替罪羊”。草原面積逐漸縮小,承載畜力能力下降,以較小面積的草場支撐較大規模的畜產品生產,勢必導致系統崩潰。古往今來,土地都是我們賴以生存的依靠,但是,我們不能以破壞作為獲得的代價,親手摧毀美麗的草原。
“圍封轉移”“退耕還林還草”“禁牧”“休牧”“輪牧”等等,這些是我們遭遇“黃色風暴”之后的反思。十年間,我終于看到了這些詞醞釀的詩意,那是屬于草原的,屬于每一棵綠草每一只牛羊,屬于馬背上驕傲的民族。
四
望不盡連綿的山川
蒙古包像飛落的大雁
勒勒車趕著太陽游蕩在天邊
敖包美麗的神話守護著草原
……
喜歡這首歌詞營造的氛圍,所以每次有朋友遠道而來,在篝火晚會上我都會以這首歌歡迎尊貴的客人。不知道聽者如何,我自己是陶醉了,陶醉于草原最原始最本真最古老的景象。或許,我們都更熱愛原生態的草原。現在現代因素早已融入草原深處,歌曲《牧人》所描繪的牧人也很少存在。在草原上看到騎馬放牧,看到牛拉勒勒車行走,那無疑是一種幸運是一種享受。而氈房,蒙古人世代居住的房子,也大多數跟旅游生意關聯存在,《蒙古人》歌唱的“潔白的氈房炊煙升起,我出生在牧人家里”則成為蒙古包永恒的回憶。
草原變了。如果草原會說話,我不知道她會說什么。或許她什么都不會說,像一位老人端坐在歲月門口,任敕勒川的美景、成吉思汗的雄風、御馬苑的馬群,以及一切的一切風一樣掠過,濃縮成她皺紋里的老年斑,恍惚而又迷離。
當降央卓瑪渾厚婉轉深情的《呼倫貝爾大草原》,通過飛機耳麥傾覆我心海的時候,我不由得把視線移向舷窗下的茫茫草原。我看到了傷口,巨大的深深的星羅棋布的流著黑血的傷口!傷口處煙塵彌漫鋪天蓋地,人類熱衷于這種掠奪游戲而不顧所有。
鄂爾多斯草原有煤,錫林郭勒草原有煤,呼倫貝爾草原有煤,科爾沁草原有煤。
“圍封轉移”“退耕還林還草”“禁牧”等等的詩情畫意,還未來得及在草原肆意描畫,草原又迎來了一種新的詩意。這詩意猛烈火熱迫不及待排山倒海,替代了原來的浪漫和柔情。鄂爾多斯草原淪陷了,錫林郭勒草原正在淪陷。“羊煤土氣”(羊毛、煤炭、稀土、天然氣)讓鄂爾多斯人真的揚眉吐氣了,“一輩子放牧摸黑又起早,馬背上顛簸的歲月累彎了腰”的時代永遠不復返了。
當GDP數值升上草原摩天大樓的時候,當路虎車隊浩浩蕩蕩穿越草原沙漠的時候,當運煤車狼煙四起碾過草原草場的時候,我似乎看到草原上空以及大地深處云朵、水流、綠色在集體逃離,留下一個干涸荒蕪風沙橫行的世界,草原像一具巨大的霉變風干后的尸體無聲無息。當一切塵埃落定,我的思緒化作一聲嘆息一陣悲涼的時候,我仿佛聽到一種悲愴的、凄婉的、起伏跌宕的、悠長綿遠的聲音在草原上空蔓延回蕩,這時,我感到草原動了幾下,我知道那是她的心在猛烈地抽搐。
責任編輯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