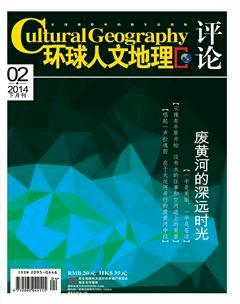一半是美麗,一半是蒼涼
辛華

揭開800公里廢黃河的深遠時光
公元1855年的清明節,陰雨綿綿,黃河和以前一樣開始漲水……但誰也沒有想到,這次漲水居然持續到了當年的農歷六月。
就在那個月的十一日,在河南蘭考縣東壩頭一個叫做“銅瓦箱”的地方,黃河水突然改道向北奔流而去。從此以后,黃河不再經過江蘇進入黃海,而是改由山東進入渤海。
事先沒有任何征兆,黃河從此與廢河在此分手,河道在這里轉了一個大約90度的彎,由東西向變為了南北向。只留下愕然的廢黃河沿線民眾,和空殼一般的河堤。
從此,地圖上將以下這條黃河故道,明確標注為“廢黃河”:
按照黃河水利委員會的劃分方法,廢黃河分為三段,從河南蘭考縣到江蘇豐縣為上段,長約300公里;往下到江蘇淮陰市為中段,長約323公里;最后再到射陽的廢黃河口,約181公里。在地圖上,廢黃河的絕大部分是用虛線畫出的,代表它時而干涸,時而有細流。地圖上只在淮安市以東到廢黃河口,是以實線劃出,代表有穩定的水流,那一段也叫中山河,是后來為了治理黃淮而進行人工導流的結果。
戰爭改變地理
如今的廢黃河,其實也不是最早的黃河故道,但卻是最為著名的一條黃河下游故道。追根溯源,這條道最早是古淮河的路線——公元1194年到1855年間,黃河下游全面搶占了古淮河路線。所以在這661年中,這就是黃河,而在1855年黃河再次變道后,它被稱為廢黃河。
這661年,被稱為黃河“奪淮入海”(簡稱奪淮)的時期,而究其動因,是戰爭改變了地理。激烈的宋金戰爭,促使黃河全面奪淮,最終造就了今天的廢黃河。
南宋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冬天,金國軍隊繼續南下,大有吞并剛剛宣稱建立的“南宋王朝”之勢,宋汴梁太守杜充在迫不得以的情況下,為阻擋金兵,扒開了黃河大堤,從此黃河開始侵入淮河流域。而戰爭愈演愈烈,金兵為了摧毀南宋的力量,對自己所轄的黃河段任其流淌,多次決堤之后,公元1194年,黃河下游全面奪淮進入黃海。
奪了淮河道路,卻不像淮河那樣溫馴,猛烈的黃河在豫東、蘇北大地上我行我素,給蘭考以東到黃海地區的人帶來了幾百年的考驗。為了保證京杭大運河的漕運,為了沖走黃河下游的淤泥,人們不斷筑堤修堤,靠激流沖刷河道。大堤靠人力一層層筑成,硬生生把黃河治成了一條懸河。而黃河水裹挾著大量的泥沙沖出古淮河曾經的入海口,層層疊疊的沙積成淤泥,如云如梯,最后的結果是——造就了蘇北廢黃河三角洲。
一直到公元1855年,黃河在今天河南蘭考縣突然又決口改道,奪了北邊的大清河河道而匯入渤海,于是現代黃河下游成形。
流淌了661年的黃河水突然走,剩下一個軀殼叫做廢黃河。上段在缺失主力水流的日子里,空剩下河工們年復一年勞作而成的廢黃河大堤,它們空蕩蕩地高出地面十多米,任憑時間的風吹雨打……而時間就這樣又過去一百多年,漫漫的黃沙崗之間,摻雜綿延著灘涂,時而有水時而無水,成為蘇北平原上的地理標志、以及江蘇省內南北水系劃分的標識。
從戰爭史的角度來看,廢黃河就像是戰爭的傷口,雖然不流血了,卻有隆起干涸的疤痕。
張老三 你的家鄉在哪里
站在當年懸在百姓頭頂之上的生死大堤下面,人頓時顯得渺小,望著高高在上的河堤,仿佛還聽得到當年滔滔的黃河水聲。從1194年到1855年,這條河還被稱為黃河。確切地說,是1855年過后,這里才叫做廢黃河。
劇烈變遷的自然環境,對于廢黃河沿岸的居民生活造成了極大影響,這里的文化既蒼涼又混雜。
有人說,過去的黃河一半是黃河水,一半是災民淚。那無數次的淹城沒地,橫卷平吞:除了我們都知道的七朝古都開封,八次被埋入地下的史實,還有魯西南、蘇北、皖西北等等,曾經多少城池,一夜之間在地球上消失。僅河南虞城縣就因為黃水之害在歷史上消失過兩次。歷史上還因為黃河的數次改道,使這地方的許多縣城總是沒有歸屬,整日在河南、山東、安徽與江蘇幾省轄區內徘徊,這一帶許多的縣城,歷史上就是隨黃河的改來改去,一會兒歸了山東,一會兒歸了河南,弄得這地方人說起祖上,一會兒說,俺們是山東人呀,一會兒又得說,祖上也曾在河南。
張老三,我問你,你的家鄉究竟在哪里?
鄉關究竟何處?這里的人們面對自己的后代,總是一臉的迷茫,心里永遠是一份解不開的謎。所以這里的戲劇熱烈又蒼涼,被稱為拉魂腔;所以廢黃河上的大型廟會,豫、魯、徽、皖四省人都來參加,民俗混雜。
若說黃河沿岸人文薈萃,那么廢黃河流域在源遠流長的文化傳承中,更多了一份哲學意義上的反思,這是一種激進又古樸,淳樸又尊貴,苦難又幸運的獨特人文。
奇異生態美景的排列
黃河被廢之后,曾有各種不同的惡劣生態組合一一登場。然而近幾十年的治理,卻給廢黃河沿線,帶來了各種不同的奇特生態美景。
在廢黃河的上段,曾經是荒寂的黃沙崗。記得上個世紀60年代,曾有外國專家斷言:“中國的華北大平原有可能變成沙漠”。同時他們認為,廢黃河的起點蘭考,首當其沖。因為蘭考縣地處豫東黃河故道,是個飽受風沙、鹽堿、內澇之患的老災區。然而焦裕祿帶領下的蘭考人徹底否定了這個預言,他們科學地種植泡桐,最終讓那位提出悲觀論斷的專家親口說:“我們在河南省平原地區所看到的樹木遠遠超過了中國長城這個奇跡。在這里,我擔憂世界將變成沙漠的想法被證明是錯誤的。”除了蘭考,如今陽春四月,走在廢黃河上段種植著槐樹的耐旱防風林中,那槐花在枝頭一派朦朧,漫坡遍野,恰似江南二月。有男女養蜂人在近處忙碌,臨時的小板壁旁邊蜂箱累累,黃蜂成群結隊。蜂涌蝶舞的世界,草暖云昏。
來到廢黃河的中段,是京杭大運河與廢黃河并行的區域。雖然在這一地區,廢黃河已經退出了主要的生產生活;雖然淮安人可以很冷靜地說,黃河對于淮安而講主要是條害河……然而在這一切愛恨情仇中,廢黃河逐漸深深地融入了當地的人文血脈中。所以,住在南船北馬之城的淮安人,選擇了在廢黃河道上,修建中國南北地理的分界標識。
到最后,蘇北廢黃河三角洲的內陸頂點——古淮河的入海口云梯關,見證了滄海變桑田,也在此段黃河廢掉之后,看到海岸又一點點退縮回來。或許當代人看不到蘇北廢黃河三角洲的最終結果,但是人們知道,后代會看到。所以現在的人,要盡全力去保護這個三角洲的灘涂上那珍貴的珍禽保護區……
在所有關于廢黃河的評價中,最經典的一句話是:歷史確實無情,山河并不依舊。
或許這一段黃河,終于在猛烈之中老了。或許山河歷史確實無情。
但是廢黃河不廢,它朝著自己的方向,正在變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