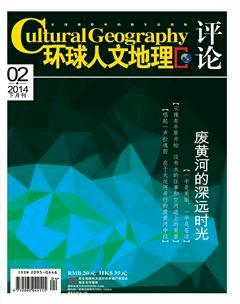漢畫像石:無字的“漢書”
杜潔芳
年少讀書時,校園角落處的一座具有上百年歷史的文廟似乎并沒有為我們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只是偶爾聽說那里有一些文物。由于保護意識并不強,文廟內的文物一直處于散落狀態,直到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時才被人發現,后又收進了山西呂梁漢畫像石博物館。多年之后,當筆者再次尋訪這些文物時才發現背后竟有不少顛沛流離的故事。
呂梁漢畫像石博物館修建于1998年,2002年正式開館。博物館主體設計造型為仿漢代建筑,7000平方米的廣場四周點綴著石質的漢燈。呂梁漢畫像石博物館自建成以來就成為當地的標志性建筑之一。在車水馬龍的城市里,這里更像是一塊世外凈土。從進入廣場開始,仿佛是一種時空的轉換,瞬間從喧囂走入了寧靜。仿漢畫像石的車騎出行文飾環繞著古銅色的大門,仿佛在墻壁上開出了一個時空隧道,馬上將你的思緒從現代帶到了1700多年前的東漢時期。
據館長董樓平介紹,漢畫像石被人們稱為“無字的《漢書》”。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以孝為仁之本的倫理道德規范開始深刻影響著當時的社會風氣。“事死如生”“事之如存”的厚葬風氣開始形成,并推動了厚葬制度和畫像石藝術的發展。東漢時期,選拔官員推行“舉孝廉”制度,而孝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對父母先人奉行厚葬。從西漢中期至東漢末,社會上出現了“以厚葬為經,薄終為鄙”的現象。
用畫像石營造的墓室、祠堂等墓葬建筑物開始得以發展興盛。之后,隨著東漢王朝的衰落,社會經濟基礎和思想意識發生了變化,漢畫像石也就隨之銷聲匿跡,先后延續了約300余年的歷史。
呂梁在漢代隸屬于西河郡,因“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尚氣力,以射獵為先”,民風粗獷、彪悍。這里漢畫像石也就有了其獨特的藝術風格,濃墨重彩、質樸豪放、古拙而靈動。呂梁出土的漢畫像石,大多采用當地的砂質葉巖,這種石吸水、吃色,畫在上邊的墨線和色彩歷經千年不變。
當筆者走進博物館后發現,有兩塊裂開又拼合起來的漢畫像石與其他畫像石不同,這便是“火牛陣”和“羽人嬉馬”。據說這兩塊就是當年從筆者就讀中學的文廟內收集過來的。這兩塊畫像石1919年出土于呂梁市離石區的東漢桓帝時期(公元150年左右)的左表墓。 左表字元異,是使者持節中郎將莫府奏曹史,是負責管理匈奴進貢和禮品的小官吏。1919年,從其墓室中發掘出14塊漢畫像石(一說13塊),其中有兩根刻字石柱最為珍貴。第一條上刻有“和平元年西河中陽左元異建筑萬年盧舍”字樣,另一條上刻有“使者持節中郎將莫府奏曹史左表字元異之墓”。據博物館的講解員介紹,這14塊漢畫像石被發掘出來后,當時京城有名的文物商人黃百川勾結當地的一些文物販子,將這些畫像石裝車運往北京。其中有文字的兩塊流落到了加拿大的多倫多博物館,有的后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但是其中的“火牛陣”和“羽人嬉馬”兩塊畫像石卻在運輸時被遺落在路邊。當地人不知道這兩塊石頭是什么東西,見上面有畫便將其放在了位于今呂梁一所中學校內原文廟的大成殿內。直到上世紀80年代,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時,才被當地的文物工作者發現。“火牛陣”如今已裂成三塊,但畫面上的戰斗場面仍讓人有種親臨其境的感覺。火牛雙角上綁著利刃,低著頭,四蹄奔騰直沖前面的敵人。整個場面用極簡單的線條勾勒而出,火牛的氣勢和敵人的慌張躍然石上。“羽人嬉馬”由上下兩塊組成。漢畫像石上的羽人是漢人所認為的仙人,而馬則是漢人最為信任和喜愛的動物之一,這塊畫像石表現的是羽化升仙后與馬嬉戲的場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