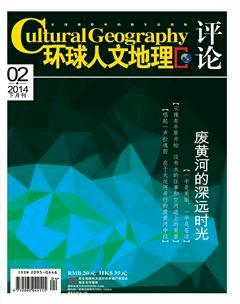驩兜與崇山
摘要:崇山文化是伴隨著人類遠古文化而產生并且延續至今的古老文化,部落的遷徙實現的文化的傳承和蛻變,在歷史的記載中崇山文化和驩兜有著密切的聯系,在我國崇山在數量上和地理位置上都存在著很多種說法,但是從歷史考究上進行深入的研究,崇山與驩兜究竟應該歸屬何處仍是我們需要深入探究的話題。本文從驩兜和崇山的歷史溯源為切入點,以文化記載進行梳理,具體解讀驩兜與崇山的歷史淵源,旨在探尋驩兜與崇山歷史文化價值和文化歸屬。
關鍵詞:驩兜;崇山;歷史考究
崇山是我國非常著名的文化景觀,關于崇山的和驩兜的關系就存在著四種主要的假說,放驩兜于崇山將這座名山賦予了神秘的文化色彩,也因此蘊含了豐富的文化歷史價值。驩兜流放至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鯀于羽山,在崇山各地也發現了很多的歷史文物史跡,證明這這段歷史的存在,從各種記載中我們試圖求證崇山所在。
一、驩兜與崇山的歷史考究
在崇山一帶有很多關于驩兜的傳說,這些傳說的記錄著驩兜因何而起、因何流放以及流放后的生活,在《崇山驩兜考》(陳自文2002)中就記錄著關于驩兜的傳說,如驩兜廟的主殿體現著五間相連的建造特色,因此而得名崇山連五間。掛鼓巖、將軍巖、相公洞等遺址記錄著驩兜的戰斗和生活,驩兜傳說為崇山賦予了更多的文化價值,分別從驩兜和崇山各自的歷史文化特點進行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其中的千絲萬縷的關系。
(一)驩兜的歷史溯源
《史記》中有記載,“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咸服。”驩兜在史書之中有諸多的記載,驥兜亦可稱之為灌兜在《山海經》當中被稱作為驩頭、驩朱,源頭是中原地區,和炎黃、華夏部落的都曾經形成聯盟,也有稱呼驩兜為丹朱,即朱明、昭明和祝融,驩兜史學記載中是黃帝一系,驩兜是堯的屬臣,任“伯”的職務。在《通典》中有記載唐堯之時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為八伯指列。而舜同驩兜為公事,堯曾經問驩兜“治世之人”,驩兜認為是共工,但是與堯的本意相悖,因此驩兜也被看做是共工的朋黨。也就有了后來是“四兇”之稱,將其私人流放與南蠻、北狄、西戎、東夷之地。其中崇山因為驩兜流放于此而增添歷史文化的神迷色彩,造就了特有的少數民族文化的特色,并得以廣泛的傳承至今。
(二)崇山的歷史探究
崇山出于張家界市,是位于西南方位一座氣勢恢宏、險峻陡峭、山體奇異的大山。崇山素有崇山八景的自然景觀,海拔高達1164.7米,龜蛇捧足、石梯仙徑、瀑布雙懸、洞口流春、掛鼓鳴巖、石門鎖翠、云中插錫、佳門古坼下的八峰傲然挺立,風景獨到,注經撰記、吊讀遺文成就了崇山深厚的文化意蘊。以驩兜為文化內涵的崇山文化有著眾說紛紜的解釋,主要有四種說法,即大庸,廣西歡州,江西崇義縣旗山,滬溪縣原崇山衛所在地。還有學者認為崇山并無具體所指,而是泛指崇山群嶺,還有四說:豐鎬說、秦晉說、嵩高說和塔兒山說(董琦《虞夏時期的中原》第270頁,科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不僅于此,還有晉南崇山、河洛崇山、湖廣崇山、驩洲崇山之說,崇山中能夠探尋到諸多的驩兜遺跡,各地的文獻記載和遺跡發現都闡釋了關于驩兜與崇山之間的關系,諸多證據都需要深入的考證。
二、驩兜與崇山
驩兜與崇山不僅僅被作為一種歷史所傳承,更體現著文化的追源,其歷史考證的方法體現著一定的原則性,也因為周遭的文化、地理環境和人文因素被賦予了不同的文化價值內涵。所以從文化追源的視角下對驩兜與崇山的歷史淵源進行探究,將二者有機的聯系在一起去探究就更具有現實價值。
(一)歷史文化特點
驩兜歷史文化的特點充滿著深化的色彩,在《大荒北經》中以“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白苗民。額項生嗜頭,灌頭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
《大荒南經》中以“灌頭,人面,烏嚎,有翼,食海中魚,權翼而行維宜芭芭、移楊之食。有灌頭。”為記載,是苗族文化的起源,從地域特點上來說驩兜部落的生活生產主要依靠狩獵和打漁為生,驩兜流放的歷史典故成為了少數民族文化發散,苗族文化聚集的重要契機,每一時期的歷史文化都能帶來深刻的社會歷史的變動,歷史事件、文化傳說、地理遷移都是歷史文化特點呈現的重要源泉,所以驩兜歷史文化的研究必然和崇山文化聯系在一起。
(二)歷史文化研究的影響因素
從驩兜和崇山之間的歷史溯源我們可以發現歷史文化的研究需要把握重要的文化影響因素,一方面文化特點形成需要依靠部落的聚集,驩兜部落的流放于崇山地帶,在形成了歷史遺跡中就能找尋到歷史文化所呈現的片段,從發源地到文化的歸屬地,地域因素造就了文化的不同特征。而從歷史傳說的片段解讀中我們又可以看到部落間的爭斗,文化的更替對少數民族由發展到積聚的變化,從而經歷了長時期的磨合,在保留了原有文化特色的基礎上形成具有各自民族特點的文化風貌。歷史文化研究需要考量很多的人文、地域和歷史因素,挖掘內在的文化意蘊。
(三)驩兜與崇山的歷史淵源
崇山險峻,驩兜部落盡管遭遇了流放和遷徙,但是能夠在惡劣的自然爭斗中形成自己的民族就可以得知其自身的強悍和剛毅,這種毫無畏懼的品格一直延續至今,成為了苗族地區文化歷史流傳至今,保留文化特色、文化風貌的和總要保障。驩兜與崇山文化歷史本為一體,脫離任何一方進行的文化研究都是毫無根據。
三、結論
綜上所述,驩兜流放于崇山具有非常積極的歷史效果,將少數民族的文化得以繼承和延續,盡管經歷了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甚至于殘跡稀存,但是驩兜與崇山的千絲萬縷的聯系還是將崇山文化得以融合發揚下去,在文化歷史上積淀更多的價值內涵才是現實社會所應該深刻求索的,這些都需要我們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參考文獻
[1]張岳奇:《試論‘三苗”與苗族的關系》載《貴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
[2]童書業:《說貓兜所放之崇山》載《禹貢半月刊》要四卷第五期.
[3]董琦:《虞夏時期的中原》第270頁,科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
[4]拙作:《古代彭部族的繁衍與遷徙》載《徐州師范學院學報》1982年第4期.
作者簡介:向良喜(1973.8),男,土家族,湖南,職務:湖南張家界市博物館館長,哲學碩士,單位:湖南張家界市博物館,研究方向:民族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