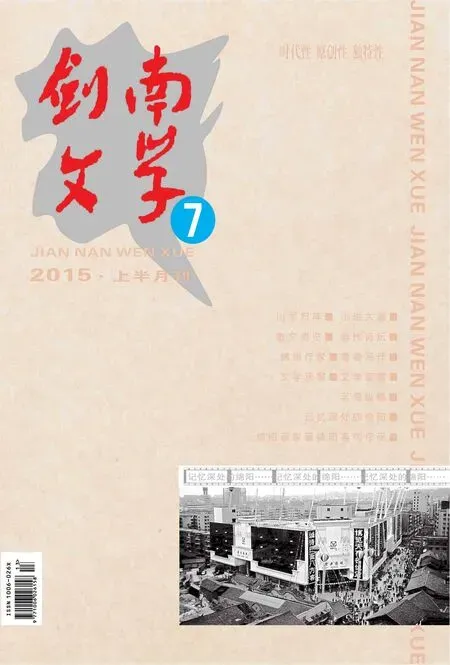名家典藏中國·綿陽“第一屆李白詩歌獎”得主洛夫特輯
名家典藏中國·綿陽“第一屆李白詩歌獎”得主洛夫特輯

洛夫(1928.5.11~),原名莫運端、莫洛夫,衡陽人,國際著名詩人、世界華語詩壇泰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者、臺灣最著名的現代詩人,被詩歌界譽為“詩魔”。
現聘任為北京師范大學、南華大學、華僑大學、衡陽廻雁詩社名譽社長。1938年舉家從鄉下遷居衡陽市石鼓區大西門痘姆街,就讀國民中心小學。1943年進入成章中學初中部,以野叟筆名在《力報》副刊發表第一篇散文《秋日的庭院》。1946年轉入岳云中學,開始新詩創作,以處女詩作《秋風》展露才情。1947年轉入含章中學,與同學組成芙蘭芝劇社和芙蘭芝藝術研究社,自編自演進步節目。1949年7月去臺灣,后畢業于淡江大學英文系,1996年從臺灣遷居加拿大溫哥華。
代表作:《石室之死亡》、《漂木》
主要成就:
中國十大詩人首位
開創中國臺灣現代主義詩歌新時代
《漂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獲得首屆孔子國際文學獎
獲得中國當代詩歌創作獎
“李白詩歌獎”得主洛夫授獎辭
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在現實與魔幻之間,在感性與理性之間,洛夫以詩為橋,連接了時間之河的此岸與彼岸。他以活潑生動、讓人過目不忘的意象,豐富了漢語的諸多可能;他的詩歌創作時間跨度久遠,是百年新詩為數不多的見證者、參與者、親歷者,甚至是標志性的擺渡者與領航者。他是詩壇的長青樹,他的詩風,有虎之長嘯也有蝶之輕盈。對于中國新詩的發展,無論意象廣度,哲學深度,還是創作手法,他都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在詞語的密林里,他是一個跋涉者,也是一個探險者。
洛夫獲獎感言
這次,我帶著興奮,帶著榮譽,也帶著最高的敬意從萬里之外的加拿大來到李白的故里綿陽。去年(2014)是我從事詩歌創作70周年,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我追求過、實驗過、成功過、也失敗過。一路走來,腳印歷歷可數。我的創作版圖大概是這樣:由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擁抱到八十年代對中華傳統文化,尤其是古典詩詞的回眸審視和價值的重新評估,再到九十年代試圖將現代與傳統、西方與中國的詩歌美學,作有機性的交融與整合,而在近二十年中,我的精神內涵和藝術風格又有了脫胎換骨的蛻變,由激進張揚而漸趨緩和平實,恬淡內斂,甚至達到空靈的境界。
我自認為,我是一個抱著夢幻飛行的宇宙游客,也是一個熱愛生活,從現實中發掘超現實詩情的詩人。我是仍在路上踽踽獨行,堅持數十年如一日的詩人,到了晚年我卻成了一塊流放海外、漂泊天涯的漂木。我這七十年不變的關鍵詞是“堅持”,而我的核心價值就是創新。
1949年由于時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由家鄉湖南獨自去了臺灣,我稱之為“第一度流放”。40年后又因故移居加拿大,我稱之為“第二度流放”。在異國我雖享受到平靜安適、條件優越的生活,但這總讓我覺得空虛、不踏實,尤其每當黃昏出外散步時,獨立蒼茫,在北美遼闊的天空下,我經常像丟了魂似的感到彷徨無依,雖然強烈地意識到自我的存在,卻也發現自我的定位竟是如此的曖昧虛浮。“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這是一種多么凄美的境界,但面對異國的時空,不免有一種失魂落魄的孤寒,因為在形式上我已失去了祖國的地平線。湖南、臺灣、溫哥華,我生命中認同的對象,其焦點已模糊不清了。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作家托馬斯曼流亡美國,有一次記者問他:“在異國他鄉的流放生活,對你的寫作有何影響?”他當時理直氣壯地答道:“我托馬斯·曼在哪里,德國便在哪里。”你看,這話說得多么豪氣干云,我雖說不出如此大氣度的話,但我也毫無愧色地說過:“我洛夫在哪里,中國文化便在哪里。”有點狂妄,是不?其實不然,因為我常年游走五湖四海,永遠都抱著中國文化走,與莊子、屈原、李白、杜甫、蘇東坡結伴同行,中國文化使我膽氣大增,使我特別感到充實而尊貴。臨老遠奔天涯,我雖一時割斷了兩岸的地緣以及政治的過去,卻割不斷養我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激勵我的心智,培養我的尊嚴的中國歷史和文化。我今天之所以能在異國安心立命,能在這詩歌遭受冷落的消費主義時代仍創作不懈,今天能夠站在這領獎,接受你們的肯定和與祝賀,這都是由于有一個偉大而深厚的文化傳統在引導我、支持我。
我有幾句近似座右銘的話,在鼓舞我誘導我,使我一直堅守著詩歌的堡壘,例如我說:“以小我暗示大我,以有限暗示無限,”所謂“暗示”其實就是隱喻。一種象征手法,亦如佛祖的“拈花一笑”。其次我說:“詩人有時是詩的奴隸,但必須做語言的主人”,這表示創作時必須取得感性與知性的平衡點。我又說:“詩不是激情,不是表層世界的拷具。詩是一種發現,詩人不僅要寫已知的世界,也要寫未知的世界。”再說:“壞的詩是腦子想出來的,好的詩是在偶然中從內心流出來的。”以上我這些詩性思維似乎陳義過高,但的確是從我數十年創作經驗中提煉出來的精華,也可說是我寫詩的秘笈。
寫詩是一種悲苦的行業,因為在這個渾濁的現實中,詩人必須保持清醒和足夠的自覺,否則你就無法堅守你的信念。所以我一向認為寫詩不只是一種寫作行為,而是一種創造,一種價值的創造。今天,浮夸而矯飾的大眾文化,把重視精神內涵的精致文化逼到邊緣地帶,詩歌的式微,并未超出我們的意料。今天詩歌真的已成為一只被放逐,任其自生自滅的野狗嗎?其實也未必如此悲觀,只要我們能以更純粹、更精美而深刻的小量作品來對抗淺薄的、低級趣味的一次消耗性的大量讀物,何嘗不可視為另一種戰略性的文化顛覆。詩人是一種超越時空的純美創造者,詩歌從來不是為了取悅大眾的讀物。當然,詩歌仍然需要讀者,我經常自覺到,名利對詩人是一把雙刃劍,多求無益,詩人夢寐以求的:一是價值,一是知音,有價值的知音更是可貴,因此這次本人和五位國內外享有盛譽的漢語詩人共同獲得首屆“李白詩歌獎”和“李白詩歌獎”提名獎,得到評委們的公平、公正的評價和肯定,這就是“有價值的知音”的證明。
李白是中國詩歌藝術中一座屹立萬世不搖的高峰,是中國文化最具象征性的最高標桿,綿陽是李白的故里,在綿陽頒發“李白詩歌獎”確是一項最富歷史意義的事件。人到晚年,本應榮辱不驚,但我這次獲獎仍不免感到莫大的喜悅和幸運,因為今天我挨著李白最近,我隱隱地聽到了他那來自遙遠的神性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