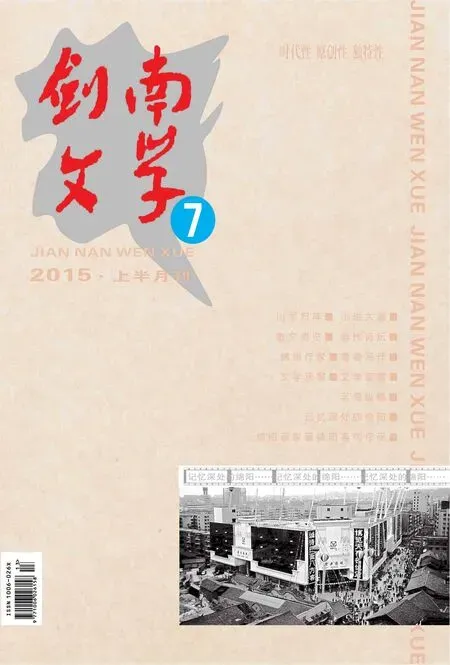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兩性倫理觀在《苔絲》中的體現
■廖春周 俞獻隆
前言
一部文學作品往往是作者所處時代的社會縮影。換言之,文學作品是反映作者那個時代的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作品中的人物、情節以及價值觀念都是作者所處時代的真實寫照。聶珍釗先生提出了“文學倫理學批評”,并他在其專著中寫道,“文學之所以成為倫理學批評的對象,主要在于文學利用自身的特殊功能把人類社會虛擬化,把現實社會變成藝術社會,具有了倫理學所需要的幾乎全部內容,提供了更為典型的道德事實”。此外,他還強調,文學倫理批評必須重視對文學的特定的歷史倫理環境地分析,避免對文學文本進行誤讀。因此,本文以作者生活的時代背景為立足點,分析哈代所處的倫理環境。通過對主人公悲劇命運地剖析來探討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的兩性倫理觀,從而得出:苔絲的遭遇不僅引領作者同時代的人們進行反思,而且同樣值得當今社會的人們思考。
一、虛偽的“雙重標準”
不幸被浪蕩的阿歷克蹂躪的苔絲是一個善良,純潔,勤奮的農村姑娘。她與安琪兒相識于牛奶廠,安琪兒覺得她是一個純潔美麗的姑娘,不懈地追求于她。不斷的折磨、悔恨、拒絕中苔絲最終答應了安琪兒的求婚,她多次想告訴安琪兒自己的過去,卻都被耽誤。終于,新婚之夜他們互相坦白了自己的過去。安琪兒的失貞獲得了苔絲的諒解。然而,苔絲的同樣的過錯卻得不到安琪兒的原諒,他的冷酷無情令苔絲感到窒息。安琪兒對自己和苔絲的過錯用雙重標準來判定凸顯了他的虛偽。安琪兒和苔絲都有權利去獲得幸福的愛情和婚姻。但是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或社會輿論的偏見仍將思想開明的安琪兒囿于維多利亞時代虛偽的雙重標準里。正如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的,“凡在婦女方面被認為是犯罪并且要引起嚴重的法律后果和社會后果的一切,對于男子卻被認為是一種光榮,至多也不過被當做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點”。對此,哈代在文中借苔絲之口發問,“貞潔這個東西,一旦失去了就永遠失去了嗎?”,這足以說明哈代對男權社會虛偽的雙重標準,不公平的道德觀念表示質疑。在《性審判史:一部人類文明史》一書中,美國著名作家伯科威茨曾寫到,“不過,處女魔怔更有可能是男人控制和主宰女人的一個手段,對男人而言,處男情結從未存在過”。 無獨有偶,有學者也認為,“哈代通過克萊爾對待男性“失足”和女性“失足”的態度來反映維多利亞時期的兩性不平等,對男女不公的社會現象進行了強有力的控訴。故而,從安琪兒的“雙重標準”可以洞察出植根于人們心中的不平等的兩性倫理觀。苔絲的悲劇命運與這一虛偽的“雙重標準”脫不了干系。
二、女性自身的世俗謬見
在19 世紀,像苔絲這樣失了身的女人往往被認為是“淫蕩,不名譽,不體面的”。安琪兒也正是因為這種世俗偏見而殘酷地離她而去。但是苔絲的悲慘命運也與自身的性格、世俗眼光密切相關。世俗的道德和宗教觀念深深地植根于苔絲的潛意識,因而她時時懷著“失身”的罪惡感,備受良心的折磨。
自從被阿歷克玷污之后,苔絲就總懷有一種負罪感、自卑感,不斷地對自己進行心理上的道德譴責。回家途中,苔絲遇見了一個人在木板上寫了一行《圣經》語錄,感到恐懼不安。這就說明了苔絲開始覺得心虛,覺得周圍的人都在死死地盯著自己,說她是一個淫蕩的、不體面的人。在教堂里看到別人竊竊私語,她會想到《圣經》里的淫婦,不由地把自己當做淫婦。牛奶廠老板偶爾說笑的幽默故事,也會令苔絲對號入座,揭起那塊最疼的傷疤。
試穿結婚禮服時,苔絲想起了兒時母親唱過的一首民謠——“兒童與絲袍”。歌中唱道:“曾經做過錯事的妻子,永遠穿不了這件衣服”。她害怕自己穿上這件長袍后會像那位妻子那樣泄露自己的秘密。這說明了苔絲內心的恐懼和憂慮,她害怕別人知道自己的過去,更擔心會失去這份來之不易的愛情和幸福。
苔絲的痛苦、不安之所以如此強烈,是因為她深受基督教義、世俗謬見的影響。盡管在沒有人知道她過去的新環境,她的內心卻還是有一掠揮之不去的陰影。聶珍釗教授認為,“她往往都會從傳統習俗、社會輿論上對自己所謂的“過失”作出道德判斷,從而扭曲了自己的正常心理,并對自己的行為予以錯誤評價。從苔絲寫給安琪兒的信中,也可以看出其自身的世俗觀念根深蒂固。綜上所述,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及世俗偏見浸潤到了苔絲的意識和性格中,使她自己陷入令人窒息的痛苦深淵。
三、冷眼旁觀的社會
19 世紀的英國進入工業革命,其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社會結構的急劇變化導致當時的制度與社會現實的不協調。傳統世俗觀念和先進工業發展的不同步使那個時代的偽樂觀主義造成了悲劇的發生。,當時的社會是苔絲悲劇命運形成的關鍵肇因。這里“社會”更多地可以理解為苔絲周遭的社會環境、世俗、宗教道德,還包括她的朋友、鄉鄰、甚至其父親的眼光,這些都足以讓苔絲窒息。
木板上涂寫的《彼得后書》中的“他們的滅亡必速速來到和摩西十誡之一的“不要犯奸淫”,使苔絲感到了被指控的恐懼。 因而,有學者指出,“在世俗倫理觀念和宗教道德地束縛下, 她感受更多的是內心的痛苦與折磨,是恐懼、羞恥、不安和悔恨。這一切表明苔絲的個人自由正受到他人自由的限制,讓她無法卸掉背在自己身上沉重的精神十字架。 ”朋友們的閑聊、歡笑、善意影射、議論、竊竊私語令苔絲痛苦不堪。 就算是她父親也沒有絲毫同情過她可憐的遭遇。苔絲想要請牧師到家中給將死的小孩洗禮都得不到允許。 面對牧師的無動于衷、父親的自私自利、朋友們的人情味的缺失,苔絲只能無能為力地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因為沒有人同情她,將她帶離痛苦的深淵。 由此看來,苔絲的悲劇命運與她所處的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人們人情味、同情心的缺乏,讓苔絲失去了精神支撐,陷入了極度焦慮、羞恥、懊悔的萬丈深淵。
結語
一個心靈純潔的女性被誘奸是值得同情的,如果因此而失去女人的價值、被所愛的男人拋棄、為周遭的環境所鄙夷,那么這些世俗偏見對于那個失身的女人極為不公平。《苔絲》不僅道出了資本主義男性霸權統治下女性的生存困境,質疑了不平等的兩性倫理觀的合理性;而且鞭笞了父權制度下虛偽的倫理道德和傳統貞潔觀念的偏見。在維多利亞時代,《苔絲》引領著同時代的人們反思這一不合理的存在;并指引著當今讀者對女性的身份地位以及命運這一亙古不變的問題進行思索和體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