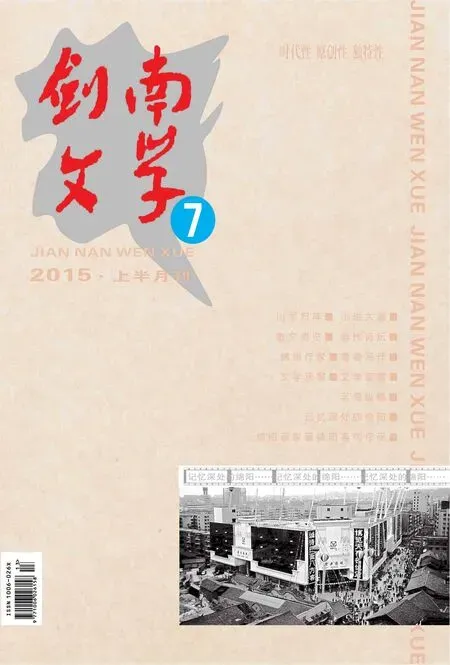新時期鄉鎮敘事中民俗文化的審美想象
■楊高強
新時期鄉鎮敘事中民俗文化的審美想象
■楊高強
城鎮化進程的加速,使得傳統鄉村社會的經濟、文化、政治各方面秩序有了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而鄉鎮這一文學敘述空間,為當代新世紀文學提供了豐富的話語資源與新的書寫經驗。本文旨在通過對新世紀“鄉鎮”敘事小說的解讀,探討“鄉鎮”這一新審美空間在鄉土中國現代性轉型期所呈現的別樣的新風景,揭示“新鄉鎮中國”的時代進行時主題在文學創作領域展開的現代性思考。
“地域文化是指在特定地理位置和自然疆域內形成的具有強烈區域特征和明顯地方特色的社會文化系統。”作為人類社會化進程中的精神產物,民俗風情傳統不僅可以視作地域文化的精神徽標,更以直觀而外在的形式構成了傳統文化的歷時性載體。小鎮的風情風物描寫,是新世紀鄉鎮敘事小說具有文化內涵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新世紀鄉鎮敘事小說的獨特魅力之所在。鄉鎮這一特殊的地理空間自它出現之日起,就被賦予了別具一格的意蘊內涵。鄉鎮在中國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歷程中有著特殊的意義,在整個鄉鎮中國的發展前景下,鄉鎮空間和鄉鎮敘事的特殊性應該被揭示、多樣性應該被建構、復雜性應該被重視。
一、小鎮風情風物的原鄉審美
所謂風情,也就是風俗人情。宋德胤認為,由自然條件不同而形成的習尚稱為“風”,由社會環境不同而形成的習尚稱為“俗”。風俗可以看作是由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所決定的風尚、禮節、習慣等,是特定社會文化區域內歷代人們共同遵守的行為模式或規范。而人情則是風尚、禮節、習慣等體現出來的世風民情。小鎮是一個特定的地域空間,其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個性特征決定了小鎮風情與都市風情的不同。新世紀鄉鎮敘事小說從不同的角度書寫了小鎮風情。從作家的審美情感來看,小鎮尚未被現代化進程徹底顛覆的傳統風情風物,成為他們精神棲息的寄托,帶有鮮明的原鄉意識。
(一)時空交錯視角下的溫情回望
遲子建在《布基蘭小站的臘八夜》這部作品中所描寫的小鎮,偏僻寧靜,民風淳樸。在布基蘭小鎮這個遠離塵世喧囂的敘事空間中,人們的善意與溫情隨處可見,這種善意是出于對人的人性化關懷,有時可能不合法理卻合乎情理。比如小偷劉志由于家庭貧困迫于無奈才走上盜竊之路,派出所的老劉得知這種情況后故意擾亂了破案線索,放了劉志一條生路。深受感動的劉志為了表示自己改過自新、決不再偷的決心剁掉了自己右手的三根手指,而老劉給了劉志5000塊錢治療斷手指。在這個美麗的小鎮上,不僅人與人之間充滿了善意的關懷,人與動物之間也有著動人的故事。云娘撿養了獵犬嘎烏,嘎烏長大后云娘發現嘎烏是狼與犬交配產的后代,因為她的丈夫老獵手烏魯達是被狼害死的,于是無法面對嘎烏的云娘數次想把它放回山林間獨自求生,然而嘎烏對云娘已經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和深深的依賴。這些故事情節體現著人性的溫暖,無不讓人為之動容。陳旭紅的《人間歡樂》里,小鎮上生活著一對有智力缺陷的患難夫妻小乙,質樸善良的居民并沒有輕視他們,反而對這對夫妻照顧有加。小鎮人的行為,如同金雞鎮一樣古樸而溫暖。在作品中,小乙夫婦的相濡以沫、毛屠夫的一句問候、秋葫蘆媳婦遞過去的一捆稻草,還有鐘老師的那把二胡,都是這人間的歡樂。鎮上的每一個人都是那么善良淳樸,使得敘述者所要呈現金雞鎮這個空間的淳樸涵義愈發深刻。
(二)現代視域中的別樣審視
新世紀的鄉鎮敘事作品中,有關小鎮風物描寫的主要內容大概有:地域風貌描寫或風光景物描寫、風俗物產描寫、民間技藝描寫等。年輕一代的作家們不遺余力地展示了自己記憶中的鎮街及鎮街上的風光景物,。比如薛舒的劉灣鎮、徐則臣的花街以及小葫蘆街、魏巍的吉安、魯敏的東壩鎮、溫亞軍的桑那鎮、白天光的香木鎮等。
街道是小鎮的一個重要的地域空間,日本建筑學家蘆原義信認為“:街道是當地居民在漫長的歷史中建造起來的,其建造方式同自然條件和人有關。因此,世界上現有的街道與當地人們對時間、空間的理解方式有著密切關系。”在薛舒的筆下,劉灣鎮街道是美麗祥和的:“這個五月暮春季節,劉灣鎮南街上,稀疏的苦荊樹粉紅色的花朵正接近頹敗,枇杷樹上的果子還青澀,風吹在身上是有些涼意的。”通過作品中對自己故鄉小鎮風光景物的動人描述,可以看出作者是帶有理想化的色彩來回憶自己的家園。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徐則臣、張國擎、鐘求是、魯敏、薛舒等新生代作家們的創作中,小鎮的地域風貌或風光景物描寫都具有某種隱喻功能。比如徐則臣的作品中有關“青石板路”或“花街”的描寫,都是帶有一種具有隱喻意味的特定意象。
二、小鎮風情風物的民俗學意識建構
小鎮風情風物的描寫與民俗學意識有著內在的聯系,所謂民俗學意識即是“文藝民俗學意識”。新時期的小鎮風情風物描寫有顯著的民俗學意識支撐,比如《水葬》、《慘霧》、《菊英的出家》等作品,是現代文學階段民俗描寫的重要作品。彼時作者描寫鄉野風俗是為了揭露、批判,并高聲吶喊以引起療救的重視。這些作品的整體描寫還沒有從民俗學角度切入,作家們對客觀存在的民俗的關注是“無意為之”,作家們的整體描寫不是關注鄉情民俗本身,而是指向作家的精神世界和鄉村社會。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當代文學的創作出現了“有意為之”的民俗學意識,在許多作家的筆下,民俗本身成為觀照對象,民俗事項被意象化。如王安憶的《小鮑莊》、韓少功的《爸爸爸》《馬橋詞典》、鄭義的《老棒子酒館》、莫言的《紅高粱》、賈平凹的《雞窩洼人家》、邵振國的《麥客》等作品關于鄉風民俗地描寫,都能顯示出民俗學意識有了新地變化與發展。這種“有意為之”的民俗學意識,體現出民俗學意識的進步,對鄉鎮敘事的民俗學描寫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在“自覺”的民俗學意識的引領下,出現了以鄉鎮風情風物為主要描寫對象的作品和作家。如20世紀80年代的汪曾祺、林斤瀾等少數作家及其作品。新世紀以來,這樣的以鄉鎮風情風物為主要描寫對象的作品數量眾多。鐘靈秀的《小城人物》著重展示依山傍水的三峽小城昨天的淳樸民風與地方物產;孫方友“小鎮人物”系列中的一些作品既寫民情又寫風物。以小鎮風情風物為主要描寫對象的作家通常創作“系列作品”展示小鎮風情風物,“系列作品”是作家們整體創作的核心部分。比如何申的“熱河系列”、陳世旭的“小鎮系列”、孫方友的“小鎮系列”、“陳州系列”與“潁河人物系列”、薛舒的“劉灣系列”、魯敏的“東壩系列”、范小青的“楊灣系列”、徐則臣的“花街系列”等。鄉鎮敘事的作家們具有敏銳的洞察力,發掘出鄉鎮風情風物所特有的價值與存在意義。
隨著“有意為之”的民俗學意識的不斷增強,小鎮風情風物描寫成為鄉鎮敘事小說審美觀照的主要對象。作品中看似很隨意的風情風物描寫,作者的筆下或是展示了小鎮深層的文化內涵,或是揭示小鎮社會的舊貌換新顏,或是緬懷一個遠逝的時代,或是抒發作者的感傷情懷,風情風物的描寫在作品中發揮出了強勁有力的敘事作用。
(重慶人文科技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