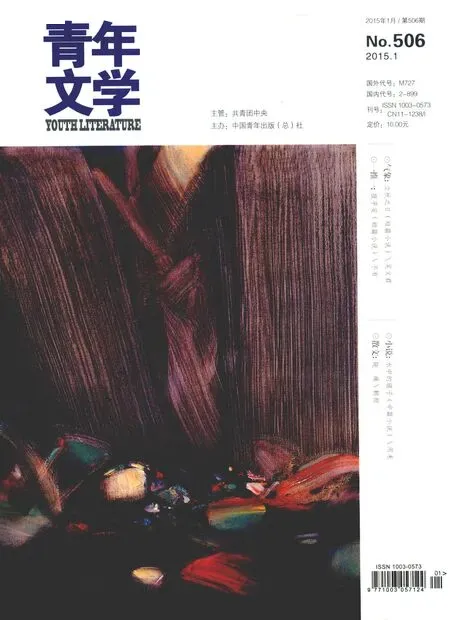報(bào)平安
⊙ 文/不 有
報(bào)平安
⊙ 文/不 有

昨晚在火車(chē)上,又是一夜無(wú)眠。
剛一進(jìn)列車(chē),就感到冷氣逼人。短暫的適應(yīng)之后,才漸漸發(fā)覺(jué),車(chē)廂內(nèi)的溫度并沒(méi)有因?yàn)殚_(kāi)著冷氣就得到有效的改善,反而造成了局部的冷熱失調(diào),在短短一節(jié)車(chē)廂里尋找鋪位時(shí)竟生出陰陽(yáng)交錯(cuò)的感覺(jué)。
費(fèi)了點(diǎn)勁兒爬到上鋪后,發(fā)現(xiàn)空調(diào)口正對(duì)著躺下后擱頭的地方,呼呼的冷氣已將枕頭吹涼了一段時(shí)間。還來(lái)不及為躺下后的問(wèn)題擔(dān)心,空間的局促使得我只能佝僂著身子觀察下方的情況。中鋪雖然空著,但被子都已經(jīng)散開(kāi),枕頭上也壓了一個(gè)凹形。兩邊下鋪上共坐著四五個(gè)像是相熟的人,只有一個(gè)男孩看去和我年紀(jì)相仿。當(dāng)他抬起頭注意我時(shí),我便趕緊向他示意,請(qǐng)他幫忙把我還留在下面的行李提上來(lái)。這時(shí)坐著的幾個(gè)女人也都抬頭看我。男孩彎身托住行李的底,斜舉著送上來(lái),我拉住行李的提手,全身別在護(hù)欄上,使了腰上的力,總算拽了上來(lái),抱在懷里。鋪腳處的行李格中已經(jīng)有了一件大行李箱,我推開(kāi)它一些,把自己的箱包塞了進(jìn)去。
經(jīng)過(guò)這樣一番“勞作”,腦門(mén)上沁了汗,便索性躺下身來(lái)。
最終還是沒(méi)能忍受住冷氣的吹拂。車(chē)廂里的壁燈熄掉后,我悄悄順了扶梯爬下來(lái),踩住自己的鞋,離開(kāi)近在咫尺的鋪上人的鼻息,挪出了半封閉的隔間,來(lái)到了過(guò)道上。
過(guò)道一側(cè)的窗簾被列車(chē)員拉到嚴(yán)絲合縫的程度,列車(chē)似乎已經(jīng)移出城市很遠(yuǎn),很久才有一點(diǎn)灰蒙的光撲滅在行進(jìn)的窗戶上。
窗沿下的折疊椅翻開(kāi)來(lái)后,面積卻很短小,我雙手置于膝上,脊背繃直,如面對(duì)著旅人們的夢(mèng)境聽(tīng)講。正在心里打鼓如何這么一夜坐過(guò)去,想起之前下鋪的幾個(gè)人商量著換鋪位的事兒,其中一個(gè)是從臨近的隔間中換過(guò)來(lái)的(我們這間隔段里有一處下鋪始終空著)。考慮到她的年紀(jì),既然是換鋪,要么是因?yàn)橄惹暗匿佄浑x自己的旅伴有些遠(yuǎn),要么大概就是上下不便了。列車(chē)員很久不再巡視了,我離了座位,到相鄰的隔間中察看,果然余有一個(gè)鋪位,竟然還是有窗戶可看的中鋪。也不知已在深夜中坐了多久,當(dāng)我再次攀爬上扶梯的時(shí)候,車(chē)廂已經(jīng)進(jìn)入了最寧寂的時(shí)刻。
我抓緊時(shí)間把自己的身體放平,體味這奇怪的好運(yùn),同時(shí)感到尾椎因久坐而受了傷一般隱隱刺痛。這樣躺了一會(huì)兒后,再也感覺(jué)不到空間的局促和擠壓,不自覺(jué)把被角拉到了下嘴唇上;如果不是窗外突然出現(xiàn)的火情,我恐怕真要睡著了。
當(dāng)覺(jué)出那種光照是在延續(xù)著的時(shí)候,已經(jīng)明顯感到車(chē)廂里越發(fā)燥熱了,空調(diào)的嗡嗡聲也聽(tīng)不見(jiàn)了,冷氣的蹤影似有似無(wú)。直到嗅到一股尖利的焦煳味道,我才旋著身子,掀開(kāi)了頭頂一側(cè)的窗簾。隨即發(fā)現(xiàn)山火已經(jīng)近在眼前了!一道斜坡點(diǎn)滿滾動(dòng)著的火團(tuán),從車(chē)窗上方掠過(guò),火苗的中心猶如快速綻開(kāi)的笑靨,在視野中曳出黏稠的糖絲般的劃痕。如果此時(shí)有人睜開(kāi)睡眼,映在瞳仁里的火苗馬上就能為仿佛已有流火四溢的車(chē)廂再點(diǎn)燃兩盞小汽燈!我擔(dān)心人們被熱醒后會(huì)發(fā)出喪心病狂的號(hào)叫,但由于不知這樣的恐怖騷動(dòng)究竟何時(shí)會(huì)發(fā)生,便再也無(wú)法躺下,只是一味用發(fā)麻后漸漸失去知覺(jué)的臂肘支撐著,向窗外忽然興起的獸群一般的火焰望進(jìn)去。
火勢(shì)終于一點(diǎn)點(diǎn)黯淡下去,但并不是減弱了,只是隨著列車(chē)的遠(yuǎn)離,將火留在了山野中。我渾身已經(jīng)濕透,而所有在鋪上還未蘇醒的人似乎正是靠了夢(mèng)的抵御,才免于慘死。天色漸漸轉(zhuǎn)亮的時(shí)候,我早早離了鋪位,一個(gè)人閉了門(mén)在洗手間里。在鏡中,我眼中的血絲仿佛還留有熱度。
洗罷臉后,略覺(jué)清爽些,便又趕回自己原先的鋪位。我對(duì)面鋪上的女孩兒已經(jīng)醒來(lái),被子推到了腰際,弓著的上身像剛從蟬蛻中脫出的蟲(chóng)腹,脖頸向前延出,嘴里叼著皮筋,正將散亂的長(zhǎng)發(fā)歸整在腦后。她的臉瘦小、枯干,梅紅色的近視鏡架擠占了眼眉之間不多的空間。我在掛梯上停頓了一會(huì)兒,終于還是爬回鋪上,坐在了靠近扶梯口的一端。
我看她整理,并試探著跟她搭話(如果忽略兩鋪之間的空中鴻溝,此時(shí)我們的對(duì)話就如同來(lái)自床頭和床尾)。“總算快到站了。”我說(shuō)。仿佛如果不是我說(shuō),她還蒙在鼓里似的。
她低頭、眼睨斜著向我這方打量過(guò)來(lái),從口里解下皮筋,五個(gè)指尖鉆入皮筋的圓圈,手掌一擴(kuò),便已將皮筋褪在腕上,同時(shí)手在腦后仍舉著黑發(fā)。
“是啊。昨天你真在外面坐了一夜?”
后半句來(lái)得有些突然,我這才想起,起初因?qū)錃獾牟贿m,曾經(jīng)面露難色地半坐半躺在鋪板上,也許因?yàn)檫@種難挨的神情被她發(fā)現(xiàn),而在一問(wèn)一答之間向她輕微地抱怨過(guò),透露了自己不想睡在上鋪的打算吧。來(lái)不及細(xì)想,便遲遲疑疑地回說(shuō):“沒(méi)有啊,剛開(kāi)始確實(shí)有這打算,但后來(lái)在隔壁找到一個(gè)空鋪,還是中鋪,總算睡下了。”
接著又想起什么,趕緊補(bǔ)充說(shuō):“還逃過(guò)了補(bǔ)差價(jià)。”
這時(shí)她已經(jīng)把頭發(fā)束好,徹底扭過(guò)臉來(lái)說(shuō):“那就好啊。”
我稍稍將身子抬起些,好讓承重的手臂略獲休息,并就在調(diào)整身體的過(guò)程中間趕緊追問(wèn):“昨晚你有沒(méi)有被熱醒?”我知道,即使昨晚她真的被熱醒了,由于上鋪已沒(méi)有窗口可看到外面,她仍可能在最初的不適后繼續(xù)沉入夢(mèng)鄉(xiāng),而無(wú)法對(duì)外面真正發(fā)生了什么有所了解。
看她停在鋪上,我懷疑她并沒(méi)聽(tīng)清我的問(wèn)話。但隨后她就回答:“我醒過(guò)。還看到你就坐在外面的走廊上。我還想,你真要在火車(chē)上坐一夜,干嗎不直接買(mǎi)硬座。是不是?”說(shuō)完,她翻身,面向床鋪,把腳板摸到梯桿上,準(zhǔn)備下去了。
我一時(shí)接不上話,耳邊再次傳來(lái)她的聲音,“我下去了”。待尋到她的視線,她正仰頭看我,我感到緊張,生硬地頓了頓下巴。她轉(zhuǎn)身出了臥鋪,下面的人頭也已經(jīng)都動(dòng)起來(lái)了。否是故意,借此從我僵硬的視線中察覺(jué)出什么,我每次都必須加快步伐,遠(yuǎn)遠(yuǎn)地離開(kāi)這雙重的注目。我想,我對(duì)女性的欣賞絕對(duì)不亞于父親,但我不想因這層未加解釋的注目而將父親的目光逗引起來(lái),或者說(shuō),只要父親在一天,我就不愿讓他知道,我在這方面已然比他還成熟,有多少東西都觀看過(guò)了呢。
她回來(lái)后,在她的幫助下,我便開(kāi)始把同一隔間內(nèi)幾個(gè)人的行李依次小心順下去。下鋪像我昨晚剛剛登上列車(chē)時(shí)那樣坐滿了人,走廊上也擠擠挨挨了不少心急的人,將大小行囊或背在身上,或放在腳邊,等待著終歸要來(lái)的進(jìn)站時(shí)刻。
沒(méi)有地方坐,我和那個(gè)女孩兒只好站在過(guò)道中,將行李擺放在一起。因?yàn)閷?shí)在不習(xí)慣緊緊挨在一起卻沒(méi)人說(shuō)話的情形,我還是率先發(fā)問(wèn)了:“你這是回家還是外出?”
“是回家啊。”她說(shuō)。同時(shí)一動(dòng)不動(dòng)地盯著窗外。
“昨晚還是多謝了。”想起昨天露出一副窘態(tài)之后她教我把報(bào)紙展在臉上抵擋冷氣,不由得說(shuō)出了感謝的話。只是話出口后才覺(jué)得唐突,沒(méi)前沒(méi)后的讓人摸不著頭腦。
她自然是有幾分詫異,眼珠在眼眶里含了一回,但很快又恢復(fù)了常態(tài),竟沒(méi)有再說(shuō)什么。
如果是在以前,在父親領(lǐng)我坐車(chē)的年月里,恐怕難以有這樣的機(jī)會(huì)好好觀察一個(gè)女孩的容貌吧。一旦意識(shí)到父親幾乎和我同時(shí)發(fā)現(xiàn)了那些好看的人時(shí),體會(huì)到他正因視線的轉(zhuǎn)移而扭轉(zhuǎn)頭部,我就感到渾身的難堪和羞澀。——我不愿在父親的這重目光之上再追加我自己的一重。我們走在街上,那些好看的背影在空氣中掀起了遲緩的“波浪”,令他腳步放慢,而正常步速的我?guī)缀趿⒖烫幱谒颓懊娴哪贻p肉體之間,無(wú)法知道他是
到站時(shí)間最終定格在六點(diǎn)零一刻。最后這段路程足足走了有四十來(lái)分鐘!車(chē)速的每一次減緩都能引起車(chē)窗旁人們的一陣激動(dòng);車(chē)廂內(nèi)外的溫差引起中年婦人的關(guān)注,拾掇起行李箱中過(guò)分整齊的衣物;因道邊擁擠的居民樓而惹起的關(guān)于房?jī)r(jià)的議論更讓人感到,在列車(chē)奔馳了整整一個(gè)夜晚之后,原本以為已被甩掉的現(xiàn)實(shí)生活此時(shí)又扒住了車(chē)窗,再次成為時(shí)間的主人。
面前這位冷冰冰的姑娘越發(fā)給人孑然一身的印象。但只要一到站,她的形象就將如同一片雪花,立刻消融在如流的人群中,那些未完成的對(duì)話也就能從形同陌路中得到寬慰和解脫。這樣一想,我也就暗自放松了因始終想嘗試再次打破堅(jiān)冰而繃緊的神經(jīng)。
我從衣兜里摸出手機(jī),發(fā)現(xiàn)不知什么時(shí)候屏幕上已經(jīng)停著兩條信息,分別是“快到站的時(shí)候給我短信”和“到哪兒了?”看看顯示的時(shí)間竟是發(fā)自一個(gè)小時(shí)之前。老許怎么會(huì)起這么早?這樣想著,一陣燥熱襲上腦門(mén),趕緊回復(fù)了短信。同時(shí)想象著一出站將會(huì)看見(jiàn)的老許的模樣。
離開(kāi)站臺(tái)后(大大小小的拉桿箱下各樣的轱轆依次滾過(guò)地面發(fā)出的喧嘩,猶如向前散落的一串串瑣碎的經(jīng)文),便進(jìn)入了一個(gè)狹長(zhǎng)的通道,隨后是陰暗的車(chē)站大廳,陳舊的站內(nèi)設(shè)施被劫掠過(guò)一般撒滿了各樣卷翹的報(bào)刊、紙張,腳下傳來(lái)幾種硬物的觸感,似有人丟落了無(wú)人撿拾的分幣。人流向門(mén)口的檢票員集中,蜿蜒如數(shù)群被河口的逆流限制住的鱒魚(yú)。這一次,排隊(duì)的人們倒是出奇的安靜,將粉紅色的車(chē)票穩(wěn)妥地出示后隨即放入了門(mén)楣上方懸垂下來(lái)的一個(gè)小紙盒中。我以為這是本地的特色,想到在此趟出差之前,老許曾說(shuō)在火車(chē)站盡量多收些車(chē)票回來(lái),就順手從紙盒中揀出了浮擱著的幾張,雖然并沒(méi)有人阻止我這樣做,但身后的動(dòng)靜卻催促得越發(fā)緊急,幾乎是將我推離了出站口。
還是清晨,到站的旅客在廣場(chǎng)上疏散開(kāi)后,露出了對(duì)面尚未開(kāi)始營(yíng)業(yè)的商業(yè)街,竟是海港般的模樣。——張揚(yáng)的路旗廣告仿若桅桿上扯開(kāi)的風(fēng)帆,一間間暗色的門(mén)面則扮演了望向水面的游艇,在輕輕擺蕩。就連天空也染上了氤氳的水汽,分?jǐn)?shù)次浸潤(rùn)的云層襯出濃淡不同的鉛灰,而在薄到即將透露天光的地方,灰色的水汽中又加入了一道反復(fù)稀釋的鈷藍(lán),像是稀薄的海風(fēng)。
我將行李歇在汪著水漬的石灰地上,正想按短信中的提示確認(rèn)老許的所在,老許卻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視野中了。一身米色尼龍防水外套,靛青色牛仔褲,草綠色登山靴,土黃色的雙肩背包單挎在一邊的肩膀上,他夾著紙煙的手沖我一示意,隨即捂回嘴前狠吸了一口,將煙蒂踩滅在腳下,回身上了一輛白灰兩色的小巴,車(chē)門(mén)未拉閉,司機(jī)已經(jīng)將車(chē)開(kāi)出了車(chē)位,向我這邊駛來(lái)。
車(chē)上一行七人。老許和一個(gè)女孩兒坐在第三排的雙人座上。拉合車(chē)門(mén)后,我彎身向車(chē)廂后部晃過(guò)去,落座在最后面的單人折椅上。幾乎是剛一落座,便感到這個(gè)單獨(dú)的座位不僅與我在全車(chē)人當(dāng)中最顯稚嫩的年齡、資歷相匹配,而且也正好是我一直以來(lái)在任何場(chǎng)合都不會(huì)拒絕的那種座位。既毫不起眼,又不會(huì)囿于偏僻,車(chē)廂內(nèi)的一舉一動(dòng)不費(fèi)絲毫力氣就自動(dòng)排列到我的眼前。
車(chē)子駛離火車(chē)站后,接連的幾個(gè)轉(zhuǎn)彎便將街景帶動(dòng)起來(lái),流轉(zhuǎn)如傳送帶上的景觀。沿途的公交站點(diǎn)上,上班的人們像被填充的棉絮,塞緊在一個(gè)個(gè)方形的空間內(nèi),被整齊地從清晨的旁邊運(yùn)離,而我們坐在小巴車(chē)上,似乎與這個(gè)自然的時(shí)刻再無(wú)關(guān)系。
老許轉(zhuǎn)回頭來(lái)對(duì)我說(shuō):“東西都帶了吧?”
“帶了。”我摸摸左手邊的行李,在它前面,是空著的一排雙人座。
這時(shí)老許身邊的女孩兒也回轉(zhuǎn)身來(lái),從問(wèn)話中帶出了本地的口音:“你姓王?北京來(lái)的啊?”
“是啊。您怎么稱呼?”我欠身向前,用手按住膝蓋,肩膀也聳起來(lái)。
“叫我小黃就行。”她快速地回了一下頭,瞅了瞅行駛的前方,又繼續(xù)回過(guò)頭來(lái),“餓不餓?”這回她干脆有些斜側(cè)著身了。我同時(shí)注意到,她肯定已經(jīng)不能再稱之為女孩兒了。雖然燙著時(shí)新的發(fā)型,漂染過(guò)的頭發(fā)卻在發(fā)絲的根部裸出了灰色,因此不如說(shuō)是對(duì)年輕事物的熱衷,才使得她的面容變?yōu)槟贻p。
“不餓啊。”我簡(jiǎn)短地回答了一句,但在火車(chē)上,實(shí)際卻是滴水未進(jìn)。
似乎再想不出別的問(wèn)話,女人轉(zhuǎn)回身去,坐正了。隨著她的動(dòng)作,我的視線被重新放置到前方的路況上,路中白色的虛線勻速地從遠(yuǎn)方移來(lái),被車(chē)窗吞入,像消失在熒屏下方的字幕。雖然只是幾句略顯拘謹(jǐn)?shù)目吞祝韵褚粋€(gè)有力的拉手,將我以盡可能快的速度抽入到一個(gè)新的交際人群中,這樣想著,我對(duì)車(chē)上的對(duì)話多了幾分留意。
坐在副駕駛座上的人有著濃重的山東口音,頭發(fā)稀疏的后腦殼頂住靠枕,略向左側(cè)偏轉(zhuǎn),與坐在第二排靠窗留短寸的男人說(shuō)著話。言談中,消瘦的短寸男人顯露出一副故地重游的神態(tài),點(diǎn)評(píng)式的話語(yǔ)逐漸勾勒出一個(gè)離鄉(xiāng)數(shù)載的游子形象,如今竟借著返鄉(xiāng)之機(jī),成功抒發(fā)了一回家鄉(xiāng)巨變給心靈帶來(lái)的震撼。甚至連坐在后排座上的本地人老許,也不禁隨著兩人的指點(diǎn)而左右交替著觀看。
坐在短寸男人旁邊、頂著一頭彈簧卷、裹著披肩的胖婦人,看年齡,她大概就是老許在電話中提到的教研主任王秀霞了,而副駕駛座上侃侃而談的定是教育局的相關(guān)領(lǐng)導(dǎo)無(wú)疑。當(dāng)車(chē)還在市區(qū)里時(shí),短寸男人下了車(chē),被囑咐了稍后會(huì)合的地點(diǎn)后,就消失在灰撲撲的街巷中了。
似乎因起得過(guò)早,當(dāng)汽車(chē)再次啟動(dòng)后,已經(jīng)有了些倦意的老許往空出的座位上展了展身體(黃姓女士已經(jīng)去和彈簧卷主任坐到了一起),隨即將后腦仰在頭枕上,任憑來(lái)自各個(gè)方向的擾動(dòng)持續(xù)打亂頸部的平衡,將頭顱搖成一桿水中的蘆葦。我坐在那里,無(wú)意中細(xì)看到老許的頭發(fā)楂兒,竟是紅棕色的,像是由于腦袋腫大而充了血。回想起在父親的引見(jiàn)下初次見(jiàn)到老許,看到他那膨脹的眼泡兒難過(guò)到了擠壓視力的程度,竟不免為老許的智力擔(dān)心——這雙多少失去了對(duì)稱的眼珠在眼白中緊張地漂浮,像說(shuō)不出話的胖頭魚(yú)。
在頭腦中這樣對(duì)老許排遣了一番之后,車(chē)廂中新一輪對(duì)話的重心已經(jīng)來(lái)到了司機(jī)的身上。“呂彪,可是我們這兒最好的司機(jī),”教育局領(lǐng)導(dǎo)嗓音成熟,咬字松弛,帶有拖腔(出入各種需要發(fā)言及無(wú)論何時(shí)都必不可少的調(diào)侃的場(chǎng)合的有效憑證),“彪子昨天睡了幾個(gè)點(diǎn)兒?”
“四個(gè)。”呂彪一打方向盤(pán),汽車(chē)在一個(gè)十字路口轉(zhuǎn)向,迅速傾斜的窗景里,屬于工作日的交通剛剛延伸出一個(gè)繁忙的長(zhǎng)度。
“啊?”老許忽然叫了一聲,“能行嗎?”
“沒(méi)問(wèn)題。”在呂彪的后腦勺上,靠近天柱穴,繃著幾塊橫肉,像多余的脂肪。
“贏了多少?”領(lǐng)導(dǎo)問(wèn)。
“贏不多,都是小錢(qián)。”
“彪子孩子多大了啊?”王秀霞問(wèn)。竟是奇怪的啞嗓,讓人想起沙地上出現(xiàn)的一圈圈字跡。
后視鏡里呂彪壓扁的臉上,黑眼珠拐向眼眶邊緣,快速地看了一眼右側(cè)的超車(chē)鏡,隨即眼瞼又恢復(fù)成半合的狀態(tài),輕輕說(shuō)了句:“還不到滿月呢。”
似乎該有人在這時(shí)起個(gè)哄——滿月里酒席已經(jīng)置辦好,就等著有人來(lái)扎破那第一個(gè)氣球了——我聽(tīng)著,但再?zèng)]人吱聲。汽車(chē)偏離了主干道,歪扭著拐上路旁的斜坡,對(duì)準(zhǔn)車(chē)位,停住了。
拉合門(mén)“嘭”的一聲關(guān)閉后,面前是一幢外觀樸素的小灰樓。空氣中仍是涼潤(rùn)的感覺(jué),像是美玉。天上的云海正一點(diǎn)點(diǎn)調(diào)配出浮島,直至有大片的魚(yú)形云跡從島隙中游過(guò)。
教育局領(lǐng)導(dǎo)、王秀霞和黃姓女青年已經(jīng)掩身在旋轉(zhuǎn)門(mén)中。另一截扇面空間接續(xù)著在老許、司機(jī)和我的面前徐徐展開(kāi),將我們投入到了仍是一片燈火輝煌的大廳當(dāng)中。
看到古金色的電梯間里已經(jīng)進(jìn)去了七八個(gè)人,團(tuán)團(tuán)站立,老許決定去走樓梯,我當(dāng)然跟隨著。
“你父親最近怎樣?”老許盯著腳下的水泥臺(tái)階問(wèn)。由于走在他的外側(cè),在轉(zhuǎn)彎處,我不得不加緊步伐,以保持跟他說(shuō)話時(shí)仍處在同一平面。
“還可以啊。就是剛一退休還有些不適應(yīng)吧。”我忽然想起還未和家里通過(guò)電話,告訴父母,我已經(jīng)和老許在一起了。
“都是這樣,過(guò)一段就好了。”
來(lái)到二樓的樓口(最后這半層樓梯老許仍舊踩得有條不紊,而我已經(jīng)迫不及待地想躍級(jí)而上,一股趕緊沖進(jìn)明亮怡人的空間中去的渴望被無(wú)聲地壓制下來(lái)),幾步之外,沉重的電梯門(mén)正往兩邊的墻內(nèi)退去,拉開(kāi)了一張張高低雜厝、被燈光映照得黯然的人臉,仿佛合影前的一刻。
“呀,你們走樓梯也這么快啊。”隨著人影從電梯間里釋放出來(lái),黃姓女青年再次站在了我們面前,她的話就像發(fā)現(xiàn)了一個(gè)新的游戲項(xiàng)目。
老許禮貌地回應(yīng)著:“你們也不慢啊。”
腳下的猩紅地毯托住了走廊向前延伸,在鉆過(guò)前方的一個(gè)玻璃門(mén)后,又進(jìn)入新的空間。在我們前后的人都走在這同一個(gè)方向上。
裝飾著枝蔓花卉圖案的暗紅色通道壁板邊,一輛金屬小推車(chē)減緩了人們的腳步,先后有人堆積在那里,拿走了什么。走近一看,原來(lái)是餐盤(pán)和取餐用的鑷夾。
這個(gè)安排老許并沒(méi)有對(duì)我說(shuō)過(guò),想不到還有一份早餐等在這路途的起始,想必是沾了同行領(lǐng)導(dǎo)的光。我也拿了自己的一份,向左手邊的餐室走去。
一進(jìn)去,竟是一個(gè)敞廳,隔音良好,從外面根本察覺(jué)不到內(nèi)部的熱鬧。從一入門(mén)的地方餐車(chē)就擺好了迎接的隊(duì)形,貼著墻壁一路配比停當(dāng)。適應(yīng)過(guò)后,在持著鑷夾選菜的同時(shí),便也感到這種熱鬧還只是視覺(jué)上的生動(dòng),并不涉及聽(tīng)覺(jué),實(shí)際上,來(lái)往走動(dòng)、閑散聚談的用餐人員仍有幾分困意未消的克制,即便是站在餐車(chē)后協(xié)助食客的服務(wù)人員,也三兩一群,互相攀比著慵懶的儀容。
尋找座位時(shí),我注意到敞亮的餐室中間有七八張可坐十來(lái)人的圓桌,在前面卻是一個(gè)小型的舞臺(tái),無(wú)人使用的黑色握柄的麥克仍遺留在臺(tái)上。餐桌上方的天花板上,遠(yuǎn)近各吊著四只炫彩的燈球(此時(shí)發(fā)著銀色的反光),看來(lái)當(dāng)圓桌撤出后,這里便是人們獲取歡樂(lè)的舞池。
在最靠近舞臺(tái)的一張空桌旁坐下后,老許端著餐盤(pán)尋過(guò)來(lái),坐穩(wěn)后,看了看我面前的餐點(diǎn)對(duì)我說(shuō):“多吃點(diǎn)兒。這趟路程遠(yuǎn),下一頓可不一定什么時(shí)候吃了。”
我看看老許的餐盤(pán),足夠豐盛了:一碗淡綠色荷葉粥,兩只泛著褐色亮汁的茶雞蛋,兩根厚實(shí)墩壯的油條,一碟五個(gè)短圓的黃金小窩頭,一屜油汪白軟的小籠包,還有配菜,是木樨肉和一小盤(pán)香芹豆干。
我起身,又到餐車(chē)中間走了一圈,此時(shí)門(mén)外還不斷有人進(jìn)來(lái),秩序仍是井然的,像是被某種西式的氛圍所籠罩,熟悉的人之間也保持著禮貌的客氣,眼神的寒暄。而在這么一頓收斂的用餐之后,我和其中的大多數(shù)人都不再有見(jiàn)第二面的機(jī)會(huì),到底只是一面之緣的過(guò)客而已。
好不容易等來(lái)新?tīng)C出的水餃,也沒(méi)看見(jiàn)黃姓女青年、同車(chē)的領(lǐng)導(dǎo)在哪里落座,待回到餐位,呂彪?yún)s已經(jīng)將自己安排在了老許的身邊,偌大的圓桌只供應(yīng)著我們?nèi)齻€(gè)的進(jìn)餐,仿佛蛋糕上羞澀的一角。
趁著用湯匙攪涼米粥的當(dāng)兒,我也觀察了一下呂彪,發(fā)現(xiàn)他取了不少肉食,餐叉捏在手中(像棵搖光葉子的小樹(shù)),頜骨上一拱一拱(像皮膚下對(duì)稱著擰了兩顆在上緊的螺絲),臉色鮮亮,并不像熬夜過(guò)度的模樣,甚至從快速的一瞥中,我還發(fā)現(xiàn)他顴骨上飛著兩朵沒(méi)來(lái)由的紅暈,略顯滑稽。
舞臺(tái)兩邊對(duì)應(yīng)著側(cè)幕條的位置,各架起一臺(tái)電視,都在播放早間的新聞,音量較小而顯得播報(bào)員也有幾分敷衍和不自信:“……華北、黃淮、華南……全國(guó)大范圍地區(qū)出現(xiàn)降水過(guò)程,局部地區(qū)出現(xiàn)暴雨及冰雹……”鏡頭轉(zhuǎn)到街邊,斜伸的話筒前,一位市民身著盛夏時(shí)的涼爽打扮,正接受記者的采訪,從聲音(該死的巨響)、畫(huà)面(夜里的手電筒)兩方面回憶著昨夜的響動(dòng),并給記者指出今早在街上發(fā)現(xiàn)的幾處陌生景致。“氣象專(zhuān)家預(yù)計(jì),本市今天還將出現(xiàn)暴雨過(guò)程,并伴有短時(shí)大風(fēng),瞬間風(fēng)力可達(dá)七級(jí),請(qǐng)市民……”
“昨晚雨下得很大嗎?”這條有關(guān)氣象和災(zāi)害的新聞一過(guò),我問(wèn)老許,嘴里已經(jīng)停住動(dòng)作。
“大啊,”老許對(duì)著我的這側(cè)腮幫子上團(tuán)起個(gè)小肉瘤,“你在火車(chē)上不知道?”說(shuō)完他將筷子伸向呂彪從餐盤(pán)上端下來(lái)的小碟子里,往嘴里塞了兩條咸菜絲。
“不知道啊。昨天……”我決定還是收回不必要的描述,“車(chē)上那么吵,就是下冰雹也聽(tīng)不到吧。”
老許似乎挺認(rèn)可我的話,沉重地點(diǎn)了點(diǎn)頭。
“還會(huì)再下的,這個(gè)地方常年雨水不斷。”呂彪忽然直接對(duì)著我說(shuō)道,“到這個(gè)地方來(lái)出差還是得準(zhǔn)備幾件保暖衣裳。”
呂彪似乎并不清楚我有一個(gè)長(zhǎng)年跑這條線的父親,早已給了我許多忠告,但這建議對(duì)我仍是傳遞了寶貴的善意。“已經(jīng)準(zhǔn)備了,謝謝您啊!”我回道。
說(shuō)過(guò)話,三個(gè)人又各自低下頭去吃飯。因?yàn)椴辉敢獍l(fā)出任何惹人注意的聲響,我把一個(gè)煮雞蛋在桌布上滾了幾個(gè)來(lái)回,終于弄出了陶瓷開(kāi)片似的紋路,一邊剝著,耳朵里又聽(tīng)到新聞。這回是日食。
對(duì)啊,今天有日全食。新聞提醒市民,注意不要用裸眼觀測(cè)日食。記者沿街調(diào)查了幾款紙片日食眼鏡,鏡頭里,好奇的市民正佩戴上這種簡(jiǎn)易“墨鏡”向天空望去。同時(shí)天文臺(tái)的專(zhuān)家也站在鏡頭前指導(dǎo)市民如何利用隨手可得的材料制作觀測(cè)工具,材料包括:曝光后的底片、X光片上的深色區(qū)域,或者,被火燎過(guò)的玻璃片,還有從廢棄的3.5英寸軟盤(pán)上撕下的黑色磁片,以及賽璐珞膠片(更像是出于編導(dǎo)自己的喜好)。
雖然沒(méi)記住具體的時(shí)間,但憑借曾經(jīng)觀測(cè)日食的經(jīng)驗(yàn),天空暗下來(lái)的時(shí)刻,一定是能察覺(jué)的吧。
日食的消息過(guò)去之后,在“每日奇聞”這個(gè)標(biāo)題下,記者們轉(zhuǎn)戰(zhàn)火葬場(chǎng)準(zhǔn)備破除“尸體在火化過(guò)程中會(huì)坐起來(lái)”的恐怖傳聞。這樣的小科教片節(jié)奏拖沓,旁白虛張聲勢(shì)。看到短片里出現(xiàn)了一具焚燒中的骷髏微微抬起上半身的畫(huà)面后,我不再盯著電視,在胃口徹底敗壞前吃完了自己的這一餐。領(lǐng)導(dǎo)會(huì)合了。在等待女士們手拉手前去占領(lǐng)一個(gè)洗手間的空閑里,呂彪已經(jīng)來(lái)到大堂外面,在駕駛座上,把車(chē)發(fā)動(dòng)著了。隔著咖啡色的玻璃墻,外面街道上的聲音也被染上了茶銹的顏色。
大樓外面,濕潤(rùn)的風(fēng)所攜帶的信息越發(fā)印證了呂彪的說(shuō)法,頭頂?shù)幕以茦O少形單影只的,都潑在一起,漫染到整個(gè)天際。
回到車(chē)上后,車(chē)?yán)锏淖恢匦抡{(diào)整過(guò)了。老許和黃姓女青年坐到了第四排(這回黃姓女青年坐在了臨窗的位置);第三排(老許他們之前的座位)是一對(duì)先前并未見(jiàn)過(guò)的青年男女,頭倚著肩(墨鏡強(qiáng)調(diào)出了女孩兒棱角堅(jiān)硬的臉型),做出親密的樣子;短寸男人再度和王秀霞坐到了一起,像一對(duì)老搭檔;副駕駛座上依然是右手緊緊抓住側(cè)窗上方把手的教育局領(lǐng)導(dǎo)(大伙都叫他“趙局”),老邁的手腕依然沉著有力,提醒人們真正對(duì)方向的掌控是來(lái)自這里。
汽車(chē)平穩(wěn)地滑入主路,周邊的事物恢復(fù)了快速的輪廓(不再是平日里在城市中步行所習(xí)慣的景色)。比起剛從火車(chē)站到用餐處的短途駕駛(一次對(duì)近距離目的地的悠閑命中),從現(xiàn)在開(kāi)始,起碼從主觀感受上,汽車(chē)改變了前行的風(fēng)格,而更趨堅(jiān)定。
在輕松超越了幾輛風(fēng)塵仆仆的皮卡之后,道邊視野逐漸變得疏闊,瀝青路面也配合著收卷起來(lái),只留下一來(lái)一往兩條車(chē)道,和許多雨后明亮的水坑。
在大堂里,中途下車(chē)的短寸男人如約和
趙局長(zhǎng)回憶起了什么,用一邊肩膀頂住椅背,回過(guò)頭來(lái),越過(guò)情侶的“丘陵地帶”,好好看著老許身邊的小黃,說(shuō)道:“我說(shuō)嘛,以前肯定是見(jiàn)過(guò)面,黃玲,黃玲,哎呀,剛才吃飯時(shí)怎么也想不起來(lái)。小黃現(xiàn)在在哪個(gè)學(xué)校干?”
黃姓女青年說(shuō)了個(gè)學(xué)校名。原來(lái)她并非本地的教員,而是在某個(gè)遙遠(yuǎn)的小縣城里生活。
“九幾年那會(huì)兒您就說(shuō)要把她調(diào)上來(lái)的。”王秀霞的啞嗓慢慢轉(zhuǎn)了一回。
“哦?還有這事兒?”局長(zhǎng)面向小黃,“那你當(dāng)時(shí)怎么回事?哪點(diǎn)兒卡住了?”
“當(dāng)時(shí)孩子太小,沒(méi)人看,就耽誤下了。”
趙局長(zhǎng)和王秀霞相視一笑:“現(xiàn)在孩子多大了?”
“在城里上大學(xué)了。”
待局長(zhǎng)坐回身去,老許接著孩子的問(wèn)題和黃玲聊了起來(lái)。
也許是年齡上的接近,兩人挺聊得來(lái)。老許正為孩子入哪所幼兒園的問(wèn)題煩惱。借助老許的孩子(一臺(tái)粉嫩的時(shí)間機(jī)器),小黃老師也回到了親子關(guān)系的起始,談?wù)撈鹑胪兄?lèi)的話題,更是輕車(chē)熟路。老許干脆把手機(jī)掏出來(lái),猶如從身上拔下來(lái)一根羽毛,邀請(qǐng)他粉色的兒子在旅途中擔(dān)當(dāng)一個(gè)過(guò)渡節(jié)目的嘉賓。
百天、滿月、爬行,在手機(jī)中,嬰兒們成長(zhǎng)得更快、更秀氣。“這不太像你啊,還是像你媳婦多一些!”這評(píng)價(jià)讓人稍感意外,但又馬上能激起反駁的樂(lè)趣,讓話題滾動(dòng)著不至半途墜地。“都這么說(shuō),但,你看這眉毛,還有鼻頭。”老許上套了。“哈哈,你這么一說(shuō),倒是真像!”
車(chē)上的對(duì)話如果不是有意壓低分貝,便是說(shuō)給全車(chē)人聽(tīng)的。在讓車(chē)后方的這兩個(gè)人獨(dú)自交流了一會(huì)兒后,趙局長(zhǎng)再次轉(zhuǎn)回頭來(lái),對(duì)短寸男人說(shuō):“公子已經(jīng)工作了嗎?”
短寸男人四根指骨戳在頭頂上,停住不動(dòng),想了想,說(shuō):“還沒(méi)有,”隨即回過(guò)頭來(lái)向情侶中的男孩兒發(fā)問(wèn):“是大四吧,今年?”
車(chē)?yán)餂](méi)有音樂(lè)。情侶選擇共用一副耳機(jī),將同一段音樂(lè)同時(shí)奏響在兩個(gè)大腦。一路上,兩人的背影像一個(gè)敞開(kāi)的琴盒,低聲的交談除了使人意識(shí)到他們剛剛也許說(shuō)了什么,并不透露言語(yǔ)的細(xì)節(jié)。
此時(shí)男孩兒的頭從女方的肩膀上抬起來(lái),伸手將耳機(jī)移開(kāi):“是大三好不好。過(guò)完這個(gè)暑假才大四。”
“在大學(xué)學(xué)什么的?”趙局長(zhǎng)又問(wèn)。
男孩已經(jīng)把耳機(jī)填回了耳郭中(好像微小的紫砂壺蓋),頭也跟著重新攏回一旁的女生肩膀上。這一次,對(duì)話的漣漪只是輕輕漫過(guò)了男孩的頭頂,而在距離觸發(fā)漣漪的中心不遠(yuǎn)處,短寸男人回答了局長(zhǎng)。
“畢業(yè)后有什么打算,打算讓他接你的班嗎?”趙局長(zhǎng)又恢復(fù)成正向前方的坐姿,搭在把手上的四個(gè)指頭依次起落了一回,與下方的拇指捏合。
“沒(méi)有沒(méi)有!”短寸男人否定得很堅(jiān)決,但又想起了某種可能,“還得看他自己,這次帶他出來(lái)也是讓他見(jiàn)見(jiàn)世面。”
“哦,這是好事。”趙局長(zhǎng)說(shuō)。
我看到前風(fēng)擋上長(zhǎng)起了白色的水斑,陰沉的天終于再次破了一個(gè)洞。
時(shí)間一久,隨著雨勢(shì)的加大,由于僅有雙向兩條車(chē)道,加上迎面而來(lái)的多是車(chē)速極快的重型載貨卡車(chē),在這條公路上超車(chē)變得越發(fā)困難。呂彪已經(jīng)在前面一輛卡車(chē)的后面跟了很久。從前車(chē)的尾部掀起白色的水霧口袋,雨刷奮力游動(dòng)卻不能再將雨幕掃開(kāi),如穿行在水簾洞中,前方的視野花白一片。持續(xù)了幾個(gè)不安的瞬間后,車(chē)子忽然加了速,后背上傳來(lái)推力,身體一側(cè)輕微失重,車(chē)子向左側(cè)傾出,鉆出了雨簾的阻擋,逆行將慢條斯理的卡車(chē)超過(guò)。前方遠(yuǎn)遠(yuǎn)的有一個(gè)黑點(diǎn),當(dāng)它迅速變大時(shí),呂彪已經(jīng)將車(chē)開(kāi)回了正常行駛的車(chē)道,一道淺白的黑影便貼著左側(cè)的車(chē)窗倏忽向后面落去。
車(chē)上沒(méi)有睡去的人看到了這段歷險(xiǎn)。趙局長(zhǎng)輕輕地夸贊車(chē)子:“這車(chē),穩(wěn)啊。”老許也醒著,加進(jìn)來(lái):“是啊,這種路況,跑起來(lái)一點(diǎn)兒不打晃兒。”在雨中,我也體會(huì)到了這車(chē)的舒適,才一改先前車(chē)身的外形留在心中的呆板印象。紛沓而至的雨滴一次次退卻在玻璃的表面,侵襲不到裸露的皮膚;至少在這暴雨淹沒(méi)的瞬間,在這四面郊野的省際公路上,坐在快速向前推進(jìn)著的革制座椅上,這個(gè)長(zhǎng)方形盒子是我們最后的庇護(hù)所。
我試著將側(cè)窗推開(kāi)一道縫隙。馬上有傾斜的風(fēng)混著雨絲強(qiáng)灌進(jìn)來(lái),將低溫扎進(jìn)了皮膚上的毛孔。這風(fēng)在耳畔盤(pán)旋、更新,我已無(wú)法聽(tīng)清車(chē)?yán)锸欠襁€有人在說(shuō)話,以及是否有人被這呼嘯的噪聲所吵擾(用詫異的神情轉(zhuǎn)過(guò)頭來(lái),衡量我的舉動(dòng)潛藏的對(duì)他們休憩的威脅)。
有時(shí)獨(dú)獨(dú)有一棟院落立在田地的中央,獨(dú)自承受著翻卷的烏云所傾倒下的所有的雨,它本身也被淋濕成了一片著陸的雨云,和它看守的莊稼一起,永遠(yuǎn)地停止了進(jìn)化。
當(dāng)我回過(guò)頭來(lái),發(fā)現(xiàn)不知什么時(shí)候,小黃老師也已將她那側(cè)的車(chē)窗敞開(kāi)了一道大縫,正舉著手機(jī)把窗外的山梁拉進(jìn)她那一小方虛擬的彩色空間中。在屏幕里,水汽繚繞的山景后退得更慢,一格格在閃爍。老許對(duì)半山腰的停云發(fā)生了興趣,特意指出它們,還有些筒形的豎云,干脆就要掉到山腳下的洼地里去,好像遺失的玩具。
中途,小巴車(chē)開(kāi)進(jìn)了道邊的服務(wù)區(qū)。響了幾聲喇叭,卻并不見(jiàn)有人出來(lái)。地上畫(huà)著白線,但除了我們的在雨中打轉(zhuǎn)的車(chē),并沒(méi)有別的車(chē)輛停泊。汽車(chē)終于還是挨著服務(wù)區(qū)的門(mén)口停下了。
車(chē)上的人坐久了,都不免有幾分疲勞,加上雨中車(chē)窗長(zhǎng)時(shí)間緊閉,空氣難于置換,越發(fā)憋悶,此時(shí)便都撐了傘走下車(chē)來(lái)。
我和老許共用一把花傘,腳尖剛一沾地,瀝青地面上便鼓蕩起了涌出紋路的小浪,打濕了鞋尖。面前一個(gè)積水的凹坑,把我和老許一下分開(kāi)左右,傘柄慌張著像頭小鹿,從我的肩頭移走,更多的雨流注下來(lái),我索性扯開(kāi)了步子,躍上臺(tái)階,沖到了服務(wù)區(qū)商店的前廊下。
商店內(nèi)還只是毛坯房的樣子,并不見(jiàn)售賣(mài)的柜臺(tái),也沒(méi)有照明開(kāi)啟,一條通道卻很深邃,直向內(nèi)降落。先行進(jìn)入的短寸男人和小情侶不時(shí)丟出一段段回聲。我靜下來(lái)轉(zhuǎn)身看著雨簾外白色的天地,汽車(chē)被澆在雨地里,車(chē)頂上長(zhǎng)起了白色的水花,每一朵開(kāi)了又滅,滅了又開(kāi),不留一寸空閑。
老許在我旁邊點(diǎn)了根煙,吸起來(lái),呼出的紊亂氣流帶散了一些煙霧。車(chē)中部的拉門(mén)洞開(kāi)著,正露出王秀霞坐著的座位。我覺(jué)得老許也在留意車(chē)?yán)铮銌?wèn)他:“她是在吸氧嗎?”
王秀霞坐在那里,胸前抱起了灰綠色的充氣枕頭,鼻前的軟管若隱若現(xiàn)。
“她的一側(cè)肺今年切除了,肺癌晚期了。”老許邊說(shuō),邊用夾著煙的那只手的拇指指背蹭了蹭下嘴唇,“你沒(méi)聽(tīng)她聲音嘶啞,這是肺氣不足了。”說(shuō)完,老許把煙移近,吸紅一個(gè)圈。
“啊?!”這著實(shí)讓我驚異,在我來(lái)出差之前,父親曾對(duì)王秀霞在領(lǐng)導(dǎo)面前的做派頗有微詞,而現(xiàn)在,她卻已經(jīng)是一個(gè)風(fēng)燭殘年的晚期癌癥患者了!
“她病成這樣還來(lái)干什么?這一路這樣辛苦,不要命了嗎?”我不禁說(shuō)出我的疑問(wèn)。
老許搖搖頭,“那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心里說(shuō)不出是因吃驚而感到困惑,還是為這個(gè)去年還曾跟父親打過(guò)交道的活生生的人在短短一年之間竟至如此境地而感到有幾分難受,聽(tīng)完老許的話,我愣在原地。
直到恍惚看見(jiàn)黃玲在車(chē)中做出揮手的動(dòng)作,老許已換成一副緊急的表情,滅了煙,按住我的肩頭說(shuō):“快,快去拿東西,日食要開(kāi)始了。”
“什么?”
我被老許一推,已到了雨中,呂彪從車(chē)前繞過(guò)來(lái),掀開(kāi)了車(chē)廂的后蓋,翻身在我的行李上干著什么。
我心里有點(diǎn)兒急,不知發(fā)生了什么,身后又傳來(lái)老許的聲音:“讓你帶的吸水紙,快,拿出來(lái)。”
見(jiàn)我行動(dòng)遲緩,這時(shí)老許也顧不上雨了,超過(guò)我,率先一步到了呂彪身邊,竟一起把我的行李撬開(kāi),翻開(kāi)了衣物。吸水紙,是墊在行李最底部的啊。
忽然身邊有輕飄飄的紙?jiān)诼淞耍姨а劭纯此闹埽蛏弦屏艘暰€,才看見(jiàn)從陰雨的云層中已破出一個(gè)方形的洞口,露出太陽(yáng)的藏身所在,白熱刺目的圓盤(pán)上已有蠶豆大小的陰影黑起來(lái)了。而從那一點(diǎn)兒令人不安的黑里,正著起火來(lái)!飛蛾般的小火球源源不斷地自那里往外滲出,但在從天而降的過(guò)程中,逐漸長(zhǎng)大到紙船模樣的火苗又都開(kāi)始有條不紊地熄滅。終于,在半空中,眼看著從一簇簇火里燒出完整的紙來(lái)!一枚枚紙幣就這樣輕旋著托在降雨之中……
地面上,老許和呂彪兩個(gè)人彎了身,淋得透濕,專(zhuān)注地收納那些飄落在水中的紙幣,抖一抖就夾在手中的兩大幅吸水紙之間。我蹲下身去,看著一張被封在水洼里的紙幣,認(rèn)清了那上面的人像,是玉帝。
我沒(méi)有去撿冥幣。身后是去商店深處探險(xiǎn)回來(lái)、呆若木雞的三個(gè)人,我想往有前廊遮擋的臺(tái)階上避避雨,卻邁不動(dòng)步,就看著他們?nèi)齻€(gè)。摟著那個(gè)“女孩兒”的已換成了短寸男人,而“女孩兒”也早已摘下了在黑暗中成了無(wú)用裝飾的墨鏡,暴露了自己已不年輕的年齡。歲月的修飾加速著她臉的釀造,當(dāng)她再和那個(gè)依傍過(guò)她的男孩站在一起時(shí),她的臉就只剩了精心保養(yǎng)的疲憊。一對(duì)關(guān)系奇異的母子,被過(guò)分寵溺的男孩,生意場(chǎng)上的父親,此刻也許正在冰凍的頭腦中快速地掂量自己的處境吧。
黃玲向我招手了?我想起剛才的畫(huà)面,就往車(chē)子走去。經(jīng)過(guò)老許身邊,我起了一點(diǎn)兒想為他打傘的念頭,但腳下沒(méi)有停頓,縱身上了車(chē)。
王秀霞已經(jīng)停止吸氧,呂彪扔上來(lái)的紙板就堆在過(guò)道里,如同爛泥。她正像制作標(biāo)本一樣,用吸水紙盡力干燥冥幣,再把它們壓整齊,壘成磚形,一轉(zhuǎn)手熟練地塞在了座位底下。黃玲在車(chē)廂后部、我坐的位置附近舉手轟著什么蠅蟲(chóng)。副座上局長(zhǎng)的背影仍然伸出了影子般的手臂,指頭抓在把手上,像一個(gè)無(wú)人理會(huì)的毒誓。
“小王,還記得嗎,我們?cè)谟曛谐?chē)出了車(chē)禍……”老許隔著車(chē)窗,嘴唇一開(kāi)一合,我卻分明聽(tīng)懂了他說(shuō)的話。
火車(chē)上奇怪的炙烤、新聞里挺起的尸身、長(zhǎng)久的雨水……原來(lái)我竟早已被火化、被撒了親人的眼淚和祭奠的紙錢(qián)嗎?“你早就知道?……”我吞下了后面的話:可一路上你們談的都是活人的事情,心心念念的都是生,又怎么可能真的明白自己此時(shí)在哪兒?在干什么?就算今天撿了這些活人給我們燒來(lái)的紙錢(qián),又怎么知道它在前面的路上一定用得上?
我心下已經(jīng)凄然。下了車(chē),走到車(chē)廂后蓋處,滴落下來(lái)的雨湯砸在水地里的幾張冥幣上,從紙中挖出了窟窿。黃玲看到我,有些奇怪,說(shuō):“怎么還不去撿紙錢(qián)啊?以后的路要用的!”
在膝前,是我敞開(kāi)的行李箱。我翻出夾層里的手機(jī),界面中輸入的信息內(nèi)容還是“我和老許在一起了,放心”。看到它,我不死心,又按了發(fā)送鍵。久久沒(méi)有信息發(fā)送成功的報(bào)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