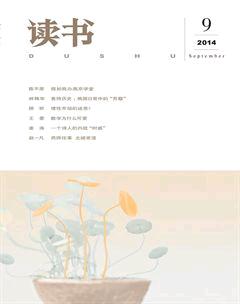假如我辦燕京學堂
陳平原
說“假如”,就是不可能的意思。既然沒有這種可能性,為何還要如此自作多情?因為不當家,不知柴米油鹽貴。相對來說,批評暢快淋漓,建設則困難得多。那就換一個角度,假如我是北大校長,正雄心勃勃地推進很有挑戰性的“燕京學堂”計劃,應該怎么做?不提“戰果輝煌”,就說“實現既定目標”吧—為何如此低調?因北大就像魚缸里的金魚一樣,在享受恩寵的同時,被全國人民拿著放大鏡觀察、挑剔、評論,稍為偏離既定的航道,就會招來鋪天蓋地的質疑與批評。這種狀態下,只能小心翼翼,平安駕駛,很難期待驚天動地的制度性創新。
可是,我們又都希望北大能奮起直追,迅速地“世界一流”。不動制度,通過增加經費,是能提升若干水平的。但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制度非動不可,這個時候,牽涉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及習慣思維。怎么辦?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謀定而后動”。可以不斷地打雷,好一陣子下不來雨;但不能沒做任何預報,就來場正義的滂沱大雨。雨是遲早要下的,但怎么下、下在什么位置、多大的量、有無節奏感等,都必須認真考量。不僅要馳想“春雨貴如油”的妙境,還得防止決堤潰壩的災難;“有百利而無一弊”的改革,那是神仙才能碰到的。很可惜,北大這回創辦燕京學堂,明顯低估了其“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難度,未曾做過認真的“沙盤推演”—我說的“沙盤推演”,是指主事者自我設置對立面,站在另一個角度立論,來回辯駁,直到基本上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
籌巨資創建一個新的教學機構,對于北大是件大事,事先其實征求過不少中層領導及名教授的意見,不可能是校長腦袋一拍就出來的。問題在于征求誰的意見,以及如何征求,程序正確不等于效果就一定好。做過行政的人都明白,討論同一件事,找誰不找誰,談論宗旨還是敲定細節,會得到截然不同的效果。一般來說,中層領導怕校長,普通教授則不怕,更有可能直言不諱;而同樣是名教授,有人習慣于“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有人則熱心公共事務,就看你能否及時發現潛在的“反對派”。若真想征求意見,應該多找有勇氣、有見解、有擔當且歷來特立獨行、敢于自我立論的普通教授,既給他們解釋,也聽他們抱怨,甚至允諾一切可以商量,大不了推倒重來。若怕人多嘴雜,想快刀斬亂麻,等生米做成了熟飯,再來努力解釋,希望廣大師生“顧全大局”,這在別的學校做得到,在北大不行。因為,說到底,這是一所民主傳統根深蒂固的大學。
平心而論,從社會募集巨額經費,創辦培養國際人才的燕京學堂,應該說是很有創意的好事。可如今好事不但多磨,且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對北大聲譽造成了不小的傷害。弄成今天這個樣子,為何當初匆忙上馬,高調宣布,而不可以稍微等一等,多邀請敢于直言的反對者參與協商,或吸納意見,化解對立;或調整節奏,優化計劃?那樣做肯定效果更好。問題在于,這都是事后諸葛亮,當初被征求意見的諸君,大都并沒意識到事情竟然這么復雜。
這就說到北大人的特點,無論校方還是教授,多志存高遠,擅長侃侃而談,看不起斤斤計較,尤其不太注意細節。可在現實生活中,確實是“細節決定成敗”—誰能想到一張“流光溢彩”的靜園修繕效果圖,會掀起如此大的風波?我相信北大校方之創辦燕京學堂,確實是用心良苦;問題可能出在懸的太高,用力太猛,操之太急,加上論述時的若干瑕疵,以致引起部分師生及校友的猛烈批評。不想“高屋建瓴”地說風涼話,我希望站在建設者的立場,幫著出出主意,看能否進一步完善此計劃。相關意見適時提交給了校方,至于是否被采納,不在我考慮范圍內。選擇九月方才刊行的《讀書》雜志發言,是假定那時大局已定,風波也基本上過去了,發文章只是為了“立此存照”。
都是模仿羅德獎學金(Rhodes Scholarships),著眼于培養國際化的“各界領導精英”;也都是一年制的學習計劃,為何清華的“蘇世民書院”波瀾不驚,北大的燕京學堂卻風急浪高?除了兩校師生處世及表達風格的不同,更因清華計劃可操作性強,北大則過于理想化,不太可行。后者選擇了學校中心且帶有標志性的靜園六院來建寄宿制書院,乃極大的敗筆,此舉引發了學生及校友的公憤,學校不得不做出妥協。如此“敗走麥城”,不全然是思慮不周,還是我所說的用力過猛,即太想把事情辦好,以至于不考慮前后左右、上下里外。在我看來,這燕京學堂即便圓滿達成目標,也只是為北大增加一個新的發展方向,不可能成為整個大學的中心。順便說一句,香港中文大學也有一個以英語講授、以國際學生為對象、“肩負提供世界級中國研究教學重任的中國研究中心”,但在整個大學處于很不起眼的位置。
我想辨析的是,為何北大這升級版的國際化計劃不太可行,以及到底該如何修正。具體論述時,不斷以清華計劃為參照系。說北大創辦燕京學堂是為了與清華的“蘇世民書院”競爭,這本身沒什么不對;兩校之間你追我趕,是個好現象,只是不要因急功近利而腳步變形。記得當年北大剛創辦文史哲實驗班時,清華提出的追趕方案是文史哲再加中外文,在征求意見的座談會上,我提醒清華校方注意:學生只有一個腦袋,且每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時。這回清華走在前,北大為了趕超競爭對手,把好幾個功能不同的計劃糅合在一起,表面上是“高大上”了,實則模糊了戰略目標,留下不少招人攻擊的把柄。
首先必須搞清楚,北大籌辦的燕京學堂,到底是“中國體驗”,還是“高端學術”。對照燕京學堂的官網,英文稱“為未來的世界領導者提供精英式的中國體驗”,與中文的強調“高端學術研究”,明顯對不上號(參見高峰楓:《誰的“燕京學堂”?》)。二者之間,我并不厚此薄彼,只是認定功能不同,不宜混淆。而且,我相信英文的介紹是有所本的,因那正是清華走的路:“五十年內,將有逾一萬名學生從這個占地二點四萬平方米的書院中畢業,他們會與自己在書院的同學和清華大學其他學生建立起私人的朋友關系,在遇到問題時,這些未來的領導人可以‘直接打電話討論。”(參見《清華獲三億美元捐建蘇世民書院 系研究生培養特區》)這明擺著不是培養專家學者,并不需要嚴格的學術訓練,是服務于國家戰略的長期的感情投資。只不過作為后來者,北大希望更上一層樓,話說得太大、太滿,反而弄得不可收拾。無論校方如何辯解,這一年制的用英文講授中國文化的碩士課程,是不可能成為“高端學術”的。一定要這么做,只有兩種可能性,或學校降低水準,法外開恩;或學生拼了小命,最終也達不到預想目標。endprint
第二,這到底是“學者項目”還是“碩士項目”?同樣是面向全球頂尖大學選拔優秀本科畢業生,清華開設的是“蘇世民學者項目”,沒說給不給學位;北大非要標新立異,說是“一年制的中國學碩士項目”,馬上引來很多質疑。先不說“中國學”,就說這一年制的碩士課程,怎么看怎么不對勁。因北大校內現有兩種不同的碩士學位課程,一是學術型,學制三年;二是專業型,學制兩年。一般認為三年的比兩年的好,如今再來個一年速成的碩士,還說是“高端學術”,確實讓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再說,國外大學的一年制碩士,大都屬于創收性質,不怎么被看好,我們為何會格外優待,且高看一眼呢?
第三,這“中國學”到底是“課程”還是“學位”?按照相關法規,北大可獨立開設新的二級學科,但頒授“中國學碩士”,必須得到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授權。二零一一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頒布了新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原屬文學門類的藝術學科獨立出來,成為第十三個學科門類。換句話說,我們國家頒授的學士、碩士、博士三級學位,只能是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軍事學、管理學、藝術學中的一個。前些年關于“國學”能不能成為一級學科,給不給頒授獨立學位,曾爭論了好長一段時間,最終還是被否決。北大這回的“先斬后奏”,我不認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能接受。
第四,在中國大學里設置“中國學”,這到底是揚長補短,還是東施效顰?清華沒有這個問題,他們在已有的學科體系中運作;北大非要棋高一著,弄出個“除了要文、史、哲貫通,還要中西學術貫通”的“中國學”。無論校方如何強調“堅持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中國問題的主體性”,這用英語教授的“中國學”,怎么看都是舶來品。中國都這么強大了,還有必要擱置現行學科體制,引進歐洲的“漢學”或美國的“中國學”嗎?我很懷疑。打破凝固的學科邊界,建立一個開放的教學科研體系,這與抄襲美國的“中國學”,完全不是一回事。從北大百年校慶開始,我就不斷強調,放眼各國好大學,其外國語言/文學/歷史/文化研究,與本國語言/文學/歷史/文化研究,走的不是一條路。不該以哈佛東亞系或牛津漢學系的立場及趣味,來評價北大中文系,反之亦然。我們有我們的問題,但絕不是移植漢學系或東亞系的眼光能解決的。若這么做,不僅不能“迅速地融入世界”,反而喪失了自家的學術立場與比較優勢。
第五,既然主要目標不是培養漢學家或中國學家,而是搶“全世界最聰明的學生”,那就不能要求人家預先學過漢語。基于這一特點,清華實行全英文授課,首期設置的公共政策、經濟管理、國際關系這三個領域,全都屬于社會科學。北大希望發揮自家人文學功底深厚的優勢,于是設計了“哲學與宗教”、“歷史與考古”、“文學與文化”、“經濟與管理”、“法律與社會”、“公共政策與國際關系”六個方向的課程體系,打出來的旗幟是兼及國際化與本土性。殊不知這么一來,用什么語言上課成了大問題。講中國文學或中國哲學,只說英語,似乎不太對勁;可中英文兼修,學生受得了嗎?讓這些“全世界最聰明的學生”臨時抱佛腳,在一年時間里,又學漢語又趕專業,做得到嗎?即便學生咬牙跺腳表決心,沒日沒夜地趕工,有這個必要嗎?兩相對照,你會發現,清華的計劃基本可行,北大的設想則過于天馬行空了。
第六,清華只是籠統地說請大師來講課,不提待遇,也不說與清華原有教授的關系。這是一個獨立運作的項目,授課者是否拿高薪,跟局外人沒關系。北大可好,把底牌都翻出來了—為這一百名獲得全額獎學金的優秀學生,北大準備從現有教師中聯合聘任三十人,從國內外公開招聘“杰出學者”二十人,并邀請“國際頂尖訪問教授”二十人,并允諾為這些教授提供高薪。七十名教授,一百位學生,如此師生比,很容易給人留下無限的遐想空間。加上后來有關人士不太恰當的解釋,坐實了校方想用這“校中校”來改造北大人文學科的猜忌。
總的感覺是,清華引進了“蘇世民書院”,沒動自家根基,卻坐收漁利。北大含辛茹苦,自籌經費,創辦燕京學堂,但因立場搖擺,思路不清,論說含糊,留下了一大堆爭議,實在很可惜。
若要我提建議,那就將燕京學堂分解為各自獨立的三大塊,第一塊是辦一所面向國際的高端的寄宿制學院的原計劃,但定位改為類似清華的“蘇世民書院”,“為未來的世界領導者提供精英式的中國體驗”。也因此,第一,只發畢業證書,不談學位問題。這么一來,可化解很多矛盾,也避開了若干激流與暗礁。至于擔心因此削減了競爭力與影響力,那是多慮了。因為,在歐美學界,碩士本就不是重要的學位。在北大拿了個一年制的碩士,對于日后從事專業研究的學者來說,可以說不值一提;而對于從政或經商者來說,也沒什么實際意義。第二,既然不是培養漢學家或中國學家,可采用全英文教學,但局限在社會科學三個領域,取消原先設計的“哲學與宗教”、“歷史與考古”、“文學與文化”,改為開設若干人文學方面的選修課。理由是,若專修中國哲學或中國文學,完全不學中文,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第三,取消這百分之三十五的中國學生,以免成為“留美預備班”。第四,不要再糾纏什么中國特色的“中國學”了,沒這個必要,且容易貽笑大方。
第二塊是培養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學家”,那就按北大的學制及標準,考核及格的方才頒授相關學科的碩士或博士學位。既然拿中國學位,必須學中文,學校不得放水(沒聽說在哈佛用中文撰寫碩士或博士論文的)。給愿意到北大來留學的各國年輕人提供足夠的獎學金,尤其關注那些相對貧窮的國家或地區(如非洲以及目前處于轉型階段的東歐國家),這比跟哈佛、牛津搶“最聰明的學生”要有意義得多。目前在北大就讀的留學生數量不少,但多屬于自費,某種意義上乃學校的創收項目。改變這個思路,招收留學生時,更多著眼于國家的長遠利益或學術發展需要。我相信,北大這么做,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第三塊是努力促成“高端學術”的誕生。說實話,研究中國問題,主要還得靠中國學者。不該過多寄希望于美國的中國學或歐洲的漢學,中國大學應立大志向,勵精圖治,方能重鑄輝煌。我多次談及中國學者如何“不卑不亢”地走出去:“依我淺見,當下的中國學界,不要期待政府拔苗助長,也別抱怨外國人不理睬你,更不靠情緒性的政治口號,關鍵是練好內功,努力提升整體的學術水平。若能沉得住氣,努力耕耘,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等到出現大批既有國際視野也有本土情懷的著作,那時候,中國學術之國際化,將是水到渠成。”(參見《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如何與漢學家對話》,收入《讀書的“風景”—大學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學出版社二零一二年版)與目前國內各大學之紛紛催逼教師留洋相反,北大完全可以做成吸納國內精英從事專業研究的平臺。考慮到北大已有得到國家大力支持的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可設立專項基金,支持學有所長的國內學者(含臺港澳)來燕園從事一年的專題研究,既出成果,也培養人才,更是盡到我們的社會責任,何樂而不為?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七日初稿于京西圓明園花園
七月三十日改定于香港中文大學客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