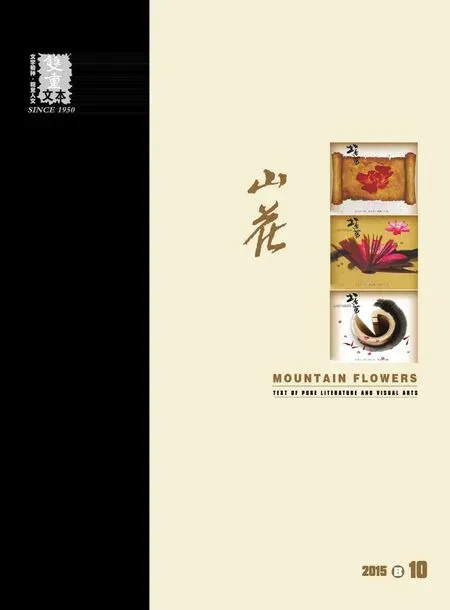“鏡”與“燈”的契合
李睿+譚武英
《馬戲團之夜》是英國當代著名女作家安吉拉·卡特的長篇小說代表作之一。其魅力在于使披露現實的“鏡”與指引現實的“燈”得以契合:客觀復現與主體表現結合,內外考詰求索, 在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后最終回歸到內心經驗的真實樣態和意向,由“鏡子”轉向“燈”;借助戲仿和奇想以開放的姿態模糊了理想與理性的界限,在既定現實之內展示了希望維度下的另一種真實,如此既具有突破和引導硬化的現實的意義,又避免了說教意味。
著名女作家安吉拉·卡特(1940—1992)可謂是上世紀英國文壇的一朵奇葩,被薩爾曼·拉什迪稱為“英國文學界仁慈的巫后”,曾獲得諸如毛姆獎、萊斯獎等多個英國重要的文學獎。其作品眾多且體裁廣泛,但她主要還是作為一個小說家闖入人們的視線并漸漸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肯定與熟知的。
本文主要探討卡特發表于1984年的長篇小說《馬戲團之夜》。瓦倫丁·科寧翰曾在《觀察家》上激動地稱:“布克獎的評委們沒有把《馬戲團之夜》如此有魅力的書列入候選名單,看來是該檢查他們的腦袋瓜和評判標準的時候了。”可見其價值非同尋常。
女性主義傾向現實主義精神的“鏡子派”強調模仿的批評,傾向浪漫主義精神的“妖女派”則強調對表現的贊揚,而兩者最終會達成一種妥協。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曾提到:心靈,成為它自身的誘惑者、交付者,成為一種機能,于是鏡子轉向燈。卡特也認為,不應勸說別人如何去做,而應把小說的道德功能看成解釋和發現事物的真諦。以下筆者將通過分析其手法與主題展開論述《馬戲團之夜》里批露現實的“鏡”與指引現實的“燈”的契合。
理性的顛覆與詩意的展望
小說的背景設在1899年的最后幾個月,這是有著深刻用意的。卡特向讀者展示了維多利亞末期的社會鏡像,看似彰顯了當時“世紀末”的政治和文化語境, 實則一面復現現實,一面批判現實。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國首先開始了婦女爭取選舉權運動,婦女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有所提升,從事的工作種類增多,并開始參政,逐漸從“家庭天使”向“新女性”轉變。維多利亞時期偽善死寂的價值體系和社會規則如家長制作風,實證哲學及19世紀中期確立的道德標準受到質疑,“世紀末”成為當時英國表達這種盛世沒落感的代名詞。蓋思瑞克認為《馬戲團之夜》預示著19世紀末后一個嶄新的勇敢的女性主義世界即將到來。當女主人公菲弗斯經過多次嘗試后,終于能張開翅膀飛行時,主張婦女參政的妓院老鴇瑪奈森高興地說:“當新世紀來臨時,所有的婦女都將展翅高飛。”菲弗斯的身世戲仿了希臘神話“麗達與天鵝”,她與生俱來的翅膀使人聯想到“家庭天使”,而事實上她卻是個經濟獨立的新女性——一個馬戲團明星,在彼得堡巡演時,她甚至住的是一流的賓館。和《新夏娃受難記》(卡特發表于1977年的一部長篇小說)中作為傳統女性美化身的電影明星特里斯特莎不同的是,她代表了一股對父權體系的破壞力量。盡管菲弗斯關心自身的經濟利益,卻并不妨礙她去捉弄那些男看客,也正因為她不安于傳統價值對她的定義,瑪奈森的妓院逐漸衰敗,斯克瑞克夫人的怪物婦女博物館也最終關門。妓院被燒,那里的妓女離開后,也都開始從事“新女性”從事的如旅店經理、秘書等工作,她自己則成為了馬戲團中一個表演空中飛人的演員。
然而在卡特睿智犀利的洞察力下,美好的假象土崩瓦解,一些潛在的因素浮出水面。經濟獨立后的“新女性”是否已成功擺脫一直以來的客體地位呢?在維多利亞社會偽善的面紗背后,傳統的女性角色早已被定格在更多維護其“莊嚴”的衛道士尤其是男性的頭腦中,當他們漸漸意識到這些新女性對男性在家庭和社會里的優勢地位均有所威脅時,這個時代所特有的焦慮已日益明了化,即維多利亞社會對新女性潛在的憂患意識。因此,卡特認為“在這個并不自由的家長制社會,追逐自由的女性就只能是怪物”。于是菲弗斯以“鳥人”的形象出現,并且沒有肚臍。她只是男人目光下的客體,在他們眼中她并非一個真實的個體,而只是一個個概念:“純潔的妓女”、“小愛神丘比特”、“勝利天使”、“死亡天使”。她擁有一雙象征自由的翅膀,卻只限于在舞臺上飛行,明星身份并不能改變她的境遇,反而使她成為男性競相物化的對象。
卡特通過塑造菲弗斯新女性的形象在模仿披露現實的同時巧妙地表現出展望的姿態,打開解放的前景。個人實現自我的主體意識努力突破女性內心的“小世界”,投射進物質的和文化的“大世界”與資本主義物化抗爭。菲弗斯先后曾有兩次險些被物化的經歷:在小說第一章,一個富有的紳士柯爾尼上校從瑪奈森手中買下她,并試圖殺死她作為五朔節祭品以確信自身的生命價值和權力;而在彼得堡時,公爵則將她塑成冰雕像,企圖將她變成他眾多玩偶中的一個。二者企圖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手段剝奪其生命力來主宰她。至于小說的男主人公華爾斯——一個周游世界采訪荒誕事件主角的美國記者,起初也只是抱著把菲弗斯物化的心態來顛覆其身份,他眼中的菲弗斯不過是個騙局,她只是一只“金絲籠中的鳥”,可見“現代資本主義統治下異化現實的非人道非人性”,眾多男性已“喪失了合理批判社會現實的能力,淪為單向度的人”。因此,男性能否擺脫霸權意識與女性主體性的高揚密切相關,要沖破樊籠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就得改善“異化的交往結構”,促進兩性間“交往行為的理性化”,鋪就一條通往自由的愛與美的引路。
小說中,菲弗斯并不甘心淪為男性的犧牲品,而是積極地宣揚自身的主體性,并且成功地維護了自己的主體地位。起初她依靠的武器是一把隨身攜帶的小劍,后來則是靠性魅力,但究其實質也只是為與父權制抗衡,體現了卡特對解放的女性形象的乞靈。因此,張中載先生認為卡特“是一個敢于闖入文學中的性這個禁區的嚴肅作家。她是帶著為婦女爭取獨立、平等、自由、解放的思想和動機闖入這個禁區的”。
在冒險中尋求的母題
《馬戲團之夜》采用的是卡特所偏愛的冒險小說的形式,用她自己的話說:“人物在不斷的冒險中尋求能心無旁騖地探討哲理的地方。”在小說主題背后還隱匿著一個“尋求”的母題。于是,小說的場景從倫敦轉移到彼得堡,再到遙遠的西伯利亞荒野,在此,“鏡子”轉向“燈”,最終完成觀念性的升騰。endprint
朱莉婭·西蒙曾指出:卡特后期的小說反映了一種道德觀——人不應去天堂尋找無限,而應在他者的眼中尋找。這意味著應承認其他主體與自身的差異并實現主體間的認可和信任,與哈貝馬斯對交往行為理性化的理解不謀而合:交往行為的理性化意味著根除存在于人的頭腦中和人際聯系中的交往屏障,使沖突得以自覺平息和交感式調解。其進步性應以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獲得的理解的主體間性和交互領域的擴展來衡量。 他認為應建立一個理想的話語環境,主體間通過真實、真誠和正當的話語將達成一種共識。在《馬戲團之夜》中,我們讀到了憂慮、介入、渴望、重生、愛欲及肯定,卡特以展望開放未來的姿態進行反事實思考,從對女性自我主體意識及兩性交往行為理性化的探尋中,生發女性自身的生活姿態和生存價值——渴望掌舵自己的人生并得到社會特別是男性的理解和認同,從而實現兩性間和諧的愛與美。
愛欲不應是建立在固有的經驗基礎之上,而應植根于自由的土壤中,如此才能作為審美主體感受到美的存在。在倫敦時,憤世嫉俗的菲弗斯“并不期待神奇王子的一吻”,而華爾斯的記者身份則使其以懷疑的眼光看所有事物,對菲弗斯與自身差異的懷疑和不理解加上菲弗斯因戒備心理而故意閃爍其詞,不僅使第一次采訪的目的不夠正當,對話也缺少真誠。華爾斯因好奇化身為馬戲團的小丑追隨菲弗斯來到彼得堡進行巡演,當看到菲弗斯為馬戲團里深受蹂躪的婦女米格南流下同情的眼淚時,他意識到自己已愛上菲弗斯,這之前從未有過的感覺使他感到深深的焦慮。而菲弗斯的小劍也在逃離伯爵的宮殿時遺失在那兒,在離開彼得堡的火車上,她試圖抓牢華爾斯的眼神,開始流露出心底本真的感情。火車在西伯利亞意外脫軌爆炸,象征著脫離“正常軌道”——父權社會下的男女二元對立。至此,“武裝菲弗斯身體和心靈的小劍以及父權時間都已不再存在”。于是,男女主人公在桑塔亞納口中的“性的第二個領域” ——遠離城市虛偽文明的自然界尋求自救,在西伯利亞的荒野最終因交往行為的理性化相互認可并達成共識,實現了理解的主體間性。
在西伯利亞荒野,卡特賦予歌唱和舞蹈以解放的力量。在與薩滿教徒的熊跳華爾茲的時候,華爾斯驚喜地想起了自己的名字;米格南充滿愛的春風般的歌聲勾起他在車禍前模糊的記憶,使他感動,他想象在這里之外是否有另一個世界,這時的他有了完全屬于自己的內心世界,“如果說他以前只是一間有待裝飾的屋子的話,那么現在至少已經有人入住,盡管那個內在的自我并不那么堅實,就像個幻影不時消失一段時間。”在他眼中,菲弗斯已不再只是個反常的現象,還是個女人。當薩滿教徒使失去記憶后的華爾斯通過夢境見到已失去往昔光華的菲弗斯時,他不禁喊道:“我見過她……我對她很熟悉……女人、鳥、明星。”
同樣菲弗斯不論從外表還是內心都發生了質的變化。金色的頭發和被染成紅色的羽毛逐漸變回原來的棕色,一只翅膀也在車禍中受傷,她現在看上去似乎更像一只“倫敦的麻雀”。她的獨白也直抒胸臆,她想“受傷的不只是翅膀還有她的心”, “她期待,她渴望能再次從華爾斯灰色的眼睛里看到曾經神采奕奕的自己”,即男性主體的肯定。于是,她決定用愛來改變華爾斯,將他重新孵化,成為與她這個新女性匹配的新男性、一個雙向度的人,然后一起攜手走入新的世紀。 她對新的世紀充滿憧憬:“玩偶店的門大開,妓院里的 ‘囚徒重獲自由,世界的各個角落不再有牢籠,大家一起高唱黎明之歌。”
在華爾斯和菲弗斯失散期間,各自內心世界的變化反映了兩人真實而相似的心路歷程。盡管另一方缺席,但并非缺失,因為在其中一方的意識深處,已視其為平等的主體存在,故可看作自我與另一主體間內心的對話交流。當兩人重逢時,菲弗斯張開翅膀,在華爾斯面前展現獨一無二的自己,已有了真實的感情并害怕失去所愛的華爾斯急切地問道:“你有靈魂嗎?能愛嗎?”阻礙兩人進行理性交往的障礙和外在壓力此刻已消除,菲弗斯要求重新進行一次采訪,她要告訴他真實的自己。與前一次不同的是,這次采訪表明二者進入了一個平等的共同語境,實現了真實和真誠的對話,而愛與美則是他們達成的共識。華爾斯的記者身份在他重生后才真正給了婦女一個發出自己聲音的機會,聲音在此與前文提到的歌唱跳舞同樣具有解放的力量,“藝術使僵硬的世界說話、唱歌、跳舞,它這樣來同物化斗爭。”卡特女性主義者的理性在其詩人的情感中展露無遺。
結 語
綜上所述,《馬戲團之夜》不失為一部帶有浪漫精神的女性主義小說。它之所以能引發讀者心靈深處的共鳴皆因“鏡”與“燈”的契合,將理想照進現實,既具有突破和引導硬化的現實的意義,又避免了說教意味。卡特關注女性的生活欲求,同時擅于利用文學的政治功用,在小說中進行女性自我的重塑及整體環境與文化傳統的改造:以客觀復現的手法反映父權社會中女性的真實處境和生存狀態,并借助戲仿和奇想,重建理性化的交往行為以構建未來平等和睦的兩性關系。《馬戲團之夜》創造了一個理想與理性界限模糊的世界,有著自己特有的意義和真實性,字里行間更多的是對現實和生命的一種反思,也帶給我們心靈的震撼和靈魂的升華。
參考文獻:
[1] Rushdie,Salman,Obituary“Angela Carter,1940-92:A Very Good Wizard,A Very Dear Friend”[N].New York Times,1992-3-8.
[2]Valentine,Cunningham. “High-Wire Fantasy”[N]. The Observer,1984-9-30:20.
[3]林樹明.多維視野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M].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81,351.
[4]Gasiorek,Andrzej.Post-war British Fiction:Realism and After [M].London and New York,1995:131.
[5]Carter,Angela.Nights at the Circus [M].London:Vintage,1994.(注:文中引用的原文系作者自譯,文中引文直接標明出處頁碼,不再一一說明.)
[6]Carter,Angela.The Sadeian Woman:An Exercise in Cultural History [M].London:Virago.1979:27.
[7]張中載.當代英國文學論文集[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8:226.
[8]馬新國.西方文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31,529-530.
[9]Simon,Julia.Rewriting the body:desire,gender and power in selected novels by Angela Carter[M].Peter Lang,2004:17.
作者簡介:
李 睿(1984— ),女,江西南昌人,江西理工大學南昌校區文理系講師,主要從事英美文學和英語教學研究。
譚武英(1979— ),女,江西南昌人,南昌工學院基礎教學部講師,主要從事語言文學和英語教學研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