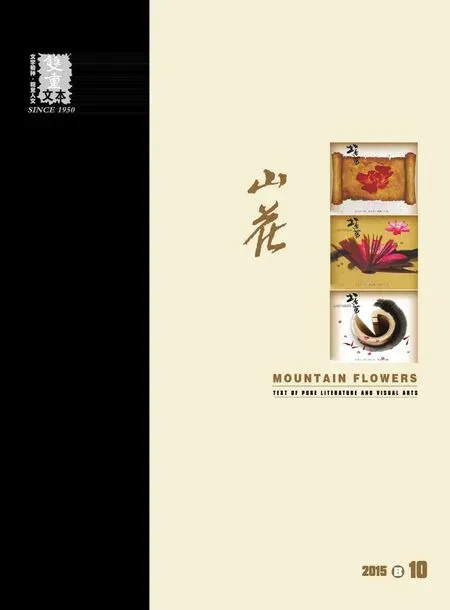淺析莫言小說飛揚的鄉土情結
姚溫麗+朱博
莫言,中國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縱觀他的小說,最大的特點是處處飛揚著鄉土情結,這也是中國文人作品歷來的風格。但是莫言的鄉土特征有其自身的特點,那就是在天馬行空的幻境中扎根現實,不粉飾、不批判筆下的人物和社會,雖時時暴露農民的愚昧、落后等劣根性,但是更體現了他們堅韌、樂觀、張揚而有活力的生活態度。本文試圖從三個方面淺析莫言小說中飛揚的鄉土情結,從而引起我們對鄉土中國以及今后文人創作的思考。
鄉土小說歷來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一支不可忽視的強大力量。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魯迅先生就開創了“離鄉——返鄉——離鄉”的現代鄉土小說模式,同時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他也曾指出:“蹇先艾描述過貴州,裴文中關注過榆關,凡在異地無論用主觀或者客觀形式描寫故鄉情懷的作品,都可稱為鄉土文學。”“鄉土小說”的概念,作為一種文學現象第一次被提出來,后來,茅盾、劉紹棠、周作人等都對鄉土文學做過不同的界說。當代學者金宏達也指出:所謂 “鄉土文學” ,是指作家描寫故鄉等自己熟悉地方(農村和小城鎮)的風土人情,并且通過特定的人物和環境表現當地的風俗習慣和心理特征等,具有濃厚的地域色彩和鄉土特色,因而能很好展現一個地方生活風貌的文學作品。他還總結了鄉土文學的特點:一是大多運用客觀寫實的手法表現作品內容,二是較多描繪地方風物和各類風俗。因此我認為“鄉土文學”主要是指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繼承了中國傳統鄉土文學的創作方法、體現中華民族鄉土精髓的文學作品。因此,鄉土小說應該是那些強烈折射出民族鄉土精神,表現中國濃郁鄉土文化特色的小說。
莫言的小說以其濃厚的鄉土氣息在中國鄉土小說寫作的道路上獨樹一幟,他的小說無論是長篇還是短篇、抑或是中篇,無不透露出一種對故鄉拳拳的眷戀之情,他通過為數眾多的小說建立了一種特色鮮明的民間立場,并且建構了“高密東北鄉”這塊代表普遍意義、瑰麗無比的鄉土大地。作家對自己的文學故鄉懷著一種愛恨交織的深情,在這塊黑色的肥沃土地上既生活著“敢愛敢恨”、“精忠報國”等傳奇色彩濃郁的生命個體;又有成群結隊在草甸子上奔跑的牛馬羊群;還有游弋在水中的白鱔魚、小螃蟹等地方特有的動植物。這是一個歡樂與困頓交織的世界,但處處卻體現著故鄉人民樂觀、勇敢、善良的美好品質,這里散發出的濃厚鄉土氣息,讓作者深深地迷戀。莫言的小說就是站在這種民間立場上肆意地抒寫著故鄉的草木和人群,并且從未離開過。
1985年,莫言以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引起了文壇的矚目,從此之后,他的小說創作處處飛揚著濃重的鄉土情結,小說大多以“高密東北鄉”這塊郵票大小的地方為背景,如長篇小說《娃》、《生死疲勞》、《檀香刑》、《紅高粱》等;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白狗秋千架》等,這些典型的鄉土小說,它們的故事都發生在這塊熟悉的土地上。他在長期的創作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即以老百姓的身份為老百姓寫作,把發生在高密東北鄉——這個被人稱之為:“地球上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的民間故事寫得如此豐富和動人,他們敢愛敢恨的精神折射出一種優美、健康、自然的人性。莫言在經歷了探尋之后終于找到了自己創作的源泉,并且筆耕不輟,在創作中體會快樂和滿足后深深地愛上了這塊土地,就像他自己所說:“我雖生活于異鄉,但我的精神卻從未離開故鄉;我的肉體雖在北京,我的靈魂卻生活在對于故鄉記憶的點滴中。”對于故鄉的土地,他有著一種生于斯長于斯愛于斯恨于斯的復雜情懷;城市給他的印象是冷漠和隔閡。于是他以“鄉下人”自居,始終圍繞著“鄉土中國”展開小說的故事,并且他的鄉土小說在經歷了時間的審視之后,厚積薄發地登上了世界諾貝爾文學獎的寶座。讓世界給中國的文學以尊重,為更好地了解中國鄉土文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筆者認為他成功的關鍵是所有作品都飛揚著一種獨特的鄉土情結,下面就從三個方面對這一情結進行淺析。
小說內容來源于故鄉的民間故事
諾貝爾文學獎給莫言的頒獎詞為“魔幻現實主義作品將民間故事、歷史和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小說內容都是來自故鄉的民間故事。從早期作品《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到《娃》、《檀香刑》、《四十一炮》,再到2005年的《生死疲勞》等小說,雖然創作風格變化較大,但是他始終把民族文化的 “根”扎在“我爺爺、我奶奶那里”,扎在故鄉的那片土地上。
《紅高粱》取材于一個發生在作者故鄉鄰村的真實故事。“我”奶奶被迫嫁給了一個擁有酒廠的麻風病人,但是卻被“我”爺爺余占鰲所吸引,在新婚第三天回娘家的路上與“我”爺爺在血紅的高粱地里面野合。丈夫被人殺死后,奶奶成了釀酒廠的主人,帶領大家釀出了噴香的好酒。9年后,日本人來了,殘忍地殺死了羅漢大爺,為了報復日軍,鄉人們全死了,奶奶也悲慘地死去,“我”爺爺精神失常,站在奶奶尸體旁,放聲高歌……
《蛙》以新中國70年代開始的農村生育史為背景,通過講述“我”姑姑50多年來從事鄉村婦產醫生的復雜工作經歷,形象地描述了國家為了控制人口急劇增長,實施計劃生育國策復雜而艱巨的歷史進程,內容符合中國農村實情,能達到管中窺豹的效果,同時深深地剖析了知識分子卑微、尷尬、糾結、矛盾的精神世界。
《檀香刑》講述的是清朝末年,山東民族英雄孫丙因抗德被抓,遭受了慘絕人寰的酷刑——檀香刑的故事。作品真實還原了百年前中國農村社會的生活現狀。
《四十一炮》最能體現莫言民間化創作的努力,他模仿古代說書人的口吻,講述了四個故事:以老蘭為首的屠宰村的發家史;羅小通的家族史,父輩之間的感情糾葛;老蘭的叔叔蘭老大的性愛史;羅小通講故事時,五通神廟外真實或想象出的故事。羅小通以兒童視角為我們描繪了一個藏污納垢的真實民間社會。如:在利益的驅動下,屠宰村往豬肉中大量注水、用福爾馬林處理病豬、死豬等,這些情況在當前中國社會真實存在著,莫言從當前社會問題出發,以純粹的民間視角,展示給我們一個真實的農村社會縮略圖。endprint
《生死疲勞》講的是1950年一個被冤殺的地主西門鬧經歷六道輪回的故事:第一世轉生為驢,即“驢折騰”;第二世轉生為牛,即“牛犟勁”,第三世轉生為豬,即“豬撒歡”;第四世轉生為狗,即“狗精神”,第五世轉生為猴,即“廣場猴戲”;第六世轉生為人,即“世紀嬰兒”。在半個世紀里,西門鬧不斷以動物的身份回到他熟悉的土地和親人中間,見證了西門鬧一家和藍解放一家生死疲勞、悲歡離合的故事,同時讓我們體味了五十年來中國鄉村社會龐雜喧嘩、充滿苦難蛻變的沉重歷史。
他的小說寫的都是中國鄉村故事,《檀香刑》沿襲了《紅高粱》、《豐乳肥臀》講農村傳奇;《四十一炮》開始涉及中國農村的各類改革;《生死疲勞》則有很深的歷史厚度,跨越了新中國成立50年多個階段的歷史,巨大的社會、歷史變革穿插其中作為故事背景,是最具現實感的一部小說。由此可見,莫言的創作內容自始至終都沒有離開民間這個鄉村舞臺,在這個舞臺上他的小說處處飛揚著一種親切的鄉土情結。
小說人物來自故鄉的土地
莫言小說中的人物并不是那些有豐功偉績的英雄,也不是處于社會上層的佼佼者,而是生活在故鄉土地上可愛的普通人。他們粗魯、愚昧、落后,往往還帶有破壞性,但是他們有強大的生命力,更能展示中國廣大農民的本性。《紅高粱》中“我奶奶、我爺爺”之輩都是草莽百姓,他們不知道抗日就是愛國,卻憑著故鄉人特有的良知和天性去積極抗日,但在抗日道路上又干出了殺人越貨的土匪行徑,在未接受任何思想解放教育的前提下,卻自由戀愛、追求自己的幸福,做事不需要偉大精神的指引,只是憑著自己滿腔的熱情,隨性而為,這正符合當時農民的本性。
中篇小說如《白狗秋千架》中的主角大都來自故鄉的普通農民;長篇小說如《娃》、《食草家族》等中的人物都是生活在故鄉土地上的普通老百姓,但是他們卻用自己的英雄事跡,精彩演繹著自己的生命故事和心理歷程,閃耀出獨特的人性光輝。莫言的小說創作擺脫了以往宏大敘事的模式,還原真實歷史,把歷史交給普通民眾,讓他們成為故事的主角、歷史的主流,再現民間真實的社會以及農民自由自在的生活狀態。
莫言小說中塑造了眾多光彩熠熠的女性形象,她們雖來自不同的生活背景,卻擁有花容月貌和旺盛的生命力,并且風情萬種。她們都是來自民間的強者,敢想敢做,敢愛敢恨,永不向生活低頭,但無論她們如何抗爭卻始終面臨著生活的苦難和悲慘的命運。《紅高粱》中剛剛年滿十六歲的“我奶奶”便出落得豐滿美麗,生命力極其頑強,但卻悲慘地嫁給了麻風病人,后又經受了爺爺感情背叛的殘酷事實,最后勇敢地死在抗日的戰場上。奶奶始終是悲劇的承載者,莫言在作品中是這樣評價她的:“我堅信,奶奶敢干她愿意做的任何事情,她不僅僅是抗日的英雄,更應該是個性解放的女性先驅和婦女自強自立的榜樣。”可以說奶奶是來自鄉間的野草,生命雖短暫但一樣芬芳四溢。莫言喜歡塑造這類女性形象,比如“孫媚娘”、“四老媽”、“上官魯氏”與她的女兒們等。因為她們身上所散發出來的野性、善良、堅韌的多重人格魅力,正好代表了生活在中國民間社會大多數的普通勞動婦女。
莫言小說中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甚至孩子都很鮮活,個性十足,符合人物身份,原因是他能扎根于民間,講述生活在故鄉土地上形形色色的人們的各種真實故事,并且在寫作過程中不粉飾、不貶低,一切隨性而動。
小說語言體現著鄉土的味道
小說的語言最能體現作家的審美傾向,莫言的小說中很少有華麗的辭藻,敘述描寫、人物語言、修辭手法等多用平實樸素的方言和口語,彌漫著濃厚的鄉土風味和地方特色,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語言風格。
車輪破了,哧哧地泄著氣。汽車轟隆隆地怪叫著,連鐵耙犁都被推得咔噠咔噠后退,父親覺得汽車像吞了一只刺猬的大蛇,在萬分痛苦地甩動著脖頸。” (《紅高粱》)
“豬十六,古人曰:出水才看兩腿泥!咱們騎驢看唱本,走著瞧!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陽光輪著轉,不會永遠照著你的窩!” (《生死疲勞》)
“哧哧地”、“咔噠咔噠”等擬聲詞語帶有濃厚的地方特色;像“常言道”、“古人曰”這類從中國古典小說民間文學中繼承來的詞語在其他小說中頻頻出現,充分表現了作者對民間通俗語言中習語、套語的偏愛。
莫言小說中人物的語言更具有鄉土性,如《白狗秋千架》中,暖說:“進屋吧,我們多傻,就這么站在風里。”“……那是頭大叫驢,見人又踢又咬,生人不敢近身……春上去買了頭牛,下了犢才一個月”。“進屋”、“近身”、“春上”等這一系列的方言詞匯,既體現了暖的農婦身份,談話內容多圍繞著農事展開,又體現了農民語言的特點,鄉村風格明顯。
許多小說中修辭方法的運用也體現了很強的鄉土性,如《生死疲勞》中洪泰岳在勸單干戶藍臉入社時說:“不要再單干,不要再獨立,常言道:‘螃蟹過河隨大流,‘識時務者為俊杰,不要頑固不化,不要充當擋路的石頭,不要充硬漢子。” 這一串排比和諺語的使用,完全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很好地體現了農民語言的特色和活力。
莫言小說的語言在多方面體現著一種鄉土情結,如《天堂蒜薹之歌》以民間快板為引子組織和結構文章,長篇小說《蛙》中的語言帶有較強的鄉土特色,從說話內容到說話習慣,都帶有故鄉人特有的民間痕跡。
莫言小說以其獨特的鄉土特色享譽文壇,他被人們稱為民間的現代之子,他在藏污納垢的鄉土民間找到了的現實文化發展的土壤, 普通人的生命精神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張揚,這種生命精神又代表了中國民間文化精神的核心,它來源于民間現實并且頑強地生存在民間社會中,莫言深深地意識到鄉土文學的生存之道。他的筆端從未離開過故鄉,在對故鄉人情世故的描述中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本土化的藝術世界,這種藝術世界,就是他通過大量作品塑造了一種不斷飛揚的鄉土情結來實現的。通過他對中國鄉土世界的書寫,我們也對一直批判的農村和農民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重新正視歷史和歷史的主流。他所開創的鄉土小說寫作模式,不僅能夠使我們對傳統的寫作方式進行重新的審視,而且也給我們以后的創作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
參考文獻:
[1]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2]莊漢新,紹明波.中國二十世紀鄉土小說評鑒[J].上海:學苑出版社,2000.
[3]莫言.我的故鄉與我的小說[J].當代作家評論,1993(2).
[4]莫言.紅高梁家族[M].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4.
[5]張閎.莫言小說的基本主題與文體特征[J].當代作家評論,1999(5).
[6]莫言,王堯.從《紅高粱》到《檀香刑》[J].當代作家評論,2002(1).
[7]劉秋云.試論莫言鄉土小說語言的鄉土特征[J].中外名作賞析,2000(3).
[8]莫言.生死疲勞[M].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
作者簡介:
姚溫麗(1980— ),女,河北滄州人,碩士,河北傳媒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教學管理。
朱 博(1983— ),女,河北石家莊人,河北傳媒學院助教;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