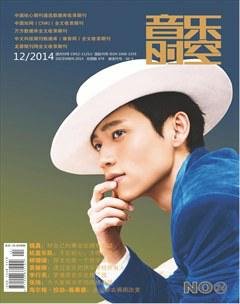中國(guó)音樂(lè)史上的文化交流與影響
吳佳文
摘要:中國(guó)音樂(lè)文化作為各個(gè)民族的精神娛樂(lè)項(xiàng)目,在我國(guó)源遠(yuǎn)流長(zhǎng)的五千年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但具有獨(dú)特的藝術(shù)風(fēng)格與特點(diǎn),也表達(dá)了當(dāng)時(shí)人們豐富多彩的思想情感。本文主要通過(guò)對(duì)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shí)期音樂(lè)文化交流的介紹,闡述了中國(guó)音樂(lè)史上的文化交流對(duì)于人們?cè)诂F(xiàn)實(shí)生活中的影響。
關(guān)鍵詞:中國(guó)音樂(lè)史 文化交流 影響
音樂(lè)文化作為我國(guó)歷史文化發(fā)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是各個(gè)民族的重要娛樂(lè)文化項(xiàng)目,同時(shí),它也是我國(guó)各民族之間以及與其他國(guó)家之間相互交流的重要媒介。很多人擔(dān)心近代音樂(lè)受西方文化影響太多而走錯(cuò)方向,迷失自己,其實(shí)不然,各國(guó)間音樂(lè)文化的交流不但不會(huì)使我國(guó)音樂(lè)文化走向衰亡,還會(huì)對(duì)我國(guó)音樂(lè)文化的豐富和發(fā)展起到相當(dāng)大的推動(dòng)作用,因?yàn)槿魏蚊褡寮词拐Z(yǔ)言不通,但卻都可以通過(guò)五線譜來(lái)進(jìn)行音樂(lè)交流,通過(guò)音樂(lè)演奏的形式將現(xiàn)實(shí)生活的情感體驗(yàn)淋淋盡致地表達(dá)出來(lái)。
一、中國(guó)音樂(lè)在歷史上的文化交流
中國(guó)音樂(lè)具有幾千的文化底蘊(yùn),在世界文化文明發(fā)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較好地帶動(dòng)了世界各國(guó)和各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文化發(fā)展,尤其是對(duì)東南亞一些國(guó)家。從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guó)到張騫出使西域,再到唐詩(shī)、宋詞、元曲等多種詩(shī)詞歌賦的盛行,都對(duì)中國(guó)音樂(lè)文化的發(fā)展起到重大的推動(dòng)作用。盡管歲月流逝,我們?nèi)阅軌驈哪切┮魳?lè)中感受到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風(fēng)俗和生活方式,重溫曾經(jīng)的歷史情景。即使是在經(jīng)濟(jì)文化水平大大提高的今天,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文化依然具有很多值得我們探究和學(xué)習(xí)的地方,甚至很多音樂(lè)文化較為發(fā)達(dá)的國(guó)家也在研究和引進(jìn)中國(guó)古典音樂(lè)文化。這里主要列舉了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和隋唐時(shí)期的音樂(lè)文化交流,來(lái)展現(xiàn)中國(guó)音樂(lè)在歷史上的文化交流狀況以及中國(guó)音樂(lè)文化的形成發(fā)展。
(一)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的音樂(lè)交流
在中國(guó)民間音樂(lè)史上,從漢代以北方音樂(lè)為主的“相和歌”與“相和大曲”到六朝以南方音樂(lè)為主的“清商樂(lè)”,再到隋唐時(shí)期的“清商大曲”,中國(guó)音樂(lè)文化的交流主要集中在南北方之間,而張騫出使西域使得西域音樂(lè)在短短幾年間便風(fēng)靡中原。南北朝時(shí)期相繼由漢化的鮮卑人和鮮卑化的漢人統(tǒng)治,與西域更是血緣相近,地壤相接,這便使得西域歌舞幾乎暢通無(wú)阻地涌入中原,風(fēng)靡南北,形成了西域音樂(lè)在中原廣為流行的蔚為壯觀的局面,也為隋唐宮廷燕樂(lè)多民族音樂(lè)風(fēng)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礎(chǔ)。同時(shí),印度佛曲也從天竺的佛教傳播到了南北朝時(shí)期,由梁武帝親制佛曲。
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是歷史上一個(gè)最混亂的時(shí)期,這時(shí)期的音樂(lè)文化都處在一種各個(gè)民族音樂(lè)文化相互交流與相互融合的發(fā)展?fàn)顟B(tài)。一方面,具有漢族傳統(tǒng)特色的“清商樂(lè)”依然受到上層社會(huì)的青睞,被廣泛傳唱與宮廷宴會(huì)與門閥士族等一些顯貴家庭中,另一方面,被稱為“胡樂(lè)”、“胡舞”的各種少數(shù)民族樂(lè)曲又勢(shì)如破竹之勢(shì)風(fēng)靡了大江南北。例如:清商樂(lè)中著名的舞蹈《白紵舞》,起初只是三國(guó)時(shí)吳地一種民間舞曲,后被改編,與佛曲相融合,因與當(dāng)時(shí)統(tǒng)治階級(jí)的享樂(lè)需求相一致,很快便被引進(jìn)宮廷,并受到統(tǒng)治階級(jí)的贊賞、喜愛(ài)。此時(shí),被改編后的《白紵舞》已經(jīng)失去了曾經(jīng)質(zhì)樸、健康的民間舞曲風(fēng)格,取而代之的是感傷與消極的格調(diào)。但在魏晉南北朝那樣一個(gè)混亂不安的動(dòng)蕩時(shí)期,改編后的《白紵舞》也很好地表達(dá)和反映了當(dāng)時(shí)人們對(duì)于和平穩(wěn)定生活的無(wú)限向往。從這方面來(lái)講,《白紵舞》又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由于此時(shí)期常年戰(zhàn)亂,人們心靈都已疲憊不堪,此時(shí)的玄學(xué)盛行,與其并存的還有佛學(xué)思想的傳入。換個(gè)角度來(lái)講,在人類最為悲苦的年代,能使人的心靈得到慰藉的是宗教,藝術(shù)只有很小的功能。
除了《白紵舞》是這一時(shí)期的代表之外,還有“胡樂(lè)”、“胡舞”均與當(dāng)時(shí)的中原舞蹈有著很大差別。少數(shù)民族的樂(lè)曲中具有鮮明的陽(yáng)剛之氣,因此“胡樂(lè)”與“胡舞”的傳入,恰巧符合了當(dāng)時(shí)人們對(duì)放蕩不羈、超脫自然的一種生活追求,受到人們的廣泛喜愛(ài),在當(dāng)時(shí)的上層社會(huì),也成為一種時(shí)尚的標(biāo)志。這也為隋唐樂(lè)舞的空前繁盛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
(二)隋唐音樂(lè)交流
一個(gè)民族音樂(lè)文化的高度發(fā)展,有的時(shí)候需要幾個(gè)世紀(jì)的文化積淀。隋唐三百余年間,音樂(lè)文化的發(fā)展之所以能夠達(dá)到中國(guó)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shí)期,原因是多方面的。這一時(shí)期,國(guó)家經(jīng)濟(jì)水平的大大提高,各民族的團(tuán)結(jié)統(tǒng)一,人民生活穩(wěn)定富足都為文化藝術(shù)的提高提供了充足的養(yǎng)分,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各族人們物質(zhì)精神水平的全面提高,也使得隋唐時(shí)期在很多領(lǐng)域均取得了重大突破,包括詩(shī)歌、繪畫、書法、音樂(lè)、舞蹈、服飾、器皿制造、建筑等。在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西域音樂(lè)大規(guī)模傳入的基礎(chǔ)上,建立起了以多民族音樂(lè)為特色的文化體制。宮廷燕樂(lè)得到高度發(fā)展,“部樂(lè)”與“部伎”的建立標(biāo)志著隋唐音樂(lè)的最高成就,在中國(guó)歷代宮廷音樂(lè)中具有登峰造極的劃時(shí)代意義。
唐朝的歌舞音樂(lè)的形式極其豐富多樣,有歌舞大曲、琴歌;有各種器樂(lè)獨(dú)奏形式,如:琵琶、五弦、古箏等,而其中代表各類音樂(lè)形式最高水平的乃是“燕樂(lè)大曲”。這是繼漢代“相和大曲”、魏晉“清商大曲”之后,我國(guó)歌舞大曲最具質(zhì)量、規(guī)模與水平的形式,其中包含“清商大曲”、“龜茲大曲”與“西涼大曲”三種不同的風(fēng)格流派。《霓裳羽衣曲》是唐代大曲的經(jīng)典作品之一,是一部將我國(guó)歌舞伎樂(lè)推向歷史頂峰的作品。民間音樂(lè)、文人音樂(lè)和宗教音樂(lè)在唐朝也有較大規(guī)模的發(fā)展。民間音樂(lè)中的“曲子”有較大發(fā)展;文人音樂(lè)中的“琴樂(lè)”和“詞樂(lè)”,成為文人階層傳統(tǒng)音樂(lè)形式和新興音樂(lè)形式兼而有之的兩大類別;佛教說(shuō)唱音樂(lè)“變文”的出現(xiàn),標(biāo)志著佛教音樂(lè)的形成。唐朝對(duì)西域音樂(lè)的開(kāi)放性政策,體現(xiàn)了唐王朝對(duì)國(guó)家、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yáng)家家學(xué)胡樂(lè)”。說(shuō)的就是一個(gè)“外來(lái)音樂(lè)”盛行的時(shí)代。白居易的《楊柳詞》:“《六幺》、《水調(diào)》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也是表現(xiàn)唐朝社會(huì)各階層普遍喜愛(ài)音樂(lè)、歌舞成為一種時(shí)代風(fēng)尚。這些都和唐朝統(tǒng)治者“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喜好音樂(lè)的傳統(tǒng)和導(dǎo)向作用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
二、音樂(lè)文化交流給人們現(xiàn)實(shí)生活帶來(lái)的影響
(一)通過(guò)音樂(lè)能夠真實(shí)地展現(xiàn)出國(guó)家和民族的傳統(tǒng)和形象
與其他藝術(shù)形式不同,音樂(lè)能夠直接并客觀地展現(xiàn)出一個(gè)國(guó)家或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和社會(huì)風(fēng)俗。了解一個(gè)區(qū)域的民俗風(fēng)情和人文特點(diǎn),音樂(lè)是其非常簡(jiǎn)便和快捷的研究方法,很多文學(xué)家在研究其語(yǔ)言的時(shí)候,都會(huì)將音樂(lè)作為一項(xiàng)重要的研究項(xiàng)目來(lái)進(jìn)行研究。音樂(lè)的聲樂(lè)和文字能夠非常具體和形象地概括出一個(gè)民族的人文特征。音樂(lè)不僅傳遞了一個(gè)國(guó)家或民族的精神文明,也是人類文明的形象代言。對(duì)于我國(guó)音樂(lè)文化而言,悠久的發(fā)展歷史和豐厚的文化底蘊(yùn)為其提供了得天獨(dú)厚的優(yōu)勢(shì),傳統(tǒng)的音樂(lè)文化也一直是我國(guó)很好的形象代表。在與其他不同國(guó)家與民族的文化文明交流中,音樂(lè)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使得世界各國(guó)家與各民族間的交流變得更加容易,如商務(wù)談判、學(xué)術(shù)交流、婚喪嫁娶等。另外,在對(duì)外進(jìn)行溝通時(shí)音樂(lè)文化能夠很好地表現(xiàn)出一個(gè)國(guó)家或民族的傳統(tǒng)和形象,如歷史上在與一些國(guó)家進(jìn)行外交活動(dòng)時(shí),經(jīng)常會(huì)用到音樂(lè)進(jìn)行交流溝通,甚至將音樂(lè)作為一種外交手段而進(jìn)行合作洽談。由此可見(jiàn),音樂(lè)在一個(gè)國(guó)家或者民族的發(fā)展中占有重要位置。
(二)當(dāng)代音樂(lè)文化作為一種工具更好地應(yīng)用于溝通交往
由于音樂(lè)對(duì)情緒的表達(dá)是直接的,人們?cè)谛蕾p某一首樂(lè)曲的時(shí)候,便很容易被其中蘊(yùn)含的情緒所感染,即使是在不同國(guó)家、不同地域,人們對(duì)情緒感受的心理機(jī)制卻是大致相同的。隨著社會(huì)水平的不斷提高,世界各國(guó)之間的聯(lián)系日益密切,音樂(lè)在當(dāng)代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除了起到娛樂(lè)、抒發(fā)情感等作用,還越來(lái)越廣泛的被應(yīng)用于外交中。這是因?yàn)楦鲊?guó)在外交中的交往不僅僅包括在經(jīng)濟(jì)方面,還存在于以更為廣泛的經(jīng)濟(jì)與思想水平為基礎(chǔ)的文化交往,而音樂(lè)又是文化交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音樂(lè)自身所具有的互通性,以及其對(duì)情感的鮮明表達(dá)和對(duì)美好的向往追求,是社會(huì)在其政治屬性方面所不具有的。在人們?nèi)粘=煌校魳?lè)作為一種溝通工具,其所具有的一些特性和功能通常能夠更直接和更淋淋盡致的被展現(xiàn)出來(lái)。例如,在每年的學(xué)生畢業(yè)時(shí),尤其在大學(xué)生中,學(xué)生通常都會(huì)精心編制和準(zhǔn)備一場(chǎng)有關(guān)音樂(lè)的畢業(yè)晚會(huì),來(lái)表達(dá)對(duì)教師的教育之恩、與同學(xué)的相處之情,以及對(duì)未來(lái)生活的美好向往和憧憬;在結(jié)交朋友或平時(shí)玩樂(lè)時(shí),現(xiàn)代人們都喜歡去一些KTV或者歌城之類的音樂(lè)相關(guān)場(chǎng)所一展歌喉,在玩樂(lè)的同時(shí)加深感情,抒發(fā)情緒。
三、結(jié)語(yǔ)
作為當(dāng)代中國(guó)青年,將中華五千年的音樂(lè)文化不斷傳承與發(fā)揚(yáng)光大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zé)任,與此同時(shí),還應(yīng)在此基礎(chǔ)上,結(jié)合傳統(tǒng)音樂(lè)獨(dú)特的藝術(shù)風(fēng)采,將世界各個(gè)國(guó)家與民族的音樂(lè)特色和音樂(lè)精華與其進(jìn)行融合并創(chuàng)新,形成新的、具有中國(guó)特色的個(gè)性音樂(lè)文化。另外,自然與社會(huì)環(huán)境不斷發(fā)生變化,音樂(lè)文化也應(yīng)適應(yīng)當(dāng)代人們不斷變更的心理需求,堅(jiān)持各地區(qū)音樂(lè)文化平衡發(fā)展,使中國(guó)多元化音樂(lè)文化的發(fā)展大放光彩。
參考文獻(xiàn):
[1]劉婷婷.試論跨文化音樂(lè)交流:1949年以來(lái)德奧古典音樂(lè)在中國(guó)的交流與接受[D].北京:北京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2007年.
[2]田青.漂流音樂(lè)長(zhǎng)河──讀馮文慈先生《中外音樂(lè)交流史》[J].人民音樂(lè),1998,(12).
[3]陶亞兵.輔叔對(duì)中國(guó)音樂(lè)史和中西音樂(lè)交流史研究的貢獻(xiàn)[J].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3,(05).
[4]陳明.培養(yǎng)多元文化的“音樂(lè)耳朵”——由跨文化音樂(lè)交流想到的[J].星海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