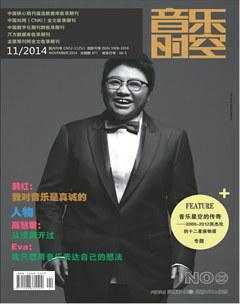風雨黔劇路
傅莎
一直以來,中國大地充斥著流行音樂和西方歌劇,卻不知在祖國西南邊陲也回蕩著文琴長笛,只是它的聲音太輕,以至于常被人們忽視。
貴州省黔劇院作為致力于黔劇藝術發展的主力軍,這些年在黔劇事業的推動上發揮了自身的力量。走進貴州省黔劇院,立刻會被滿墻的照片所吸引,這是黔劇建團以來所有劇目的演出劇照及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黔劇藝術家們的記錄和見證。這是黔劇院在以家珍示人,也是他們面向大眾對黔劇藝術這一“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宣講和守護,劇院以這樣的形式向人們闡釋了他們的藝術實踐,使得來者可以在短暫的駐足中明了歷代黔劇藝術家付出的艱辛與取得的成就,從而拉近與黔劇的距離。
經過多年的積淀與發展,黔劇院在朱宏院長的帶領下一步一步走向輝煌,這些光彩熠熠的成績當然包括2007年黔劇第一次走進央視的《名段欣賞》;包括2008年國務院批準黔劇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包括朱宏院長和鄧健廳長北上赴京,叩開中國戲曲學院附中的大門,委托中國戲曲學院附中為貴州培養一批11至13歲優秀的黔劇苗子;更是包括今年10月,在朱宏院長的帶領下,黔劇院在北京連續三天的演出。在京的三場演出,從國家大劇院——中央民族樂團音樂廳——中央財經大學,寓意著從匯報——音樂殿堂——未來這樣一個完整的演繹過程。在戲曲危機的時刻,可以說是開拓了一片由傳統精神邁向未來的“樞紐天地”,它的絕妙、它的豐富融入在了每一個音符中。
朱宏深知,民族音樂是孕育我們的胞胎,是我們生長的搖籃。優秀的音樂作品深深植根于民族音樂和文化傳統,那里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藝術營養與優良基因,黔劇院民族樂團所做的正是將貴州的靈氣和秀色摘取了來,敬獻給了人民、敬獻給了祖國。
為劇種謀發展,為職工謀福利
走進院長朱宏的辦公室,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為劇種謀發展,為職工謀福利”幾個大字,這是我省著名書法家鄧健先生為朱宏所書的座右銘,這是朱宏的心聲,也是這么多年朱宏對于黔劇藝術的堅持與實踐指南。透過這幾個字,也能隱隱感受到朱宏的抱負,理解他對黔劇愛得有多深。
1983年,考入貴州省藝術學校黔劇班的朱宏,師從鄒秀鐘、陳曉鵬、王詩林等黔劇前輩,主攻文武老生、文武小生。自1987年進團工作至今,朱宏已成為國家一級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文化部優秀專家、貴州省“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黔劇傳承人。
或許,你早已在黔劇《珍珠塔》、《貞女》、《大學生村官》等劇中看過他精湛的表演,還知道他獲得過貴州省政府文藝獎、貴州省“五個一工程獎”、“多彩貴州”戲劇比賽銀瀑獎等。當然,在地方戲劇處于低谷的時期,他也曾在夜總會和歌舞廳當過歌手,擔任過節目主持,但他依依不舍的仍然是對黔劇的那份敬畏和熱愛。黔劇吸苗嶺的秀色,取黃果樹的雄姿,借花溪一縷幽深,引夜郎古國的神秘,才形成了它的藝術高峰。它的絕妙,它的天然黔籟,地道黔味早已融入朱宏的血液之中。也正是因為有了較為豐富的人生閱歷和諸多的舞臺經驗,才使他今后的從政有了一種獨特的魅力,這魅力與他的藝術創作環環相扣,相得益彰,使他極具人氣。
2000年,朱宏擔任了省黔劇團副團長,上任之初,正逢黔劇式微,團里所有設備都很落后,可謂受命于百廢待興之際,但他的文化感悟已超越了他的專業定位,又因他的文化使命不允許他在超越之后再有退縮,他只能迎難而上,擔負起“關乎文人,以化成天下”的使命,于是有了2006年他任團長之后的模式。他時而登上“優秀共產黨員”、“五好基層黨組織”的領獎臺,時而面向手捧鮮花的觀眾深深鞠躬,并一直在尋找這兩者微妙的契合點,所謂文化,就在這相護相守之間。他認為政治功業和戲劇情節生死與共,從政、從藝他都做得極佳。從政,他有識人之慧、用人之才、容人之量,將劇院領導班子緊密團結在一起。從藝,他用舞臺這塊方寸之地,秉斯坦尼體系,追布萊希特之意,續梅蘭芳之風,摘其英華,佩其芳菲,以敬業之心演繹黔劇。
身后是傳統,眼前是未來
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黔劇的傳承人,朱宏曾隨中央文化部代表中國出訪過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歸國之后,“傳統藝術如何面對現代”,“黔劇有無希望走向國際”等關乎黔劇未來的問題一直縈繞在朱宏心頭,久久不能釋懷。
為了讓更多的人們聽到來自貴州的黔聲韻律,讓人們真正有機會走近黔劇藝術,聽一聽生旦凈末的唱腔,看一看手眼身法的表演。2007年,朱宏率團與中央電視臺《名段欣賞》欄目牽手,錄制并播出了《秦娘美·約逃宿洞》、《貞女·迎親》、《珍珠塔·贈塔》等七期黔劇片段。由此,黔劇終于走進了央視。隨著這些黔劇名段播出,縮短了黔劇與觀眾之間的距離,搭建起了一座世界與貴州對話的橋梁,將黔劇這一藝術的瑰寶、高原的明珠呈現在了世人眼前。因為朱宏想讓世界知道,中國除了北京、上海,還有貴州,更想讓所有的觀眾了解,除了電影電視、流行音樂,還有值得一看的黔劇。
一個有成就的藝術家,人們通常根據他已獲得的獎項或者通過擁有的作品來評價他,而事實上,塑造角色只能反映出藝術家的某些方面,尚不能熔鑄他的整體人格。2012年,黔劇更“團”為“院”,朱宏沒有止步于藝術創作,他又把目光和精力投入到如何“為劇種謀發展”的深度思索當中,他不愿失去每一個欣賞藝術的靈魂,也不甘心黔劇只留下一些保留劇目。擺在他面前的一個新課題——黔劇,亟待補充新鮮血液。他渴望用這新鮮血液去適應下一個歷史階段藝術的風云際會,渴望在強手如林的競爭中保留黔劇的一席之地。一個想法也隨之從心底奔騰而出:北上赴京,委托中國戲曲學院附中為貴州培養一批11至13歲優秀的黔劇苗子。當朱宏把這一想法向省文化廳匯報后,立刻得到了廳黨組的支持和贊許,分管人事的鄧健廳長深知,戲劇特別是地方劇種面臨人才青黃不接的窘況,黔劇如失去觀眾,勢必會造成民族文化的斷裂。于是鄧廳長與朱宏一起毅然赴京,叩響了中國戲曲學院附中的大門,這一叩意味著黔劇這一劇種將迎來新的轉機,這一叩也讓朱宏把自己這個傳承人的生命和使命都與黔劇緊緊連在了一起。“為劇種謀發展”朱宏認為這是他應盡的天職,他把這句話貼近了實際,貼近了蒼生,他對黔劇的這份熱愛令人感到何等神圣!中國戲曲學院附中的領導們被這份執著所感動,答應了替貴州培養黔劇人才的請求。貴州之幸!黔劇之幸!endprint
招生的消息傳開,世界也被黔劇所驚醒,人們一致轉過頭來關注著它,短短幾天,數百個孩子踴躍報名。莫小看了這踴躍的報名,這是對黔劇的聲聲呼喚,是空谷足音,是黔劇的希望,是文化的共榮,是這個劇種后繼有人的信號!
背靠黔劇,面向未來;身后是傳統,眼前是少年。我們寄希望于中國戲曲學院附中黔劇班,六年之后,這30個黔劇新苗將回到貴州,為家鄉獻上一份厚禮。前奏已經鳴響,一顆顆閃亮的黔劇新星,即將在貴州乃至全國的戲劇舞臺上冉冉升起……
風華黔韻,潤物揚帆
2008年,國務院正式批準黔劇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消息傳來,不單令全團職工增添了一份由衷的喜悅,也讓關注和支持黔劇藝術的人們對黔劇的前途增添了幾分樂觀。彼時的朱宏沒有熱衷于排練場的喧騰,而是帶領全團職工多方位頻繁參與到各種比賽和演出之中去,牢牢把握住每一個潛在的機會。通過他的思考和實踐,他的團隊成員們總能探悉到他在各個實踐中蘊含著的激情。2014年10月,一臺大型民族音樂會“風華黔韻”呈現在首都國家大劇院和國際友人面前,這也是一場非常成功的演出。其實,貴州省黔劇院民族樂團自成立以來,一直在醞釀一件事:走進首都北京,在國家大劇院上演一臺民族音樂會。說起來是一個愿望,做起來卻是一份艱辛。這一愿望融注了黔劇院所有演職員的拳拳之心,匯聚了貴州民樂人的殷殷之情。終于在2014年的金秋十月,一個偉大的行程出發了,全團演奏員帶著對藝術的熱情與感悟,在院長朱宏的率領下走進了國家大劇院這一藝術的圣殿。即將演出的消息傳出,人們都在期待:“風華黔韻”會是怎樣的一臺音樂會?當天去到劇場的觀眾,都在黔劇的魅力中找到了強烈的情感共鳴。
音樂會如同一幅純凈的國畫在觀眾眼前徐徐鋪展開來,令觀眾在感受到黔劇魅力的同時,也完成自我靈魂的某種升華。民族管弦樂《端節》用了水族斗牛的旋律,把一個個故事向觀眾娓娓道來,人與自然是生活的重現,也是生命的境界,他們在韻律與節奏中抒發著心中的情懷。板胡與樂隊《秦香蓮》融合了古典與時代元素,發揮了戲曲“詩性”的魅力,提升了對人性的思考層次,把古代婦女的反抗精神演繹得如泣如訴,催人淚下。胡琴與樂隊《珠郎娘美》,選自黔劇《秦娘美》。黔劇誕生于民間,是個“接地氣”的劇種,歷經傳承與發展,如今已榮登高雅的藝術殿堂,這首樂曲將黔劇的戲曲元素與民族音樂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更透徹、更深刻地鍥入了觀眾的審美心理,樂曲有著“梁祝”的風格,將凄美的神話傳說賦予了至情的悲劇性呼號,令人擊節嘆息!
黔劇彩唱《濤聲震得人心寒》,選自黔劇《九驛圖》,這是由黔劇和管弦樂融合而成的精彩之作,這段彩唱九轉回腸,表現了民族女英雄奢香的深沉寄寓。用民族管弦樂來表現黔劇片段,這對以演唱為主的黔劇來說是一個大膽的嘗試,是一個重大的進展,二者渾然一體,從某種程度上顛覆了固有思維。將黔劇藝術融入民族管弦樂創作,這不僅是在黔劇范圍,還面向著廣闊的音樂領域,也給戲曲和民族管弦樂提供了一個新注解,也標志著民樂結合黔劇這種形式將成為今后的一個表征,也給今后的戲曲創作提供了靈感和延伸的空間,黔劇院的藝術家們會不斷再嘗試、再創新,他們知道:唯黔劇與民族音樂不可辜負。
民族打擊樂《山鼓》,有著古夜郎的神秘,將方音、俗調別具一格的組合在一起,其音調質樸,生活氣息濃厚,作曲家不執著于曲譜,不束縛于形式,那鮮明的節奏好似貴州人民從遠古走來,邁著強有力而堅定的步伐走進小康。這些在鄉村阡陌間孕育出的曲調和故事,在遠村農舍中挖掘的腳本和韻律,已成為一種有影響的存在,留存于民族音樂的歷史。作為一種沉積的文化遺產,它被技藝高超的演奏家們雕琢得太精致了,具有永久的欣賞價值,人們通過樂曲認識了貴州,認識了多彩而美麗的貴州民族特點。民族管弦樂《水龍吟》表現了古代軍隊出征的情景,是剛與柔的交織,悲與喜的交融,是用生命在譜寫華章,作為壓軸節目,氣勢磅礴,行家們都驚呼:“太棒了!”
演出完畢,觀眾禁不住為音樂會而喝彩,紛紛暢談感受,索要節目單,演員再三謝幕,觀眾仍蜂擁臺前,遲遲不舍離去,可謂曲終人不散。天籟之音久久回旋在偉大首都,回旋在天安門廣場火樹銀花的夜空。
這臺音樂會的成功,推動了民族管弦樂的發展。人們欣喜地發現,在廣闊的原野上,民族音樂的生機不僅始終在躍動,而且出現了這樣一臺不可忽視的優秀作品,貴州省黔劇院有著海納百川的氣魄,這場演出足以構成中國民族音樂史上一個濃墨重彩的新篇章!
文化部董偉副部長說:“演出很成功,很精彩,很震撼,多聽專家意見,把曲目提煉得更精彩,一定能推出去。”
三天的演出結束了,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為這臺音樂會召開了研討會。專家們激動地說:“這樣一臺清新質樸、扎根于民間沃土中,沒有污染的音樂會,北京的舞臺久違了。你們向戲曲學習,以簡示繁,做到了‘我們的文藝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反映的是正能量,很接地氣。”“這支隊伍充滿希望,非常寶貴,這是人民的音樂會,是天籟之音。”“黔劇好比西方的歌劇,必須立足于地域,加強史詩性和創作性,加強貴州特色,走地方特色道路。”
這臺晚會看似平常,但它卻有著驚心動魄的力量,貴州只是開了一道門縫,卻沖出一股強大的新鮮氣流,這股氣流足以讓觀眾沉醉,更深深打動了專家們,觸動了他們一顆熱愛民樂的心。這股原汁原味的清新之風,瞬間吹散了籠罩在北京上空的霧霾。專家們說:“我們呼吸到一股新鮮的氧氣,渴望再次呼吸到這股氧氣,不離不棄。”專家們如此欣喜,如此激動,甚至紛紛表示愿自費赴貴州,為民族音樂做點貢獻。此舉令貴州黔劇院的同仁們極為感動!
貴州民族管弦樂學會名譽會長鄧健先生說:“貴州有著更真實、更美好的土地,期待專家們來辛勤耕耘,專家的指導是我們前進的動力。樂團要成為擁有強大生命力的隊伍,就必須打造出自己的品牌,這個品牌要涵蓋作品創作、團隊打造,包括市場攻略,但其立根之本一定是作品。我們要腳踏實地打磨出史詩性與藝術性相結合的精品來,力爭將它打造成貴州的一道風景,一張文化名片。”
回頭望去,貴州黔劇院的院長朱宏,因有著黔劇意識而使樂團有幸正在走著這樣一條道路,朱宏深深領悟到:只有在層巒疊嶂中,才有巍峨的山峰。大俗即大雅,我們既要陽春白雪又要下里巴人。朱宏率領著全院領導班子為貴州黔劇人圓了一個夢,他們為黔劇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