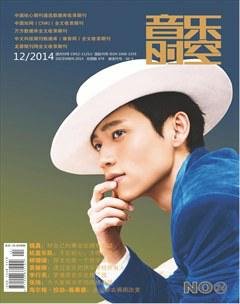今日大師
羅莎琳·杜蕾克
美國杰出的鍵盤大師、巴赫的演繹專家羅莎琳·杜蕾克,1914年12月14日出生于芝加哥。
杜蕾克早年就開始學習鋼琴,1928年師從恰普索,十四歲已經能背譜以各種調性彈奏巴赫二部創意曲,1931年進入紐約茱麗亞音樂院跟隨奧麗嘉·薩瑪羅美學習。她帶了巴赫《十二平均律》中十六首前奏曲與賦格參加入學甄試。獲準進入音樂院后,她在第一堂課就要求薩瑪羅美教她剩下的三十二首。在茱麗亞音樂院的第一年結束,杜蕾克已經能自如地演奏全部四十八首前奏曲與賦格。進入茱麗亞音樂院前,杜蕾克在她的出生地芝加哥跟隨索菲亞·布里恩-列文(安東·魯賓斯坦的學生)及恰普索學習。
恰普索是研究巴赫相當有心得的學者,他在杜蕾克的第一堂課上指定彈奏《十二平均律》第一輯的C大調前奏曲與賦格。兩天后的第二堂課里,杜蕾克憑著記憶演奏這首曲子;而在接下來的每一堂課上,她都為恰普索演奏一首新的前奏曲與賦格直到第十六首。
按照杜蕾克的說法,在她每周固定鉆入《平均律》的世界里,她就會失了神一般瘋狂的研究,“但是我知道當我清醒時,我已經透視巴赫作品的結構。巴赫的音樂心理學、他形式上的感受,都帶有一套不同于當時作品的全新觀念,而當巴赫寫作曲子時,這套觀念就由音樂的源頭與結構當中產生出來。”
在茱麗亞兩年,她的曲目增加了《哥德堡變奏曲》;1935年首度在卡內基音樂廳登臺,并獲得青年藝術獎。1936年與奧曼第一費城管弦樂團合作演出勃拉姆斯第二號鋼琴協奏曲,一年后,也就是1937年秋天,年僅二十二歲的杜蕾克已經可以演奏《十二平均律》全集、《哥德堡變奏曲》、《英國組曲》、《法國組曲》、《組曲》、《意大利協奏曲》與巴赫其他五花八門的作品。
杜蕾克六度為《哥德堡變奏曲》留下商業錄音,錄音年代橫跨四十八年,最近的一次是1997年秋天在德國完成的。其中有五次她是以鋼琴演奏,一次使用大鍵琴。1973年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里,杜蕾克第一次在大鍵琴上演奏《哥德堡變奏曲》而且得到空前的成功,休息時間過后,她又在鋼琴上重復彈奏這部作品。不過由于鋼琴豐富的色彩以及對位平穩明晰的聲音,杜蕾克還是以鋼琴演奏的版本最著名,而且是鍵盤演奏更上重要的里程碑。對杜蕾克來說,真理并不是那么容易探求或改變,思想的連貫已經是她成功演奏事業上的注冊商標。她曾經說過:“我身為演奏家的目標不止是彈得優美動聽而且得到肯定這么簡單,我希望能把自己的感受傳達給其他聽到生命中一點新感覺的人。甚至所有聽眾中有一個人產生了一點點新的感受,那就值得了。”
然而巴赫的鋼琴作品不是只有簡單的美感或風格合宜與否的問題。如同杜蕾克所指出,“《哥德堡變奏曲》在整個十九世紀都被認為無法在鋼琴上演奏,因為音樂里有太多復音以及(演奏者)型體上的問題,因為富時認為雙手在鍵盤上是不可能交叉演奏的,布梭尼因而重新修訂這部作品。用布梭尼的話來解釋他的意圖是最好的:‘為了挽救這部極為優秀的作品在音樂廳里的命運,縮短全曲或重新釋義好讓聽眾能夠接受、演奏者能夠彈奏是相當必要的。在這個版本里,樂曲后半部的建議是盡量一開始就忽略反復記號。附帶說明,經過考慮后,我認為省去其中幾段變段是最適合對一般大眾演出的方法。所以布梭尼建議在音樂會中省略十段變奏,其中有七段是卡農,由此打破全曲的架構與卡農的旨趣。他也建議使用一些簡化、添加與擴展后的技巧,布梭尼都是遵循巴赫的版本變更,然而不幸的是,有時候布梭尼會往沒有指示的地方讓譜上的主題合并,這是布梭尼,不是巴赫。布梭尼的觀點廣為后代所采用與宣傳,這是巴赫作品失真的背景原由之一,反對這種作法的音樂家都努力地想以更明確的想法接近巴赫。”
1960年杜蕾克的《巴赫演奏法概述》出版問世,成為此領域的經典書籍。并且在處理以鋼琴或大鍵琴來演奏巴赫作品的問題上,杜蕾克這樣駁斥那些大力主張巴赫還不知道有鋼琴這個樂器存在的人。“巴赫是否知道鋼琴存在的根本問題,”她這樣寫,“很明顯已經有西爾伯曼鋼琴公司販賣鋼琴給布蘭茨基伯爵的收據這個歷史文獻提供答案。這份歷史文件的內容有經說明是巴赫真跡的簽名,日期是1749年5月,萊比錫,表示這樁買賣是由巴赫辦理。”
這位巴赫音樂的最高女祭司,七十多年以來致力于巴赫音樂研究。連向來獨斷獨行的古爾德也在訪談中承認杜蕾克對他在巴赫音樂的演奏與詮釋上有相當的影響,而且他發現杜蕾克在巴赫音樂上早已做過與他相同的嘗試了。在一段時間里,很多人都曾問過古爾德:“你最欣賞誰演奏的巴赫?”每一次古爾德的回答總是:“女鋼琴家杜蕾克”,可見杜蕾克被稱之為“巴赫音樂之神”,被著名樂評家哈羅德·勛伯格譽為“巴赫音樂的最高女祭司”絕非頭有虛名。
杜蕾克居于英國牛津。“它(指音樂)已經完全被我征服。”她會這樣毫不客氣的告訴你。“謙遜”不在杜蕾克的字典里,而她也沒有必要認識這兩個字。杜蕾克是個女人,也是個藝術家,她知道自己好在那里,她的自知、學識與自信就像一件閃亮耀眼而且合身的盔甲,這件盔甲會替她的所做所為提供最好的解釋。
廣博的學識與對歷史的興趣是杜蕾克演奏及思考音樂的最佳后盾。她為自己的藝術增添獨特的個人品味,豐富了本世紀的音樂表現。和大部份長于彈奏巴洛克音樂,特別是巴赫作品的鋼琴家相比,杜蕾克的詮釋也是從個人風格以及對音樂的認知著手,進而把音樂轉換為自我的藝術。“巴赫怎么告訴我,我就怎么彈。”杜蕾克曾經這么表示,也是杜蕾克演奏巴赫的座右銘。“我從來不告訴音樂你該以什么方式呈現,我不會替音樂做任何決定,我讓音樂自己去判斷。不過,事前得非常深入的了解并熟讀樂譜。(讀譜)不能光用眼睛,得全心全意從心里、精神與肉體去感受。”
對杜蕾克而言,把心底的音樂彈奏出來的那一刻只不過是冰山的一隅。經過多年研究與思考,她把這一刻放置在“冰山的最底層”。她會告訴你,“我(對音樂)的狂熱不只在演奏。當然,演奏音樂得要有熱情,熱愛(自己)所彈奏音樂。但是對我而言,有樣東西比演奏更深刻、更重要,那就是(音樂的)概念。概念與構思是我音樂中最根本的要素。這就是為什么我經常捫心自問:‘這座冰山的頂端與底層該是什么?它們究竟是什么東西?”endprint
經過多年等待,杜蕾克于五零年代末期為EMI錄制的巴哈組曲全集終于以CD的面貌重新問世。這套專輯可為如何欣賞杜蕾克的音樂,以及她的天賦、思考音樂的方式提供最好、最詳盡的解答。在杜蕾克有力而且可以完全分離獨立的十指帶領下,音樂就像在她所創造的環境下十分自然的深呼吸。在錯綜復雜的旋律線中,你會對她奇妙觸鍵下所流泄的清澈琴音感到訝異,這種聲音有如天鵝絨般的輕巧舒適。對樂曲結構的敏銳感受再加上清晰的音色、獨一無二的轉換樂句以及表達概念的方法,這就是杜蕾克的音樂。本世紀有三位音樂家讓我們更明了巴赫鍵盤音樂的藝術以及各種不同詮釋方法的可能性,那就是藍道芙絲卡、杜蕾克與古爾德。這三位音樂家的音樂風格都很鮮明,他們的巴赫都具有迷人的吸引力與個性,但是詮釋方法卻全然不一樣:藍道芙絲卡極度浪漫,顧爾德的音樂線條古典且簡潔,杜蕾克則特別注意樂曲的結構。她用音符與樂句來“構筑”音樂,因此我們彷佛可以從她的音樂里“看”到樂曲的形貌樣式,就像一個個單獨的細胞成長并結合成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再加上杜蕾克的十指觸鍵能夠完全獨立不受影響,因此她能任意把單純的樂句彈得豐富多彩,這里所選錄的六首組曲最能呈現杜蕾克的樂思與音樂概念。燦爛的樂音伴隨著無窮的節奏,音樂如同在她的指尖下跳躍。不過在第二號組曲一開始,音樂又洋溢著高貴典雅與莊重的風味。在一成不變的樂譜束縛下,杜蕾克能夠跟隨音樂的腳步,她知道音樂的魅力在于強烈的對比與情感。這是杜蕾克的使命,也是讓她得到肯定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你認為杜蕾克只會彈奏巴赫的作品,那么接下來的消息會讓你大吃一驚。杜蕾克在前幾年同意發行她從一九三九年起的音樂會實況錄音,這個消息的震撼力就像在音樂界投下一顆炸彈。這批錄音的曲目包括莫扎特鋼琴協奏曲、李斯特練習曲、勃拉姆斯變奏曲以及許多重要的現代音樂首演錄音。杜蕾克從來不聽自己的錄音,但是由于同意發行唱片,她必須重新親自檢閱審視部分收藏在紐約表演藝術圖書館里的母帶。這些母帶差不多有五十年的歷史了!杜蕾克聽后的反應為何?“坦白說,一開始我不確定自己會聽到什么。不過一個小時過后,我得老實說,我非常震驚:‘天啊!那個女孩真的能彈琴!”
杜蕾克的成就也不能單以演奏論定。她對學生的期望不亞于對自己的要求。“有人到我這兒一對一學琴時,我會從最基礎開始教起。”杜蕾克說:“但是我一開始就告訴他們,能做到以下兩點:第一,忘掉以前所學的任何東西;第二,丟掉以前對音樂所有的想法觀念時,我才會承認他是我的學生。我的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自我獨立發展。我不想,也不要制造出一堆‘小杜蕾克。不過,從跟著我學習到被我承認大約要花七年的時間。”杜蕾克開設大師班時又是持另一種不同態度。由于大師班的教學時間有限,杜蕾克的大師班授課內容以樂曲或學生的某個概念為主,然后利用這個概念讓學生能夠更深入的了解音樂。”“我所做的,就是讓他們試著從自己彈出的音樂中感受到樂曲的結構。”她說:“不管是演奏帕勒斯替納、巴赫還是莫扎特的音樂,我的中心思想始終一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