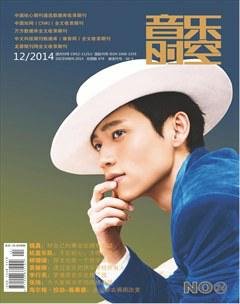蒙古族歌曲于受眾營造的文化想象
摘要:本文以蒙古族歌曲為研究對象,以蒙古族傳統文化為背景,通過對跨文化傳播方面較為成功的歌曲(即廣為流行的歌曲)的內容分析,揭示出蒙古族歌曲本身對于受眾的文化想象造成的影響。
關鍵詞:蒙古族歌曲 蒙古族文化 跨文化傳播 文化想象
“全球時代”,地區與地區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距離再一次被戲劇化地壓縮了,基于時空分離的脫域機制在此時正充分地展示和發展著其現代性。誠如吉登斯所言,全球化的總體圖式如今已被視為當然,那么,整體的過去便被認為亦是世界性的,時間和空間已經被重新組合以便構筑起關于行動和經驗的世界—歷史的真實框架。
當前,無以計數的社會組織和私人組織時刻在從事著再生產、管理、監視、恐嚇以及娛樂,有賴于技術創新和社會組織創新的共同作用,而全球化帶來的跨文化傳播現象無疑在諸多領域加劇了地區之間的競爭關系,無論認同與否,無論跨文化是原因還是結果,它都被認為是具有象征意義的巨大力量而決定著范圍廣泛的結果輸出。
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一直面臨著不同文化融合和不同價值共同體整合的問題。以改革開放為標志,在中國流行音樂的創作領域誠然發生了諸多改變,相當數量的音樂創作者基于新的社會背景與文化需要,在音樂藝術方面展開了具有一定開創性的實驗。而在這些作品之中,帶有少數民族特色和文化風格的音樂更是一抹難掩的亮色。
值得一提的是,蒙古族流行音樂以其特有的吸引力和影響力,引發了一波接一波的文化熱潮。其歌詞內容及曲調風格之中蘊含大量文化符號,給廣大聽眾以相對陌生化的感受,從而實現跨文化傳播。
一、蒙古族流行音樂文化熱現象
從德德瑪、騰格爾,到斯琴高娃,再到近年來廣為傳唱的歌曲,例如,2006年,《吉祥三寶》街頭巷尾廣為傳唱。詞曲由布仁巴雅爾創作,并與妻子侄女一同演唱。他們身著蒙古袍以一家三口,有問有答的說唱形式和樸素而有哲理的歌詞內容,讓眾多聽眾喜歡上了這首蒙古族風格的歌曲。2011年,《中國達人秀》節目中,一名蒙古族男孩演唱了一首《夢中的額吉》,感動了現場所有評委和觀眾。視頻網上播出后,大量網民被這個小男孩的動情演唱所感動,這首蒙文歌曲一時間廣泛流傳。2012年,《中國好聲音》舞臺上,來自內蒙古的云杰動情演唱《鴻雁》,再度受到眾多網民追捧,《鴻雁》這首歌也再度成為熱門歌曲。
二、跨文化傳播途徑
從傳播途徑來看,蒙古族歌曲以四類形式傳播,即文字、音頻、現場和影像,其載體分別是報刊、廣播、電視電影、舞臺和互聯網。傳播媒介的不同造成在傳播特長和傳播效果上的差異,相比之下較能全方位展示蒙古族歌曲及文化的媒體是電視和網絡。比較有前瞻意義的是蒙古族歌曲在國際傳播領域的傳播效果,而對此貢獻最大就是衛星電視和網絡電視以及民族性影片和文化交流活動中的蒙古族歌曲的劇場演出。因為其在國際上獲得的聲譽同時也會反饋到國內,從而在藝術造詣上,得到國內聽眾的認可。
因此,不能把歌曲單獨提取出來,而應該把它作為蒙古族整體文化傳播當中的一個部分加以理解,蒙古族歌曲是與蒙古族服飾,相關題材電影及旅游等諸多方面混合在一起,共同發展且相互作用,從而形成蒙古族文化的整體形象,在蒙古族文化圈以外的受眾的意識中形成文化想象。
三、蒙古族文化
內蒙古大草原富饒美麗,名副其實,是中國北方草原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一千多年前的南北朝時期便有民歌一直流傳至今,“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現牛羊”。
蒼茫草原的歷史,是由烏桓、匈奴、柔然、女貞、敕勒、鮮卑、突厥、契丹、回紇以及蒙古共同譜寫的英雄贊歌和激昂史詩,然而,經歷歷史的流轉和選擇,蒙古族以自身的勤奮與質樸、勇氣與堅毅送去歷史中的諸般過客,終成為北方廣袤草原的真正主人。
烏恩等人為代表的內蒙古社科院草原文化課題組曾將草原區域的歷史發展進程作為主線進行了長期而深入的研究。他們認為蒙古族是草原文化當之無愧的集大成者,而這一觀點基于兩個主要原因:首先,蒙古族文化確實匯聚和提煉了自匈奴而形成的、將游牧作為典型特征的草原文化的全部基本要素;其次,蒙古族文化的建構實屬草原文化思維邏輯進程的延展,是草原文化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結果。在精神文化層面,蒙古族格守并發展了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騰格里”——“天”概念為核心的宇宙觀;草原文化——以貫之的人生觀、價值觀和審美觀的濃縮——英雄主義;“崇尚自然、踐行開放、惜守信義”的基本精神。
四、蒙古族歌曲的傳播內容
(一)以不同時期流行起來的三首歌曲為例:
《蒙古人》
潔白的氈房炊煙升起/我出生在牧人家里
遼闊無邊的草原 /是哺育我成長的搖籃
養育我的這片土地 /當我身軀一樣愛惜
沐浴我的那江河水 /母親的乳汁一樣甘甜
這就是 /蒙古人/
熱愛 /故鄉的人
《烏蘭巴托之夜》
有一個地方很遠很遠/那里有風有古老的草原
驕傲的母親目光深遠/溫柔的姑娘話語纏綿
烏蘭巴托的夜/那么美/那么美
歌兒輕輕唱/風兒輕輕吹
烏蘭巴托的夜/那么美/那么美
唱歌的人不許掉眼淚
有一個地方很遠很遠/那里有一生最重的思念
草原的子民無憂無慮/大地的兒女把酒當歌
烏蘭巴托的夜/那么美/那么美
你遠在天邊/卻近在我眼前
烏蘭巴托的夜/那么美/那么美
聽歌的人不許掉眼淚
《鴻雁》
鴻雁/天空上/對對排成行
江水長/秋草黃/草原上琴聲憂傷
鴻雁/向南方/飛過蘆葦蕩endprint
天蒼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鄉
天蒼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鄉
鴻雁/北歸還/帶上我的思念
歌聲遠/琴聲長/草原上春意暖
鴻雁/向蒼天/天空有多遙遠
酒喝干/再斟滿/今夜不醉不還
酒喝干/再斟滿/今夜不醉不還
(二)曲調
就其音樂特點來說,蒙古民歌可以分為兩種形式,即長調子歌曲和短調子歌曲。“烏爾吐”節奏自由,氣息綿長,音域較為寬廣而速度較為舒緩;“烏火爾”在節奏上則非常鮮明和規整,速度頗為輕快伶俐。
蒙古民族的音樂多以不帶半音的五聲音階架構而成,五聲音階中的每個音均可以作為調式主音。其中,以羽音和徵音為主音的調式最為多見。而其曲調則是大起大伏,多運用六、七、八、九、十度的大跳;音域亦十分寬廣,一首歌曲包含十四、五度,奔騰、遼遠之感體現得淋漓盡致,豪放、浪漫的民族性格更是在歌曲中展示得一覽無余。
(三)配樂
蒙古音樂中馬頭琴自然是最常使用同時亦是最具代表性的樂器,其音色低沉悠遠,柔美動情,具有極其豐富的表現力。馬頭琴不僅用于為說唱伴奏,更常常進行獨奏以及合奏;而其最具特色之處莫過于表現馬匹的奔跑與嘶叫。除此之外還有三弦、四胡、蒙古琵琶、火不思、興隆笙、蒙古箏、笛子以及胡笳等樂器。蒙古器樂柔軟和諧、靜謐安詳。制作唱片時,加之西洋樂器進行伴奏,電子設備加以后期制作處理。
(四)節奏
節奏大約可分為兩種:其一是節奏較為清晰,常見二拍或四拍,雖然有復合拍子,其性質仍為二拍或四拍。其二是節奏并不明顯,速度較慢,許多樂曲的節拍甚至不能用小節線進行劃分。即便以一定節拍劃分,每拍的時值也難于絕對相等,與此同時,輕重拍的區分亦不明顯。故而,有學者認為蒙古族歌曲實際上是一種“曲調性強、節奏性弱”的歌曲。
(五)唱法
演唱方法上,多為真假嗓音分別使用,而由于定調高,更顯出音調的高亢、明亮、極具戲劇性變化。在演唱長音的過程中,歌者時常會加入一些裝飾性的顫音,用以構成婉轉或活潑的風格,并且多以長音之后的短小上滑音作為結束句,從而使得整個曲調顯示出柔和圓潤的特色。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名為“潮爾”的蒙古演唱方法,也就是“呼麥”唱法。此種方法的原理是:利用口腔內空氣振動聲帶以產生共鳴,同時準確地調動舌尖在上顎停留的位置,從基音中選取它所包含的不同泛音,進而在形成持續低音的基礎上,不斷發出屬于高音區的曲調。在聆聽此種方法演唱時,可清晰地聽到一人同時發出兩種不同的聲音,即屬于高音區的曲調和低音區的持續音。在此類傳統演唱技巧的基礎上,歌者結合現當代通俗歌曲演唱方法演繹作品。
(六)歌詞
對以上歌詞進行分析后發現,歌詞多使用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比喻及象征的修辭手法,意在表達蒙古族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密而深厚的情誼,而此種感情的抒發又帶有悲傷地色彩,與嘹亮婉轉的曲調一起,形成廣闊的空間感,呈現出遠離現代文明、城市文化蒙古人質樸而又自然的草原生活情境。
五、文化記憶與文化想象
窺此一斑可勾勒出通過這些信息,加之先前的文化記憶,蒙古族文化圈以外的人可能建立起如下的文化想象:
游牧:蒙古人賴以生存繁衍的環境是草原,草原蒼茫遼遠,塑造了蒙古人的精神氣質。在廣袤的大草原之上,人煙稀少,難于定居,因而游走放牧的生活方式便世代相傳。畜逐水草而動,人隨牲畜而居,四時遷徙,肉奶為食,皮毛當衣,車馬為家,這便是對蒙古族人自然生活場景的寫實素描。
飲食:特殊自然環境為蒙古族人提供了極具特色的衣食之源。蒙古族的飲食以牛羊肉類,奶制品,奶茶為主。好飲酒,食用風干肉或生肉,同時也會打獵。
運動:騎馬,射箭,摔跤——傳統的男兒三藝。
信仰:信仰或者圖騰。信奉“天和地”,“萬物有靈”的意識觀念,這是蒙古人尊重自然的比法律更具效力的動因之一。
性格:豪爽大方,自然隨意,不拘小節,喜歌善舞,易于沉醉于狂歡狀態。
參考文獻:
[1]潮魯.蒙古族長調牧歌研究[D].福州:福建師范大學,2003年.
[2]盧靜,王春.關注蒙古族音樂流行現象[J].大舞臺,2003,(03).
[3]蒙古族和蒙古族民族文化[N].重慶商報,2006-11-1.
[4]田廣金,郭素新.北方文化與草原文明[A].魏堅.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輯)[C].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
[5]蔡麗寧,盧靜.于流行中依托民歌——探討“蒙古族流行音樂文化熱現象”[J].作家,2009,(24).
[6]楊紅梅.云南歌舞文化的跨文化傳播探析[J].東南傳播,2008,(06).
[7]孫迎春.跨文化傳播學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8][英]約翰·厄里.全球復雜性[M].?李冠福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集團,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作者簡介:
[1]王書斌: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
[2]墨日根高娃: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音樂學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