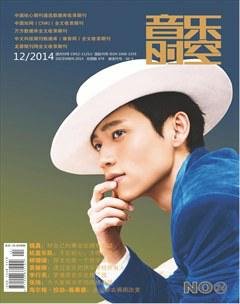從普契尼的歌劇《圖蘭朵》看音樂作品中的“異國情調”元素
王秀
普契尼是十九世紀下半葉意大利歌劇創作的杰出代表。在他的歌劇創作中延續了意大利歌劇創作優雅旋律的特質,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個性。其中異國情調的因素在普契尼的歌劇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縱觀作曲家歌劇創作我們會發現《西部女郎》、《蝴蝶夫人》、《圖蘭朵》等歌劇中除了女性角色的塑造特點外,其異國情調的因素也格外值得關注。特別是歌劇《圖蘭朵》就是這樣一部從故事主題、音樂形象及旋律均充滿異國情調的作品。
在學術界對異國情調的界定會有所不同,這里所探討的“異國情調”——即浪漫主義時期以后,認為自己居住在世界中心的西方人對其它地方國家文化的理解。讓作品充滿“異國情調”的創作方法在很早就已經被西方的作曲家運用到自己的音樂創作之中,直至十九世紀下半葉、二十世紀初的音樂舞臺上,它一直是作曲家的常用手法之一。我們發現“異國情調”因素作為歐洲對其他國家的的描述已經由來已久,倘若對“異國情調”產生和發展的過程進行考察就會發現,這種觀念隨著時代的變遷其傾向也隨之多樣化。這種傾向可能會表現為對不同于己的事物的渴望和恐懼;表現為對“他者”的重視與輕視;當然它也可能表現為一種綜合體。
普契尼對《圖蘭朵》的創作是他精心選擇與醞釀的結果。他對歌劇腳本的選擇非常嚴格,與意大利文藝界人士的交往可能對作曲家的選材與創作產生重要影響,這其中包括與歌劇《圖蘭朵》的兩位劇本作者的交往——即西莫尼(Renato Simoni)與阿達米(Giuseppe Adami)。劇作家西莫尼曾在中華民國初年被《晚間郵報》派駐北京當記者,他的中國之行必會為劇本增添不少中國因素。不但歌劇腳本的選擇嚴格,體現異國情調的音樂素材的選擇也很重要。《茉莉花》主題在歌劇中的運用就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例證。
歌劇《圖蘭朵》講述的是具有夢幻般的且又有中國故事的題材。西方國家很早就對中國開始關注,這源于其最初與歐洲繁榮的貿易往來。文學作品中的鼓吹使人們更對中國抱著奇妙的“異國情調”的想法。這些可以從當時歐洲對中國的描述上窺見一斑。比如,在當時的巴黎產生了中國娛樂劇院;十七世紀意大利等國家出現了專門以中國因素命名的喜劇演出。雖然當時作品中的中國只是一個稱謂,而且戲劇中也沒什么真正的中國喜劇技巧,但是正如當時評論說所,正是這些簡單而自然的喜劇,與幾乎獨占十七世紀舞臺的古典派悲劇的嚴肅的特點形成鮮明對比,培養了觀眾對這種變化風格的喜愛。在音樂的世界里,撥弦古鋼琴曲《中國人》可被看作最早被歐洲音樂家創作的中國風格作品,而它是由法國作曲家庫普蘭(1668-1733)創作的,雖說這首作品與中國音樂文化并無直接關聯,但這首作品的曲調輕盈飄逸,再看作曲家的其他作品,互比之下,作曲家已然是想在這首作品中呈現出“異國風格”的中國音樂特點。
在普契尼的歌劇《圖蘭朵》中,有對三位充滿怪異、荒謬表演大臣形象描述,相信對觀眾來說是記憶猶新的,其真實反映的是對中國社會制度的一種折射。作者在歌劇創作中也許無意去了解真正得中國文化甚至可以說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誤讀,但是正是因為中國元素的加入使作品格外具有“異國情調”的特點,也許是想借用中國―他們筆下的“異想天開”的形象來取悅觀眾而已。我們發現在十八世紀上半葉,西方社會在對中國因素的描述中,這種傾向性就已經顯現出來。正如法國神父于十七世紀末在中國旅游返回返國后在其著作《中國現勢志》中,對中國的描述掀起了人們對“中國工藝古玩”的迷戀熱潮一樣,這一熱潮波及至藝術界后,其表現形式就是這一時期的藝術家們常常會在自己的作品中借用中國形象,因為在當時,這對于吸引觀眾有著非常好的利用價值。然而,就算是1754年格魯克創作了芭蕾舞劇《中國女士》劇中用了中國標題,可不論是從音樂方面還是舞蹈方面來講,在當時仍然是純粹的歐洲音樂語言,而作者只不過是在作品中創造出了一個想像的異國性格來而已。
由此看來,西方早在十九世紀之前,關于對“異國情調”的描寫多停留在因為對“他者”的憧憬和好奇,亦或是期望借助對“他者”的敘述來實現自己內心的心愿。然而他們只是將一種情調附加在了自己的作品中而已,并沒有真正地了解和認識異國。
音樂學家保羅·亨利·朗格曾經評價說:“18世紀是世界的世紀;十九世紀是一個反動的時期;是哥特藝術復興的世紀;是浪漫主義的世紀;是異國美發現的世紀;是神秘的、曖昧的、哲學盛行的悲觀的世紀”。那么當歷史的車輪駛進19世紀西方浪漫主義音樂時期,作曲家以“異國音樂”作為其創作的原則,并運用于專業的音樂創作中,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浪漫主義本身就是發現不同美的價值的時期。
創作完成于二十世紀的普契尼的歌劇《圖蘭朵》,可以說是一部具有浪漫色彩的歌劇,而它同時又表現為是異國情調在音樂中的體現,而異國情調跟浪漫主義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在那個不斷發現異國美的時期,異國情調更多的是出現在作曲家的作品中。威爾第的歌劇《阿依達》的創作源于法國作曲家佛里西安·塞孔爾·達維德(1801-1876)對古老東方旅行后的作品創作。柏遼茲在其創作中也體現了異國的風格情調。歌曲《囚犯》,創作于1831年,創作者將歐洲與地中海東部接壤地區的一種節奏類型運用到伴奏聲部里,進而使整首樂曲在一種輕輕搖擺的節拍中獲得些許異國魅力。十九世紀中葉在法國巴黎舉行的幾次世界博覽會為西方人更多接觸東方音樂提供了更多窗口。德彪西在參觀完世界博覽會之后創作的作品《版畫》就是基于印度和柬埔寨的音樂。其作品中有一首名《塔》的樂曲,就模仿了一種爪哇地區特有的節奏類型“斯林多羅”。著名作曲家瑪勒的作品中對中國古代詩人詩作的理解和運用致使歐洲的音樂也久而久之帶有一種新的東方浪漫主義的曲風。如此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紀末期,愈來愈多的藝術家們紛紛將“異國情調”寫作方法運用到自己的創作之中,因此,異國情調也越來越起著突出的作用。由于創作者在異國音樂的運用中看到了新的價值:當把異國情調音樂的一些元素融入進西方音樂中以后,不僅會克服浪漫主義的一些顯著危機,并且還能夠打破德國對西方音樂的專制。endprint
普契尼在歌劇《圖蘭朵》中對中國進行的是一種不確定的描述:不確切的年代、不確切的文化背景、人物的虛構等,均體現了當在對“異己者”進行闡述的時候,“他者”的形象并不是不可更改的,而是往往是跟隨雙方力量的對比不斷地變化。“中國”這個相對于西方國家來說的“異國”,在發展史上就歷經了一個從神秘莫測的令人向往的地方直至罪惡淵藪的改變。
從羅馬時期西方與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開始接觸,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給西方人留下了充滿幻想的繁榮景象。后來歐洲的旅行家們,像馬可·波羅等人在中國前所未有的富麗堂皇面前,都是頂禮膜拜。十六世紀時中國精美的瓷器在歐洲的盛行一直延續著西方人對中國富饒、文雅的美好的想象。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更是把博大精深的文化達到西方人的想象的高峰。這種對美的贊譽,更多是因為好奇、不了解只是對異國情調之美感興趣而已。在后來的文獻著作中對中國的描述發生了變化,這是基于對商業、政治目的的考慮,中國越來越由美而轉為被“妖魔化”。
孟德斯鳩在他的書籍《法的精神》里面,對中國進行了很多的探究和思考,從中總結出一個結論——即塔認為中國不存在所謂民主而且充斥著專制的政權。雖然伏爾泰有許多對中國進行正面描述的作品——其《世界史》便是從中國開始的,但同時他并不承認中國有發展的可能。在18世紀,在歐洲的美學領域中,有很多新的名詞都和“中國風”(Chinoserie)有關。而實際上這個詞已帶些貶義的意味,因為這正說明中國的文化已是由自身淪落為成了某種玩物,變成了一種有點被理想化了、具有裝飾性的東西。來自意大利的傳教士利瑪竇在他的著作《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如此講述當時的中國音樂——單一、沒有更多創作技巧,雖然這樣的判斷有失偏頗,但利瑪竇的著作在當時的歐洲確實流傳廣泛,甚至于只有這些書才是西方國家獲取對他國文化的認識和了解為數不多的方法之一。
以此可以看得出,西方國家對他國的關注尤其是對中國這個有著悠久歷史國家的關注,歷經一個令人憧憬的充滿著神奇色彩的神秘之地,以至于再到后來對一個“原始的、野蠻的”地方描述的轉變。這種轉變已經給后人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圖蘭朵》的創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旅美學者王申培提出:“《杜蘭朵公主》整段歌劇的旋律以《茉莉花》的旋律為經,以中國民間故事為緯,在此的結構上建立起來的”。這大概是大多數人特別是中國人對這一曲目熟悉并接受的重要原因。1998年北京太廟的張藝謀版本的《圖蘭朵》演出被贊為:圖蘭朵公主回家了;魏明倫對圖蘭朵故事的改編更是充滿了國人對圖蘭朵公主美好的期待。追溯《圖蘭朵》的發展軌跡,我們會看到,幾個世紀以來,這個虛構的“中國公主圖蘭朵”一直是藝術家和文學家所關注的對象。
圖蘭朵故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紀。而最早將這個故事翻譯并傳播到歐洲的是精通波斯語的法國學者彼狄斯·迪·拉·克羅依克斯。其中,猜謎招親的情節與圖蘭朵故事情節相似。圖蘭朵——即Turandot ,這個詞是由Turan 和Dot結合而成的,Turan——指土耳其斯坦這個國家,而這個國家建國國王的名字正是詞根Tur;Dot 則為“女兒”之意。中國公主的形象出現在當時的文藝作品中絕非偶然,這實際上是流行于西方國家的“中國熱”在文藝舞臺上的一種呈現,而在十八世紀,意大利劇作家戈齊(Gozzie)最先將圖蘭朵公主這一故事搬上了戲劇舞臺。此后,經過戈齊改編創作后的關于異國公主圖蘭朵的故事便成為日后音樂舞臺和戲劇舞臺上諸多藝術家創作參照的藍本。
十八世紀意大利作曲家戈齊創作的第四部作品就是《圖蘭朵》,這部作品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創作財富。隨后,《圖蘭朵》經過作曲家席勒整編成為一部經久不衰的代表作品。席勒在作品中將三個謎底設為日歷、眼睛和犁頭,呈現出更多的中國文化、禮儀的特征,而使作品具有不同于一般的“異國風味”。
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同時也是音樂家的盧梭編著的《音樂辭典》中收入引用了古希臘、中國和波斯的音樂。其中引用的一首中國作品,據考證便是我國的民間音樂《萬年歡》。1806年,韋伯在盧梭的書中發現了這條旋律,并在1809年將此旋律運用到席勒翻譯改編的意大利劇作家戈齊的《圖蘭朵》的配樂中,因為這條旋律,整首作品的曲調才能如此別具一格。十九世紀,又有許多音樂家以席勒的改編版本為題進行創作。其中有萊西格(Carl Gottlieb Reissiger1853年)、丹齊(Franz Danzi)在1817年的創作、巴齊爾Antonio Bazzini)、何芬(J.Hoven)、雷包姆(Theobald Rehbaum)、巴西尼(Bassini)(他曾是作曲家賈科莫·普契尼的老師)、拉赫那(Lachner)、韋伯(Weber)等的音樂作品問世。這些藝術家 在創作之時都會對原劇作進行改編,才可以根據劇情的變化而變化。現如今,我們可以發現雖然這些作曲家在當時均為默默無聞之士,但也因為這些默默無聞知識的創作才使中國公主圖蘭朵的故事在歐洲舞臺上延續下去。正是這些作曲家的創作延續了異國強調在圖蘭朵作品中再現的可能。
在歌劇《圖蘭朵》中,中國是被普契尼想像和杜撰出的中國。而正是因為歌劇《圖蘭朵》所產生的歷史環境,以及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國所描述時態度的改變才使得這樣一部關于中國的歌劇成為了一部經典的作品。當我們審視相互文化交流間的關系時,更應該以一種互動的、雙向的思維方法去思考,通過這種交流過程,去探索新的想像與創造,去追尋新的文化。
音樂家們對異國因素的運用只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或者是離奇的需要或者是為了豐富音樂的色彩和魅力等等,其實質并沒有把異國的和自己國家的音樂放在同等地位上來。無疑有“歐洲中心論”的陰影。如今,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日益頻繁,文化的融合與多元是我們更清楚的意識到,在文化交流中如何保持自己并確認自己文化身份的重要性,這將是當今多元文化交流的主題!
參考文獻:
[1]蔣一民.音樂美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德]利齊溫.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M].朱杰勤譯.北京:商務印刷館,1991.
[3][美]保羅·亨利·朗格.19世紀西方音樂文化史[M].張洪島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2.
[4]史景遷.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5]樂戴云.跨文化之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6]顧彬.關于“異”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