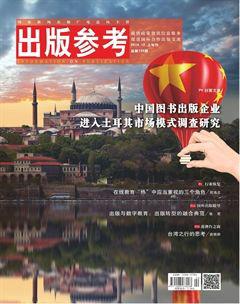在線教育“熱”中應當重視的三個角色
周海忠
當下,在線教育是教育界關注的熱點,也是互聯網企業和技術公司關注的熱點,風險投資機構也在緊鑼密鼓考察與在線教育相關的項目。而許多習慣于傳統教材教輔出版的出版機構似乎還在以旁觀者的角色猶豫,覺得在線教育屬于“教育”,不是“出版”。一大批靠教育剛需吃飯的出版社只有少數果斷介入,試水探新。以微課開發為例,許多出版人幾乎對觸手可及的碎片化教育資源(其實也就是出版資源)毫不動心,倒是網絡巨頭與培訓機構已經展開身手,開發的“教育產品”紛紛上線,甚至借此上市。
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我們要關注“在線”,更要重視以下三個角色“在場”。
一、出版人
互聯網模糊了行業界限,“教育產品”和“出版產品”之間的交集太多,差別幾乎就在于誰在做。把視頻作品看成出版物,不會有任何爭議,就傳播方式與盈利模式的問題而言,在線教育更像甚至更是數字出版。當網絡傳播的作品恰恰是教育的內容甚至就是課堂教育的內容,傳播的過程就成了教育實施的過程。而消費者是不會在意是消費了“教育產品”還是“出版產品”。當教育機構出場成為主角,或者互聯網企業涉足教育,他們可以從“教育產品”的角度宣傳、營銷。但是不要忘記,教育,恰恰是出版活動最主要的功能之一,網絡省卻了大量復制的時間,但保留了復制與傳播的功能,只是更為保真與迅捷。這正是數字化的優越之處。認識不到這一點,我們還搞什么數字出版呢?出版轉型又會有什么前景可言呢?
有位資深出版人在給新編輯做策劃講座時坦言:“后評議教輔時代”以在線教育為代表的數字化教育出版恐怕是離我們最近的金礦。在數字時代、移動學習時代、碎片時代,在線教育中出版人不能缺位,必須進場、在場。
二、管理者
以教育視頻作品為主的網站既然傳播的是“教育產品”,就不能完全交給市場來決定枯榮生滅。離開了把關,不加選擇,這類產品的質量問題無法控制。稍加留意,我們就能發現已經發布的視頻中僅是字幕上的錯訛就已司空見慣,細究內容、編排上的科學性合理性,結果也是可以料想的。當然,經營者為提高市場競爭力有努力改善的本能,但限于專業水平及其他主客觀條件,難以做到符合出版要求達到發表水準的地步。而教材、教輔,即使在較為嚴苛的編校質量保證體系下,尚有不合格產品成為漏網之魚,面世之后還需靠抽檢等措施加以彌補,視頻類的教育產品缺乏行業規范與標準、缺乏監管,又如何能成為放心產品、精神與知識的安全食糧呢?這需要引起教育界和出版界高度重視。
在線教育的網站,本質上經營的正是典型的數字出版活動,需要納入出版管理的范疇,但目前絕大多數只是申請報批了ICP的資質,這實際上忽略了“互聯網出版專有權”,似有“無照駕駛”之嫌(當然,已經取得互聯網出版專有權的出版機構無所作為,“有證無車”甚至“有車不開”也需引導)。職能部門應當加強監管,出版管理者不能缺位,必須進場、在場。
三、傳播服務者
相比上面兩者的“在場”,這個角色的在場事關如何進一步做好在線教育服務,遵循教育規律、回歸教育本質的問題。
理論上,教育可以是多種形式的。即便沒有教師在場,學生仍然可以自學自悟習得。但畢竟不同的學生基礎不同,不同的地域學情有別,無論從因材施教的角度還是情景教學的角度,加進了教師的在場因素,教學的質量與效果可能要好得多。一些在線教育的先行者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們或是設置了學習群,用合作學習的理念架構了學生在場的情境;或是安排教師線上答疑解惑以點帶面解決一些共性的問題。事實證明這樣的安排是受歡迎的。
視頻課程開啟了新的學習方式,可以移動學習、隨時隨地學習,正因為便利了學習者分享優質的教學資源,才會有巨大的市場空間。傳播服務者的概念,從數字出版的角度而言,其主體應該是懂教育的網絡編輯,相當于選課的參謀、觀影的引座員,也是教學資源(出版資源)的配置人。這包括為消費者提供個性化服務。技術再先進、標簽再完備、搜索定位功能再強大,在眼花繚亂的視頻資源面前消費者難免無所適從。有了這個角色的在場,在線教育才能真正有效組織與實時反饋評價,這有利于提高教學效果與出版效益。
(作者單位系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