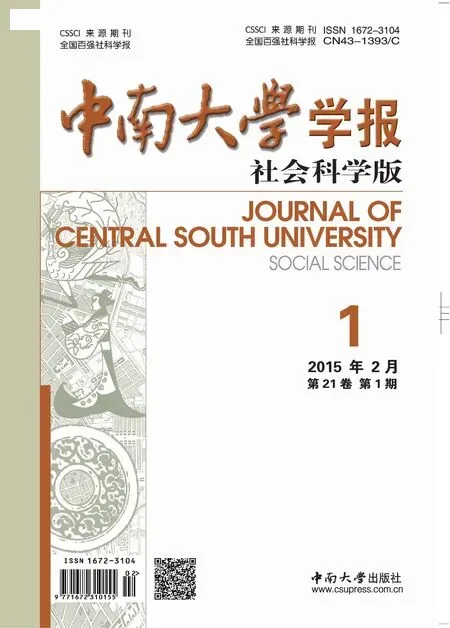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關系模式及其反思
袁彬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北京,100875)
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關系模式及其反思
袁彬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北京,100875)
刑法與相關部門法關系的一元化立場認為,刑法具有從屬的、補充的性質,是民法、行政法等相關部門法的保障法。但法律的邏輯起點與價值追求差異、二元化的刑事違法性、刑法側重事實關系保護的特點和刑罰輕緩化趨勢,決定了刑法作為保障法的一元化模式不能適應現代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發展,容易造成刑法對民法、行政法等部門法領域的侵犯。刑法與相關實體部門法之間應當堅持相對的一元化關系模式。只有在法益和行為重合的范圍內,民法、行政法規范才能上升為刑法規范。
刑法;相關部門法;從屬性;獨立性;關系模式
一、問題的提出
現代國家的法律部門繁多。但以訴訟程序為參照,實體部門法規范基本上可以被分為三大類型,即刑法(對應刑事訴訟程序)、民法(對應民事訴訟程序)和行政法(對應行政訴訟程序)。因此,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關系在實體法上主要體現為刑法與民法、行政法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刑法與民法、行政法等相關實體部門法的關系,是我國現代刑法實踐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一方面,“從1979年刑法典頒布至今,我國刑事立法已在犯罪化的道路上行進了三十余年”[1],刑法立法的擴張導致大量民事、行政違法行為入罪,這在不斷擠壓民法、行政法空間的同時也模糊了刑法與民法、行政法的界限;另一方面,隨著刑法與民法、行政法等相關部門法規范體系的日益完備,各部門法逐漸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目的與話語體系,部門法的各自繁盛也帶來了不同法規范之間的沖突,并體現在近年來發生的如四川帥英保險詐騙案、廣東許霆盜竊案、浙江吳英集資詐騙案等典型刑民沖突案件的法律適用上。
德國著名刑法學家羅克辛教授認為,刑法是“社會政策的最后手段”,只有在其他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不起作用的情況下,才能允許被使用。[2](23)按照刑法的這一原理,刑法只有依附于行政法、民法等其他部門法并作為其他部門法的補充才可能存在[3],民事違法、行政違法是刑事違法的前提。但著名法律學家伯爾曼認為,法律不是一個簡單的規則體,它“只有在制度、程序、價值和思想方式的具體關系中才具有意義”[4](13)。“禁止盜竊”規則在民法、行政法與刑法上的意義可能大不相同,其民法意義主要是“恢復原狀”“賠償損失”,但其刑法和行政法的意義則主要是剝奪金錢與自由。不同的制度、價值和思維方式決定著規則的不同內涵與關系。傳統的“刑法保障法”立場,無法解釋為何有些民法、行政法規范(如契約違反、無責任能力者的看護)不能上升為刑法規范。因此,我們有必要將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關系置于多元的利益主體和價值格局中,以尋找更有效的解釋路徑,為刑法“規范效力的合法性”提供更合理的“解釋證明”。[5](150)
二、刑法與相關部門法關系的一元化模式
(一) 刑法與相關部門法關系的一元化模式內涵
刑法與相關部門法關系的一元化立場認為,刑法具有從屬的、補充的、二次的、副次的、制裁的性質。刑法是以違法行為中的重大者為目標,如果完全可以用其他較輕微的法律來制裁的場合,就不允許科以刑罰。[6](2)只有當一般部門法不能充分保護某種法益時,才由刑法保護;只有當一般部門法還不足以抑止某種危害行為時,才由刑法禁止。[7](30)據此,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關系模式是一元化的,即刑法是其他部門法的補充法、保障法。其依據是刑罰的嚴厲性和殘酷性。“刑法是以刑罰這種殘酷的制裁作為手段的,不能輕易使用,只有在使用其他法律不足以對法益進行保護的場合,才將該侵害法益的行為作為犯罪進行處罰,由此而徹底實現對社會秩序的維護。”[8](4)
(二) 刑法與相關部門法關系的一元化模式體現
“法律將各種法律體系融為一體,每一種體系中的各種成分要素,其含義都部分地來源于整個體系。”[4](13?14)它“并不樂于提倡與之相悖的行為,即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受同樣的目標和政策的約束”[9](217)。刑法和其他部門法雖然基于自身的體系而具有各自獨立的目的和政策,但在法的整體性上,它們是一致的,有著一起維護法的整體秩序的共同義務。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一元化模式認為,刑法和其他部門法必須服從于法的整體秩序。“國家對刑法的期望,就是制止犯罪的機能和通過它而實現的維持秩序的機能。”[10](44)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門法則是通過對民事違法、行政違法等行為的制止來恢復法秩序。在傳統的一元化關系模式中,刑法與民法、行政法對法秩序的維護關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刑法對民法的絕對補充。刑法與相關部門法關系的一元化模式認為,刑法和民法相互獨立而又相互補充,民事責任體現的是對受害個體利益的彌補,刑事責任體現的則是對一般個體利益的保護,它們是一個問題的兩個不同方面,共同構成了對法秩序的整體維護。以不法行為造成他人的損害為例,民事賠償責任體現的是對被害人受損害利益的賠償,而刑事責任體現的是防止其他人免受不法行為侵害的抑制,民事賠償責任不能取代刑事責任。“如果以行為人是否進行民事賠償作為衡量行為人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那么法律警戒和抑制的內容就被置換成對民事責任的不承擔行為,如此,則使法律的警戒和抑制方向發生嚴重的錯位和偏離,而且會導致刑事責任承擔的不平等。”[11]但在違法性上,刑事犯罪必須以民事違法為前提,只有不法行為對被害人利益的侵害上升到了需要運用刑法進行懲戒以防止其他人再受不法行為的侵害時,刑法才能介入。在任何情況下,民事合法行為都不能上升為刑事犯罪,否則將導致法秩序保護的沖突。
第二,刑法對行政法的相對補充。刑法與行政法所針對的都是涉及一般公眾利益的不法行為。刑法對行政法的補充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對應的行政刑法領域,行政法既是法秩序的建立者,也是法秩序維護的優先選擇,只有行政法基于自身手段的限制對部分違法行為制止無效或者效力不足時,才需要刑法的介入。刑法是行政法的補充法和保障法,不到萬不得已,沒有必要動用刑罰手段。二是在對應的自然犯輕罪領域,行政法是不法行為治理的優先選擇,刑法則是行政法的補充。例如,對傷害、侮辱、誹謗等行為,只有行政法因其制裁手段的有限性而不足以制裁該類行為時,才能動用刑法。但在對應的自然犯重罪領域,刑法是法秩序維護的優先選擇,行政法是刑法的補充。行政權的特點決定了行政處罰的力度不能過大,它只能適用于危害性不大的侵犯公共利益的行為。對于故意殺人、搶劫、強奸、綁架、拐賣兒童等嚴重危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刑法是當然的首選,而行政法則只是補充的地位。從這個角度看,刑法對行政法的補充是相對的。
(三) 刑法與相關部門法關系的一元化模式實現
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一元化關系要求刑法與相關部門法在法律概念、行為模式和法律制裁等方面保持一致。
第一,法律概念的銜接。法律概念包括常用概念、常用的但在法律中有其專門含義的概念、專門法律概念和技術性概念。[12]刑法中的法律概念很多,其中不少概念,如“集資”“惡意透支”“金融憑證”“有價證券”,都與民法、行政法等相關部門法的概念相同或者類似,表明了兩者在規范上的競合。[13]但也有許多刑法概念,如“結婚”“占有”“信用卡”,與民法、行政法等相關部門法上的概念明顯不同。法律概念的差異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銜接。一元化關系模式要求加強刑法與相關部門法在概念上的銜接。
第二,行為模式的協調。這主要體現在空白罪狀和不純正的不作為犯、過失犯等典型的開放性犯罪構成場合。其中,刑法上的空白罪狀需要借助其他法律規范來明確犯罪的行為要件,其標志是罪狀表述上存在“違反某特定法律法規”。由于所參照援引的非刑事法律規范對犯罪構成起著補充說明的作用,空白罪狀具有明顯的補充規范性質,是對民法、行政法等相關部門法的補充。[14](11)而不作為犯、過失犯以行為人的作為義務和認識義務為前提,民法、行政法等相關部門法規定的義務是不作為犯、過失犯等開放性犯罪構成的主要義務來源。如不作為犯之作為義務的主要來源是“法律明文規定的義務”,包括憲法、法律(狹義的)、行政法規、條例、規章等。[15](67)可以說,刑法上不作為犯、過失犯等犯罪類型的存在,就是為強制人們履行其應盡的義務,體現了明顯的補充法色彩,也是刑法與民法、行政法等相關部門法的銜接手段,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一元化關系模式要求加強它們之間的銜接。
第三,法律制裁的平衡。刑事制裁與民事、行政制裁共同構成了一國法秩序的保障體系。基于刑法的補充法立場,行政制裁的強度不能大于刑事制裁。但目前兩者倒置的現象在我國并不鮮見。例如,我國行政處罰上的吊銷許可證在處罰力度上可能要嚴于刑事制裁中的罰金、管制等刑罰,同時作為行政處罰的收容教育要重于作為刑事制裁手段的拘役、短期徒刑。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國刑法上的附加刑種類嚴重不足,導致不同類型的刑事處罰與行政處罰的嚴厲性倒掛;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國對行政權的限制不足,過去長期存在的勞動教養、收容教育就因其處罰嚴厲卻又缺乏必要的司法審查程序限制,導致刑事處罰與行政處罰的倒掛。合理的做法是增設相應的附加刑種類,同時改造收容教育等行政處罰制度。
三、刑法與相關部門法關系的一元化模式反思
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一元化模式對限制國家刑罰權的濫用、最大化地保障公民的自由,發揮了極其重要的歷史和現實作用。但隨著社會的變遷,現代法律的觀念、功能和結構正在分化,逐漸形成了各自獨立的思維范式,并在法律思維的邏輯起點、實質違法觀和法的價值等方面自成體系。刑法與相關部門法關系的一元化模式正面臨著新的矛盾和沖突。
(一) 一元化模式不符合不同部門法的不同邏輯起點要求
邏輯起點是思維的出發點和支點。法律思維的不同邏輯起點導致了不同的法學流派,自然法學以價值為邏輯起點,規范法學以規范為邏輯起點,社會法學以社會事實為邏輯起點。[16]與法學流派不同,現代法律都是建立在事實之上,行為被認為是法律當然的、事實的邏輯起點。
但不同法律對行為這一邏輯起點的側重并不相同。“民事責任之基本,全在客觀之實害,刑事責任之基本,則全在主觀之惡性;故依社會進化趨勢,以后民事責任當愈為客觀化,刑事責任當愈為主觀
化。”[17](2)這種認識雖然未免過于絕對,但也的確指出了不同法律之間的邏輯起點差異。例如,我國刑法不承認嚴格責任,刑事責任的有無及程度與行為人主觀過錯的有無及程度密切相關;我國民法承認公平責任,在無過錯的場合,行為人也要根據公平原則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我國行政法上的強制措施重視行為的危險性,“包含著預防、制止危害行為或事件的發生或蔓延的因素”[18](189)。這導致了刑法與民法、行政法的不同:刑法強調行為的主觀責任,無罪過則無刑事責任;民法注重行為的客觀實害,無實害即無民事責任;而行政法則側重行為的危險性,行政手段的種類和強度取決于行為危險性的大小。因此,刑法與民法、行政法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互為前提關系。正如依法成立的合同給相對人造成的損害再大,也不能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因為他簽訂、履行合同時主觀上沒有罪過;實施犯罪預備行為的人主觀惡性再深,也不能追究其民事責任,因為他沒有造成客觀實害。這對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一元化關系模式提出了挑戰。
(二) 一元化模式不適應刑事違法性的二元化要求
英美刑法理論認為,犯罪行為有本質惡與禁止惡之分,前者是指某種行為就其自身性質而言是不法的,后者則指違反制定法的作為與不作為。[19](58)德日刑事違法性理論則逐漸由一元的規范違反說、法益侵害說走向了折中的二元論,認為刑法的實質違法性既是對國家、社會倫理規范的侵犯,也是對法益的侵害或威脅。[20](116)犯罪有自然犯與法定犯之分。從形式上看,自然犯和法定犯都可看成是對規范的違反或者法益的侵害。但進一步地看,自然犯與法定犯的實質違法性并不相同。
自然犯屬于“本質惡”的犯罪,無論是否有制定法的規定,它在倫理道德上都是不法的,而法定犯的違法性源于制定法的特別規定,它“侵害或者威脅法益但沒有明顯違反倫理道德”[7](116)。沒有實定法的設定就不會有法定犯。這如同沒有稅法關于納稅的規定,就不會有刑法上的逃稅罪;沒有金融法關于信用卡的規定,就不會有刑法上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法定犯的刑事違法是以民事、行政違法為前提,但自然犯的刑事違法性則源于它對作為自然法的倫理道德的違反。
自然犯的行為雖然也可同時構成民事、行政違法,但這只是從不同的角度對同一違反倫理道德行為的法律規制,民法、行政法乃至憲法等制定法是否將這些行為設定為違法并不影響自然犯的刑事違法性。正因為如此,殺人、搶劫、強奸等嚴重違反社會倫理的行為可不經由行政法的調整直接上升為刑法上的犯罪。刑法、民法、行政法對這些違法行為的規制之間并不存在嚴格的先后關系。法的違法性判斷“應當以各個法領域所固有的目的、政策考慮為基礎,針對各個不同法領域,分別進行”[21](130)。要求刑事違法必須以民事、行政違法為前提的一元化關系模式不符合刑事違法性的二元化要求。
(三) 一元化模式不符合不同部門法的價值追求
公法與私法的分立是學理的創造。古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認為,“公法是有關羅馬國家穩定的法,私法是涉及個人利益的法”[22](33)。現代西方法學家認為,公法主要是調整國家與個人之間關系的法律,私法主要是調整個人之間關系的法律。[23](403)公法與私法對利益的保護差異決定了刑法與民法不同的價值追求:民法強調意思自治、契約自由,注重個人私益的保護;而刑法強調秩序與人權,注重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刑法要達到的效果是對規范同一性的保障、對憲法和社會的保障。”[24](101)這要求立法者既要確保私人契約權利和意思自治神圣不可侵犯,又要有效防止自利行為的失控。[25]這難免會產生沖突或失衡。
按照《合同法》第52條的規定,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訂立的合同經受損方補正后仍然有效。從內涵上看,這里的“欺詐”“脅迫”包括了我國刑法上的詐騙、搶劫、強迫交易等犯罪手段。在受損害方不請求變更或者撤銷的情況下,行為人以這些不法手段訂立的合同在《合同法》上是合法、有效的。“如果當事人自愿接受該合同的拘束,愿意履行合同,或者用不使合同無效的其他方式補救,如果立法使其無效,那么可能違背了當事人意愿,消滅了一些不應當消滅的交易,不利于保護善意第三人”,而且“由受欺詐、脅迫人根據其自身利益的考慮決定是否撤銷更有利于其利益的充分保護”,[26]因而允許受損害方事后追認合同的有效性。但被害人事后的寬恕與追認并不能改變行為人既成的犯罪事實。[18](127)刑法對秩序的追求決定了它必須禁止詐騙、暴力、強迫等有損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民法與刑法的價值差異導致了同一行為的不同法律性質。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一元化關系模式顯然無法解決這種沖突。
(四) 一元化模式不符合刑法重事實關系保護的特點
按照一元化關系模式,刑法是其他部門法的保護法。如果把其他部門法比作“第一道防線”,刑法則是“第二道防線”,沒有刑法作后盾、作保證,其他部門法往往難以得到徹底貫徹實施。[15](8)按照這種思維,刑法對社會關系或者法益的保護應以民法、行政法等部門法的確認為前提。但現實的情況卻是“民法上的承認不是刑法保護的前提。不具有民事合法性的事實利益,也是財產犯罪的保護法益”[27]。刑法注重的是對事實關系的保護,該關系是否在其他部門法上受保護,不是刑法保護的前提。財產關系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
刑法上的盜竊、詐騙等財產犯罪的成立并不以他人對財物的占有符合民法或者行政法為前提。盜竊違禁品、他人非法占有的財物(如搶劫、盜竊、賭博所得)、警察非法扣押的財物等民法、行政法上不予保護的財物都可構成盜竊罪。此種情況下,盜竊所侵害的依然是財物占有關系,但這種占有關系因其不受民法、行政法的保護,不是一種合法的占有關系,而只是他人對財物的一種事實占有關系。刑法對這種事實上的財物占有關系的保護表明,刑法并不只是其他部門法保護的“第二道防線”,不以其他部門法對事實關系的合法性確認為基本前提。
(五) 一元化模式不符合現代刑法的輕緩化趨勢
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一元化關系模式是基于刑罰的嚴厲性和殘酷性。刑罰是所有法律手段中最嚴厲的強制性制裁方法,“能夠不使用刑罰,而以其他手段亦能達到維護社會共同生活秩序及保護社會與個人法益的目的時,則務必放棄刑罰的手段”[28](128)。但如今看來,“這卻是一種落后的刑罰觀,與現代社會中的刑罰現狀有很大的差別,也與我國刑法中的有關規定不符”[29](330)。
現代刑罰的手段日益多元化,并呈現出明顯的輕緩化傾向:一是刑罰處罰的行政罰化。許多以保安為目的的行政處罰措施,如日本的“科料”、德國的“禁止駕駛”、俄羅斯的“義務勞動”、我國的“社區矯正”,逐漸上升為刑罰手段并成為刑罰適用的主要方式;二是刑罰處罰的民事罰化。民事賠償、擔保、向被害人賠禮道歉等民事處罰措施逐漸成為影響刑罰適用的重要因素和替代傳統刑罰手段的措施。這在降低刑罰懲罰性的同時,也加強了對被害人的補償和對行為人的風險防范。在一些輕微的刑事案件中,行為人甚至寧愿接受刑罰處罰,也不愿接受被害人提出的巨額賠償要求。因此,在法律意義上,刑罰只是犯罪行為的法律效果,是“區分刑法與其他法律部門惟一的外部標志”[30]。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一元化關系模式不符合現代刑罰的這種發展趨勢。
法律的邏輯起點差異與不同的價值追求、刑事違法性的二元化、刑法重事實保護的特點和刑罰輕緩化趨勢表明,刑法與相關部門法之間不是單一的保障法關系,民事、行政違法行為不能直接上升為刑事犯罪行為。
四、刑法與相關部門法關系的一元化模式修正
“刑罰的功效在于,從另一個方面與對具有同一性的社會規范的對抗相對抗。”[24](103)從法秩序的統一性角度,作為國家意思的適法還是違法的判斷,在全體法秩序可能的限度內不應該發生沖突,違法具有統一性。但從部門法的角度,基于不同的法秩序調整需要,不同部門法的調整范圍必然存在一定差異,違法性在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領域具有相對性,并可能發生一定的沖突: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即便為民法或者行政法所許可,也有成立犯罪的可能性;而民法或者行政法上禁止且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在刑法上也可能不具有違法性或者可罰性。[31]違法的相對性表明,刑法與相關部門法之間并非純粹的一元主義關系,除了補充性,它們之間也存在獨立性。
(一) 私益保護下的民法獨立
“追求利益是人類最一般、最基礎的心理特征和行為規律,是一切創造性活動的源泉和動力。”[32](220)私益是市民社會的基礎。對私益的維護是現代法律的重要任務,對私益的特殊保護決定了民法的獨立性。這是因為:
第一,私益侵害是許多公益侵害的起點。公共利益是社會上一般人的共同利益。“公益的維護和提倡,可以說是現代國家積極的任務,也是許多實際政治運作行為所追求的目標之一。”[33](181)不過,除了公共財產、公共場所秩序等可見的利益外,公共利益更多的是從個體私人利益中抽象出來的共同社會利益。例如,搶劫罪的設置是為了保護一般的財產權和人身權,但這里的“一般”是從具體個體中抽象出來的。搶劫罪立法所要保護的一般財產權和人身權是否受到侵害,最終還是體現為個體的人身權和財產權是否受到侵害。被害人的私益是否受到侵害是公共利益是否受到侵害的判斷起點,也是許多公共利益保護的基礎。加強被害人私益的保護對刑法的公共利益保護而言,意義尤甚。
“犯罪是針對社會之害”,是“加害于社會整體的行為而不只是針對特定被害人的行為”[34]。“如果某種行為根本不可能給社會帶來危害,法律就沒有必要把它規定為犯罪,也不會對它進行懲罰。”[15](44)侵犯私人利益的行為只有同時侵犯了公共利益才能進入行政法和刑法的調整范圍。公共利益是連接民法與刑法的紐帶。我國《著作權法》第47條規定,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只有“同時損害公共利益”,才可以由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給予行政處罰,進而構成犯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而《刑法修正案(八)》第41條也規定,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行為只有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的,才可上升為刑法上的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可見,僅僅侵犯私人利益的行為被劃入了民法的調整范圍,只有由私益引發對公共利益侵害的行為才是行政法和刑法的調整對象。
第二,私益保護是公益保護的歸宿。“利益是主體所追求的目的,權力和權利則是主體追求目的的手段。”[35](33)在保護手段上,民法是私益保護的主要法律手段,而刑法則以保護公益為己任。不過,從根本目的上看,刑法對公共利益的保護終歸要落實到私人利益之上。以故意殺人罪為例,刑法設置故意殺人罪的目的是要保護一般的生命,而不僅僅是被害人的生命。但刑法上的一般生命仍可細化為社會上不同個體的具體生命。刑法通過故意殺人罪立法所保護的一般生命終究要體現為具體個體的生命沒有受到侵害。從這個角度看,私益保護是刑法保護的歸宿。
在私益保護的目的下,民法與刑法的規范沖突得以存在,并強化了民法的獨立性。《德國民法典》第134條規定:“違反法律禁令的法律行為無效,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我國《合同法》第52條第5項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但該法第54條第2、3款同時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當事人請求變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不得撤銷。”可見,民法允許被害人基于私益補正無權代理行為、以欺詐、脅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簽訂合同行為的效力,是基于私益保護的需要,它并不影響刑法對詐騙、強迫行為的責任追究。
(二) 行為差異下的相互獨立
基于法目的的不同,作為法調整對象的行為在刑法、民法、行政法上的屬性不可能完全相同。在行為差異的范圍內,刑法與民法、行政法之間應當各自獨立。
刑法、行政法、民法的行為概念差異主要源于刑法、行政法和民法的法目的不同。刑法追求的目標是“欲求允許”,即保障意志載體的意志自由,行政法追求的是福利,民法的目的主要是對已經造成的權利損害和財產損失給予填補和救濟,使其恢復到未受侵害的狀態。[36](45)從結果上看,刑事和民事不法造成的是實際的損失,而行政不法造成的是通過行政行為所欲達到的更大的福利的不可實現。[37]因此,刑法更注重違法行為已經造成的法益侵害和威脅。犯罪“對法益的侵犯性包括對法益的侵害性和威脅性(危險性)。侵害性是行為造成了法益的現實損害;威脅性是行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險”[7](97)。責任以損害賠償為核心,賠償損失是所有民事違法行為的最后責任,其前提是違法行為已經造成了他人的損失(實害)。[38](186)而行政法強調的是行為的危險屬性,行為的危害后果、主觀惡性雖然也是行為危害性的判斷依據,但并非決定因素。“為了社會秩序的需要,應當對行為本身給予處罰,其目的是威懾,而不是懲罰。”[39]對行政管理秩序的實際或者潛在威脅是判斷行政違法行為的關鍵。
行為概念的差異導致了各部門法規范的不同以及刑法與民法、行政法之間互補關系的有限性。例如,在賄賂罪的場合,因無實際受損害人,行為人就不必承擔民法上的責任而只承擔刑法或者行政法上的責任;同理,在行為人無過錯致人受傷的場合,因無罪責和危險,行為人只需承擔民法上的無過錯責任,而不須承擔刑法或者行政法上的責任。在此范圍內,刑法、民法、行政法對其不法行為的調整是完全獨立的。部門法內在目的的一致性要求其價值的統一性。“當以國家或社會必要性或目的,以多重意義的,受時代制約和具有爭議性的價值觀名義處刑時,施刑的手就不能不顫抖。”[40](88)因此,無論此種民法違法、行政違法行為的危害如何嚴重,也不能將其直接上升為刑事犯罪,除非刑法對行為的屬性要求發生了變化。從這個意義上看,刑法作為保障法的一元化模式形式上具有限制刑罰權的作用,但在行為不重合的范圍內,它也可能導致刑法對民法、行政法領域的侵犯。從這個角度看,在我國2013年廢止勞動教養后,筆者不贊同許多學者主張的據此對刑法進行結構性調整,因為勞動教養制度調整的對象只是具有較大危險性而不具有較明顯法益侵害性的行為,它們主要屬于行政法調整的范圍,而不應將其作為犯罪處理。
可見,刑法與民法、行政法等相關部門法之間具有補充性,但并非單純地刑法補充民法、行政法等相關部門法,而是基于法整體秩序之保護需要的互補關系,它們之間是一種相對的一元化關系。在法益和行為不重合的范圍內,民法、行政法規范不能上升為刑法規范,以防止刑法對民法、行政法領域的侵犯。
[1] 劉艷紅. 我國應該停止犯罪化的刑事立法[J]. 法學, 2011(11): 108?115.
[2] [德]克勞斯·羅克辛. 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 犯罪原理的基礎構造[M]. 王世洲譯.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3] [意]杜里奧·帕多瓦尼. 意大利刑法學原理(注評版)[M]. 陳忠林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
[4] [美]哈羅德·J·伯爾曼. 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M]. 賀衛方, 等譯.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3.
[5] [德]尤爾根·哈貝馬斯. 合法化危機[M]. 劉北成, 曹衛東譯.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6] [日]瀧川幸辰. 犯罪論序說[M]. 王泰譯.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7] 張明楷. 刑法學(第2版)[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8] [日]大谷實. 刑法總論[M]. 黎宏譯.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9] [美]德沃金. 法律帝國[M]. 李常青譯.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6.
[10] [日]西原春夫. 刑法的根基與哲學[M]. 顧肖榮, 等譯.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11] 楊忠民. 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不可轉換——對一項司法解釋的質疑[J]. 法學研究, 2002(4): 131?137.
[12] 李希慧. 論刑法的文理解釋方法[J]. 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 1995(1): 26?32.
[13] 朱鐵軍. 刑法與民法之間的交錯[J]. 北方法學, 2011 (2): 48?57.
[14] 蔡墩銘. 刑法總論[M]. 臺北: 三民書局, 1993.
[15] 高銘暄, 馬克昌. 刑法學(第5版)[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16] 張善根. 西方法學流派的邏輯起點及其局限[J]. 求是學刊, 2011(6): 76?81.
[17] 陳瑾昆. 刑法總則講義[M]. 北京: 中國方正出版社, 2004.
[18] 羅豪才. 行政法學[M].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9.
[19] 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M].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1999.
[20] [日]大塚仁. 犯罪論的基本問題[M]. 馮軍譯.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3.
[21] 黎宏. 日本刑法精義[M]. 法律出版社, 2008.
[22] [意]桑德羅·斯奇巴尼. 正義與法[M]. 黃風譯.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2.
[23] 沈宗靈. 法理學[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24] [德]格呂恩特·雅科布斯. 行為 責任 刑法——機能性描述[M]. 馮軍譯.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7.
[25] 李蘭英. 契約精神與民刑沖突的法律適用——兼評《保險法》第54條與《刑法》第198條規定之沖突[J].政法論壇, 2006(6): 165?172.
[26] 王利明. 無效抑或撤銷——對因欺詐而訂立的合同的再思考[J]. 法學研究, 1997(2): 67?83.
[27] 黃桂武, 等. 新論財產罪法益—與張明楷教授商榷[J]. 學術研究, 2007(1): 69?72.
[28] 林山田. 刑罰學[M]. 臺北: 商務印書館, 1985.
[29] 黎宏. 刑法學[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2.
[30] 陳自強. 刑法的調整對象新界說[J].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1(2): 110?115.
[31] 童偉華. 日本刑法中違法性判斷的一元論與相對論述評[J].河北法學, 2009(11): 169?172.
[32] 張文顯. 法哲學范疇研究(修訂版)[M].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1.
[33] 陳新民. 德國公法學基礎理論(上冊)[M]. 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1.
[34] 夏勇. 刑法與民法[J]. 法治研究, 2013(10): 5?9.
[35] 葉必豐. 行政法的人文精神[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36] 魏振瀛. 民法[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37] 王瑩. 論行政不法與刑事不法的分野及對我國行政處罰法與刑事立法界限混淆的反思[J]. 河北法學, 2008(5): 26?33.
[38] 張俊浩. 民法學原理[M].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0.
[39] 王文華. 行政違法與行政犯罪若干問題研究——以中國與加拿大比較為視角[J]. 南都學壇, 2008(5): 86?89.
[40] [德]拉德布魯赫. 法學導論[M]. 米健, 朱林譯.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7.
Refle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inal law and the relevant department laws
YUAN Bin
(College for Criminal Law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unifi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inal law and relevant department laws, criminal law is subordinate and complementary, functioning as the security law for relevant department laws. But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law and value pursuit, normalized criminal illegality, the focus on the fact protection and the tendency of the alleviation of criminal law, all determine that criminal law as the unified model of security law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riminal law and the relevant department laws. As a result, it is easy for the criminal law to infringe upon such fields as civil law, administrative law and other department laws, according to the absolute unified relationship. Therefore, relative relationship model should be advocated between criminal law and the relevant department laws. Only in the identical scope of benefit and act, can the rules of civil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law be stipulated in criminal law.
criminal law; relevant department laws; subordinate property; independent property; relationship model
D914
A
1672-3104(2015)01?0044?07
[編輯: 蘇慧]
2014?05?08;
2014?06?11
袁彬(1976?),男,江西臨川人,法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教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檢察員,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