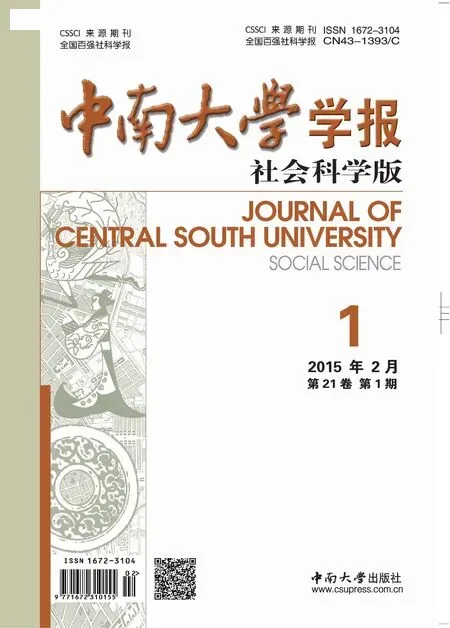我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綜述:解釋模式與發展啟示
許源源,楊茗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湖南長沙,410083)
我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綜述:解釋模式與發展啟示
許源源,楊茗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湖南長沙,410083)
在我國,國家與社會在傳統社會中是緊密結合的;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全面控制和主導社會;在市場經濟時期,國家不斷放權,社會越來越多地承擔公共職能。針對不同時期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釋模式。他們結合了我國的歷史經驗和現實發展,試圖從“強國家、弱社會”向“強國家、強社會”轉變,構建本土化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我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未來發展是一個雙向建構的過程,只有兩者分工合作、互相監督的同時,進行良性互動、相互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目標才可能實現,新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才可能形成。
國家與社會關系;解釋模式;傳統社會;計劃經濟時期;市場經濟時期
隨著我國政府改革的逐漸深入,社會組織越來越多地承擔了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供給職能。一方面政府逐漸放松管制,其控制的范圍縮小、力度減弱,手段逐漸走向規范化;另一方面,社會在蓬勃發展,涌現了大批社會組織,參與公共事務的范圍越來越廣,程度越來越深,社會與國家(政府)、市場一起共同成為調控社會資源的重要手段。合理地調整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既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又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積極性,是當前的重要任務。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從政治學上來說,即為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從20世紀末期以來,學術界在借鑒國外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對我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試圖梳理學界關于我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不同解釋模式,并結合三個不同的階段進行論述,為未來我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良好發展提供借鑒。
一、傳統社會中的“士紳社會”模式
與我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自然經濟形態相適應,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國家一直處于絕對的統治地位。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限制了人們的交往和交換行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基本上是依賴血緣和地緣建立起來的。個人被看作是家族的一分子而進入社會,個人權利湮沒在政治權力中,家庭的行為準則和國家的規范準則高度一致,道德和政治互相滲透,國家與社會緊密結合在一起,是一個典型的宗法社會。我國古代雖也有“皇權止于縣政”的傳統,鄉村由鄉紳、士紳組織協調,通過創辦“善堂”“會館”等民間基層組織,進行自我管理,在維護社會治安、發展經濟、賑災慈善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以封建皇權為代表的國家權力通過宗族、家族實現對社會及其成員的完全的支配和控制,社會也因此被國家化。近代以來,盡管西方資本主義給我國封建國家造成了極大的沖擊,很多人也試圖通過各種努力來改變國家主導的格局,但都成效甚微。“近代中國政治變革勢力試圖依照西方社會制度模式,建立憲政基礎上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近代體制,但國家的過渡性和國家統一的雙重使命使這一任務不能實現。”[1]
對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研究,以“士紳社會”的解釋模式得到最廣泛的認可。卜正民(Timothy Brook)認為“士紳社會”是“一個由獲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會,它處于由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事務領域與個人及其家族的私人領域之間”[2]。所謂“士紳”,主要強調他們在鄉村社會中作為地方精英的公共職責。士紳的公共性可以讓他們在國家之外行使地方管理職能,彌補傳統中國政治權力和鄉村社會之間存在的權力真空,促進了社會的自治。蕭公權、瞿同祖等學者都意識到國家權力影響、控制地方社會要依靠“士紳”的支持,但兩者的關注點不同。前者主要關注政權控制力與地方精英之間的互動關系,認為國家權力試圖通過鄉約、宗教等管道實現對地方社會的控制,但最終僅完成意識形態的控制[3],而后者則聚焦于政府對地方的控制,試圖解決中國社會不能向西方社會一樣現代化的問題[4]。隨后,黃宗智提出的“第三領域”[5]使得“士紳社會”的模式更具有解釋力,并且有更多學者將其運用到中國的實踐中來。如Mary B. Rankin研究浙江的士紳階層[6],William T. Rowe研究漢口的商人團體[7],均證明了這個介于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領域的存在,并且強調“士紳”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但由于士紳階層本身的局限性,導致“士紳社會”模式僅限于解釋傳統的中國社會:一方面,士紳階層內部存在分化,他們的社會地位和作用發揮差別很大;另一方面,隨著公共事務的日益繁多,士紳的能力不足以獨自組織大規模的公共活動,時常需要向政府求助。
二、計劃經濟時期的“全能主義”模式和“總體性社會”模式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在社會資源極度匱乏的環境下,只有迅速建立起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使國家政治權力和社會結構高度一體化才能快速發展。因此,我國走上了計劃經濟的發展道路。在這一時期,國家處于絕對主導地位,政治權力幾乎滲透了社會的每個方面。國家對各種社會資源進行統一的調度和分配,通過行政手段“把所有的經濟成分都統一于國家計劃經濟框架之中, 使經濟成為政治的附庸”[8],社會也依附于國家而生存與發展。
這種體制催生了“單位制”的產生。如同自然經濟下的家庭一樣,單位成為社會最基本的結構和功能組織。單位集政治、經濟、安全、福利等種種功能于一身,處于單位制中的人們的日常生產和生活都處于政治的控制之下,單位制保證了所有社會成員都納入到國家的統一計劃管理之中。“這種社會組織與其說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組織,還不如說是政治學意義上的政治組織,其功能、活動方式和范圍都具有‘小政府’的性質。”[9]單位制造成個人對單位的依附和單位對國家的依附,而國家依靠對單位的嚴密控制實現了對社會和政治的全面整合。單位成為連接國家與社會的紐帶,國家權力通過單位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層面和角落,從而使社會失去了自由成長的空間。
這種國家全面控制與主導社會的一元模式,因其強大的政治整合能力和資源動員能力,在建國初期卓有成效。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其弊端也逐漸顯露出來。由于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利益追求和價值取向并不完全一致,兩者的關系越來越緊張。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雖然有助于樹立領導人權威,保持政令暢通,但缺乏社會監督與制度約束的國家行為極易失控,權力濫用、官僚作風嚴重。計劃經濟體制雖然有效推動了工業化建設,卻無法同時兼顧社會秩序與社會動力,并逐漸阻礙著經濟的發展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對計劃經濟時期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研究,有“全能主義”和“總體性社會”兩種有影響力的解釋模式。
“全能主義”是鄒讜等學者基于政治權力和政治體制的角度來解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模式。他認為,從建國后到改革開放這段歷史時期中,我國樹立了以“政治結構的權力可以隨時地無限制地侵入社會每一個階層和每一個領域”[10]為指導思想的社會政治制度。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通過自身的領導體系和組織體系,對中國社會進行了重新整合,尤其是在“三大改造”結束后,黨和政府高度重合,通過各種手段占領了社會的大部分領域。國家權力憑借城市中的單位制和農村的人民公社體制,實現了對整個中國社會的全面控制。“國家通過政治權力可以無孔不入地侵入社會生活的私人領域,社會中的個人或集體的自由和權利沒有受到憲法、法律和各種制度的保障。整個社會的資源和人們的自由空間都被納入政治之內,由政治結構決定。”[11]
“總體性社會”是孫立平等學者基于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角度來解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模式。他們認為,建國后至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一個“總體性社會”,即“社會的政治中心、意識形態中心、經濟中心重合為一、國家與社會合為一體以及資源和權力的高度集中,使國家具有很強的動員和組織能力,但結構較為僵硬、凝滯”[12]。這種社會結構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系列改造過程的結果,這種改造的實質是“抑制分化”,即通過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和各種政策制度來人為地限制個人位置以及各種社會要素的分化。這種社會結構具有下列特征:社會動員能力極強,可以利用全國性的嚴密組織系統,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資源,以達到某一國家目標;缺乏中間階層的作用,國家直接面對民眾,中間缺少緩沖;社會秩序完全依賴于國家控制的力度,當國家控制受到削弱時,社會具有一種自發的無政府、無秩序傾向;社會自治和自組織能力差,中間組織不發達,控制系統不完善;全部社會生活呈政治化、行政化趨向,社會的各個子系統缺乏獨立運作的條件。換言之,總體性社會是一種社會高度一體化,整個社會生活幾乎完全依靠國家機器驅動的社會。[13]
這兩種解釋模式是基于不同角度做出的研究,“全能主義”側重于國家層面的權力、體制,而“總體性社會”側重于社會層面的結構變遷。 由于側重點不同,它們往往只聚焦一個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的影響。無論從國家角度還是從社會角度對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單一向度的強調,都無法準確概括這一時期我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新變化。但它們都認為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天平明顯地傾向了國家,國家與社會緊密結合的同時又高于社會。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在不斷嘗試由“一元”走向“二元分化”,而這種改變在市場經濟時代得以實現。
三、市場經濟時期的“解釋模式叢林”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我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也進行了巨大的調整。經濟方面,國家開始逐步減少對經濟領域中微觀層面的行政干預,順應市場規律的發展,市場日益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機制和手段;政治方面,國家由“無限政府”逐漸轉向“有限政府”,逐步將可以賦予社會而對國家權威不會產生沖擊的權力歸還給社會,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范圍減小、力度減弱、手段也更加規范化和程序化。社會的自主性和積極性大大增加,整個社會領域都逐步脫離政治領域的控制和功能限制,社會的流動性和活力不斷增強,獨立的社會力量悄然萌發。各類民間社團,如行業協會、學術性團體、公益性組織等自發組織不斷產生且力量不斷壯大;帶有國家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群眾團體,如工會、婦聯、共青團等開始轉變職能;基層民主自治組織,如村民委員會、街道居委會等逐漸制度化并實現自我管理。這表明一個介于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公共領域正在形成。然而,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公共領域的發展依然十分緩慢。這是因為,在國家和社會關系的調整過程中,國家依然掌握著絕對的主導權,一旦國家發現社會力量的變化超出了國家對社會力量的預期,就會立刻對社會的自我發展進行干預,將其納入到國家的體制之內。而社會組織只有在國家的授權和承認之下,才能在國家規定的范圍內開展工作。
因此,我國的國家與社會的邊界雖然在逐漸清晰,但兩者力量對比十分懸殊,遠未能實現平等的互動與交流,還是“強國家、弱社會”的格局。社會不能對國家的政策和管理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也無法監督和制約國家權力。
首先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權力和自下而上的社會力量無法平衡。國家的權力過大且缺乏限度,社會的力量過小且無法限制國家權力的擴張。當國家和社會的利益存在沖突時,政府會借口國家利益對社會利益進行侵犯,結果往往是社會利益受到損害而國家的權威性降低。國家權威的削弱會導致國家在行使權力過程中遭遇更多的社會阻力,而國家又不得不采用強制力量迫使社會服從,進一步削弱了國家的權威。這種不平衡的力量對比以及國家權威的消蝕不僅不利于構建平等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更會危及國家的合法性和社會的長治久安。
其次是政府改革的單向性和形式化導致社會的成長機制缺失。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但是市場經濟體制所要求的政府職能轉型一直未能真正做到,政府依然承擔了較多屬于市場和社會的事務。政府主導的改革有單向度的特點,沒有合理地培育社會組織,對社會組織的發展有太多的限制,甚至是將社會的發展納入到政府的體制內。這樣的結果就是社會難以獨立自主地發展,不能在具體的公共事務管理和供給當中得到鍛煉,更不能發揮培育整個社會理性發展的職能。在政府改革不夠深入的情況之下,市場發展緩慢,社會發展缺少經濟基礎,看起來整個國家范圍內都在改革,但都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國家依然處于唯一的高位,甚至是非常傲慢地對待著社會。
最后是社會組織的自身成長和主動參與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當國家產生之后,社會是被國家型塑的產物。在國家塑造社會的過程中,國家往往把對社會的管理當作目的,而不是在推動社會走向成熟;而社會也在過度依賴國家,沒有提高自身能力,爭取與國家平等對話。社會對國家權力的下沉多是無條件的接受和被動的執行,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會力量的發展。
基于對這些問題的思考,為改善國家與社會關系,我國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一時期的國家與社會關系進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這些解釋模式主要集中于“新權威主義”“市民社會”“法團主義”“治理與善治”以及“分類控制”。
“新權威主義”作為對上世紀80年代改革中產生的社會失序現象的反思,繼承了美國新保守主義政治學家塞謬爾·亨廷頓的思想。主張這種模式的中國學者認為,新權威主義是“作為對第三世界國家議會民主制的反動而出現的,由具有現代化意識及導向的軍事、政治強人而建立的權威政治”[14](55)。這種模式的顯著特點是政治和經濟相分離。為此,改革要達到雙重目標:經濟上“建立以明確產權為基礎,以組織良好的市場為條件的商品經濟”;政治上“建立集權式的政治體制”。[14](55)“新權威主義”的具體內容可以表述為“以強有力的政黨和權威維護穩定的政治秩序,推動國內的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通過經濟發展的績效來獲得政治合法性,在市場經濟得到充分的發展后再發展民主,從而實現政治經濟的全面轉型”[11]。這種模式對于國家的片面強化,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它的解釋力度,引起了學術界的爭論。
我國對“市民社會”的研究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作為對80年代國家本位的反思,市民社會為“研究中國的國家和社會關系以及中國社會發展等論題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框架或解釋模式”[15]。懷特(S.H. White)[16]和麥迪森(R.Madsen)[17]等國外學者也發現,由于市場經濟和社會力量的發展,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與工業革命之后的西方出現了類似的變化,因此,源自于西方的市民社會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市民社會從“社會中心論”的角度出發,反對國家本位,強調國家與社會的分離,且社會應處于主導地位。主張市民社會的學者嘗試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關注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并把市民社會作為制約政治權力的一種力量。如鄧正來等學者認為,“在現代化基本問題的認定上必須用‘國家與社會的二元觀’替代‘權威本位(轉型)觀’,提出要在逐漸確立二元化結構的基礎上,形成國家與社會的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8]。張慶熊等學者認為,“市民社會的概念對于現階段的中國具有反對封建主義、促進多元化和保證社會秩序、機會平等和分配平等以及克服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和防止國家權力的過分膨脹的作用”[18]。但市民社會是直接借鑒了西方的概念,強調獨立于國家之外的社會領域,而我國的市民社會是否存在或者能否形成,都是需要進一步討論的。
基于對市民社會的反思,一些學者試圖用法團主義(corporatism,又譯為合作主義、統合主義)理論來研究當前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古德斯坦(Steven M. Goldstein)通過對比中國與蘇聯的經濟改革,指出法團主義比市民社會更符合中國的轉型實質[19]。法團主義強調“中介(intermediation)”和“規制(regulation)”,認為國家與社會之間不是“零和博弈”的對立局面,而存在著制度化的上傳下達的聯系通道。“社會的自主活動不足以形成秩序,國家對于市民社會的參與、控制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制度化的聯系渠道成為法團主義思想的核心。”[20]法團主義視角下的國家與社會互相承認對方的合法性,并試圖建立兩者長期的合作關系。昂格爾(Jonthan Unger)等通過對工會和商業協會的研究,認為其是為填補控制弱化而創制的“中介”,并預測我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最終發展趨勢是“社會法團主義”[21]。奧伊(Jean C. Oi)通過剖析基層政府、企業與基礎農村社會之間的權力關系格局,將中央控制松懈之下的地方政府與社會之間新的結合過程稱為“國家法團主義”[22]。顧昕等通過對專業性社團的調查,認為中國已經完成了從國家主義向國家法團主義的過渡,并且“一個國家與社會相互增權的局面是可以期待的”[23]。但是,同市民社會一樣,來源于西方的法團主義在中國的適用性也受到了學者的質疑,賈西津等學者認為中國不存在法團主義賴以生存的“強國家、強社會”的建構基礎[24]。
治理理論的興起源自于政府和市場的雙重失靈,20世紀90年代,西方各國開始通過“治理(governance)”進行重塑政府的改革。區別于“統治(government)”,治理的主體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其他社會組織,治理過程中的權力運行是上下互動的,因此治理強調的是多元主體之間的合作與協商,以及對共同目標和公共利益的認同。“治理是政府與社會力量通過面對面合作方式組成的網狀管理系統。”[25]在俞可平等學者的研究中,治理的基礎是市民社會的不斷發展與強大,而治理的理想狀態是達到善治(good governance)。“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其本質特征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26]在這種狀態下,政府“還政于民”,國家權力向社會回歸,政府對公民的回應性增強;而社會對權威普遍認同,公民自愿合作、積極參與。治理與善治凸顯了國家與社會形成相互協作的良性互動關系的可行性,兩者合作不僅可以克服國家干預的失效,也可以彌補市民社會的不自足。治理與善治的基礎在于市民社會的健全和發達,而我國市民社會的建立仍然需要時間,因此治理的實現也必然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無論是“市民社會”還是“法團主義”,都是建立在國家—社會二元分立的基礎上。而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國家與社會發生分離的同時,也不斷產生新的結合,但國家依然處于明顯的主導地位。國家缺乏開放性、社會缺乏自主性,導致西方的“市民社會”與“法團主義”在中國缺乏現實土壤,很難適應中國的當前發展。而“治理與善治”也是基于市民社會的發展壯大,市民社會在中國能否存在尚且存在爭論,善治也始終只能是公眾對政府的理想與期待。因此,一些學者試圖突破西方的理論框架,對我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進行本土化的解讀。
“分類控制”是我國學者針對我國現實情況,提出的新的解釋模式。康曉光、韓恒等學者通過考察國家對不同類型社會組織的實際控制,提出了“分類控制體系”。這一體系的根本特征是“國家控制社會”,至于“實施什么樣的控制策略和控制強度,取決于政府的利益需求以及被控制對象的挑戰能力和社會功能”[27]。他們認為,改革前的權力分配格局和改革中的政府主導地位,使得政府有能力根據自身利益建立起一套對不同的社會組織實施不同控制策略的“分類控制體系”。在這種新的國家與社會關系中,“國家不再全面控制經濟活動,也不再干預公民的個人和家庭生活,但仍然控制著‘政治領域’和‘公共領域’。……國家允許公民享有有限的結社自由,允許某些類型的社會組織存在,但不允許他們完全獨立于國家之外,更不允許他們挑戰自己的權威。同時,國家也有意識地利用各種社會組織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使其發揮‘拾遺補缺’的作用。”[27]“分類控制”體系符合我國現階段的國家需要以及社會組織不太發達的現狀,有利于維護國家和社會的穩定,但由于這一理論提出的時間較短,其有效性和可行性還需要驗證。
除了上述幾種解釋模式,還存在著諸如“組合主義”[28]“行政吸納服務”[29]“利益契合”[30]等多種具有合理性和現實可行性的關系模式。它們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為我們描繪了我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現狀和未來,形成了一種解釋模式叢林的特征。總體而言,都是結合了我國的歷史經驗和現實發展,試圖從“強國家、弱社會”向“強國家、強社會”轉變,構建本土化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
四、啟示與發展
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發現,我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發展至今,雖然已經初步實現了國家與社會的分離,但國家與社會力量不均衡、地位不平等,呈現“強國家、弱社會”的格局。而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必然要求良好的制度環境和結構體系,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調整就顯得尤為重要。要構建良好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必定是以國家和社會的共同發展為目標,因此也需要兩者的共同努力。
從國家的層面來考慮,首先國家自身必須具備足夠能力和權威。國家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保障人民安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面對我國復雜的經濟社會環境,國家的管治力量必須要強大。這種強大不是體現在國家對社會的控制之上,而是體現在國家對公共事務的執行之上。其次,必須合理地界定國家界限。如黑格爾所說,公民社會的不可自足的缺陷決定了國家對社會進行干預和調節的必要性,但這種干預和調節的界限必須予以確定。“一般地說,國家的干預表現為把社會本身所具有的契約性規則賦予法律效力,或者是社會成員在公民社會的‘私域’中意識到僅憑社會契約性規則無法解決他們的沖突時,國家才可以出面裁決與調解。”[31]最后,為社會的發展提供條件。一方面承認社會的獨立性,為其發展提供制度性的法律保障,給予其較大的合法活動空間;另一方面,將政府的部分職能轉移給企業、行業協會和其他社會組織。
從社會的層面來考慮,首先社會組織必須不斷提高自身能力。政府不再是社會管理的唯一主體,社會中的各種組織將與政府共同承擔公共事務的管理職能,社會要表達其利益訴求,就必須有能力與國家進行平等的對話。其次,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培育公民的主體意識和法治觀念。增強社會的理性化、自主性的品格和自我管理、自我調節的能力。最后,形成對國家權力的制約和監督。這不僅能使自身免受國家權力的干預和侵犯,也能有效彌補體制內權力制衡機制的缺陷。
總之,國家與社會關系是一個雙向建構的過程,只有兩者分工合作、互相監督的同時,進行良性互動、相互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目標才可能實現,新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才可能形成。
[1] 白貴一. 當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嬗變[J]. 貴州社會科學, 2011(7): 12?16.
[2] 卜正民. 為權力祈禱: 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M].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5: 21.
[3] Hsiao Kung-chua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256?257.
[4] Chu Tung-ts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97?198.
[5] Philip C C. Huang. “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J]. Modern China, 1993, 19(2): 216?240.
[6] Mary B.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5?30.
[7]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
[8] 鄧正來, 景躍進. 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C]// 鄧正來.國家與社會: 中國市民社會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33.
[9] 孫曉莉.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與社會[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 53.
[10] 鄒讜.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 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M]. 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4: 3.
[11] 朱春雷. 建國后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綜述[J]. 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2007(1): 44?46.
[12] 孫立平. 轉型與斷裂: 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M].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4: 5.
[13] 孫立平, 王漢生, 王思斌, 等. 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J]. 中國社會科學, 1994(2): 47?62.
[14] 劉軍, 李林. 新權威主義: 對改革理論綱領的論爭[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1989.
[15] 鄧正來. 國家與市民社會: 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474.
[16] White S H. The politics of NGO development in China [J]. Voluntas, 1991(2): 16?48.
[17] Madsen R. 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A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J]. Modern China, 1993, 19(2): 183?198.
[18] 張慶熊. 市民社會的概念及其對當代中國的意義[J]. 科學?經濟?社會, 1998(4): 63?68.
[19] Steven M. Goldstein.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incremental reform [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5(12): 1105?1131.
[20] 張靜. 法團主義[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 23.
[21] Jonthan Unger, Anita Chan. China, c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J].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5, 33(1): 28?53.
[22] Jean C. Oi.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corporatism in China [J]. World Politics, 1992, 45(1): 99?126.
[23] 顧昕, 王旭. 從國家主義到法團主義——中國市場轉型過程中國家與專業團體關系的演變[J]. 社會學研究2005(2): 155?175.
[24] 賈西津. 民間組織與政府的關系[C]// 王名. 中國民間組織30年. 北京: 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8: 199.
[25] Kettl D F. Sharing Power: Public Governance and Private Markets [M].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3: 21?22.
[26] 俞可平. 治理與善治[M].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0: 8.
[27] 康曉光, 韓恒. 分類控制: 當前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J]. 社會學研究, 2005(6): 73?89.
[28] 顏文京. 調整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第三種模式——試論組合主義[J]. 政治學研究, 1999(2): 85?93.
[29] 唐文玉. 行政吸納服務——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新詮釋[J]. 公共管理學報, 2010(1): 13?19.
[30] 江華, 張建民, 周瑩. 利益契合:轉型期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個分析框架——以行業組織政策參與為案例[J]. 社會學研究, 2011(3): 136?152.
[31] 時和興. 關系、限度、制度:政治發展過程中的國家與社會[M].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 172.
Research 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terpretation mode and suggestions of development
XU Yuanyuan, YANG M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In China,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have been traditionally bonded together. In planned economy, the state governed and manipulated the whole society, while in marketing economy, the state has gradually delegated power to the society and the society has gained more public functions.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modes have thus been put forward at these different period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Researchers have combined the historic experience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to structure a localized development mod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attempting to transform from the pattern of “strong state, weak society” to “strong state, strong society”. In th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in China will be a two-way process. Only wh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cooperate with, supervise over, and excise positive interaction and cultivation between each other, can the targe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e reached, and the neo-relationship of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be realis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interpretation mode; traditional society; planned economy; market economy
C93-05
A
1672-3104(2015)01?0134?06
[編輯: 顏關明]
2014?03?31;
2014?12?16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我國農村扶貧中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11BZZ002);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湖南省貧困地區新農村建設中的政府作用研究”(11YBA332);第54批中國博士后基金“基于農村扶貧的政府與社會組織互信關系研究”(2013M542150)
許源源(1974?),男,湖北黃梅人,管理學博士,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地方治理,社會組織,公共行政理論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