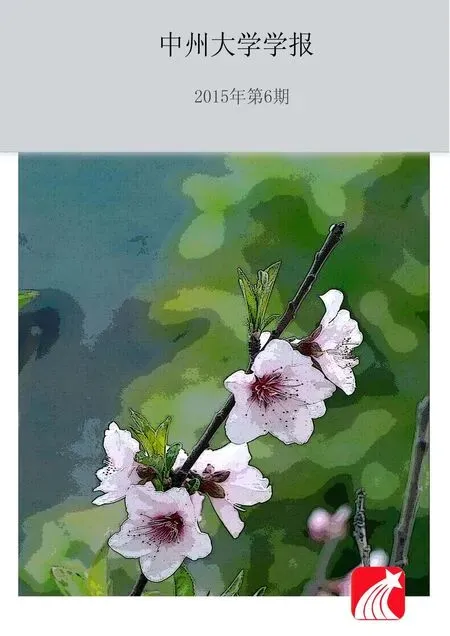官員證婚的法律分析
胡利明
(中央民族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081)
?
官員證婚的法律分析
胡利明
(中央民族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081)
官員證婚是比較新潮的社會現象,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并頗受追捧,民眾和官方為之“叫好”,特能引起新聞媒體的特別關注。其實,官員證婚是官員不經意地代表政府默默地從事違法行為,原因在于沒有獲得過授權而任性為之,而且還與婚姻登記“隔空打牛”,造成兩者之間的法律效力尷尬沖突,扭曲官員公正行政的中立者角色,嚴重背離“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法治理念,嚴重沖擊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則。據此,有必要從法律性質、合法性、主體身份、正當程序、權力運行、法治異化、法律效力和法治危害等方面深析官員證婚的不正當性和違法性。
官員證婚;婚姻效力;依法行政
“官員證婚”是與時俱進的“潮名”,所涉及的事項見諸新聞報端,但在學術期刊網上卻是“學術荒地”,經查詢數家學術期刊網站沒有發現與此相關的學術論文。十年前,筆者開始關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時至今日仍然經常遇之,例如法院辦婚禮法官來證婚:“法庭首辦婚禮,院長來證婚”“法院為‘三無殘疾人’辦婚禮,法官為新人證婚”。限于篇幅,沒有必要詳述上述事例的具體細節,讀者可以根據需要搜索相關網站查閱。普通民眾結婚儀式上經常會邀請新郎新娘單位領導(特別是機關單位)或者現職公職人員,以貴賓公職人員身份宣布證實當事人結婚,從而將婚禮推向高潮,來賓隨之熱烈鼓掌,但所鼓掌的核心并不是新郎新娘結婚的消息,而是內心對官員宣布“證婚”的“鼓與吹”,事實上是“敬仰”公權力。可見,平民百姓的生活瑣事,蘊含著無數法治因素,雖然老百姓對此贊許諸多,感覺“很有面子”,但在靜悄悄地違法,新聞媒體更是為之“鼓掌”。據此,筆者冷靜思考并作法治多維分析,希望引起全社會根據法治思維重新審視官員證婚的合法性和“現實客觀存在”的合理性。
一、官員證婚的法律性質
官員證婚所涉及到的法學理論與行政法最為密切,從整體上分析法律性質需要事先厘清行政關系、行政權力、行政主體之間的關系。行政活動中行政主體的發號施令、行政相對人的安順服從,行政關系中行政主體的優益地位、單方意志性,皆源于行政權是一種國家權力,而權力一般以“命令—服從”的軌跡運行,因而行政權是一種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管理與被管理的權力,即行政主體代表國家強制被管理者服從的力量[1]201。據此分析,官員證婚雖然不符合嚴格的行政活動標準,也與命令服從不太有關系,但與其中的核心“權力”有千絲萬縷的關聯。婚禮參與人特別相信權力,即使官員不在法定的“工作場所”,他們仍能發現隱藏于官員身份上的“行政權力”。雖然官員所從事的權力工作與婚姻“毫不粘連”,但官員身份為婚禮營造新的高潮,不可能與官員的職權工作沒有學理關聯。可推之,官員證婚的法律性質并不是法定的職權行為,是在沒有法定職責的情形下任性形成的“事實行為”,與行政主體法定要求更是“十萬八千里”,是隱性權力暗地運行的客觀結果。
探析官員證婚的法律性質,還可以著手分析與其緊密聯系的行政權和稍遠關聯的司法權,根據行政權和司法權的相關原理,可以有力地透析官員證婚的法律特性。行政權與司法權都屬于國家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在憲法地位上皆居于立法權之下,都是一種法律適用權,但兩者亦有不少相異點:行政權是積極的權力,司法權是消極的權力;在靈活性方面,行政權與司法權存在極大差異;從行為效力看,行政權效力具有先定性,司法權效力具有終極性;司法權是判斷權,行政權是管理權[1]204-206。據此,官員證婚的“身份行為”與行政權的關聯相對較少,與司法權的實質更近似,在不考慮其主體性合法與否的前提下,一般屬于消極性“權力”(原則上只有受婚姻當事人的邀請才啟動),對當事人婚姻關系作“身份判斷”具有判斷權屬性,在確認當事人婚姻關系上具有終極性,更傾向于沒有被“行政許可”的事實行為,是否有客觀合理性和合法性且聽下文分解。
二、官員證婚合法性分析
依法治國的重點是依法行政[2]15。官員證婚與依法行政有關聯性,總體上歸屬于事實行為,沒有取得法律上的“主體地位”,要判斷其合法或者違法有理論難度,但可以借鑒行政行為理論探析之。合法行政行為指符合法律法規要求的行政行為,其要件包括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符合法定程序、法定權限,符合法定目的等等。違法行政行為指違反法律法規要求的行政行為,其要件包括主要證據不足,適用法律法規錯誤,違反法定程序,超越職權,濫用職權,不履行法定義務等等[3]209。可知,合法和違法的界定標準主要在于:法律法規要求、法定程序、法定目的、法定權限和法定職責等方面,也就是說,如果完全符合上述標準即合法,否則將是違法。
以法官證婚為例分析官員證婚,需要明確法院和法官的應然法律定位。 根據《法官法》:法官必須忠實執行憲法和法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第三條);法官依法履行職責,受法律保護(第四條)。據此可知,法官應當忠實執行法定職責并受到法律保護,是法院職務行為的“代表”,法院通過法官的職務行為履行國家的法定職責,這要求法官行為應當身份相符,超然和居中(居于利益當事人之外)地裁判、解決法律糾紛,衡平當事人間的利益關系,力求達到和諧穩定狀態。根據上述合法、違法標準和《法官法》的強制性要求,法官證婚既沒有宏觀上的法律根據,又不是根據法院授權履行職務行為,更不是完成法定本職工作,完全是在“無法”狀態下偷偷完成的“法外工作”,與法定權限、法定職責和法定目的無涉,根本沒有“合法”的基因。因此,法官證婚是徹頭徹尾的“無法式違法”。另外,中國法官是身份非常特殊的官員,據此完全可以類比推理出官員證婚的違法性,官員在日常證婚中“導演”違法性角色。
三、官員證婚的主體身份分析
官員證婚中的主體是具有公職身份的官員,尤其是擁有較高行政級別的單位負責人,從主體屬性上分析其身份是否符合“依法行政理念”,是否符合“官場潛規則”,剖析其是否具備違法的因子,可以借鑒行政行為的若干理論深入解析。行政行為的基本特征:主體特征——行政主體所做的行為;職能特征——行政主體行使職權、實施行政管理的行為;法律特征——行政主體依據法律規定所做的能產生直接行政法律后果的行為;范圍特征——對外部采取的行為;目的特征——實現國家行政管理目標[4]282-285。據此分析:第一,官員證婚中的主體一般是官員,婚禮上雖然會介紹官員的官職和任職機構,但通常以個體名義利用官員職務身份完成證婚,當然不可能以機構名義(不會有機構的公文和公章)完成證婚,這表明官員證婚并不是機構的職務行為,只是與官員職務身份有關的業余型事實行為,這不能構成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不符合行政主體特征;第二,官員證婚根本不是官員代表任職機構行使行政職權和實施行政管理,根本不符合行政行為的職能特征;第三,官員證婚中官員的任職機構根本不可能承擔由其產生的任何法律后果,所有的積極或者消極的法律后果與之沒有任何關聯,也就是說,任職機構既不分享積極成果,又不承擔消極后果,這不符合行政行為的法律特征;第四,官員證婚不是對外部采取的行為,畢竟證婚與行政主體的職責、職務之間沒有任何關聯的“細胞”,這樣不符合行政行為的范圍特征;第五,官員證婚的目的是滿足當事人對婚姻關系的需要,與國家行政管理目的之間是“十萬八千里”,當然不符合行政行為的目的特征。
剖析官員證婚的主體身份,法官證婚領域同樣存在尷尬的境地。《法官法》第五條規定:法官的職責:依法參加合議庭審判或者獨任審判案件;法律規定的其他職責。《法官法》第六條規定:院長、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除履行審判職責外,還應當履行與其職務相適應的職責。這些是法官履行職責的法律保障和履行職務行為的最基本性概括。以法官證婚為例,法官是公職人員,在法院工作場所身著制服時應是職務行為和履行法定職責,事實上法官身著制服并送婚禮當事人法槌不符合法官職務要求、法定職責和職務身份,院長證婚作為證婚的主體背離院長職務的主體身份。根據公務人員無法律規定不能為原理,法院院長作為普通法官沒有法律依據擁有“證婚”職權,以院長身份“證婚”更是錯上加錯,與審判案件的法定職責、職務格格不入。
由此可見,官員證婚中官員既不是行政主體的代表,又不能依法履行法定職責,所從事的行為與職務行為要求完全“不相關”,導致主體身份非常錯亂,根本不符合行政法原理,造成在事實上的行政性違法,直接破壞法治化進程,更是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水火不容。
四、官員證婚的正當程序分析
對官員證婚作了合法性和主體性分析之后,還有必要作正當程序分析,這需要行政權運行的理論原理作學理支撐。行政權的運行的原則可概括為:行政法治原則、行政公開原則、行政公正原則和行政效率原則。其中,行政法治原則中維護社會公眾的基本權利是根本目的,行政權的運行必須依據正當程序,行政法治原則還必然包括權力制約精神。行政公正原則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1]269-277。可知,官員證婚要滿足正當程序要求,符合程序正義的法律價值,根據官員證婚的現狀,根本不可能符合行政法治原則,更不可能完成行政公開和行政公正的“法定任務”,行政效率在官員證婚中更是“空話連篇”。
正當程序是程序正義的法定要求,對官員證婚作正當程序分析,衡量判斷是否符合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現代法律程序所實現的最低限度的程序正義要求至少應當包括:程序中立性、程序參與性和程序公開性。它們反映在現代行政程序中,可分別概括為避免偏私、行政參與和行政公開這三項原則[5]247-248。根據程序正義的內涵,無法從官員證婚中探尋出程序因子,畢竟官員證婚是非常不正式的“草臺班子”,沒有事先的程序規范約束,完全是根據不同場合隨機性組合而成,程序中立性缺少客觀環境,程序參與缺少動力激勵,程序公開沒有制度保障,由于官員證婚的角色決定了官員與婚姻當事人必定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避免偏私更是“天方夜譚”。
正當程序相對于實體具有獨立的法律價值,發揮積極的法律效用,對官員證婚同樣具有規制作用。正當程序原則的價值體現了對人權的保障,有利于充分保障實體公正,有利于推進過程公開,直接體現了民主精神,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6]426-427。據此析之,官員證婚缺少正當程序的理論浸潤,無法通過正當程序獲得程序利益,而且會受正當程序缺位的影響削弱其科學性,理所當然會缺少相應的人權保障,無法實現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無法推進過程公開,更不可能有民主精神貫穿全過程,反而會影響全社會(尤其是官員社會)的法律意識。
五、官員證婚的權力運行分析
官員證婚并非簡單的市民行為,而是比較隱蔽的隱權力行為,利用官員的公職身份“光明正大”地為民眾證婚,公權力在其中偷偷作怪,為法治社會制造“負面清單”,換言之,官員證婚是變相形式的濫用行政權行為。行政權的運行是指行政主體為實現特定目的而運用和行使行政權的過程,或者說是行政權被運用或者行使的過程[1]264。可知,官員證婚并非行政主體(官員)為實現特定的行政目的而使用行政權,雖然不是以行政主體的名義完成,但官員的行政身份卻在“大行其道”并“暢通無阻”,與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理念背道而馳,在權力運行軌道上“不按規矩出牌”理應受到學理反駁。
分析官員證婚的權力運行路徑,可以借鑒意思行政行為和實力行政行為理論深析之。意思行政行為是基于意思表示對行政相對人發生作用,而實力行政行為是通過一種實際的力的作用對行政相對人所作的行為。意思行政行為因行政主體的意思表示而產生外部的法律效果,所以意思表示是法律需要規范的重點。而實力行政行為主要表現為通過力的作用產生的客觀活動,法律關注的重點應是行為的外在狀態及結果[7]352。可知,官員證婚更類似于實力行政行為理論要求,根本不可能是官員的任職機構的意思表示,不可能對婚姻當事人發生法律效力,只是官員依托職務身份通過官職的“余熱”產生的事實性客觀活動,雖然不能發生應然的法律效力,但在事實上卻有相當大的“市場份額”,婚姻當事人以此刷出婚姻“存在感”。具體析之,官員證婚是為了證明婚姻關系的事實存在,證婚主體是官員,性質是非職務行為,官員沒有證婚的“法定職責”,更不存在相對應的“法定目的”,導致官員證婚歸屬于無法型違法。與此有關聯的是公證機關證婚,證明存在婚姻法律關系。《公證法》第二條規定:公證是公證機構根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依照法定程序對民事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的活動。據此,按照公證程序公證婚姻關系,具有確定性的公信力,而官員證婚并非依公證程序證婚,完全是行政(司法)權力無序擴張,不能取得公證證婚相同或相似的法律效果。
官員證婚的權力路徑還要挖掘行政職權的理論來源。任何職權的來源與作用都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否則越權無效,要受到法律的追究,要承擔法律責任。行政職權來源于法,一切行政行為以行政職權為基礎,無職權即無行政,意味著擁有行政職權的行政主體必須依法設立,具有法定依據。行政職權受制于法,這是對權力行使的要求,構成職權法定原則的核心,越權無效,并應承擔法律責任,要求行政主體不得越權,如果越權則不具有法律效力[5]167-168。據此,官員證婚并非官員的法定職責和職權,而是權力任性擴張的結果,屬于沒有法律根據的越權行為,沒有任何法律規制之,處于法外運行的非法狀態,完全沒有法律效力,甚至還要受到法律追責。
六、官員證婚的法治異化分析
分析官員證婚的權力運行路徑圖之后,它還會異化運行,集中表現于行政權和司法權異化方面,需要作法治異化分析。根據公權力運行原理,職權與職責不可分離,權力的不可交換是公權力的一個重要特征。行政主體—行政權限和行政方式—行政客體構成一個結構嚴密的行政權內在邏輯體系。當行政權異化時,它的內部結構中的各要素發生分離:第一,行政權與行政權主體發生了分離;第二,行政權與行政權限、職責、職能發生了分離;第三,行政權與特定行政方式發生了分離;第四,行政權與行政權客體發生了分離[1]290-291。據此分析,官員證婚發生了法治異化,為了分析之特在學理技術上假定官員證婚為行政權,具體表現為:
第一,行政權和行政主體相分離,即官員證婚的行政權本身與官員的任職機構(行政主體)發生分離,表明行政主體不會口頭或者書面認可官員證婚的法律結果,會以證婚行為與職務無關拒絕承認證婚的法律效力,既不分享證婚產生的積極成果,也不承擔證婚產生的不利后果。
第二,行政權與相應的職責、職權、職能發生分離,即官員證婚作為行政權,與行政主體相對應的法定職責、法定職權和法定職能嚴重背離,既不是履行上述職責、職權和職能,又與其法定性產生價值沖突和現實矛盾,從而發生法治異化的結果。
第三,行政權與特定行政方式發生分離,即行政權必須在依法行政的范圍內行動,必須符合法律的明確規定,但官員證婚即異化行政行為方式,在法定方式之外另辟依托行政身份完成事實性行為,本質上根本不是行政行為,只是事實上的證婚,無法為證婚提供法律基因。
第四,行政權與行政客體發生分離,即官員證婚與所證的對象客體分離,婚姻關系是婚姻登記機關的法定事項,官員證婚卻在事實上“耕別人家的地”,不僅得不到感謝,而且還會受到指責隨意“跨界”,甚至還會為此承擔法律責任。
由此可見,官員證婚是權力異化的必然結果,不僅無法取得預期的法律效果,而且會使婚姻當事人產生誤解,甚至還會在全社會樹立誤導性的標志,容易產生官員證婚替代婚姻登記的法律誤解,于己于人于國都相當不利,將重創法治社會秩序,讓法治理念“損兵折將”,下一步有必要深析官員證婚的法律效力狀態。
七、官員證婚的法律效力
官員證婚是否可以發生預期的法律效力,需要結合行政權理論分析,其中越權無效原則是最有效的理論根據,即官員證婚作為行政權必須要有明確的法律根據,否則沒有充分的法律根據即為無效。越權無效原則最初創制于英國,也是英國行政法的首要原則,是行政法的中心思想和主要武器,公共機關不能在職權范圍以外行事,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理[6]357。越權無效原則的價值在于對行政權的控制和對相對人權利的保障,對程序的重視和保障,是司法審查中的重要標準[6]361-363。據此可知,官員證婚是明顯的“無法型”越權,做了不該做的事,在不知不覺的過程中違法,當然不可能發生預期的法律效果,在法律價值上受到否定性評價。
官員證婚的初衷(經濟目的)是為了節儉開支,證明婚姻關系是存在目的和行為核心。其實,證明婚姻關系是公證機關的業務范圍,不能成為官員的業余性工作,正當程序是依訴訟程序確認是否存在婚姻關系,即使是無效婚姻和可撤銷婚姻都需要依訴訟程序“竣工”。《婚姻法》第八條規定:要求結婚的男女雙方必須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進行結婚登記。符合本法規定的,予以登記,發給結婚證。取得結婚證,即確立夫妻關系。可知,婚姻關系確立的唯一標準是結婚登記,符合實質要件并完成婚姻登記才形成夫妻關系,時間起點是婚姻登記完成之時,反言之,其他任何方式都不可替代婚姻登記,婚姻登記的法律效力不能被任何事項所否決。而官員證婚沒有法律根據,更沒有法定程序可言,直接當場宣布男女雙方締結婚姻關系,如果當事人之前已經完成婚姻登記,官員證婚完全是法外性多余,根本不能改變婚姻登記的法律效力;若雙方“被證婚”之前沒有完成婚姻登記,官員證婚會引發嚴重的法律沖突,當事人沒有完成法定形式的婚姻登記,而官員宣布他們的“婚姻”有效,此時婚姻關系的法律效力并非來源于法定,當然不可能合法有效,也不可能認為是官員對婚姻關系的“事實確認行為”。造成沖突和矛盾的關鍵在于官員宣布他們之間存在婚姻關系,當事人據此僅僅邀請官員證實宣布婚姻關系合法有效,可以不用甚至拒絕完成婚姻登記程序,這將造成締結婚姻關系模式的二元格局,明顯違背婚姻法中“婚姻登記法定主義原則”(筆者首創語)。
八、官員證婚的法治危害
官員證婚具有違法性,不能發生預期的法律效力,做了法治的“無用功”,是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中衍生出法治危害的“副產品”。理解其法治危害,需要分析法治的內涵和基本理念。法治的基本理念是強調平等,反對特權,注重公民權利的保障,反對政府濫用權力。由此,法治應有幾個最基本的特征:第一,法治不只是制度化模式或社會組織模式,而且也是一種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識。第二,法治作為特定社會人類的一種基本追求和向往,構成了工業化和民主化的秩序基礎。第三,法治的最重要的含義,就是法律在最高的終極的意義上具有規限和裁決人們行為的力量,法律既是公民行為的最終導向,也是司法活動的唯一準繩[8]165。可知,官員證婚的法治危害是全方位立體的、深遠的和持續發酵的,在不知不覺的過程中發生并完成,如同長期控制性人口政策對國家和社會造成的重創傷害一樣,當時并不會覺得“陣痛”,但在數年后會感覺“慘痛”,沒有挽回的余地。
事實上,官員證婚是全面依法治國過程中的非和諧因素,與和諧小康社會建設目標背道而馳,完全不能契合“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法治標準,甚至直接破壞法治秩序,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步伐格格不入。官員證婚基于似乎既“合理”又“合情”的目的(節儉方便)而為之,客觀上公然違法挑戰法治秩序,無論如何改變不了違法的本質屬性。我國全面推進“四個全面”偉大戰略布局,將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目標,必須及時按照“四個全面”要求制止公然違法,堅決否決挑戰法治秩序的不良舉措,政府官員和社會民眾應當認識到官員證婚的法治危害,積極地改善法治生態環境,共同為推進和諧法治和實現法治和諧貢獻力量。
總而言之,官員證婚違反法律規定,超越法定職責從事法外行為導致法律沖突,是法治建設中的不和諧舉動,根本不符合依法治國理念,更不契合“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求,不僅不能提倡,而且要堅決制止之,避免制造官員行為與職務、職責相沖突的情形。因此,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行事,堅決反對“官員證婚”現象,在理論上支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踐上為兩個百年夢想“添磚加瓦”。全面依法治國需要全面深化的改革的密切配合,重點需要規制官員的生活行為,需要對官員在生活法治中提出更高的法治要求,其中官員證婚是理應制止并堅決反對的不良社會現象,它既毒害了全社會的法治細胞,又損害了官員與民眾之間的正常關系。
[1]胡建淼.公權力研究: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
[2]葉必豐.行政行為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3]胡建淼.行政法學[M].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楊建順.行政規制與權利保障[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5]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則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6]胡建淼.論公法原則[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
[7]胡建淼.行政行為基本范疇研究[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
[8]秦前紅.憲法原則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責任編輯 劉成賀)
The Legal Analysis of Officials as Marriage Witness
HU Li-ming
(School of Law,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Official marriage witness is newfangled social phenomenon, and in the daily life it is common and popular, so that people and officials applaud it and it can attract media’ particular attention. Actually, it is that officials inadvertently and quietly engage in illegal behavior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in that it not only obtains no authorization and capriciously makes it, but also makes confliction with the marriage registration, so as to result in embarrassment and conflict of legal validity between the above two, distort neutral role of official justice administration, seriously deviate from the concept of rule of law in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and have serious impact on the principle of rule of law for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 Accordingly,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analyze deeply its invalidity and illegality from legal nature, legitimacy, subject identity, due procedure, power operation, alienation of rule of law, legal effect, harm of rule of law and so on.
official marriage witness; validity of marriage; law-based administration
2015-10-03
胡利明(1979—),男,湖北孝感人,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經濟師,法律顧問。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6.006
D912.1
A
1008-3715(2015)06-002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