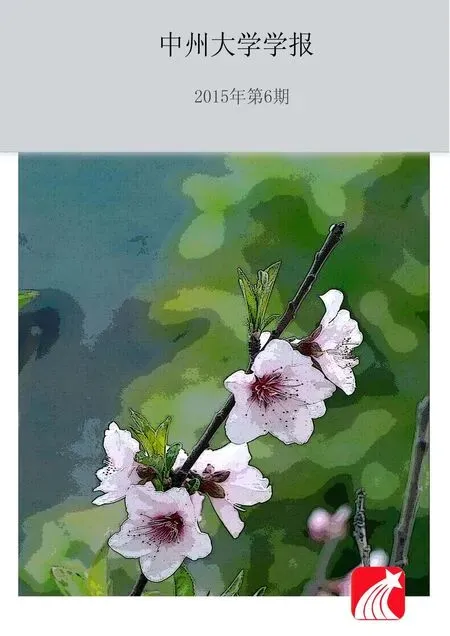灰暗的突圍
——讀墨白長篇小說《欲望》
魏華瑩
(鄭州大學 文學院,鄭州 450001)
?
灰暗的突圍
——讀墨白長篇小說《欲望》
魏華瑩
(鄭州大學 文學院,鄭州 450001)
墨白的長篇小說《欲望》,將欲望敘事與近三十年的時代背景緊緊纏繞。解讀這部作品,剖析作者如何呈現一代人的欲望,不僅可以發現作者對人生、人性的總體反思,對于一代人的成長史、精神史也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
《欲望》;斷裂;突圍
2013年,墨白的長篇小說《欲望》出版。這部57萬字的作品,故事時間跨越30年,被分為紅卷、黃卷、藍卷,講述譚漁、吳西玉、黃秋雨三個同年同月同日生且為同鄉同學的人生故事。設定這樣的巧合,是為了從不同角度闡釋同一背景的人如何“沉溺”于欲望的汪洋大海。誠如作者在后記中講述,“對權力的欲望,對肉體的欲望,對生存的欲望,欲望像洪水一樣沖擊著我們,欲望的海洋淹沒了人間無數的生命,有的人直到被欲望窒息的那一刻,自我和獨立精神都沒有覺醒”。欲望書寫是20世紀90年代文學的重章華彩,也許是因為“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個人的存在價值”[1]171。從《廢都》到《我愛美元》《私人生活》《一個人的戰爭》,對本能的欲望書寫成為擺脫意識形態壓抑后重要的文學現象,也留下了許多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橫斷面作品。墨白耗費二十年心力,將欲望敘事與三十年的時代背景緊緊纏繞。解讀這部作品,去剖析作者如何呈現一代人的欲望,不僅可以發現作者對人生、人性的總體反思,對于一代人的成長史、精神史也會有重要的意義。
一、進城故事
在訪談中,墨白多次提到自己是屬于“90年代”的,這和他在20世紀90年代發表大量的文學作品有關,也和個人的生活軌跡轉變有關。《欲望》的書寫同樣始于20世紀90年代,故事開篇,就講述小學教師譚漁在1992年春天結束了34年的鄉村生活,進入了城市。
譚漁立在城市繁華的街道邊,城市的五光十色使他眼花繚亂,他站在街道旁,如同一個旁觀者。一輛接一輛小轎車從他身邊飛箭一般穿過,粉綠色淡黃色的高層建筑在陽光下依次立在街道的兩旁。許多衣著漂亮入時的女郎和瀟灑的男士騎著摩托車或者輕便車如水一樣在陽光里流動。這一切都使譚漁感到親切,這使他想起了潁河鎮。那座骯臟的小鎮在他的記憶里突然變得是那樣地猥瑣,在城市的眼睛里那小鎮如同一個身穿舊棉襖蹲在陽光里取暖的老農。是有點像老農。譚漁長長地出了一口氣,我現在也是城里人了![2]96
“進城”故事在當代文學中一直是個重要話題,從《陳奐生上城》到“高加林進城”(《人生》)。在長期的城鄉二元對立結構中,進城也成為一代鄉村青年“奮斗”的目標及擺脫貧困生活和“恥辱”身份的象征。譚漁的進城,使我們不得不想到作者墨白,想到他的人生在這一年發生的重要轉變——1992年,墨白從工作了11年的潁河鎮小學調入周口市文聯《潁河》雜志編輯部,此前,是長久的貧困孤獨的鄉村生活。
1976年的春天,我高中沒畢業就外出獨自謀生。在我出外流浪的幾年時間里,我當過火車站里的裝卸工,做過漆匠,上山打石頭,燒過石灰,被人當成盲流關押起來。那個時候我身上長滿了黃水瘡,頭發紛亂,皮膚骯臟,穿著破爛的衣服,常常寄人籬下,在別人審視的目光里生活。我師范畢業后,又回到了那個偏僻的小鎮,在那個只有十個班級的小學里我一待就是十一年。[3]4
青少年時期的窮困,小鎮生活的孤寂,以及不言放棄的心靈,譚漁(墨白)憑借自己的努力奮斗,終于從潁河鎮來到城市,心中難免欣慰。對于譚漁,抑或對于墨白,他們是通過“寫作”走入城市,惟有寫作和文學能帶來自信,然而,“進城”之后的故事卻已然不是理想中的情節。譚漁面對城市建筑的擠壓時,是靠手中的《莽原》雜志(刊載了他的一部中篇小說)得到勇氣和自信。當他一手提著挎包,一手拿著發表自己文章的《莽原》雜志,進入文學編輯部時,卻發現自己的時間和現實的時間已經錯位,外部世界已經悄然發生改變。20世紀90年代,文學的時代激情早已經煙消云散。在偏僻的鄉鎮小學,譚漁還能和志同道合的同事結成“詩社”,互相交流習作心得。然而,當他真正走入文學的“中心”——編輯部,卻發現文學已不如他想象的那般神圣。編輯部里的同事忙著四處掙錢,“這個社會沒錢不中!沒錢你就活得寒磣,沒錢你就進不了國王大酒店!”這樣的話使他感到吃驚,因為被自己崇高的文學理想所鼓噪,他不認為自己活得有多苦,仍然認為世上再也沒有比搞文學創作更有意義的了。
昔日輝煌的文學雜志紛紛改刊,譚漁素來欽佩的編輯汪洋忙于組織中學生愛情詩大獎賽,尋求市場和發行量去賺錢,因為其所供職的內部刊物,“全靠政府給的這點事業費,就這點事業費,明年給不給還是個謎,現在不正提倡斷奶嗎?”譚漁無話可說,心中突然生出一種傷感來。對他來說,“文學就是他走進城市的精神支柱”,[2]86但是,隨著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那個曾經驚濤駭浪的文學大潮,那景象、勁勢、氣概、精髓,都已經無影無蹤,魂兒沒了,連那種‘感覺’也找不到了”[4]。
20世紀80年代是屬于文學的年代,是被許多文人知識分子所留戀的“中國的浪漫時代”。據詩人徐敬亞稱,到1986年他策劃“現代詩群體大展”時,全國光詩社就有2000多家,“自謂詩人”百十倍于此數。校園之外,人們對文學也是熱度不減。由建筑工人北島、待業青年顧城、紡織女工舒婷等人支撐的油印本民間文學刊物《今天》,在校園內外都受到追捧。[5]在墨白供職的偏遠鄉鎮小學校園里也有著溫暖的“詩社”:
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正是新時期詩歌的繁榮時代,大批的民間詩歌團體紛紛在詩歌報刊上亮相,十分壯觀。那個時候我們小學的幾個青年老師也成立了一個文學團,叫“南地文學社”,而我們當時主要是進行詩歌創作。那個時候我們不但訂了大量的文學刊物,比如《收獲》《十月》《人民文學》《世界文學》《外國文學》《蘇聯文學》《文藝報》,那個時候的《文藝報》還是以刊物的形式出刊的,同時我們還訂了許多詩歌刊物:《詩刊》《星星詩刊》《詩歌報》《詩選刊》等等。所以我對新時期的詩歌進程是十分熟悉的,而且我本人也寫詩,我自己有兩本手抄本詩集,裝訂得像正式出版的書籍一樣,從封面到版式都是我自己設計的。[6]87
“現代社會不是由相互層疊、邊界清晰的群體構成,而是由同時具有多角色、多參照標的個體組成。根據社會條件和歷史情境,他們根據自身個體或集體的以往經歷來選擇參照和身份認同的不同形式。”[7]3當譚漁或墨白拿著《莽原》雜志進入城市之后,卻發現文學的無力以及金錢的吞噬力量。作品中,譚漁一次次重返錦城,尋找過去的記憶,當文學的支柱坍塌之后,在編輯部(城市)找不到認同的他只有退守到自我的小小空間。所以在小說中,我們才會看到譚漁一直在拒絕“時間”。
他每天就在這間沒有陽光的屋里翻開作者的來稿,給作者回信,畫版,讀校樣,接待業余作者,空閑下來的時候他就讀點書,讀點新到的期刊,讀點報紙。到了夜間,他又要構思自己的小說,用力爬格子。他屋里沒有電視,沒有錄音機,沒有收音機,甚至連一個鬧鐘也沒有,在這里他幾乎喪失了時間的概念,他幾乎成了一臺機器,在城市里一個極小的空間里生存著。“我多像一只鳥呀,一只關在籠子里的鳥。”這種想象又一次把他拉進現實里,孤獨感再次襲來。[2]117
我們可以看到《欲望》故事的游離。紅卷中譚漁的故事是以時間為概念界定的,如1993年元月8日、1995年12月3日、1996年11月6日、1992年春天、1998年深秋。此后的黃卷、藍卷就變成了人物和空間,時間已然消退。當看到譚漁試圖用理想主義來對抗世俗,孤獨地在文學的小道上掙扎,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什么墨白一再強調重回潁河鎮,去繪制自己的文學地圖,“人們面對如此眾多的他人,而這些人都是陌生者,他必須越來越退守到自身當中以便能夠應付得來,這種從他者處退縮就像一只蝸牛縮回到自己的殼里。”[8]73也許,這種撕裂感不僅僅屬于墨白,它也屬于閻連科,屬于余華,屬于那樣一代離開精神故土從而在文學故事中追憶的寫作者。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閻連科重返“耙耬山脈”的努力以及余華與北京的重重隔閡。所以墨白才會說:“我是一個游離于主流之外的寫作者。由于我的生活經歷,在我言說個人的時候同時去言說現實是身不由已的事,那是我骨子里散發出來的一種氣味,我無法改變。我是以個人的言說來輻射現實的。”[6]36
二、斷裂之后
不管怎樣,隨著20世紀90年代城市化進程,進城故事的綿延越來越廣。“1985——1990年只有1.5℅的農村人口轉移出去。”[9]4“1990年我國城市只有467個,而到1995年則增加到640個,1999年更達到668個,城市以每年幾十個的驚人速度在增長著,而我國城市人口從1990年的1.1825億增加到1999年的2.3億。”[10]這一時期,進城故事不僅僅是地理空間的轉換,也意味著歷史時間的斷裂。之前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延續已久的“超穩定結構”,20世紀90年代以來,卻是一個迅速“斷裂”的社會。伴隨著城市化進程,越來越多的人成為夾縫中的人:一方面是難以融入的城市,一方面卻是無法回歸的鄉土。一定程度上,進城也意味著和之前的人生經驗告別,譚漁離鄉之后,雖然有對城市不盡人意的不滿,卻發現自己和鄉村的迅速隔膜:
現在,呈現在他面前的潁河鎮小學是那樣的破爛不堪,我在這樣的學校里一住就是十一年嗎?他仿佛看到自己昔日的身影在這所學校里走動。可我以前怎么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呢?他面前的兩間西廂房同樣是那么寒磣,土墻壁破木門,我就是在這樣的房子里一住十一年嗎?門開了,兒子朝他撲過來,他把兒子摟在懷里,妻子立在他的面前,妻子突然間顯得是那樣的蒼老,妻子撫摸他的手是那樣的干燥,這就是和我一塊生活了十年為他生兒育女的女人嗎?[2]123
與此同時,卻是城市經驗的匱乏,多年以來,譚漁一直生活在偏僻的鄉下,他從來沒有過和一個陌生女人在夜間一同走路的經歷,這種情景的出現使他有些心慌意亂。
譚漁的心突突地跳幾下,他有些緊張。他從來沒有進過這樣的餐館,以往他曾經參加過幾次外地的筆會,也算見過世面,可那都是現成的,人家上什么他就跟著文友們吃什么,他光知道好吃,卻連一個新鮮別致的菜名都叫不上來,他看著文友用筷子點著新上的菜說這是什么什么,他只有汗顏的份兒。現在他一瞅菜譜,那些菜的價錢讓他暗暗地吃了一驚,這一頓飯起碼要花去二三十塊錢,二三十塊錢都快頂住他家半個月的伙食費了,他有些后悔,今天真不應該跟著她出來吃飯。[2]105-106
雖然進城之前,有掙錢揚名的豪情壯志,但與城市女人葉秋交往中的不知所措,與商人方圣、李文國慘敗的“下海經歷”,都使得譚漁無法找到方向,他不得不感慨,“咱沒有根,咱的根還在鄉下”,“他終于明白,城市的河流仍舊在拒絕他,他們把我們當成一滴油,我只能是一滴油,只能永遠地在水面上漂浮,盡管在陽光下他做出了許多美麗的圖案,但那條河流卻不愿容納他”[2]119。譚漁“明白這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迷宮,他知道他沒法走通這個迷宮,我一個文弱書生一個從鄉間趕來的農民的后代,在這座迷宮里最終將被折磨得筋疲力盡”[2]111。他只有左右搖擺,隨波逐流,迷失自我。
這一時期,隨著“進城故事”的延續,發生斷裂的不僅僅是個人的時空,更有著社會時間的斷裂。相較于20世紀80年代文學的宏大敘事,作品與時代同構,20世紀90年代文學更加關注自我,使得欲望書寫以更加合理化的方法進行。以1993年《廢都》為標界,沖破種種障礙,寫出知識分子的壓抑和突圍,受到“嚴肅”批評,隨之而來的,卻是欲望書寫的步步張揚。女性寫作者林白、陳染、衛慧、棉棉等更是將欲望寫作推向極致化的境地。“這批作家的生存環境和人生體驗,決定了她們更多地感受并接納了當下物質主義的社會時尚與后現代的文化氛圍。體現于她們的作品中,不僅性愛欲望的隱秘性和羞恥感已不復存在,而且情愛欲望的書寫也不再作為反抗某種觀念意識的手段,直接地就構成一種目的,一種不需要意義、僅僅是單純的肉體快樂而已。”[11]雖然在當時,因寫作的大膽暴露而廣受批評,但對個體自我的關注以及人性的挖掘更加綿密深入。20世紀90年代的欲望化小說寫作“成功地扭轉了小說創作中長期硬化成結的國家話語,使國家話語轉向個人話語,使代神代政代集團立言,走向代自我立言,從而阻死了那種代歷史、群體的名義強加他人的思想之上,并進而為思想控制留下空間的做法。”[12]75
墨白更為關注人心、人性的幽暗之處,如他所言,“我們所有有著鄉村背景的人,來到城市,做人的尊嚴都會受到挑戰。在過去的城鄉二元對立的國策里,農民失去了作為人應有的尊重和尊嚴,多年的不公形成了他們自卑的心理。現在他們來到了城里,他們的價值觀、道德觀都受到了強烈的沖擊,他們會感到無所適從。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有這么多的農民離開自己的家鄉和土地,這個社會是一個動蕩的社會,面臨著巨大的心理混亂。這個心理混亂,一方面是由于生存的困境帶來的,另一方面是由精神的困惑所帶來的”[6]32。對于墨白來說,“城市就是在這樣的欲望之中無休止地膨脹著,空氣中充滿了銅臭的氣味,但又是那樣的冰冷,那樣的缺少情感”。“冰冷”也許是我們理解其寫作的關鍵詞,那就是無法找到溫暖的力量。作品中,譚漁和“紅顏”葉秋的交往是少有的溫情細節,如葉秋品讀他的作品,為他舉辦的文學座談會。
在后來的許多日子里,那次有關文學座談會上的許多細節都被譚漁淡忘了……那天他們一起走出那幢教學樓的時候,葉秋激動地對他說,講得好,講得太好了。……葉秋說話的聲音化成了一支曲子時常在我的感覺里響起來。在他們分別握手時,譚漁在夜色里拉住葉秋的手,他用了一下力,又用了一下力。那只手仿佛已經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種情感,一種情感的相互傳遞,這是那天晚上留給譚漁最深的印象。[2]121
但葉秋的身份是城市女人,她雖然被設定為一個不世俗的女人,曾因看不上丈夫的銅臭氣而離婚,卻有著現代城市的認同法則,她又會這樣教育譚漁:“看來只有你這樣傻了,你知道現在是啥年代?誰還這樣一心一意地做學問?你看人家都在干啥,都在撈錢。”“你想成為大家,就得砍斷你的根,你應該遠走高飛,你身上的包袱太重了!”心靈之友也是如此的認知邏輯,譚漁唯有以寫詩表達自己的孤獨,卻又發現“沒有文字能表達我的憂傷”,終于沉溺于欲望。作品中,越來越多的人在欲望中迷失,有金錢欲(汪洋、錢大用、譚漁)、名利欲(吳天夫、吳西玉)、愛欲(譚漁、小慧、小紅、尹琳、吳西玉、五仙女、黃秋雨、米慧等)、表現欲(錢大用)、傾訴欲(趙靜、尹琳),尤其是愛欲,更是得到極致書寫。
“提高社會等級的欲望的受挫,不僅意味著必須放棄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而且還意味著社會尊重也遭到破壞,以及隨之而來的自尊的喪失。……拉斯威爾已經證明,一旦‘成功的自我’以前的理想被攪亂以及以前的態度被弄得無目的,舊的沖動便向內轉化,并采取自我懲罰形式,從而退化為受虐狂的,或心理上自我毀壞的放蕩。”[13]84于是,譚漁和妻子離婚,在情人葉秋之外,他還在小慧、小紅的誘惑中自我放縱,甚至自己都發生質疑,“是什么驅使我來這里呢?是愛情嗎?我都快四十歲的人了,我為什么還會這樣呢?我是一個靈魂骯臟的人嗎?”墨白在作品后記中刻意表達:“人的尊嚴是我寫作《欲望》時思考最多的一個問題。”斷裂之后如何重建自我,如何尋找突圍之路,是墨白小說更為關注的內容。
三、突圍的可能
眾所周知,墨白是學習繪畫出身,對色彩有著更為深刻的認知,作品也分為紅、黃、藍三卷。我們記得聞一多那首詩歌《色彩》:“生命是張沒價值的白紙,自從綠給了我發展,紅給了我情熱,黃教我以忠義,藍教我以高潔,粉紅賜我以希望,灰白贈我以悲哀;再完成這幀彩圖,黑還要加我以死。從此以后,我便溺愛于我的生命,因為我愛他的色彩。”墨白在《欲望》中以三原色為主軸,調出形形色色的欲望。小說的精神是復雜性,每部小說都在告訴讀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復雜。”[14]20種種欲望和放縱不僅沒有改善煩惱人生,反而加速自我毀滅,在墨白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各樣欲望導致的悲傷以及死亡:錦的姥姥死去、錦的自殺、錦的兒子小漁的死、汪炳貴的死、車禍撞死的女人、季春雨父親的死、季春雨殺人及被抓、涂文慶強奸殺人、于天夫死于癌癥、七仙女的兒子被綁架殺害、七仙女的瘋和死、吳西玉的車禍、黃秋雨死于謀殺以及栗楠因車禍成為植物人等。還有形形色色的離婚與背叛:雷秀梅的夫妻爭吵、小慧父母鬧離婚、譚漁離婚、陳浩的離婚、葉秋離婚、汪洋離婚;吳西玉與尹琳的婚外情、牛文藻母親的性丑聞、楊景環鬧離婚、陳仙芝鬧離婚,以及林林總總的瘋狂,如錦的瘋、七仙女的瘋、牛文藻的瘋狂行為等等。
這種無關善惡,沒有明確道德指向的壓抑性敘事方式也被有的研究者視為“零度寫作”,但這又無法涵蓋墨白對人生、對時代的發問,對歷史的反思。在作品中,他會讓小慧來質問譚漁:“什么東西能代表我們的這個時代呢?”在關于歷史的敘述中,又有意植入各種歷史事件,如劉少奇的死、大躍進造成的信陽事件、艾滋病的泛濫、新疆的阿拉木圖、遇羅克的《出身論》、紀念碑的坍塌等等,那些被植入的宏大歷史與無法命名的瑣碎欲望形成鮮明對比。盡管三部曲以明亮的紅、黃、藍開卷,作品的底色、基調總是灰暗、陰晦的,每個人都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只能在欲望中毀滅。
作家總是“講故事的人”,不管他用何種方式。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30年中國故事在作家筆下并沒有得到有效重建,也有批評家將其稱為“介入現實的乏力”,盡管有各種因素,但對社會缺乏同構性也是不爭的事實。所以,余華才會說出“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閻連科才講到“現實的荒誕正在和作家的想象力賽跑”。跳躍性發展的社會形態也給更多的人帶來不適之感,作家的自我人生都是斷裂的,如何來表達多種復雜經驗成為令人困惑的命題。這使我們不得不想到墨白,面臨著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轉型,當眾多的先鋒作家經過市場規訓和自我調適重回現實主義的寫作旅程中,墨白卻堅守先鋒寫作,用夢幻、記憶來建構自己的文學世界。“孤獨”一直是《欲望》三部曲中揮之不去的話題。墨白和同代人莫言、閻連科有著相似的人生經歷,是饑餓生存所帶來的沒有尊嚴,家庭成員的“歷史問題”所帶來的種種挫折,卻最有責任意識的一代,因為他們的出生、成長是和共和國同構的,即便是被譽為“海派傳人”,最擅長城市書寫的王安憶,也自我強調是“共和國的女兒”,所以,他們的故事總是帶著極強的社會意識。從這個角度,我們或許可以找到墨白在欲望化城市中,試圖以“潁河鎮”作為根據地,重建“精神原鄉”的努力。
從1980年的9月到1991年的12月,整整十一年零三個月,這段時光我是在故鄉的小學里度過的。……現在夏季的太陽還沒有升起,城市如林的樓房如海的綠色樹冠已經開始增長氣溫,樓下穿梭般的汽車和遠處傾吐灰煙的煙囪,使我感覺到我離那段寧靜的鄉間生活越來越遠了,我怎樣才能在這個崇拜金錢和權勢的社會里,抵達那段生活清貧而精神富足的時光的腹部呢?[15]79
在這里,作者將外部世界詮釋為金錢和權勢,而試圖抵達理想的內心,生活清貧而精神富足。現代化、城市化既是社會進步,也是資本邏輯、財富邏輯、發展邏輯、理性邏輯的同步建構。對于墨白來說,“文學的問題首先應該是心靈的自省和自救”[16]416。在作品中,灰暗、堅硬、冰冷的城市被欲望、恐懼包裹,只有遙遠的故鄉是溫暖的腹地、理想的所在。因此,作者通過夢境、幻想和記憶來尋找精神自足的力量。“真正的藝術作品,我們時代的真正的先鋒派,完全不遮掩藝術與現實之間的這種疏遠,完全不減弱兩者之間的差異而是擴大差異,并且強化它們自己同所給予的現實之間的不可調和性,其強化的程度達到使藝術不能有任何(行為上)應用的地步。它們以這一方式履行了藝術的認識功能,……讓人類面對那些他們所背叛了的夢想和他們所忘卻了的罪惡。”[17]255
所以,他才會用龐大而駁雜的《欲望》三部曲來詮釋自己的寫作理念,在城市欲望巨大的吞噬力中,譚漁從《裸奔的年代》中的主角,失去鄉土身份卻難以融入城市的掙扎者,到《欲望與恐懼》中的看客,再到《別人的房間》中黃秋雨的故事揭秘者,通過立體交叉的方式建構一代人的生存困境。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給一代人帶來極大的精神不適,也許是懷戀20世紀80年代的理想主義和人文情感,也許是精神世界坍塌之后重建努力的種種失效,也許是荒誕、碎片化的現實難以言說,導致介入現實的困難。即便在正面直擊的作品,如閻連科的《炸裂志》,也以“神實主義”的方式自我命名。《欲望》如何來表達這個時代,作品并不明晰,那不斷穿插、跳躍的歷史,那灰暗、晦澀的夢境,都在有意模糊我們的閱讀視野,但一個個灰暗的欲望故事卻也暗合了作者對欲望的理解。從譚漁的精神坍塌,到吳西玉的不知所終,再到黃秋雨的死于非命,都是一個個黯然神傷、悲慘無比的欲望故事。在這個意義上,墨白是有自省能力的作家,他不僅僅囿于講故事,而是試圖以夢幻、記憶等多種方式將個體痛苦和時代痛苦的蓋子揭開,對他來說,“一個作家要有勇氣面對自己的內心世界,面對自身痛苦的根源,并不斷地進行自我的解剖”“我理解的寫作應該是這樣的:無論世風怎樣變化,無論在任何情景下,他們獨立的人格都不會被權勢所奴役,他們自由的靈魂都不會被金錢所污染,那是因為他們的寫作是來自他們的心靈深處,是對自己行為的懺悔與反省,他們對媚俗的反抗、對社會病態的揭示、對人間苦難和弱者的同情、對人類精神痛苦與道德焦慮的關注等等,這些因素構成了他們的姿態。”所以,他讓人物一遍遍地重訪、回到故地,也許對于墨白來說,潁河鎮更多地是一種心靈原鄉,一種精神富足的靈魂棲息地。那些壓抑性敘事所呈現的痛苦盡管隱秘,但努力打開它,使我們認識到內心的幽暗,使我們不囿于欲望的侵襲,來尋找內心深處的純凈力量。在這個意義上,盡管種種突圍是灰暗的,但其借喻的世界卻是明亮和多彩斑斕的。
[1]余華.我能否相信自己[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8.
[2]墨白.欲望[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3.
[3]林舟.以夢境顛覆現實:墨白書面訪談錄[C]//劉海燕,編.墨白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
[4]馮驥才.一個時代結束了[J].文學自由談,1993(3).
[5]歐欽平.文學遠離80年代盛況之后[N].北京:京華時報,2011-03-29.
[6]墨白.小說的多維鏡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
[7]〔法〕格羅塞.身份認同的困境[M].王鯤,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8]〔英〕英格斯.文化與日常生活[M].周書亞,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
[9]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10]薛小和.城市化道路怎么走[N].北京:經濟日報,2000-05-19.
[11]管寧.轉型社會語境下的欲望書寫與美感形態:對20世紀90年代小說創作一個側面的考察[J].南京社會科學,2001(12).
[12]王岳川.中國鏡像:90年代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13]〔德〕曼海姆.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現代社會結構研究[M].張旅平,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14]〔捷克〕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M].董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15]墨白.鳥與夢飛行[M].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15.
[16]墨白.夢境、幻想與記憶[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
[17]〔美〕馬爾庫塞.藝術作為現實的形式[M]//董學文,榮偉,編.現代美學新維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責任編輯 許峻)
The Dark Breakout ——Thoughts onDesireby Mo Bai
WEI Hua-y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 China)
Mo Bai’s novelDesireintertwines the desire narration and the past thirty years closely. Interpretation of this book and analysis of the author’s presentation of people’s desire can not only help to find the author’s overall reflection of human nature, but also have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realizing one generation’s growth and spiritual history.
Desire; fracture; breakout
2015-10-13
2015年度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1990年代‘文學事件’研究”(CWX012)
魏華瑩(1981—),女,河南鄭州人,文學博士,鄭州大學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當代文學。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6.011
I207.42
A
1008-3715(2015)06-0054-06
編者按:作家墨白是當代優秀的先鋒作家之一,數十年來一直致力于通過跨文體寫作進行文體革新實驗,并堅守對人性的復雜性、歷史問題和現實苦難的反思,在思想性和藝術性的探討上達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今天仍有必要重提立足于反思現實和人性的先鋒精神,以建構良好的人文精神生態。本期特設專欄,集中闡釋墨白小說的精神引領意義和藝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