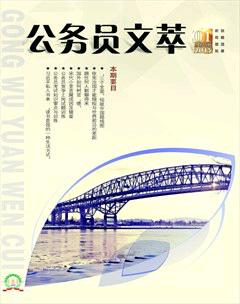宋代小吏貪腐成因及鏡鑒
祖慧
中國古代實行的是皇權統治下的中央集權管理模式,在政府機構內工作、維系國家機器運轉的主要有兩類人:一是官,二是吏。官者“管”也,是指由國家任命、在各級政府機構中擔任領導職務的官員,他們依據級別的高低享有一定的特權,并有著較完備的升遷與獎懲機制。所謂吏,則是指廣泛分布于中央及地方各級官府中,從事各種具體事務的工作人員。胥吏雖然在官府辦事,但他們的身份仍然是平民而非官員,所謂“庶人之在官者也”。宋代胥吏的工作主要有:文書抄錄與傳送、賬簿登記與賦稅征收、地方治安維護、倉場庫所管理,還要負責官員的迎來送往以及供官員驅使傳喚等。
宋代胥吏維持政府正常運轉
宋代胥吏作為各級官府中的具體辦事人員,在國家政治中發揮著重要且積極的作用。中央制訂的各項政策及法規通過詔書形式頒發至全國,地方上的各種信息也以奏章的形式上報朝廷,公文往來之頻繁勝過以往任何時期,而公文的抄寫、點檢、批勘及收發、傳遞等工作主要由各部門的胥吏完成,胥吏成為溝通中央與地方聯系的橋梁。
北宋神宗朝以后,地方官府內的胥吏除了處理文書、供官員驅使外,還要承擔原本由鄉村上三等戶差充的“職役”,主要有催征賦稅、押送官物、管理倉庫、維持治安。基層胥吏輔佐官員治理地方,在維護地方統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宋代,官員有任期限制(一般三年一任,短者數月即遷),遷移頻繁,這使他們很難對任職地區或部門內的實際情況有深入了解。胥吏則不然,他們大多是本鄉本土之人,一般長期在某一個部門辦事,熟知本部門的各項規定和法律條文,了解本地的社會現狀和風俗民情。因此,當官員愿意放下身段來聽取胥吏建議時,往往能夠找到正確解決問題的方法,避免或減少政策制定時的失誤。宋代的法制建設已比較完備,各部門都有專門的行政法規,法律條文也日益繁密,這令剛上任的官員難以適應,在處理政務時,越來越倚重部門內長期任事、精通律令的老吏。就連翰林學士起草的詔書也要經孔目吏審讀無誤后再頒下。
“蒼蠅”遍地,胥吏貪腐令人痛恨
宋代胥吏的貪腐現象非常嚴重,這也給集權統治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主有體現在:
營私舞弊,干擾法令實施。胥吏散布于中央至地方各級機構中,職掌不同,賕賂的方式也不同:進奏院的吏人通過泄漏機密以邀利;三司吏人利用審核賬籍之便以索賄,而管理官府財物的胥吏則伺機侵吞、盜取。為害最大的當屬中央三省吏員,特別是管理人事、負責官員磨勘遷徙與黜罷的吏部胥吏(銓吏),他們仗著自己對人事任免條法的熟悉,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官闕來脅迫官員,目的無非是索賄、或泄私憤。例如,釋贊寧在《王得一行狀》中講到:堂吏蘇允淑與唐州團練判官掌宣有私怨,當他奉命裁汰年高(七十以上)選人時,就把年僅三十五歲的掌宣列入應裁汰名單。
竊權弄政,侵侮士類。胥吏作為官府內具體辦事人員,受制于官員,他們往往通過與官員的周旋來達到徇私目的:遇廉勤之官,暫且收斂自己的行為;遇庸官,則竊權攬政;遇貪官,則與之狼狽為奸。對于地方官員而言,他們每當端坐堂上,環顧四周都是本鄉本土的胥吏,很容易被架空。胥吏攬權,號為“立地官人”、“立地知縣”。縱觀兩宋,真正能不被胥吏欺侮的官員很少,即便是享有“青天”美譽的包拯也未能幸免。
勾結權貴,加重吏治腐敗。胥吏既受制于官員,自然希望得到官員的庇護,而當貪官與污吏“相與為市”時,危害極大。北宋仁宗朝,開封府胥吏馮士元因貪贓枉法被抓,在審訊時,他不僅主動交代自己罪行,還檢舉揭發一批官員。朝廷下令徹查,結果查明,不僅開封府前任、現任正副長官存在貪腐問題,就連中央一些重要機構如政事堂、樞密院、御史臺的官吏也牽涉其中。從這起震驚朝野的貪腐大案不難看出,當時官場的貪腐情況是多么嚴重。特別是當熟知律條的胥吏與朝堂上的權臣相通,就會危及社稷。南宋寧宗朝,權相韓侂胄重用吏人蘇師旦專權,結果是“政出于韓,而師旦之門如市”。
敲剝百姓,危害社會。基層胥吏不僅與官員交結,還與當地的富豪相勾聯,共同欺壓百姓。有的侵占民田,有的偽造稅產簿,偷盜稅款;更有甚者,將富豪的稅賦轉嫁到普通民戶身上。這些行為既造成國家財稅的大量流失,也加重了民戶的負擔。
當胥吏看不到進遷希望時,追求財富就成了他們滿足自我需求的最好方式
從現存文獻來看,宋代的吏治腐敗問題長期存在并且愈演愈烈,士人甚至將吏貪與亡國聯系起來,認為“漢之天下失于貴戚,唐之天下失于宦官,本朝之天下則弊于吏奸。凡為朝廷失人心、促國脈者,皆出于吏貪”。宋代對吏治也進行過整頓,卻收效甚微。原因何在?也許只有透過表面現象,從制度本身著手,深入剖析官與吏之間關系變化的脈絡,才能找到答案。
官員與胥吏同在官府任事,本應相互扶持、共同維系國家機器運轉,但是,宋代官員與胥吏間的尊卑之別已達到極至,兩大群體間的矛盾也日趨激化。在此背景下,官與吏之間維持著既相互依存又沖突不斷的矛盾關系:一方面,隨著中央集權的不斷強化以及法律條文的日益繁密,對各部門內相關法律條文和工作流程的熟悉程度,官員遠不及胥吏,胥吏在政務處理過程中的作用越來越大,他們甚至能夠代官理政,越權行事,逐步成為官府中的實權派。另一方面,宋代雖然有胥吏出職為官的規定,但真正能出職的人數極少,且多需在官府任吏職二三十年以上。絕大多數胥吏只能以“庶人”的身份在官府當差,拿著微薄的俸祿,還要處處受到官員的制約、欺壓。即便是那些出職為官者,仍然受到排斥,他們一般只能被授縣尉、縣主簿、監當官之類的繁雜差遣,官階也最高只能到八品,表明流外出身者只能是最底層的官員,沒有向上升遷的可能。除此之外,胥吏群體還被禁止參加科舉考試。當胥吏看不到進遷的希望時,追求財富就成了他們滿足自我需求的最好方式。正如蘇軾所言:“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而枉法弄權、侵侮士類,也成胥吏發泄不滿、報復官員的手段。官員若馭吏過嚴,胥吏或“空一縣逃去”,造成政務癱瘓;或越級上告、制造事端迫其離去。在與胥吏博弈中,官員往往會處于下風。
總之,宋代胥吏在國家政治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他們的社會地位卻日趨卑賤,這是導致吏奸難禁、吏治腐敗的最主要原因。而胥吏的貢獻與地位之所以會形成強烈反差,與管理體制中的不合理因素有關,與胥吏既在官僚機構任職又不屬于官僚集團的角色定位有關。
(摘自《人民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