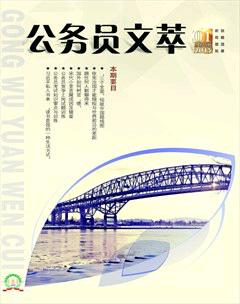“甘草閣老”徐階
樊樹志
嘉靖、隆慶之際擔任內閣首輔的徐階,人們對他的看法大相徑庭。與他同時代的海瑞,譏諷他是“甘草閣老”;比他稍晚的錢謙益贊揚他是“名相”。究竟是“名相”,還是“甘草閣老”?最好還是用事實說話。
扳倒嚴嵩
徐階最大的貢獻就是扳倒了不可一世的嚴嵩嚴世蕃父子,在嘉靖、隆慶之交,撥亂反正,扭轉先前的政治頹靡局面,因此被譽為“楊廷和再世”。正德十六年,武宗皇帝駕崩,世宗皇帝還未即位,內閣首輔楊廷和抓住時機,力挽狂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政績,無怪乎后人贊譽有加:“楊廷和總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為安。”
嘉靖、隆慶之際的政局,與正德、嘉靖之際十分相似,內閣首輔徐階所扮演的角色,令人有“楊廷和再世”之感,決非偶然。據王世貞為他寫的傳記描述,此人“短小白皙”、“眉秀目善”,一副江南士人的典型氣派,能屈能伸,隨機應變而不露聲色。在嚴嵩專權跋扈的形勢下,能夠合作共事而不被打倒,充分顯示了他的政治智慧,謀略和詭譎兼而有之。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伺機潛移帝意,導致嚴嵩嚴世蕃父子的垮臺,為撥亂反正掃清了障礙。
他主政以后,在內閣辦公室墻壁上寫了一個條幅:“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諸公論。”用直白的語言宣稱,他要撥亂反正,把威權和福祉歸還皇帝,把政務歸還政府各部門,把官員的任免與獎懲歸還公眾輿論,可以看做是他的施政綱領,目的在于改變嚴氏父子專擅朝政的局面。意圖是很明顯的,他要向朝廷上下表明,不想成為嚴嵩第二,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同時代人唐鶴征所寫的徐階傳記,對此給予高度評價:“(徐階)盡反(嚴)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風采。”
徐階的另一貢獻是,利用起草嘉靖皇帝遺詔的機會,用委婉的方式,讓已故皇帝檢討自己癡迷于道教的錯誤。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皇帝朱厚熜突然病故,他的遺詔并不是死前口授的,而是徐階代他起草的。為了撥亂反正,“遺詔”強調了已故皇帝對于癡迷道教的錯誤有所反省,為那些批評皇帝而遭到懲處的官員恢復名譽和官職,懲處慫恿皇帝玄修的道士,停止一切道教齋醮活動。一看便知,這不是執迷不悟的朱厚熜愿意講的話。但是,當時必須這樣做。十二月二十六日,穆宗皇帝即位,他的登極詔書也是徐階起草的,基調和先帝遺詔完全一致,重申起用因反對玄修而遭懲處的官員,處罰道士,停止齋醮,破格提拔賢才,裁減冗員。
嘉靖、隆慶之際的政治交接,徐階處理得巧妙、妥帖,先是以“遺詔”的形式表示先帝的悔悟,繼而以“即位詔書”的形式表示尊重先帝的遺愿,避免了“改祖宗之法”的非難。
畏威保位
徐階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而是一個務實型官僚,接手嚴嵩留下的爛攤子,必須撥亂反正。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今日的局面似乎已有更新之機,但是人心陷溺已久,一定要德高望重的人才能轉移;朝廷政務的廢弛已經達到極點,一定要高明的手段才能整頓。
他推心置腹地敦請嚴訥出任吏部尚書,整頓頹敗已極的吏治。嚴訥出掌吏部,為了扭轉“吏道污雜”局面,與同僚約法三章:一、談公事到吏部衙門,不得到他的私宅;二、慎重選擇吏部的中層官員——郎中、主事,杜絕開后門、通路子,用當時的話表述,就是“務抑奔競”;三、選拔人才不要拘泥于資格,即使是州縣小吏,只要政績優異,應該破格提升。在他的努力下,出現了“銓政一新”的面貌。這與徐階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
然而徐階主政的嘉靖、隆慶之際,政壇高層并不平靜,最突出的表現就是高拱與徐階矛盾的逐漸明朗化。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進入內閣,得力于徐階的推薦。但是此人自視甚高,入閣以后,常常和徐階發生沖突,甚至公開揚言:徐階把先帝的過錯公示于天下,是詆毀先帝。高拱的攻擊完全是意氣用事,效果適得其反,使自己處于被動境地。官員們紛紛彈劾高拱,稱贊徐階。高拱自討沒趣,以身體有病為由,辭官而去。
然而穆宗皇帝對高拱情有獨鐘,對徐階以“國師”自居的姿態,有所不滿。在這種情況下,徐階無奈地辭官而去。隆慶三年十二月皇帝召回高拱,讓他再度入閣,并且兼任吏部尚書。李春芳識相地辭職,把內閣首輔讓給了高拱。一旦大權獨攬,高拱肆意報復。史書這樣寫道:“ (高)拱性強直自遂,頗快恩怨,及再入閣,盡反徐階所為。”
萬歷二年,八十一歲的徐階逝世,神宗皇帝贈予“太師”榮譽頭銜,賞給謚號“文貞”。錢謙益對這位徐文貞公是頗為贊許的:“負物望,膺主眷,當分宜(嚴嵩)驕汰之日,以精敏自持,陽柔附分宜,而陰傾之。分宜敗后,盡反其秕政,卒為名相。”而目光犀利、言辭直率的海瑞的評價頗值得玩味:他一方面表揚徐階“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另一方面批評他“事先帝,無能救于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一方面肯定他為官清正廉潔,“不招權,不納賄”,另一方面指責他“容悅順從”,只能算作一位“甘草閣老”。這樣的評價,是否過于苛刻呢?
(摘自《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