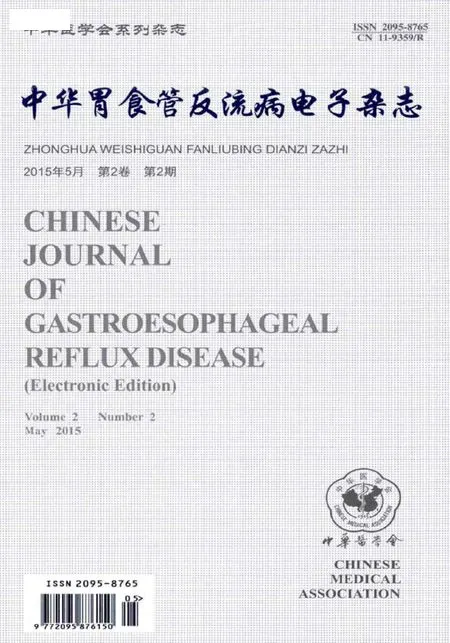食管裂孔疝外科診治17 例體會
張勇 胡良碩 張廣健 吳齊飛 李碩 李海軍 賀海奇 陳南征 付軍科
食管裂孔疝是指腹腔除食管以外的臟器通過病理性擴張的膈肌食管裂孔疝入到胸腔。食管裂孔疝分為4 型,Ⅰ型為滑動型食管裂孔疝,齒狀線移至膈肌上方,但胃體縱向解剖位置無明顯變化,胃底仍位于膈肌以下;Ⅱ型為單純食管旁疝,齒狀線保持正常位置,但胃底部在食管旁經食管裂孔疝入胸腔;Ⅲ型為混合型食管裂孔疝,齒狀線及胃底同時經食管裂孔上移進入胸腔;Ⅳ型食管裂孔疝被定義為除了胃外,伴隨其他腹腔臟器同時疝入胸腔,例如疝囊內存在網膜,結腸或小腸。Ⅱ~Ⅳ型又可統稱為食管周圍疝[1]。國內常將Ⅳ型食管裂孔疝稱為巨大型食管裂孔疝,而國外文獻多認為Ⅲ型及Ⅳ型均可稱為巨大食管裂孔疝,主要評價指標為是否超過一半的胃體積疝入胸腔[2]。本文將2009 年3 月至2015 年1 月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手術治療的17 例食管裂孔疝患者臨床資料總結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組患者17 例,男9 例,女8 例。年齡15 ~78(56.0 ±15.4)歲,體重38 ~90(72.3 ±10)kg,BMI 22.5 ~35.1(27.0 ±3.1)kg/m2,病程2 周至14 年。
臨床癥狀:燒心、反酸、呃逆8 例;胸骨后、劍突下疼痛7 例;餐后嘔吐5 例;胸腹部脹滿3 例;咳嗽咳痰3 例;吞咽困難2 例;胸悶氣短1 例;嘔血2 例;缺鐵性貧血3 例。
檢查結果:上消化道造影明確診斷15 例,其中伴有胃扭轉2 例,診斷陽性率88.2%,陰性結果的2例初次診斷為反流性食管炎;行CT 檢查15 例,診斷為食管裂孔疝者12 例,診斷陽性率80%;行胃鏡檢查11 例,診斷為食管裂孔疝者7 例,診斷陽性率63.6%;胸片見左胸腔低密度影伴氣液平面2 例。經上消化道造影或胃鏡診斷合并反流性食管炎10例,發病率58.8%,采用反流調查問卷(reflux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RDQ),反流癥狀評分6 ~16(9 ±3.7)分[3]。
臨床分型:Ⅰ型食管裂孔疝2 例,Ⅱ型1 例,Ⅲ型10 例,Ⅳ型4 例。
二、治療方法
17 例均行氣管插管全身麻醉手術。3 例經左胸行Belsey MarkⅣ修補術;1 例行開腹食管裂孔疝修補術;7 例行腹腔鏡食管裂孔疝修補術;5 例行腹腔鏡食管裂孔疝修補+Nissen 胃底折疊術;1 例行腹腔鏡食管裂孔疝修補+Dor 胃底折疊術;其中6 例腹腔鏡食管裂孔疝修補術應用人工補片。2 例腹腔鏡手術患者同時行膽囊切除術。其中他院食管裂孔疝修補術后復發來我院行二次手術1 例。
結 果
2 例出現胃扭轉,其中1 例為14 歲男性患兒,行經左胸Belsey MarkⅣ手術,術后恢復良好,癥狀消失,隨訪4 年無復發;另1 例為食管裂孔疝修補術后6 年復發Ⅳ型食管裂孔疝合并胃扭轉,行開腹食管裂孔疝修補術,術后恢復良好。
開放性手術時間120 ~270(182 ±63)min,腹腔鏡手術時間45 ~240(117 ±59)min。首次手術術中出血量平均為20 ml,1 例二次開腹食管裂孔疝修補手術出血較多,為600 ml。術后6 ~12 h 拔除胃管。術后平均住院日8.8 d[開放性手術9 ~22 d,平均(14.8 ±5.9)d;腹腔鏡手術2 ~15 d,平均(7.0 ±3.9)d]。住院花費1.7 萬~4.9 萬元,平均(2.8 ±1.1)萬元。
本組17 例住院期間未出現氣胸、食管或胃穿孔、出血等并發癥;出院后均經電話隨訪,至今未見復發;術后早期出現吞咽困難5 例,其中4 例在3 個月內癥狀逐漸消失,1 例術后1 年癥狀仍然存在,但能夠耐受;術后早期出現腹脹2 例,經保守治療恢復,其中1 例經胸行Belsey MarkⅣ手術者,術后4 年再次出現腹脹、反酸、燒心癥狀并不斷加重,行胃鏡及CT 檢查提示反流性食管炎,給予抑酸對癥治療好轉;術后20 d 出現膿胸1 例,再次住院行胸腔閉式引流術結合抗感染治療后治愈,目前恢復良好。
討 論
一、食管裂孔疝的臨床表現
多數的食管裂孔疝與先天性因素有關,甚至在嬰幼兒階段即可表現出癥狀。小兒食管裂孔疝患者癥狀多為反復的嘔吐、上呼吸道感染、腹痛,多伴有缺鐵性貧血及營養不良[4]。
成人食管裂孔疝患者癥狀與疾病分型有關,臨床癥狀復雜多變,主要包括燒心、反酸、呃逆、胸骨后或劍突下疼痛、餐后嘔吐、胸腹部脹滿感、咳嗽咳痰、吞咽困難等。食管裂孔疝多合并反流性食管炎,甚至導致焦慮抑郁狀態[5]。本組患者合并反流性食管炎發病率達58.8%,且多為來院就診的主訴。
二、食管裂孔疝的診斷
食管裂孔疝的診斷需要結合臨床表現及相關輔助檢查,包括上消化道造影、內鏡、CT、食管測壓、24 h pH 測定、超聲內鏡、核醫學檢查等。上消化道造影是診斷食管裂孔疝的重要檢查,可以觀察疝的大小、賁門與食管裂孔的關系,同時能夠觀察食管的運動狀態、反流情況。消化道內鏡檢查具有重要意義,不但能夠檢測疝的大小和類型,同時可以直視觀察食管及胃黏膜病變,能夠確診糜爛性食管炎及Barrett 食管。高分辨率食管測壓法結合24 h pH測定在指導滑動型食管裂孔疝患者抗反流術式中具有重要意義[6]。本組患者以上消化道造影診斷率最高,結合胃鏡檢查可使診斷率達到100%,而CT 檢查對于胃扭轉的患者可以提供更多的診斷信息。
三、食管裂孔疝手術指征
國際上根據食管裂孔疝的分型確定其治療方法以及是否需要接受手術治療。一般認為當合并反流性食管炎時Ⅰ型食管裂孔疝才具有手術干預的必要[7]。本組2 例Ⅰ型食管裂孔疝患者均合并長期的反流癥狀,反流癥狀評分分別為16、14 分,行Nissen 胃底折疊術后,恢復良好,癥狀消失。
而對于來院就診的食管周圍疝(Ⅱ~Ⅳ型)患者一般均有明顯的臨床癥狀,食管裂孔疝隨年齡增大、病程延長有逐漸加重的趨勢,表現為原有癥狀加重,新的不適出現,發生梗阻、胃扭轉等并發癥的概率增加,因此食管周圍疝患者均有手術干預的指征[8]。
食管裂孔疝合并胃扭轉的現象并不多見,以老年為主,但急性胃扭轉可能造成較為嚴重的并發癥,如穿孔,絞窄壞死,出血,潰瘍等,一般建議無論患者是否有明顯癥狀都應早期接受手術治療[9]。本組有2 例胃扭轉患者,分別經開胸及開腹手術,術后恢復良好。
四、食管裂孔疝手術方式選擇
食管裂孔疝的手術治療方式包括經胸、經腹、腹腔鏡下食管裂孔疝修補術,近年來隨著腔鏡技術的不斷進步,越來越多的臨床研究證明,腹腔鏡手術具有時間短、出血少、術后恢復快等優點。本組17 例患者中,4 例行開放性手術,其中2 例合并胃扭轉,另外13 例行腹腔鏡手術。手術時間、術中出血及術后住院時間,腹腔鏡手術均低于開放性手術。
多數研究認為大多數的食管周圍疝患者都合并食管下段括約肌功能不全,行食管裂孔疝修補手術需同時行抗反流術式,以預防術后出現的胃食管反流,同時能夠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而預防食管裂孔疝復發,抗反流術式以胃底折疊術為主[10]。但也有報道認為,360°胃底折疊容易導致患者術后出現吞咽困難,而只有術前就存在反流癥狀的患者能夠真正獲益[11]。為解決類似的問題,胃底折疊術也在不斷改進,由Nissen 術式演化而來的有Toupet 法、Dor 法等,但其效果尚缺乏有力的臨床研究論證。同時作為經典的抗反流術式,胃底折疊術也不斷受到新技術的挑戰,2013 年新英格蘭雜志報道應用磁性組件加強食管下段括約肌的術式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具有微創,維持原有生理結構,個體化治療的特點[12]。本組術前合并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中3例行Belsey MarkⅣ術式,4 例行Nissen 術式,3 例單純行食管裂孔疝修補術,隨訪除發現1 例患者術后4 年反流癥狀再次出現外(如前所述),余患者皆恢復良好。
五、食管裂孔疝修補術相關并發癥
包括術中并發癥及術后并發癥,術中并發癥常見的有氣胸、皮下氣腫、食管或胃壁損傷穿孔、術中出血、迷走神經損傷等;術后并發癥常見的有縱隔胸腔積液、吞咽困難、復發、吞咽困難、排氣增加、進食后上腹脹、腹瀉、補片侵蝕等。本組患者術后出現吞咽困難5 例,1 例因為食管裂孔修補過緊,手術后3 個月內癥狀消失;4 例行Nissen 胃底折疊術后吞咽困難,3 例患者3 個月左右癥狀消失,1 例患者癥狀持續存在1 年以上。出現腹脹2 例,給予保守治療后很快好轉。應用補片與未應用補片的比例為9∶6,至今兩組均未見復發及補片相關性并發癥出現,但尚需長期隨訪。
總之,食管裂孔疝修補術屬于功能性手術,立足于改善患者癥狀,術后療效確定。腹腔鏡手術具有微創優勢,但需要充分詢問病史、根據疝的分型及術前各項檢查設計手術方式,加強圍手術期管理,促進患者術后恢復,減少術后并發癥的發生。
1 Kohn GP,Price RR,DeMeester SR,et al.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hiatal hernia[J].Surg Endosc,2013,27(12):4409-4428.
2 Morino M,Giaccone C,Pellegrino L,et al.Laparoscopic management of giant hiatal hernia:factors influencing long-term outcome[J].Surg Endosc,2006,20(7):1011-1016.
3 李治仝,汪忠鎬,吳繼敏,等.食管裂孔疝與呼吸道癥狀臨床相關性研究[J].中華普通外科雜志,2013,28(1):9-11.
4 Gorenstein A,Cohen AJ,Cordova Z,et al.Hiatal hernia in pediatric gastroesophageal reflux[J].J Pediatr Gastroenterol Nutr,2001,33(5):554-557.
5 彭穗,林金坤,肖英蓮,等.胃食管反流病食管黏膜損傷程度的影響因素[J].中華消化內鏡雜志,2007,24(6):419-422.
6 季鋒,汪忠鎬,李震,等.高分辨率食管測壓法在食管裂孔疝診斷中的意義[J].中華普通外科雜志,2013,28(6):427-430.
7 Fornari F,Madalosso CA,Farre R,et al.The role of gastrooesophageal pressure gradient and sliding hiatal hernia on pathological gastro-oesophageal reflux in severely obese patients[J].Eur J Gastroenterol Hepatol,2010,22(4):404-411.
8 Stylopoulos N,Gazelle GS,Rattner DW.Paraesophageal hernias:operation or observation?[J].Ann Surg,2002,236(4):492-500;discussion 500-491.
9 Katkhouda N,Mavor E,Achanta K,et al.Laparoscopic repair of chronic intrathoracic gastric volvulus[J].Surgery,2000,128(5):784-790.
10 Swanstrom LL,Jobe BA,Kinzie LR,et al.Esophageal motility and outcomes following laparoscopic paraesophageal hernia repair and fundoplication[J].Am J Surg,1999,177(5):359-363.
11 Mark LA,Okrainec A,Ferri LE,et al.Comparison of patientcentered outcomes after laparoscopic Nissen fundoplication for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or paraesophageal hernia[J].Surg Endosc,2008,22(2):343-347.
12 Ganz RA,Peters JH,Horgan S,et al.Esophageal sphincter device for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J].N Engl J Med,2013,368(8):719-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