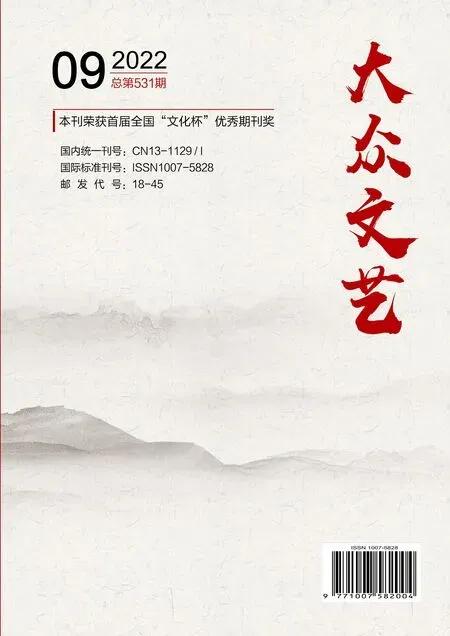斷裂與失足:從《禿頭歌女》看尤奈斯庫的反戲劇行動
鐘芝紅 (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321000)
斷裂與失足:從《禿頭歌女》看尤奈斯庫的反戲劇行動
鐘芝紅 (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321000)
《禿頭歌女》是尤奈斯庫的處女作,也是一部極為著名的荒誕戲劇。本文通過對情節的斷裂處理,突出《禿頭歌女》反傳統的先鋒基礎;同時強調對語言的異化,從而加深戲劇的荒誕主題。它的不足之處,也是一個值得探索的論題。
斷裂;異化;反戲劇
一、情節斷裂:對傳統戲劇的拒絕
《禿頭歌女》是法國著名的戲劇家尤奈斯庫的第一部作品,“反戲劇”的副標題驚心動魄,充滿了斷裂與解構的游戲意味,一開始就表明尤奈斯庫與傳統戲劇決裂的信念。亞里士多德認為戲劇中最重要的是因素是情節結構,而荒誕派戲劇家宣布自己的戲劇是反抗的,他們拒絕一脈相承的戲劇范式,拒絕傳統戲劇的情節與現實主義。尤奈斯庫對傳統戲劇有直言不諱的成見,同時對反戲劇行動進行了維護:“語言像脫臼一般斷裂,人物變了樣;話語,荒誕的,被挖空了它的內容。詞變成了一些有聲音的果皮,毫無意義;人物當然也是如此,被挖空了他們的心理,世界向我顯得是在一種不尋常的光之中,也許就是在它真正的光之中,超越了各種解釋和一種專斷的偶然性。”1
從《禿頭歌女》的創作來看,它似乎是尤奈斯庫偶然為之,然而,它是作者深思熟慮的冒險因素,是二戰背景下個體存在缺失與異化的產物。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對知識分子造成了深刻的心理陰影。尼采“上帝死了”,為西方精神世界確立了立法缺失的狀態。保羅·策蘭一度覺得無路可走,最終投塞納河自盡;阿多爾諾表示寫詩就像“一個野蠻的創舉”。薩特、加繆等先后發聲,表達了對這個秩序缺失的世界的無望之情。而知識分子的焦慮與敏感,一方面造成了個體心靈的創傷,一方面,更快速推動創傷向喪失靠近。這是一種存在根基的懷疑與喪失,人與人之間高度異化,指向道德的無意義變得清晰而無解。
尤奈斯庫的反戲劇行動貫穿《禿頭歌女》始終:毫無連貫的情節,交流僵滯的對白,共同生活多年的馬丁夫妻竟不知對方,甚至連《禿頭歌女》的名字也是口誤的結果。全劇一共十一場,但我們看不到每場的必然聯系。亞里士多德認為喜劇是對不完整的行動的摹仿:雖然丑怪,但不至于引起痛感。而到了荒誕派這里,喜劇是荒誕的“喜”,尤奈斯庫要營造的是一種“強烈戲劇”,即“強烈的喜劇性、強烈的戲劇性2”。已經模糊了悲劇與喜劇的界限,不再有悲喜之分,喜劇性的效果卻是悲劇性的,這種徹底解構是對傳統戲劇觀念的背叛,也是對梅耶荷德的遙相呼應。
比如第四場,是馬丁夫婦荒謬的“相認”:原來他們居然是一對多年的夫妻。
[馬丁太太:不慌不忙地靠近了馬丁先生。]
他們毫無表情地互相擁抱接吻。掛鐘重重地敲一下。掛鐘聲音敲得很響,使觀眾大吃一驚。馬丁夫婦卻沒聽見鐘聲。
尤奈斯庫對情節的營造,可以看作是對因果律的破壞。而尤奈斯庫仍然稱得上是一個值得信任的探索者。
二、人的異化:語言作為荒誕的呈現
語言作為社會機器的外在形式,必然要體現它時空意義上的變遷。如果說機制得以運行的條件是時間上的連續性,那么,空間上的斷裂則會使時間發生扭曲,同時破壞兩者的平衡點。而當它發生異化,我們依然希望從這個社會機制中尋求和解,或取得同步的發展。這就對應了荒誕派的戲劇行動。當社會與個體陷入無序的危機,敏感的先行者就使語言被迫出現轉機,利用它的變形空間驅使荒誕到達光怪陸離的地步。
《禿頭歌女》大部分臺詞來自于《英語會話手冊》的例句,毫無思想交流的可能性。英國中產階級式的語調,陰陽怪氣的情緒渲染的語調,平板無奇的語調,人物形象呈現抽象化和符號化特征,無任何個性可言。這是一種僵化的語言。支離破碎、詞不達意、自相矛盾、荒誕不經的臺詞,折射出人物內心的平庸與麻木。
戲劇中人物的言行都是機械的盲從的,毫無生機和思想,語言只是單純的生理現象——
史密斯先生:卡卡托埃斯,卡卡托埃斯,卡卡托埃斯,卡卡托埃斯,卡卡托埃斯,卡卡托埃斯,卡卡托埃斯,卡卡托埃斯,卡卡托埃斯,卡卡托埃斯。
……
這種荒謬的非邏輯性的直白帶來的革命,就具有一種快感。對陳詞濫調的重復,給尤奈斯庫帶來了層出不窮的戲劇性材料。安東尼奧·阿爾托在評論梵高時所說,他是具有“遲緩的童年”的那類人,非常瘋狂,非常有洞察力。語言被徹底解構,意義不再備受推崇,尤奈斯庫,包括同時代的品特、貝克特、日奈、阿達莫夫、奧巴爾迪亞等,他們依靠“遲緩的童年”和詞語的技巧,使荒誕派戲劇獲取了20世紀的合法性。
三、反戲劇行動的失足
黑格爾認為,怪誕是“比喻學中不同領域的割裂和混淆”。3這可以為后來的反戲劇行動提供理論預設性。但是,歷史上,尤其是在流派異常爭鳴20世紀,這種割裂所造成的后果一定會樹立新的規則嗎?文藝復興后期,維加發展了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獨白,盡管它為西班牙貢獻了巴洛克式的寶貴,而人物內在性的缺失則受限了這種獨白的前進。
1.并不持久的實驗
毋庸置疑,尤奈斯庫把戲劇作為更新當時整個社會生存狀態的手段,為反戲劇行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而尤奈斯庫拒絕了一切的現實主義的態度,是值得商榷的。尤奈斯庫推崇的反戲劇以傳統情節斷裂為基礎,刻意抹煞人物的心理活動,使其更接近荒誕戲劇的本質。從戲劇史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場革命;從戲劇本身來說,這可能是一場并不持久的實驗。尤奈斯庫的戲劇資源主要集中在對現實主義、并有意擴大到對“資產階級”的否決上:這個詞成為他表示不滿的代名詞。《禿頭歌女》第一場是這樣交代舞臺環境的:
“一間英國式的產階級起居室,放著一些英國式的扶手椅。英國式的夜晚。史密斯先生是英國人,坐在英國式的扶手椅上,穿著他那雙英國拖鞋……一種英國式的長時間的沉默。英國式的大掛鐘按英國方式敲了十七下。”
尤奈斯庫對“英國式”提出了猛烈與重復的質疑,而《禿頭歌女》只是他不滿的起點。之后,他的不滿更明顯地借助物體表現出來。《椅子》中那把椅子的在場感、《犀牛》中犀牛的勝利,無不暗示主動入侵的荒誕造成人的邊緣化的諷刺。這種全面、粗暴、不顧一切的創作,讓人日益感覺疲乏。到了20世紀六十年代,荒誕戲劇幾乎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漸漸地被遺忘了。
2.語言的危機
《禿頭歌女》的語言是陳詞濫調的,由此折射出“荒原”世界的麻木,而對語言毫無邏輯的重復,并不能看作是詩學傳統對先鋒戲劇的移交,遑論并置。
尤奈斯庫對語言的僵化性改造,已經到了剝削語言本身的交流功能的地步。它只負責人物的異化、自動化、機械化。《禿頭歌女》中,瑪麗毫無表情地讀著一首《火》的詩、馬丁太太沒有關聯的“巴扎爾,巴爾扎克,巴澤納!”,等等,尤奈斯庫進行的語言游戲已經完全偏離了習慣性用語的效果,語言被偶然又必然地解體。這種讓人極為不適的創造,具備影響、但并不符合流行的條件,語言極有可能只是成為更新時代觀念的工具。
注釋:
1.[法]歐仁·尤奈斯庫,《筆記與反筆記》,法蘭西信使出版社,1968:252.
2.宮保榮.《法國戲劇百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294.
3.[德]黑格爾.《美學》第2卷,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