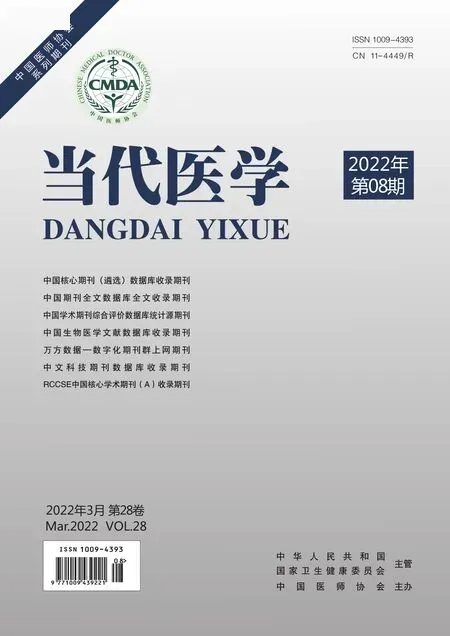結直腸腺瘤與代謝綜合征及其組分相關性研究
黃玉蓮,劉小方,張秀蓮
(北京市健宮醫院消化內科,北京 100054)
結直腸腺瘤是結直腸最常見的良性腫瘤,已被公認為結直腸癌的癌前病變,占全部結直腸癌癌前疾病的85%~90%[1]。在惡性腫瘤中,結直腸癌的發病率居第3 位,病死率居第2 位[2],隨著結直腸癌在惡性腫瘤死亡序位中逐步提前,結直腸腺瘤受到人們廣泛關注。同時,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及生活方式的轉變,代謝綜合征發病率呈逐漸上升趨勢,本研究旨在了解結直腸腺瘤與代謝綜合征及其組分的相關性,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于本院就診的215 例行腸鏡檢查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 98 例,女 117 例;年齡 33~89 歲,平均年齡(63.49±10.907)歲。經腸鏡檢查發現結直腸腺瘤患者 132 例作為觀察組,其中男 67 例,女 65 例;年齡41~86 歲,平均年齡(64.15±9.991)歲。腸鏡檢查陰性患者83 例作為對照組,其中男31 例,女52例;年齡 33~89 歲,平均年齡(62.45±12.213)歲。兩組臨床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患者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排除標準:非腺瘤性息肉;家族性息肉病;炎癥性腸病;已發生結直腸癌患者。
1.2 方法 收集患者臨床資料,包括性別、年齡、BMI、血糖、血脂及既往病史如至少為二級以上醫院明確診斷的糖尿病、高脂血癥、高血壓等病史及用藥情況等信息。參照2004年中華醫學會糖尿病學會提出的適合我國人群的代謝綜合征診斷標準,符合以下條件中≥3項者即可診斷為代謝綜合征[3]:①超重和/或肥胖:BMI≥25.0 kg/m2;②高血糖:FPG≥6.1 mmol/L和/或糖負荷后2 h PG>7.8 mmol/L,和/或已確診糖尿病并治療者;③高血壓:收縮壓>140 mmHg(1 mmHg=0.133 kPa)和/或舒張壓>90 mmHg,和/或己確診高血壓并治療者;④血脂紊亂:空腹TG≥1.7 mmol/L,和/或空腹 HDL-C 男性<0.9 mmol/L,女性<1.0 mmol/L。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 統計軟件分析,樣本均數的比較采用t檢驗,單因素分析采用χ2檢驗,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歸分析,并計算各暴露因素對結直腸腺瘤發生的OR值,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結直腸腺瘤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顯示,結直腸腺瘤組及對照組在吸煙、飲酒、高血壓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超重/肥胖、高血糖、血脂紊亂、代謝綜合征方面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結直腸腺瘤的單因素分析[n(%)]Table 1 Univariate analysis of colorectal adenoma[n(%)]
2.2 結直腸腺瘤的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排除各因素之間的交互影響后,超重/肥胖、高血糖為結直腸腺瘤的獨立危險因素。超重/肥胖(OR=3.101,P=0.000)、高血糖(OR=1.954,P=0.026)患者發生結直腸腺瘤的可能性越大,見表2。

表2 結直腸腺瘤的多因素分析Table 2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colorectal adenoma
3 討論
結直腸腺瘤有一定的惡變傾向,內鏡下切除是常用治療手段,但腺瘤切除后有一定的復發率[4],積極尋找結直腸腺瘤可能的發病原因及相關因素,從根本上積極預防、控制其發生發展有重要的意義。現已有多項調查結果表明,代謝綜合征可增加結直腸腺瘤的風險[5-6]。本研究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超重/肥胖、高血糖、血脂紊亂、代謝綜合征均為結直腸腺瘤的危險因素,但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超重/肥胖、高血糖為結直腸腺瘤的獨立危險因素。
脂肪增多是結直腸腺瘤的重要危險因素[7-8],現已有研究應用BMI、腰臀比、計算機斷層掃描對肥胖程度進行評估后發現腺瘤的發病風險會隨著脂肪的增加而升高[9-10],BMI>25 kg/m2的患者常伴有內臟脂肪的過量儲備,從而導致胰島素生長因子-Ⅰ(IGF-Ⅰ)水平的升高,IGF-Ⅰ作為一種重要的循環內分泌多肽,是細胞增生和凋亡的重要決定因素,IGF-Ⅰ升高可誘發和促進結直腸腺瘤或消化系統癌癥的出現[11]。另外,超重/肥胖結直腸腺瘤患者發生還可能與脂肪特異性分泌的脂肪因子,如脂聯素、瘦素等的失衡有關[12-13]。高血糖與結直腸腺瘤相關已被研究證實[14],原因考慮與胰島素抵抗有關,胰島素會導致胰島素樣生長因子Ⅰ的過度增加,高胰島素生長因子Ⅰ血癥和高胰島素血癥是結腸腺瘤的危險因素[15],同時有研究顯示,降糖治療如應用二甲雙胍可降低結直腸腺瘤風險[16-17]。
有研究顯示,血脂紊亂同樣為結直腸腺瘤危險因素[18-19],本研究多因素分析顯示,高血壓、血脂紊亂與結直腸腺瘤無相關性,原因考慮在分組中血脂紊亂組中納入了已用藥控制血脂的患者,已有研究顯示降脂治療,如他汀類藥物可預防結直腸腺瘤或結直腸癌復發[20-21],高血壓與結直腸腺瘤關系仍不甚明確[22],亦無降壓藥物與結直腸腺瘤關系的相關研究,在以后工作中可進一步關注高血壓及降壓藥物與結直腸腺瘤的相關性。
綜上所述,結直腸腺瘤的發生與代謝綜合征密切相關,臨床工作中對代謝綜合征患者應提高警惕,加強結腸鏡篩查,同時對有代謝異常的患者給予積極的生活方式干預,控制體重指數、血糖、血脂在正常范圍內可預防及降低結直腸腺瘤的發生、復發甚至惡變風險,值得今后研究中進一步分析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