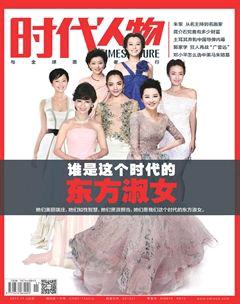“困獸”普京應對西方制裁
方亮
9月10日,從去年11月發展至今的烏克蘭危機正式迎來一次“暫停”。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在電話會談中表示,對5天前基輔與自行獨立的頓涅茨克、盧甘斯克二州,于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簽署的停火議定書的執行情況表示滿意。
該議定書規定了烏克蘭政府軍和東部二州的親俄武裝的停火,并且議定雙方開始交換戰俘和開辟人道主義走廊。但對東部二州未來地位這一根本問題,議定書則未做安排。因此,雙方的停火如外界所說的那樣是“包括俄、烏、親俄武裝乃至歐盟等各方需要所作出的權宜之計”,其持續性是沒法讓外界有信心的。
普京“以壓促和”
當天,受任于危難的烏克蘭寡頭總統波羅申科還在政府會議上表示,將于下周提交賦予東部二州特別地位的法案,但堅稱絕不會給予二州獨立或者聯邦制地位。同一天傳出的另一則重要消息是,烏克蘭部隊開始在由自己控制的俄烏邊境地區修建名為“墻”的防線。該防線由l500公里的戰備通道和數千個掩體、火力點組成,其壕溝寬4米、深2米。波羅申科將其比作芬蘭在二戰前修建的用于防范蘇聯軍隊的“曼納海姆防線”。
單從波羅申科的表態看,這位素來以深諳平衡之道著稱的寡頭政客,仍然堅持著在對俄立場的“軟”和“硬”之間進行協調。“墻”防線是一種“硬”,但順應俄立場給予東部二州特別地位則是一種“軟”。客觀來看,波羅申科做出這樣的表態并不艱難一一畢竟他仍在自己國家的領土上用兵,俄則是直接將部隊開到了別國領土上。至于議定書,那本來就不是一份有著較強法律約束力的文件。
由此,倒是值得分析—下普京的戰略及操作。8月28日,俄羅斯正式出兵烏克蘭。盡管克里姆林宮一再否認,但這終歸還是由全球見證的事實。要知道,早在6月普京就已經請求俄上院撤銷3月作出的出兵烏克蘭授權,并且得到了滿足。所以,普京出兵的決定不但違反了國際法,更是違反了俄國內法。即便這樣普京還是作出了出兵決定,此中緣由要從普京在整場烏克蘭危機中的戰略角度來分析。
2月,烏克蘭“二月革命”成功,克里米亞地方議會被“不明身份”的武裝分子劫持,并作出了舉行公投的決定;3月,克里米亞公投決定該地區加入俄羅斯聯邦并被莫斯科接納;隨后,位于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盧甘斯克二州出現大批不明身份武裝分子;5月,二州通過公投自行宣布獨立并宣布將謀求同克里米亞一樣加入俄聯邦;美歐方面在俄吞并克里米亞之后就隨之祭出了經濟制裁,并在東部二州公投之后加重制裁,直至7月17日發生MH-17客機的墜機之后將制裁措施提升至最嚴厲程度;普京在歐美制裁期間的6月作出了請求上院撤銷出兵烏克蘭授權的決定,也成為其立場發生明顯變化的開始。
如果說此前普京的戰略一直是“對烏克蘭境內持續發力”,那么這一決定之后開始明顯轉向“守成”。當7月17日MH-17墜毀,身處輿論壓力中的普京開始明確其“和平守護者”形象,為此不惜跑到東正教全俄大主教基里爾那里為和平禱告。
普京“低頭”的原因,還要從歐美的經濟制裁上來尋找。不久前盧布匯率跌破38盧布兌1美元、50盧布兌1歐元大關的事實,成為上述原因非常明顯的注腳。經濟壓力之下,普京只能選擇軟化立場。畢竟俄羅斯國力的基本面是由其經濟發展狀況決定的,普京在烏克蘭唱的這出大戲本來就是在一個較為虛弱的國力基礎上硬撐著上演的。
但是,普京并未如l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中的赫魯曉夫那樣遇到肯尼迪的壓力之后就徹底放棄既定戰略,其立場的軟化始終帶著“以壓促和”的特征。在這期間,普京先后發出了“俄羅斯是一個核大國”、“我們兩周就可以打到基輔”等強硬表態,最后更是直接出兵烏克蘭。
普京的戰略是:壓力下的俄羅斯固然要“求和”,但卻會淡化“求”字,用持續的壓力讓歐美烏三方按照莫斯科的條件來達至和平。普京的這一戰略在8月26日舉行的關稅聯盟、烏克蘭、歐盟三方的明斯克會談上得到了較為明確的表述,俄總統堅持讓基輔直接與東部二州對談,以早日確立二州的“特殊地位”。
和平計劃的背后
8月26日的這次明斯克會談成為眼下這次“暫停”之前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該會談之重要從德國總理默克爾于會談前對基輔的突訪這一事實體現出來。外界普遍認為,默克爾此舉就是為了規勸烏方接受俄立場,同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二州直接談判,確定二州未來地位。但是,到了明斯克會談時,當普京看到烏總統波羅申科仍然拒絕這一提議,立即放出了強硬表態。會談兩天后,俄軍便正式出兵烏克蘭了。而在俄出兵之后,烏方立場也發生了軟化,這才有了9月5日的明斯克停火議定書。
所以,本來在“求和”的普京卻至始至終表現得非常強勢,甚至不惜破壞國際法和國內法直接出兵別國領土。這也成為普京對外手腕的一個重要特征:多階段施壓,即便軟化立場也以主動施壓的手段求得事態以自身意愿發展。
從另一條線索來看,普京這一戰略表現得更加明顯。在普京明確“求和”路線而親俄武裝仍在同烏軍激烈交戰的這段時日之內,戰場上的總體態勢是烏軍節節收復失地,而得到俄方提供的防空導彈等武器供應的親俄武裝卻節節敗退。也正因為俄方的“強勢”,波羅申科才改變了立場,開始直接同東部二州對談,并承諾給予它們“特殊地位”。
普京手腕最終體現在他于9月3日在飛機上拋出的那個“七點和平計劃”中。這個和平計劃最終成為了明斯克停火議定書的藍本,其中雙方撤軍、保持二州現狀等內容都在后來的明斯克停火議定書及各方行動中得到體現。
突然的出兵,在戰場上達成目標后又突然拋出撤軍計劃,這一“抽撤連環”式的操作至少起到了一石三鳥的作用:首先,在被俄軍擊敗后烏方別無選擇只能接受這一建議,哪怕只是出于權宜考慮,如此俄方就可以通過一紙停火議定書而非實際軍事存在來維持二州現狀,這樣可以避免俄軍長期在別國領土上非法存在所帶來的負面輿論影響和軍事、經濟損耗;其次,保持二州現狀則讓普京的策略首度以和平的狀態持續,這與以戰爭手段對其進行支撐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第三,普京主動拋出和平計劃給了西方一個姿態,讓西方有了“借坡下驢”的機會,從而對西方后面對俄的制裁產生了動搖。endprint
在這里,第三點格外重要,西方對俄這一“抽撤連環”操作的反應可謂正中普京下懷。
西方的綏靖
當8月28日俄出兵烏克蘭東部二州的消息傳來,所有預測普京不會出兵的人士都倍感意外。經歷了俄吞并克里米亞這一先例,外界判斷普京時已經應當留有余地,因為在烏爆發“二月革命”之時外界大多可以估計到普京將強力回應,卻很難想象到回應手段會硬到吞并烏領土的地步。畢竟冷戰之后公開將別國領土據為己有的先例極為罕見。
由此,西方的回應就顯得格外重要。如果說三場公投這一莫斯科的“遙控”手段引來了歐美的經濟制裁,那么當俄直接出兵烏克蘭,歐美理所應當給出更加嚴厲的回應。但是,從西方國家在北約威爾士峰會及歐盟新一輪制裁中的表現來看,對普京的懲罰并未升級。
俄軍出兵烏克蘭之后不久,歐盟就做出升級制裁的威脅,但這只“鞋子”卻遲遲沒有落地。直到9月11日歐盟才正式作出制裁俄羅斯的決定,禁止對5家俄羅斯國有銀行和3家俄羅斯能源公司貸款,擴大對俄出口軍民兩用物資限制,并將24名俄羅斯公民新增進旅行限制和資產凍結名單中去。
從已知的制裁內容看,它并未對前幾次制裁內容有實質性突破。英國方面提出的關閉俄羅斯銀行使用“環球銀行金融電信聯盟結算體系”通道的建議被認為過于極端而未被采納,該建議如被采納將給俄銀行體系造成極為嚴重的打擊。此前曾傳出過兩次“制裁即將公布”的消息,但都放了空炮。9月11日的宣布可謂姍姍來遲。
9月5日的明斯克停火議定書是一個“包括俄、烏、親俄武裝乃至歐盟等各方需要所作出的權宜之計”,這其中歐盟的需要便是盡快讓普京收住胃口,停止在烏克蘭發力。
顯然,歐盟的目標設定僅是阻止普京進一步侵犯烏克蘭,而非讓普京將已經吞進腹中的利益吐出來。因此,默克爾在明斯克會談之前突訪基輔,目的就是勸波羅申科接受普京提出的條件——給予二州特殊地位。歐盟這一態度等于是重復了在格魯吉亞問題上的態度,縱容了普京這一戰略,對普京做了妥協,這毫無疑問是一種綏靖。
再來看看北約。歐盟所能祭出的手段最多不過是經濟制裁,但俄非法出兵烏克蘭的動作卻恰好發生在北約威爾士峰會之前,這個龐大的軍政組織有足夠的理由對俄作出強硬回應。但是,在俄出兵后的第一時間美國總統奧巴馬就否認了美國直接出兵以及軍援烏克蘭的可能,這難免讓外界對此次北約峰會可能對俄祭出的手段感到悲觀。隨后,奧巴馬訪問了愛沙尼亞——一個雖然也受俄威脅卻遠不是眼下普京強硬政策直接受害者的國家。外界會問,為何奧巴馬不通過直接訪問基輔的姿態直接對烏克蘭表達支持。
在愛沙尼亞,奧巴馬較為明確的代表西方闡述了對普京的應對戰略,那就是壓低油價,直接從財政角度向普京政權施壓。到了9月10日,北海布倫特原油價格已經降至100美元以下,自然對普京政權造成壓力。不論奧巴馬的表述是否是借油價走勢所說的“便宜話”,普京政權因經濟而受壓已是事實。不過,奧巴馬這一表態還是說明北約不打算采取強硬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奧巴馬也于同一時間宣布對俄制裁,截至9月11日制裁內容尚未公布,但估計它也將同歐盟制裁一樣“單純強調姿態”。
當峰會閉幕,外界看到的只有在東歐國家部署快速反應部隊的計劃,這一計劃尚未有明確內容,甚至不確定部隊具體部署國,其實施更是需要較長時間。此外,給予格魯吉亞以北約特殊合作伙伴地位以及向烏克蘭援助1500萬歐元的動作雖然不能說毫無意義,但也只是象征性意義。
除了這些,外界就只看到了北約秘書長拉斯姆森將俄列為北約敵人的表態以及峰會文件上對俄羅斯侵略行為的譴責。
顯然,北約同歐盟一樣,僅將目標設定為阻止普京,懲罰普京乃至讓其將克里米亞和二州吐出來的目標根本不在他們考慮之內。在這種情況下,波羅申科和烏克蘭的未來很可能跟眼下的格魯吉亞一樣,只能忍耐國土淪喪,盡管尚難肯定眼下的停火能持續多長時間。
西方的應對策略
此番西方對俄羅斯的應對確實偏軟,但還是有效果的,畢竟經濟制裁成功逼迫普京立場后退。在戰術層面來審視西方這種偏軟的政策,沒人給烏克蘭做主等國際正義問題會自然浮現,人們也會擔心未受實質性懲罰的俄羅斯會跑到別的地方搞事。
但如果將視野放到西方與俄羅斯博弈的戰略層面并且訴諸歷史,可感覺到西方領導人雖然未表現出古巴導彈危機時美國總統肯尼迪那樣的堅強意志,或是上世紀80年代里根總統用潘興導彈強硬對抗蘇聯SS-4、SS-5導彈那樣的強硬,卻從客觀上遵循了里根和老布什在蘇聯存在后期應對這一帝國的戰略。前者在防止普京繼續對外強硬政策的時候不可或缺,但是從戰略層面上看,里根和老布什的智慧更加根本。
這場烏克蘭危機同勃列日涅夫在阿富汗發動的戰爭非常相似。西方都沒有直接在戰場上同莫斯科相撞,而都采取側面行動來消耗俄羅斯人的意志,讓這個帝國的鏈條率先從經濟上斷裂。對待蘇聯/俄羅斯這種“龐然大物”,這種戰略無疑更加聰明。俄羅斯帝國幾百年來最大的弱點一直是經濟,經濟上的孱弱往往可以影響其地緣戰略乃至內政走勢和國家分合。從實際效果看,俄羅斯經濟確實遭到雪上加霜的打擊。當然,也增加了普京政權在被經濟拖垮之前再次強力出手的可能。
雖然眼下普京表現非常強勢,但掩蓋不了一個事實——俄羅斯在不斷衰弱。西方在應對普京挑戰的同時,也應當未雨綢繆地考慮如何應對上述事實可能帶來的后果,這一后果并不僅限于地緣和軍事挑戰。從蘇聯解體的后果來看,這樣的結果被較為成功地避免了,盡管也帶來了塔利班崛起等間接性惡果。但是,之后的事情仍需要一整套較為完備的戰略去加以應對。從這個角度講,俄羅斯的徹底失敗并不符合全球利益,讓俄羅斯改弦更張、實現平穩及無害的繁榮才是適宜的目標。
在與普京周旋的過程中,西方應當把握好度,在必要的時候對俄給予幫助。在俄羅斯逞兇的背景下說這話或許有些不切實際,但若考慮到這次烏克蘭危機很可能是普京政權最后一次或最后幾次之一的瘋狂,那么這一判斷就多少具有了前瞻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