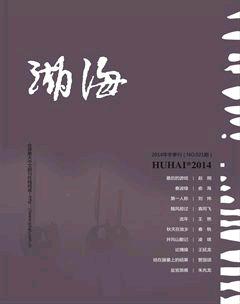我發現王艮畫像碑的經過
汪受寬
明代思想家王艮(1483-1541),字汝止,號心齋,安豐人,創立了泰州學派,奠定了明朝以降安豐文化的興盛,是鹽城市境歷史上最著名的學者。除其著作之外,王艮的遺物如今已無法尋覓,但歷經400年蒼桑的王艮畫像碑,卻至今完好地保存下來,成為人們憑吊心齋夫子的唯一實物。有人說:“王艮畫像碑是一位歷史愛好者發現的。”作為歷史學者的筆者,不得不在此述說40年前發現王艮畫像碑的經過,以表個人對鄉邦文化摯愛的拳拳之心。
那是1971年冬,我從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縣回安豐探親。當時安(豐)時(堰)河開挖不久,串場河上的太平橋被拆除,河西袁承業的淘西別墅也因挑河而消失。一次飯后沿河邊散步,走到太平橋東邊,見地上橫七豎八地堆放著許多石條,估計是挑河抬出來的。忽然,我注意到一塊圓首碑形石條上依稀有字,就用鞋底將上面的灰土蹭了蹭,“心齋王夫子像”六字映入眼簾,我一下子被震驚了。作為安豐人,上世紀60年代初在大學歷史系求學時,我就認真研讀過鄉賢王艮和吳嘉紀的著述和事跡,深為他們崛起于貧賤,傲視卿相,特立獨行,而流譽華夏的事跡和品德所吸引,并引為驕傲。這次竟能發現明中葉所立王艮像碑,真是萬幸。見碑上陰刻的心齋夫子像,面容清臞,隆準廣顙,豐骨奇古,須髯飄逸,戴峨冠,著褒大深衣,腰圍紳绖,手執書卷,十分傳神。碑的上端有郝繼可所題六行48字贊辭,言:
粵維夫子,人相厥真。仙半道氣,玉骨金筋。子曰:“不不,惟圣統天。”文成嘆曰:“鐵漢,鐵漢!”從今觀之,果然,果然。天何言哉,小子迷焉。
辭末題“萬歷壬子仲春之吉”8字,表明此碑立于明神宗萬歷四十年(公元1612年)二月。碑右側署“泰州儒學訓導后學私淑門人郝繼可頌”。查袁承業所撰《明儒王心齋先生弟子師承表》,內有《先生五傳弟子郝繼可傳》,稱,郝氏“字汝極,號桐浦,(安徽)和州人,……由歲貢授泰州學訓,刻心齋夫子石像于東淘精舍,立會宗祠,闡明心齋之學,視同志如父子,辭寒士之贄,絕私交之饋。年六十四卒于官。著有《桐蒲集》行世。”該碑或民國初年為袁承業收存于其所建淘西別墅中,因挑河拆屋而散落于此。
該碑立于王艮逝世70年后,郝氏當未親見心齋夫子。查嘉慶《東臺縣志》卷34《古跡·東淘精舍》條,附有明太常卿郭汝霖撰《東淘精舍記》,文云:“庚子先生棄世。明年,巡鹽象岡胡公植肖先生像舍中,而總督介川毛公愷顏其上。”胡植于王艮去世次年即繪成其畫像,郝氏所刻心齋畫像當摹自該像,故能如此傳神。
明萬歷王艮畫像碑的發現,令我激動不已。為保存鄉邦文化,給中國思想史研究提供實物資料,我囑托在安豐工商所工作的同學林凱旺,幫忙將該碑暫為收存,以備國家文物部門永遠寶藏。不幾天,我返青海途經上海時,致信南京博物院報告了這一發現,希望他們派員到安豐將此碑予于收藏。過了幾個月,我收到東臺縣文化館的一封來信,言,他們已將此碑妥為收藏,并表示感謝我對祖國文物的關心,云云。
1980年歲末,我和幾位研究生同學一起在北京查閱撰寫畢業論文的資料,其間曾去中國歷史博物館辦公區拜訪著名文物文獻專家史樹青先生。史先生問到我的籍貫,對王艮和吳嘉紀贊譽有加,我即告訴他發現王艮畫像碑的事。史先生道:“這一發現很有價值。據我所知,王艮的文物僅有一方硯臺,畫像或畫像碑皆未見報導。你應該將此發現寫成文章,在《文物》雜志上介紹。”由此,1981年1月4日,我給東臺縣文化館去信,說明館藏王艮畫像碑系本人發現,史樹青先生極為看重該碑的文物價值,要求我撰成文章加以介紹。故請求貴館將該碑制作拓片,郵寄給我,所需捶拓費用,由我承擔。此信發出后,如石沉大海,始終未見回音,故而我也無法撰成向國內學界介紹該碑的文章。我十分后悔當初倘若拓下一幀碑帖收存,也不至于弄得如此求人而不被理睬。好在多年來,該碑先后被列為東臺縣和鹽城市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又在圖書和網絡上見到該碑的照片,也算了卻了我的一樁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