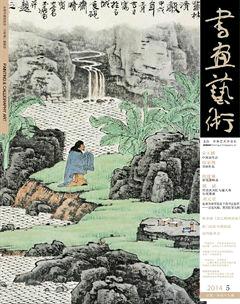小議宋文治畫竹
黃輝
一
在宋文治先生一生的繪畫生涯中,寫竹圖僅是其繪畫生涯中的一個片段,宋文治早年曾師承吳湖帆先生,而吳湖帆先生在近世曾以畫竹名顯于世,吳湖帆筆下的竹子有疏淡清雅之韻味,竹葉有“鳳尾梢卷”之勢。雖不著色,但仍有縝麗豐潤,蒼翠華滋的富麗堂皇之感。吳湖帆的寫竹之法顯然以文同、吳鎮之墨竹法為之,諸如《管道昇竹窗圖大意》《趙松雪法》《仿顧定之之筆》《仿蘇軾筆法》《擬文湖州幽篁》等遺作中可看出端倪。宋文治先生的畫竹之法主要宗法元代的趙孟頫,同時又受到了其師吳湖帆的影響,尤其喜愛吳湖帆的雨竹。宋文治畫竹以氣韻為上,同時又追求高古的氣息。縱觀宋文治的繪畫生涯,其所畫文人之竹并不多見,主要是為在創作山水畫之余的應酬之作。在所贈書法墨跡中,出于對對方的重視,一般都會用汁綠畫竹子做底子,然后再題書于上面,相得益彰。
既然吳湖帆、宋文治的寫竹之法都受到趙孟頫的影響,那么趙孟頫的畫竹情況又是怎樣的呢?探討這一問題顯然離不開趙孟頫的成長之所——湖州,而湖州這個地域又與文人畫家有著怎樣的關系呢?這同樣也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趙孟頫自小出生在竹子遍栽的湖州,竹子是趙孟頫兒時再熟悉不過的事物了。后來趙孟頫得到賞識,幾上大都,但家鄉湖州無疑是他人生留戀之所。每回到家鄉,他總是游藝于余杭、吳興間。其實,善于畫竹的趙孟頫與當時的文人畫家均有交往,而李衎和高克恭就是其中重要的兩位。李衎對寫竹之法極為重視,著有《竹譜》一書,在其首言中寫到:“登會稽,歷吳楚,逾閩嶠,東南山川林藪游涉殆盡,所至非此居者無與寓目。凡其族屬支庶,形色情狀生聚榮枯、老雅優劣,窮諏數察,曾不一致。往歲仗國威靈,遠伎交趾,深入竹鄉,區別品匯 。”趙孟頫對李衎的寫竹之法也極為賞識,曾題有《李仲賓(野竹圖)》所言:“吾友李仲賓為此君寫真,冥搜極討,蓋欲盡得竹之情狀。二百年來畫竹稱著者,皆未必能用意精深如仲賓也…… ”此外,元大德七年四月及武宗至大元年間,趙孟頫曾數次對李衎的《墨竹圖》進行跋句或題詩。
高克恭與趙孟頫也素有交往,高克恭也是寫竹之高手,趙孟頫同樣也曾題詩于他,如趙孟頫《題高彥敬畫二軸》,詩曰:“疏疏澹澹竹林間,煙雨冥朦見遠山。記得西湖新霽后,與公推杖聽潺湲。”關于二人的深厚情誼,元代的虞集在《題高彥敬尚書趙子昂承旨共畫一軸為戶部楊侍郎作》詩中記到,“趙公自是真天人,獨與尚書情最親”。尚書者即為高克恭。而高克恭的寫竹之法又得力于誰最多呢?吳鎮在《梅花道人遺墨》卷下《竹譜》中記載曰:“古今墨竹雖多而超凡入圣脫去工匠者惟宋之文湖州一人而已,近世高尚書彥敬甚得法,余得其指教甚多,此譜一一推廣其法也。”吳鎮此語道出他的墨竹之法得高克恭指教甚多,而高克恭又甚得文同之法。高克恭墨竹世已罕得,北京故宮博物院現存有《墨竹坡石圖》,為其存世精品。
二
湖州文人寫竹畫家群,曾被有的學者稱為“湖州竹派”。不僅僅是這里有著豐富的竹林環境,能為畫竹提供良好的素材,更重要的是從宋代的文同、蘇軾出任湖州始,到元代的寫竹畫家群的出現,造就了當地畫竹的繁盛,即便是到了明清時期,大部分畫家還是以承繼湖州竹派之余緒。明代晚期,杭嘉湖地區的畫竹名家包括昆山人歸昌世(1573年—1644年)、蘇州人朱鷺(1553年—1632年)、浙江崇德人費楨(生卒不詳)、浙江山陰人徐渭,其中徐渭成就最高。清末民國時期,吳昌碩接湖州竹派之余續,振臂高呼,引領諸聞韻(浙江安吉人)、諸樂三(浙江安吉人)、潘天壽(浙江寧海人)、吳茀之(浙江浦江縣人)、王個簃(江蘇海門人)等弟子,活動在上海、湖州、杭州之間,為湖州竹派在杭嘉湖地區的傳承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蘇軾在湖州竹派的確立和發展上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呢?那便是極力推崇文同,蘇軾《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有言:“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余。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從成乃凡編著有《歷代詠竹詩叢》一書來看,宋代的論竹詩最多,多達1530首。在宋代詠竹詩中,又以梅堯臣、文同、蘇軾、黃庭堅、蘇轍等人的創作數量最多。可見從宋代那里,寫竹之法、之趣、之情,已完全深入到文人士大夫那里去了。上文對趙孟頫古法的追溯,我們可以推出湖州是江南文人畫竹的發源地,近代蒲華就仰慕先賢吳鎮的畫竹成就,對文同,蘇軾也很傾倒,在一部墨竹集冊中題有“文蘇馀韻”四字。晚年寫竹,懸筆中鋒,干枝直揮沖天,撇葉如刀斧下斫,風雨驟至,尤善于結頂 。對蒲華的畫竹水平,曾宓對其評價甚高:寫竹一道,各家有別,而難在結頂,也貴在結頂。只往不復,只“造”無“破”,在章法上終非上乘。而蒲華內既自得,故不矜持,即使一竿通天,隨意開張,總能收拾得體。長毫飽墨,肆意揮灑,雖粗枝大葉,而法備氣至。打點如高山墜石,筆力千鈞,不似似之,渾然一體;寥寥數筆,穆穆皇皇。其抒寫之速,結頂之妙,組合之自由,境界之高,形簡意駭 。
以浙江籍為主體的畫竹家群體,很快影響到了周邊的地區。不僅影響到了其他畫家的寫竹之法,還使得湖州竹脈深入人心,這同樣也給湖州的地域環境植入了強大的人文精神。在近代畫竹家那里,我們往往會看到仿文同、趙孟頫、蘇軾等筆意的一類畫作,這一筆意的抒寫往往出于宗法湖州竹脈余續的畫家情結。宋文治先生于壬戌年冬日《學趙文敏筆意墨竹圖》同樣也是出于這樣的情結。竹子背后所蘊含的人文精神,亦被當時的畫竹之家所關注,比如,蒲華曾與吳昌碩合作過一幅《歲寒交圖》,一人畫梅,一人畫竹,蒲華在此圖上寫到:“死后精神留墨竹,生前知己許寒梅。”宋文治先生也常在自家畫的竹子圖中,落有“高風亮節”一款。
最后,對畫竹之法的賞鑒標準又是怎樣的呢?實際上畫竹之法則還要歸到中國畫上的“似與不似”上。宋文治講到,中國畫的傳統,由“似到不似”,然后達到“在似與不似之間”。因此,要把工夫下在解決國畫的“似與不似”上。關于這一點高克恭在談及趙孟頫與李衎的墨竹法時,曾言到:子昂寫竹,神而不似;仲賓寫竹,似而不神。其神而似者,吾之兩此君也。白居易在其《畫竹歌》中寫到: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并以“莖瘦節節竦;枝活葉葉動”為尚,而宋文治先生所畫之竹顯然暗合古法,所作墨竹濃淡相依,莖瘦節竦,枝葉間錯,折旋向背,各具姿態,曲盡生意。
到此,本文論述宋文治先生關于墨竹的文字并不多,但我們很容易梳理清楚宋文治畫竹的師法傳統,和作為山水畫大師其繪畫的另一面。宋文治的畫竹之法主要得力于其師吳湖帆的影響,而吳湖帆的畫竹之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湖州竹派”人文傳統的影響。關于這一點,我們很容易從吳湖帆的“仿畫”一類的竹圖中看出。這同樣也說明了宋文治在傾注于山水畫的同時,對傳統的墨竹圖亦有著文人化的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