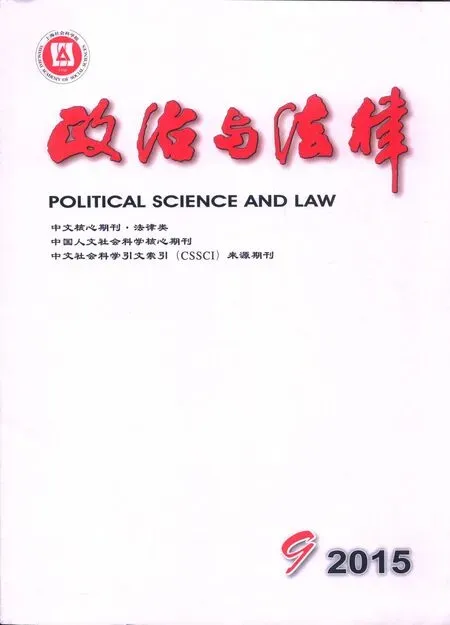家庭暴力反抗案件中防御性緊急避險的適用*
——兼對正當防衛擴張論的否定
陳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100872)
家庭暴力反抗案件中防御性緊急避險的適用*
——兼對正當防衛擴張論的否定
陳璇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100872)
對于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為了防止將來繼續遭受暴力襲擊而將施暴者殺死的案件,我國的審判實踐往往過早地求諸酌定量刑情節,從而忽視了公民緊急權對于解決此類案件所蘊含的法教義學資源。首先,無論是暴力的長期性、法益保護的有效性,還是“受虐婦女綜合癥”理論,都不能成為無限擴張正當防衛中不法侵害“正在進行”這一要件的充分理由。其次,從緊急權的體系來看,直接針對危險制造者的防衛行為,除了可能成立正當防衛之外,還可能以防御性緊急避險的名義獲得合法化。因此,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在別無其他求救途徑的情況下,為保護自身或者其他家庭成員的生命以及重大身體健康,將施暴者殺傷的行為,存在成立正當化的緊急避險的余地。
防御性緊急避險;正當防衛;緊急權;家庭暴力;受虐婦女綜合癥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家庭暴力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對象,反家庭暴力亦逐漸成為國家立法的重點領域。為了有效防止家庭成員之間的虐待、傷害等行為,固然應當完善國家機關、社區組織適時防范和介入的機制,加強對家庭暴力實施者法律責任的追究,但同時也應當重視保障家庭暴力受害者在無法及時尋求國家和社會庇護時所享有的緊急防御權。2015年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的《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首次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對公民為反抗家暴而導致施暴人死傷的案件,給出了相對具體的處理意見。首先可以確定的是,對于正在進行的家庭暴力行為,受害者有權實施正當防衛。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時常會出現這樣一類極富爭議的案件,即行為人在遭受長期虐待、毆打后,為預防可能繼續出現的暴力而趁施暴者不備將其殺害,如以下案例。
案例1:1990年,被告人劉某某(女)經人介紹與被害人張某某(男)結婚,二人育有三個孩子。婚后,張某某時常用木棍、鐵棍、皮帶、椅子、鐵鍬、斧頭、搓板、叉子、搟面杖等器械毆打劉某某。2001年以后,每隔兩三天劉某某就會遭到暴打。在此期間,劉某某想過撥打110報警,但一想到丈夫頂多被拘留幾天,放出來后一定饒不了自己,只得作罷;她也想過上法院離婚,但張某某曾威脅她:“要是敢提離婚,就殺了你全家”;村委會也調解過,但并無效果。2002年10月,劉某某被張某某用鐵鍬敲破了腦袋,這讓劉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威脅。2002年農歷11月30日,劉某某在集市購買了“毒鼠強”,并想“只要他讓我和家里人把這個年過好,我不做過分的事”。然而,2003年1月15日,張某某再次用斧頭毆打了劉。1月17日下午3時,劉某某在為張某某做咸食的過程中,將毒鼠強倒在了雜面糊中。下午6時,吃下咸食的張某某出現中毒癥狀,后經搶救無效死亡。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12年。①參見趙凌:《殺夫:悲涼一幕》,《南方周末》2003年7月3日。
案例2:被告人吳某、熊某長期遭受被害人熊某某(吳某丈夫、熊某父親)的虐待、毆打。吳某曾多次向被害人所在單位、街道等求助,但熊某某不僅沒有改過,還變本加厲;吳想要離婚,又因二者間系軍婚(熊某某系部隊軍醫)而不能。案發前兩個月,吳某在家中發現了劇毒氯化鉀。2005年3月19日晚,被害人因被告人熊某學業又辱罵兩被告。12時許,熊某某突然進入二被告人睡覺的房間,驚醒二被告人后又回到自己房間睡覺。吳某據此及近幾個月來被害人的種種異常表現,預感自己和兒子處于生死險境之中。次日凌晨2時許,吳某、熊某分別持鐵錘、搟面杖,趁被告人熟睡之機,朝其頭部、身上多次擊打,又用毛巾勒其頸部,致其機械性窒息死亡。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吳某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以故意殺人罪判處熊某有期徒刑5年。②參見遼寧省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05)大刑初字第203號,《人民司法·案例》2008年第6期。
當這類“受虐婦女殺夫”的悲劇見諸媒體時,總能引發人們的廣泛關注。被告人作案前悲苦的經歷和無助的境遇,與被害人暴虐的習性和冷酷的行徑,不可避免地使公眾心中的道德天平朝前者一方傾斜。因此,當該類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后,往往都會出現當地居民、人大代表聯名寫信請求法院對被告人開恩寬宥的一幕。③參見魯德琪、吳昊:《受虐婦女被逼殺夫,16位人大代表呼吁從寬處理》,《遼沈晚報》2002年12月27日;趙凌:《殺夫:悲涼一幕》,《南方周末》2003年7月3日。對于此類案件,《意見》第20條沿襲了我國法院此前的一貫做法,并給出了權威性的總結:“對于長期遭受家庭暴力后,在激憤、恐懼狀態下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為了擺脫家庭暴力而故意殺害、傷害施暴人,被告人的行為具有防衛因素,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顯過錯或者直接責任的,可以酌情從寬處罰。”在此,《意見》準確地提煉出了有利于行為人的兩大事實因素:一是行為具有防衛因素,二是被害人具有重大過錯。同時,《意見》選擇將這些因素置于量刑階段而非定罪階段去考量。司法機關的這一做法有其現實的考慮。在我國,由于“殺人償命”、“只要死了人總要有人負責”的觀念仍然根深蒂固,故采取“定罪輕判”的處理方式似乎能達到兩全其美的效果:一方面通過定罪能保證行為人為死亡結果承擔刑事責任,另一方面通過輕判又能兼顧那些可能使民眾對被告人產生同情的事實因素,從而保證判決結論的可接受性。可是,當案件中出現了在正義情感上有利于被告人的因素時,這種因素并非只能通過量刑中的酌定從寬情節這一條途徑來影響刑法對行為的評價,它們同樣可以在定罪環節的各類違法和責任阻卻事由中得到體現。因此,只有當定罪中所有的出罪事由都已被窮盡并均得出否定性的結論時,才能考慮能否通過法定或者酌定量刑情節來減免行為人的刑事責任。④Vgl.Rengier,Strafmilderung bei Mord,NStZ 1984,S.21.
在筆者看來,我國的刑法理論和審判實踐尚未充分地挖掘違法阻卻事由對于解決這類案件所可能蘊含的資源,而是過早地將相關問題推到了量刑環節之中。有鑒于此,筆者于本文中將對與此類案件相關的出罪事由詳加分析,希冀透過緊急權體系的整體視野,澄清我國傳統刑法學在公民緊急權理論方面存在的誤區,進而在法教義學上使該類案件的處理方式更加趨于精密、更加具有信服力。為方便對同一問題展開比較研究,以下選取出一則曾經引起德國刑法學界廣泛討論的案例。
案例3:被告人A(女)與被害人E為夫婦,R為A與其前夫所生之子,A與E育有一女S。長年以來,E經常對A及R實施虐待。A曾多次考慮帶著子女出逃,但每每慮及家中有患病的老父需要照顧,遂又放棄此念。1982年8月18日,R不堪虐待,逃至A的前夫家中躲避。E得知后暴跳如雷,打電話勒令R三日后必須返回。隨后,E余怒未消,向A大聲咆哮,聲稱等R回來要把他狠揍一頓,并且說,要是自己現在有輛車,非得馬上趕過去“抓住那小子的頭往墻上撞,直至他斷氣為止”。A十分擔心,一旦自己的兒子回家,只恐性命難保。第二天晚上,E在繼續痛罵了R一通后睡去。A因極度憂慮R歸家后可能的遭遇而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最終,為了避免自己和兒子再受折磨,A趁E熟睡之機,拿起錘子將其砸死。⑤BGH,NStZ 1984,S.20.
二、正當防衛之否定
家庭暴力屬于一種不法侵害,故針對家暴實施者采取的反擊措施,有可能成立正當防衛。然而,在相關案件中,行為人都是借被害人熟睡或者吃飯之機將其殺害的,故能否成立正當防衛的關鍵就在于,可否認為行為人實施殺人行為時,不法侵害尚在進行之中?部分學者基于各種理由得出了肯定的回答。但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
首先,從侵害具有連續性這一點,并不能推導出侵害行為一直存在的結論。
有的學者主張:受虐的家庭成員所面臨的不法侵害具有連續性和經常性的特征,故應當將持續數年乃至十幾年的家庭暴力看作一個完整的行為過程;這樣一來,就可以認定在受虐者對施暴人實施殺害或傷害行為時,不法侵害仍在進行之中。⑥參見季理華:《受虐婦女殺夫案件中刑事責任認定的新思考》,《政治與法律》2007年第4期;錢泳宏:《“受虐婦女綜合癥”理論對我國正當防衛制度的沖擊》,《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很明顯,這一見解受到了罪數理論中連續犯與徐行犯概念的影響。按照我國刑法學通說,當行為人基于概括的犯意,連續實施性質相同且獨立成罪的數行為時,或者連續實施總和構成一個獨立犯罪的多個行為時,均僅以一罪論處。⑦參見高銘暄主編:《刑法專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88頁以下。但需要注意的是,罪的單一性不等于行為的單一性;不法侵害行為的個數與犯罪個數的確定標準并不一致。因為,定罪所追求的目的與正當防衛的規范目的存在重大差異。無論是連續犯還是徐行犯,都是在已經承認行為人實施了多個獨立行為的前提下,基于入罪門檻的要求或者司法活動經濟性的考慮所進行的犯罪單一化。具體來說,在徐行犯中,之所以不能認定數罪,是因為單個的行為本身并未達到犯罪成立所需的法益侵害的嚴重程度,唯有將多個行為結合起來,才能認定一個犯罪實行行為的存在;在連續犯中,本來就已經存在多個獨立的犯罪行為,僅僅是為了使定罪量刑活動更為簡便,才將其作為一罪論處。⑧參見吳振興:《罪數形態論》,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頁。由此可見,徐行犯和連續犯都是為實現刑事責任追究的合理性而創造的產物。然而,我國《刑法》第20條第1款之所以規定“不法侵害”,其目的卻不在于追究不法侵害人的法律責任,而是在于為公民防衛權的生成確立先決條件。因此,多個行為的連續性或許是使其被評價為一罪的理由,但卻不足以成為使其融合為一個侵害行為的根據。例如,對于甲基于概括的犯意在一個月內連續對多戶人家實施搶劫的案件,盡管根據連續犯的原理,最終對甲僅以一個搶劫罪論處,但不能由此認為甲的搶劫行為在這一月內一直延續不斷,更不能認為,只要在此期間,即便甲正在從事吃喝拉撒睡等與搶劫毫無關系的日常生活時,他人為防止甲繼續實施搶劫,也有權對其實施正當防衛。同樣,雖然按照徐行犯的原理,對長時期多次實施家庭暴力者只能以一個虐待罪或故意傷害罪論處,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將多個家庭暴力行為“焊接”為一個永不停歇、毫無間斷的侵害行為。
其次,能否實現法益保護的有效性,并非決定不法侵害是否正在進行的唯一標準。
有的學者提出,在家庭暴力的案件中,施暴者與受虐者的力量對比往往十分懸殊,所以施暴者熟睡之際是受虐人有效防止未來家庭暴力的唯一時機,如果要求受虐者非要等到暴力行為開始實施之后方能采取防衛措施,那就等于是剝奪了他(她)自救的一切可能,這對于受虐者來說有失公正。⑨參見前注⑥,季理華文;魏漢濤:《正當防衛的適用條件之檢討》,《四川警官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其實,在不法侵害是否正在進行的認定問題上,刑法理論界本來就有一種完全以法益保護的時機為導向的學說。該說認為,只要能夠確定,“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旦從眼下的時間點再往后推延,防衛人將失去有效制止侵害行為的機會,那么不論侵害者是否已經開始實施侵害行為,均允許防衛人行使正當防衛權。⑩Vgl.Schmidh?user,Strafrecht AT,2.Aufl.,1975,9/94.但這一說法是難以成立的,理由在于以下幾點。
第一,正當防衛的極端強勢性,決定了其適用范圍的謙抑性。與其他緊急權相比,正當防衛權在保護法益的力度上明顯展現出較為強勢的風格,具體表現如下。(1)“不得已”要件的欠缺。也就是說,行為人并非只有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才能實施正當防衛。即便存在逃避、報警等其他同樣有效的法益保護措施,也不妨礙行為人直面侵害、出手反擊。(2)限度條件的寬松。盡管我國《刑法》第20條第2款和第21條第2款在分別規定防衛限度和避險限度時,都采用了“必要限度”一詞,但無論學界還是實務界都已達成共識:在判斷防衛行為是否超過限度時,并不需要像緊急避險那樣進行嚴格的法益衡量。那么,正當防衛何以如此“雷厲風行”呢?對此,理論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法秩序維護說,其認為:正當防衛行為之所以合法,是因為它一方面保護了具體的法益,另一方面保障了國家法秩序不受侵犯;這兩點相疊加,就使防衛人一方的利益遠遠高于不法侵害人。二是被害人利益值得保護性下降說,其主張:正當防衛的合法性根據在于,不法侵害人(即防衛行為的被害人)在本可避免的情況下以違反義務的方式挑起法益沖突,故其利益的值得保護性與防衛人相比出現了大幅下降。①相關的理論爭議,參見陳璇:《侵害人視角下的正當防衛論》,《法學研究》2015年第3期。但不管從哪一立場出發,由于正當防衛猶如刀之兩刃,它對于防衛人來說無疑是保護法益的一種有力手段,但對于侵害人來說則是一把殺傷力極大的銳器,故作為其先決條件的“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只能限定在侵害者已經開始實施對他人法益構成現實威脅的身體動靜之上。在前一學說看來,防衛行為要起到捍衛國家法秩序的作用,前提是它必須面對著一個現實違反法規范的行為;②Vgl.Roxin,Der durch Menschen ausgel?ste Defensivnotstand,FS-Jescheck,1985,S.480.根據后一見解,要說不法侵害人的值得保護性出現了嚴重貶值,也必須以侵害人通過某種舉動制造了一個具體的法益沖突局面為根據。總之,既然在眾多緊急權中,正當防衛權是在行使過程中所受限制條件最少、進攻性最強的一種,那么法律在授予公民正當防衛權時必然慎之又慎,既要保證公民能有效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要為這種激烈的自救方式的適用范圍劃定合理的邊界。據此,當丈夫進入廚房去取用于實施虐待的工具時,或者當他酗酒后滿臉怒容地拿著棍棒進入家門時,可以認為侵害者已經以具體的行動對他人的法益造成了現實和緊迫的威脅,故妻子有權果斷地對其采取正當防衛。但在丈夫熟睡或用餐之時,由于并不存在任何對他人法益構成現實威脅的行為,無法認定不法侵害處于正在進行的狀態之中。
第二,立法者也明確表達了不法侵害的現實性乃正當防衛不可動搖之前提條件的立場。在我國1997年《刑法》草擬的過程中,曾有學者主張,應增設“預防性正當防衛”的條款,從而使公民對尚未發生但已迫在眉睫的不法侵害也享有正當防衛權。①參見趙秉志、赫興旺、顏茂昆、肖中華:《中國刑法修改若干問題研究》,《法學研究》1996年第5期。但這一意見最終并未獲得采納。這充分說明,即便在當時,擴大防衛權的范圍已經成為刑法修改的共識,立法者對于能夠行使正當防衛權的前提事實仍保持著嚴格限定的態度。
第三,保證公民在緊急狀態下有效及時地捍衛自身法益,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并非只有正當防衛一條。受虐者在家暴行為實施之前不享有正當防衛權,這絕不意味著法律無情地斷絕了他(她)實行自衛的一切可能。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受虐者完全可以行使別的緊急權。
第四,所謂“受虐婦女綜合癥”理論也不能成為放寬正當防衛前提條件的理由。“受虐婦女綜合癥”(Battered Women Syndrome)的概念最早由美國臨床法醫心理學家、女性主義先鋒雷妮·沃克(Lenore Walker)提出。沃克發現,長期遭受虐待的女性會患有一種綜合癥,其特征主要有二。一是暴力的周期性(Cycle of Violence),即由于丈夫對妻子的暴力往往是階段循環式地進行,這使得受虐婦女長期生活在極度恐懼的狀態之下,故她有理由相信,丈夫對自己的暴力傷害隨時可能發生。二是后天的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即婦女在長期受虐后,會變得越發被動、服從和無助,她不相信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事態,直到家庭暴力的嚴重程度超過了其承受能力。②See Lenore Walker,The Battered Women,Harper&Row,1979,P.55.有學者根據這一研究結論認為,傳統的正當防衛理論完全建立在以男性為標準的基礎之上,但受虐婦女在心理、體力和處境上有別于男性,故該理論無法適用于受虐婦女反抗家暴的行為。受虐婦女綜合癥的第一個特征說明,即便丈夫處于熟睡之中,妻子基于以往的經驗也可以合理地相信,針對自己的暴力即將來臨,若此時不奮起反抗,則無法消除可能到來的虐待;第二個特征則能夠解釋,為何婦女在長期遭受暴力傷害的情況下也不愿采取其他方式逃避這種虐待關系。據此,在受虐婦女殺夫的案件中,應當對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的要件做出較之于傳統理論更為寬松的理解。③參見前注⑥,季理華文;前注⑥,錢泳宏文;前注⑨,魏漢濤文。但筆者對這一觀點持懷疑態度。
刑法教義學對于其他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自然應持包容開放的態度,但這種兼收并蓄并不意味著生搬硬套式的拿來主義,而是需要與刑法的話語體系相融合。在刑法理論中,某個被其他學科發現或者證實了的事實要對案件判處結論產生影響,就必須與刑法中的具體概念和原理實現對接。在經專家鑒定證實的情況下,受虐婦女綜合癥的存在固然可以成為行為人一方的辯護理由;但這種辯護理由最終是落實在正當防衛還是緊急避險,違法阻卻還是責任阻卻事由,定罪還是量刑環節,卻大有可探討的余地。盡管有的英美法系國家的審判實踐已經將受虐婦女綜合癥作為認定正當防衛的根據,但基于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在刑法體系上存在巨大差異,彼所謂“正當防衛”與我國刑法中的“正當防衛”可能不盡相同。例如,加拿大最高法院于1990年對“女皇訴拉娃莉”(R.v.Lavallee)案的判決,④R.v.Lavallee,[1990]1 S.C.R.852.是廣受援引的以受虐婦女綜合癥為由肯定正當防衛成立的判例。但需要注意的是,加拿大《刑事法典》第34(2)(a)條規定,如果某人對于自己將要被殺死或者被嚴重傷害的判斷是理性的,那么,為擊退針對自己的攻擊,被告人故意殺死或者嚴重傷害他人身體的,其行為是正當防衛。根據這一規定,關于不法侵害的認定具有極強的主觀性和情境性色彩,不法侵害是否存在主要取決于行為人的主觀認識及其合理性。只要行為人合理地確信自己正面臨被他人殺傷的危險,即便這種確信與客觀事實不符,也不影響他享有正當防衛權。⑤事實上,除了加拿大之外,其他的英美法系國家和地區也都普遍盛行這種“主觀說”。參見趙秉志、陳志軍:《英美刑法中正當防衛構成條件之比較研究》,《法商研究》2003年第5期;儲槐植、江溯:《美國刑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7-78頁。加拿大最高法院之所以能夠認定被告人的行為成立正當防衛,就是因為受虐婦女綜合癥可以用于說明,行為人在特殊情境下所產生的主觀認識是合乎情理的。①參見陳敏:《受虐婦女綜合癥專家證據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載陳光中、江偉主編:《訴訟法論叢》(第9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頁以下。但是,包括我國在內的多數大陸法系國家刑法理論卻普遍持以下觀點。其一,關于不法侵害的判斷應以客觀事實為依據,②參見前注⑦,高銘暄主編書,第429頁。Vgl.Sch?nke/Schr?der/Perron,StGB,28.Aufl.,2010,§32 Rn.27.若行為人對侵害是否出現存在誤解,則即便這種誤解“情有可原”,其行為也不能成立正當防衛,而是屬于假想防衛,至多只能以行為人欠缺故意或者過失為由(例如我國《刑法》第16條規定的意外事件)排除行為的犯罪性。其二,不法侵害的危險不等于不法侵害行為本身。即便行為人推測將遭受他人的不法侵害,而且該推測也與事實情況相符,但由于畢竟還未出現任何使法益遭受急迫威脅的行為,故不能認為不法侵害已經開始;此時,只能認為行為人面臨著某種危險狀態,故他有權對危險制造者實施緊急避險。③Vgl.Roxin,Strafrecht AT,Bd.Ⅰ,4.Aufl.,2006,§15 Rn.27.因此,有理由認為,英美法并未對正當防衛和假想防衛、正當防衛和防御性緊急避險以及違法阻卻和責任阻卻事由作出像大陸法系那樣嚴格的區分,④例如,英美刑法學者認為,當A的合法利益面臨B的威脅時,即便B并未實施違法行為,但只要這種威脅是不應得的(under served),則A也對B享有正當防衛權。參見[美]喬治·弗萊徹:《反思刑法》,鄧子濱譯,華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627頁;[英]威廉姆·威爾遜:《刑法理論的核心問題》,謝望原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頁以下。然而,在當今的大陸法系刑法學理論看來,針對并未違反義務,但對他人法益造成威脅之人所采取的防衛行為,并不成立正當防衛,只可能成立緊急避險。Vgl. Hirsch,in:LK-StGB,11.Aufl.,1993,§34 Rn.73.故在英美法的語境下,通過采納“受虐婦女綜合癥”理論被認定為屬于正當防衛的某些行為,在大陸法系刑法學看來很可能并不符合正當防衛的要件,但卻能夠借助假想防衛、防御性的緊急避險或者責任阻卻事由等原理出罪。換言之,對于相關案件的處理來說,受虐婦女綜合癥理論是一個不分國界的共享資源,但不同的法律制度和法學傳統吸納、消化和發揮這一成果的具體方式卻可能大相徑庭,故不能以“依據該理論認定了正當防衛”作為評價案件處理方式是否合理的標準。
另外,關于我國正當防衛的規定和理論沒有考慮女性作為弱勢群體所具有之特點的說法,也有失偏頗。一方面,法律對弱勢群體的關懷與同情需要各種法律制度和概念協調配合、相互補充來得到實現,而不能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其中某一項身上,甚至不惜使之扭曲變質。如前所述,之所以將不法侵害正在進行規定為正當防衛的前提條件,是因為考慮到正當防衛作為一種鋒芒最勁的緊急權,其適用范圍必須有所收斂。這是法律對行為人與被害人的利益進行總體權衡后得出的結論,同時也涉及正當防衛與其他緊急權之間的界限,故它不應受個案中行為人具體情況的左右。不過,行為人因性別、年齡、體格、處境等特殊因素而具有的弱勢性,雖不能使不法侵害由無變有,但完全可能在其他的犯罪排除事由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另一方面,正當防衛制度本身也具有體察行為人弱勢特點的寬闊空間。在確定存在不法侵害的前提下,防衛人與侵害人的力量對比關系完全可以成為影響防衛限度認定的因素。因為,防衛人越是處于劣勢,他為實現安全、有效防衛所遇到的困難也就越大,也就越有理由采取較為激烈的反擊手段。例如,同樣是面對他人的暴力毆打,武功高強之人只需略施拳腳即可將其擒服,但一名弱女子或許就只有借助匕首、菜刀等足以致人死傷的器械方能制止對方的侵害。由此可見,僅僅因為無法將受虐婦女殺夫的行為解釋為正當防衛,就指責正當防衛的制度和理論助強凌弱,是沒有道理的。
三、防御性緊急避險的發掘
(一)緊急權體系中的“盲區”
就上述案件而言,不論是實務界過早地將問題推入量刑環節的做法,還是理論界大幅擴張正當防衛適用范圍的嘗試,恐怕都與我國傳統刑法理論對緊急權體系缺乏全面的認識有關。就受虐婦女殺夫案件而言,可以考慮作為行為正當化根據的緊急權無非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兩種。通說向來都認為,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于,前者所針對的是不法侵害者,而后者的損害對象則只能是無辜第三人。①參見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頁。由于在上述案件中,行為人所殺害的均是可能實施虐待等不法侵害的人,而非無關第三者,故在通說看來,要使行為得以合法化,除正當防衛之外別無他途,于是使案件在定罪階段得到合理判處的全部希望就都壓在了正當防衛身上。擺在人們面前的似乎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將該行為解釋成正當防衛,要么承認行為成立犯罪,在量刑中再酌情考慮寬宥之事。但是,通說的理論前提即“緊急避險只能針對無辜第三人”這一命題本來就值得推敲,②較早對該命題提出懷疑的我國學者是劉明祥教授。參見劉明祥:《緊急避險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7頁,第131頁。理由如下。
第一,在緊急權的體系中,直接針對危險來源者實施的合法反擊行為,不獨正當防衛一家。緊急權(Notrecht)是公民在緊急狀態下為保護法益而損害他人法益的權利。損害他人法益的行為之所以能夠得到法秩序的認可,主要是基于以下兩個基本的原則。其一,自由平等原則。我國《憲法》第3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該法第5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據此,任何人未經他人同意,都無權損害其法益;任何人對于他人無正當根據損害自己法益的行為,也都沒有忍受的義務。其二,社會團結原則。盡管自由平等原則是法治國的基石,但每個公民畢竟都與他人共處在一個社會共同體當中,而成員間的相互扶助、彼此忍讓是社會得以存在的必備條件。因此,為了防止對自由平等的強調演變為極端的個人主義,社會團結的思想便應運而生。③Vgl.Renzikowski,Notstand und Notwehr,1994,S.188,320f.社會團結的思想認為:“社會共同體成員之間應當休戚與共,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互相照應。這就要求任何人都應當對他人負有一定責任,在必要時甚至應當適當地為他人犧牲自身利益,部分地放棄自己的自由。”④王鋼:《緊急避險中無辜第三人的容忍義務及其限度》,《中外法學》2011年第3期。緊急權的體系正是在這兩個思想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首先,當某人以違反義務的方式侵入他人的自由空間時,侵犯者作為率先僭越義務的人,失去了要求對方做出犧牲、給予照顧的資格,故基于自由平等原則,受侵犯者不負有忍受、逃避的義務,他有權在為有效制止侵害、保護法益所必要的限度內,對侵犯者的法益造成損害。這種緊急權幾乎純粹以個人自由為基礎,故它在行使過程中所受的制約條件最少。⑤Vgl.Kühl,Freiheit und Solidarit?t bei den Notrechten,FS-Hirsch,1999,S.260ff.這就是正當防衛權。其次,當某人雖然對他人的自由空間造成了威脅,但卻并未實施違反義務的行為時,公民的緊急權同時受到自由平等和社會團結原則的影響。換言之,一方面,由于這種威脅缺乏合法的依據,遭受危險的人沒有義務對之全盤容忍,他有權對危險來源者采取反擊;另一方面,由于危險來源者畢竟要么并未現實地違反義務,要么不具備實施合法行為的能力,這些值得體諒的事由使他仍在一定范圍內保留了要求對方給予照應的權利,故行為人對其展開的反擊就要比正當防衛更加克制。⑥Vgl.Pawlik,Der rechtfertigende Defensivnotstand im System der Notrechte,GA 2003,S.16f.此即防御性的緊急避險權。最后,當公民的某一法益遭遇險境時,基于社會團結原則,其他公民有義務做出一定的犧牲以協助他轉危為安。但社會團結畢竟只是在堅持自由平等原則的前提下出現的例外,故建立在該思想基礎上的緊急權必然會受到最為嚴格的規制。這便是攻擊性的緊急避險。
由此可見,我國傳統刑法理論對緊急避險的界定是不完整的,因為它只涵蓋了攻擊性的緊急避險,而未意識到還存在著一種和正當防衛一樣直接針對危險制造者,但強勢程度卻介于正當防衛和攻擊性緊急避險之間的緊急權,即防御性的緊急避險。①我國已有個別判例在事實上默認了防御性緊急避險的存在,但似乎僅限于“對物防衛”的情形。例如“王仁興破壞交通設施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第二庭編:《刑事審判參考》(第38集),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頁。這也直接導致通說將一些本應屬于緊急避險的情形歸入了正當防衛的名下。②最為典型的是,通說認為,針對意外事件的反擊行為亦可成立正當防衛。參見馬克昌主編:《犯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20頁;陳興良:《正當防衛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頁。這一觀點存在重大疑問。例如,甲遵守交通法規駕駛汽車行進在公路上,幾名嬉戲打鬧的小學生突然竄至馬路中央,甲剎車不及眼看就要撞上小學生,一旁的卡車司機乙見此情形一打方向盤,用卡車將甲的車撞翻,致其重傷。甲自始至終并未違反任何義務,故其行為根本不能被評價為“不法侵害”。雖然乙針對甲有反擊的權利,但只能成立防御性的緊急避險。
第二,將緊急避險的對象僅限于無辜第三人的見解,缺乏法律上的依據。我國《刑法》第21條第1款在規定緊急避險時,只提到“不得已采取的緊急避險行為,造成損害的”,并未如第20條第1款那樣對損害對象做出明確限定。因此,我國《刑法》關于緊急避險的規定完全可以容納防御性緊急避險。
第三,“正在發生之危險的概念寬于正當防衛中正在進行之侵害的概念,……即便是先于正當防衛情境而出現的某種狀態,亦可被看作是正在發生的危險。”③Kindh?user,Strafrecht AT,5.Aufl.,2011,§17 Rn.20.根據我國《刑法》第21條第1款的規定,“正在發生的危險”是緊急避險成立的前提條件。“凡是直接針對危險來源者的反擊行為,只要不符合正當防衛的要件,就不可能得到正當化”的觀念之所以盛行,原因還在于通說習慣于將人所制造的危險限定在“危害行為引起的危險”之上。④參見前注?,高銘暄、馬克昌主編書,第137頁;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07頁。但這一觀點存在疑問。所謂危險狀態,是指客觀存在的引起法益損害結果的高度蓋然性。正在進行的侵害行為無疑是正在發生的危險中急迫程度最高也最為典型的一種表現形式;但以人為主體能夠產生急迫危險的,卻不限于正在實施中的行為。其一,人在夢游、反射狀態下實施的身體動靜不屬于刑法意義上的行為,卻同樣可以對他人的法益造成威脅。其二,即便現實的侵害行為尚未開始,只要根據案件事實能夠認定,若不預先采取反擊措施,則有效防止法益侵害的最佳時機將一去不復返,也同樣可以認為法益正處于迫在眉睫的危險中。⑤Vgl.Roxin,Der durch Menschen ausgel?ste Defensivnotstand,FS-Jescheck,1985,S.478ff.
華南某省一駐村干部表示,“公司+合作社+農戶”是常見的產業扶貧方式,雖然上級沒有直接的合作社這項考評,但有產業考核要求。
隨著防御性緊急避險的形象從被遺忘的角落中走出,緊急行為成立正當化事由的途徑也就大為拓寬。因此,在上述案件中,盡管由于缺少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無法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成立正當防衛,但卻可以考慮成立緊急避險的可能性。接下來,還需要討論影響行為能否成立防御性緊急避險的兩個關鍵性問題。其一,被告人的殺害行為是否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實施?其二,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是否符合避險限度的要求?
(二)其他救濟途徑與“不得已”要件
雖然防御性緊急避險為直接針對危險來源者的緊急行為得以正當化提供了可能,但由于危險制造者要求他人給予自己適當照應(社會團結)的資格并未完全喪失,故依照我國《刑法》第21條第1款中“不得已”要件的要求,行為人只有在缺少其他救濟手段的情況下,才有權損害危險來源者的法益。那么,在相關的案件中,對于被告人而言,是否存在既可以有效逃脫險境,又不至于對施暴者造成傷害的出路呢?
在受虐婦女殺夫的案件發生后,時常能聽到一種聲音:被告人不應選擇以暴制暴,而應當“拿起法律的武器”去捍衛自身權益。⑥參見《拿起法律武器才能遠離家庭暴力》,《法制時報》2014年4月18日,第5版。那么,我國現有的法律制度是否為行為人提供了足夠有效的救助途徑呢?現實是,目前我國對家暴受害者的公力救濟途徑是匱乏的。
首先,能否向村委會、居委會、婦聯等組織投訴,或者向公安機關報案呢?村委會、居委會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婦聯作為婦女的群眾團體,它們對于家暴案件所能做的僅僅是對施暴者進行說服教育,而我國基層地方的公安機關受到警力、經費等因素的制約,往往不愿也無力積極介入“家庭私事”,頂多只對施暴者處以短時輕微的行政處罰或采取強制措施。
其次,能否走訴訟離婚的路呢?通過訴訟解除與施暴者的婚姻關系,似乎是一種釜底抽薪的辦法,但在現實中卻會遇到重重阻力:其一,行為人根本不敢提起離婚訴訟;其二,在我國,若夫妻雙方一方為現役軍人,則非軍人一方與對方離婚的難度較大;其三,在現實中,婚姻關系的結束往往并不意味著受虐一方真能脫離苦海;其四,縱然離婚能夠成功,從提起訴訟到拿到離婚判決也需要較長的時間。
再次,能否申請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護的裁定呢?我國2012年《民事訴訟法》修改的亮點之一,即為在原有的財產保全之外,于第100條增加了“行為保全”(即人身保護令)的內容。這一制度的出臺意在扭轉以往公權力機關在防止長期性家庭暴力方面軟弱無力、無所作為的局面。①參見謝兼明:《人身保護令:有了法律“身份證”》,《人民法院報》2013年1月21日,第2版。《意見》第23條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指出:“人民法院為了保護被害人的人身安全,避免其再次受到家庭暴力的侵害,可以根據申請,依照民事訴訟法等法律的相關規定,作出禁止施暴人再次實施家庭暴力、禁止接近被害人、遷出被害人的住所等內容的裁定。”但一方面,人身保護令裁定其實只是對施暴者的一種震懾,當施暴人違反該裁定時,法院不可能第一時間為受害者提供保護,而只能在事后對施暴者予以制裁;另一方面,施暴者即便因懾于保護令而不敢繼續實施家暴,也完全可能采取別的方式對受虐者進行報復,再加之申請和取證困難、忌憚隱私被暴露等原因,申請保護令對于受虐者而言往往無法成為真正可行的求救門路。正因為如此,一些法院在先期試點的過程中,已發現受害人申請人身保護令的數量極少。②參見康天軍、趙學玲、袁輝根:《彰顯人身保護令,有效預防家庭暴力——陜西高院關于人身安全保護裁定的調研報告》,《人民法院報》2011年9月15日,第8版;吳靜:《“人身保護令”在基層法院實施中的問題》,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1/09/id/ 464731.shtml,2015年5月15日訪問。
最后,能否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根據我國《刑法》第260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04條的規定,遭受家庭暴力者可以就施暴者構成虐待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向法院提起自訴。同時,我國《刑法》第98條以及1998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87條,也保證了即便受虐者因受強制、威嚇等原因無法告訴,亦可由他人代為告訴。然而,與選擇訴訟離婚相似,受虐者同樣會遇到以下兩個問題:自訴案件的舉證責任在于自訴人,故許多受虐者都面臨著舉證能力方面的困難;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被告人未被羈押的一審刑事自訴案件,期限為6個月,有特殊情況時還可延長3個月。這就意味著,自訴人在較長期間內仍難逃家庭暴力的陰云。
在求助公權力無門的情況下,最后能夠考慮的就只有“走為上計”。但是,在現實案件中,逃跑這一選擇所帶來的絕不是如人們一般所想象的“一走了之”那么簡單。對于眾多家庭暴力受害者來說,踏上這條路依然步履維艱。其一,獨立生存能力的缺失。受虐者作為家庭中地位較低的一方,往往既無控制處分家庭財產的權利,同時又缺少獨自謀生的技能,故一旦出逃,即會陷入衣食無著的困境之中。這也是現實中許多受虐者在短暫逃離后,最終又不得不冒著重陷苦難的危險返回家中的原因。其二,家庭成員的牽絆。如上述3個案件所體現的那樣,許多受虐者無法割舍家中的子女或父母,一旦獨自逃離則這些親人將陷入更為困難的處境,但自己又無力將其一同帶離。
綜上所述,至少就案例1和案例2來說,可以認為被告人已經處于窮途末路之境,故緊急避險中的不得已要件已經得到了滿足。
(三)剝奪他人生命與“利益衡量”要件
我國傳統刑法理論在論及避險限度的判斷時,習慣于以“人身權利大于財產權利;人身權利中生命最高;財產權利以財產價值大小來衡量”的公式為圭臬,僅對避險行為所保護和所損害之法益的抽象位階進行簡單對比。①參見前注?,高銘暄、馬克昌主編書,第139頁。然而,這種單一的法益衡量說應當為綜合的利益衡量說所取代。因為,避險限度所要權衡的是具體案件中,保護一種法益和損害另一種法益之間雙方所體現的實質利益大小。法益的抽象價值僅僅是決定這種利益對比關系的一個因素而已。危險的急迫程度、危險源與避險對象的關系、法益損害的強度、行為人對危險狀態的責任等事實,同樣會對利益衡量天平的傾斜方向產生影響。②近年來,我國有學者意識到了這一點,進而在“法益的靜態比較”之外還加入了“法益的動態衡量”的判斷。參見黎宏:《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頁以下。換句話說,“在這種具體的考察模式中,完全可能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即便某一法益從其抽象的位階順序來看具有比另一法益更高的價值,但如果根據個案的特殊性,保護后一法益所體現的利益明顯高于不讓前一法益受損所代表的利益,那么前一法益也應當讓位于后者”。③BundestagsdrucksacheⅣ/650,1962.S.159.
放眼整個緊急權的體系就會發現,利益衡量是一切緊急權的基礎,所保護之利益大于所損害之利益也是一切緊急權能夠得以合法化的共同根據。但是,隨著緊急權損害的對象與危險源之間的關系不同,其法益值得保護性的大小也會發生變化,故不同的緊急權在進行利益衡量時所能容許的法益對比關系也就存在重大差別。在正當防衛中,被損害者自己就是以違反義務的方式引起法益沖突之人,故其法益的值得保護性與他所侵害的法益相比就會出現大幅下降。因此,即使防衛人為了保護財產法益而導致侵害人重傷甚至死亡,也同樣可以認為他保護了更高的利益。在攻擊性的緊急避險中,被損害者是與危險引起無關的第三人,故其法益的值得保護性本身并無減損,只有當其法益的價值明顯低于受危險威脅的法益時,才能基于社會團結的原則認為避險行為保護了較高的利益,進而要求被損害者承擔忍受的義務。正因為如此,由于生命作為最高的法益,不可能在價值上明顯低于其他法益,它絕對不能成為攻擊性緊急避險犧牲的對象。在防御性緊急避險中,有兩個反向的因素共同影響著利益衡量的判斷。一方面,避險對象是危險的產生方,故其法益值得保護性必然會有所下降;另一方面,避險對象并未實施違法行為,故其法益值得保護性的下降幅度又不可能等同于正當防衛中的不法侵害人。由此決定,防御性緊急避險中的利益衡量標準較攻擊性緊急避險要寬松,但又嚴于正當防衛。④Vgl.Lenckner,Der Grundsatz der Güterabw?gung als arundlage der Rechtfertigung,GA 1985,S.306f.;Kühl,Strafrecht AT,7.Aufl.,2012,§8 Rn.134.所以,只要保護和損害的法益在價值上基本相當,即可認為避險行為維護了較高的利益。換言之,“防御性緊急避險行為人所代表的利益原則上占據顯著的優勢,除非他給避險行為被害人所造成之損害的嚴重程度不合比例地高”。⑤Günther,Defensivnotstand und T?tungsrecht,FS-Amelung,2009,S.151.這就意味著,在行為人不得已導致了危險來源者死亡的情況下,如果該行為所保護之法益的價值與生命法益相比并不存在明顯失衡的現象,那它就有可能以防御性緊急避險之名找到合法化的空間。①Vgl.Hirsch,in:LK-StGB,11.Aufl.,1993,§34 Rn.73;Günther,in:SK-StGB,7.Aufl.,2000,§34 Rn.43;Roxin, Strafrecht AT,Bd.Ⅰ,4.Aufl.,2006,§16 Rn.78.
接下來需要討論的問題是:何種法益的價值并不明顯低于生命呢?筆者認為,對此可以參考我國《刑法》第20條第3款關于特殊防衛權的規定。理由在于,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通行的正當防衛論在防衛限度的問題上一直奉行對以往必需說和基本相適應說加以綜合的折中說。該說認為:“必要限度的掌握和確定,應當以防衛行為是否能制止住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為標準,同時考察所防衛的利益的性質和可能遭受的損害的程度,同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性質、程度大體相適應。”②參見前注⑦,高銘暄主編書,第427頁。但事實上,該學說與基本相適應說并無本質差異,因為在折中說中,雙方法益價值是否大體相當這一標準,依舊對于防衛是否過當享有最終的決定權。于是,基本相適應說所具有的過分束縛防衛權的弊端,就根本無法在折中說中得到有效克服。③對于折中說缺陷的詳細分析,參見陳璇:《正當防衛中風險分擔原則之提倡》,《法學評論》2009年第1期。結合上述分析,其實不難發現,真正需要受到“基本相適應”標準制約的,并不是正當防衛,而是防御性緊急避險。所以,通說是將本屬于防御性緊急避險的限度判斷標準錯安在了正當防衛身上。這就難怪,當通說自認為能夠為防衛限度的認定提供萬全之策時,將該標準付諸實踐的司法機關對防衛限度的掌握卻仍然顯得過于嚴苛。④參見前注⑦,高銘暄主編書,第427頁。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立法者于1997年在我國《刑法》中增設了特殊防衛權的規定,旨在引導司法實踐放寬對防衛限度的拿捏。不過,立法者規定針對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可以致侵害人傷亡,歸根結底還是考慮到這類犯罪具有極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故即使造成不法侵害人重傷死亡,該損害結果與防衛行為可能造成的法益損害相比也不存在懸殊的差距。⑤參見趙秉志、肖中華:《正當防衛立法的進展與缺憾》,《法學》1998年第12期;高銘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誕生和發展完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頁。既然我國《刑法》第20條第3款依然是“基本相適應”思維主導下的產物,⑥盡管如此,在刑法語義能夠包容的范圍內,仍然可以賦予該條文不同于通說的內涵。筆者認為,在認定行為是否逾越防衛限度時,關鍵不在于雙方的法益損害是否基本相當,而是在于行為是否屬于為安全、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所必不可少的防衛措施。據此,對我國《刑法》第20條第3款應有如下認識。第一,該條只是一種注意規定,而非法律擬制。對于嚴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足以致侵害者重傷死亡結果的防衛措施,這本來就是為確保防衛效果和防衛人自身安全的必要之舉,自然處在正當防衛限度之內。因此,即便立法者當初沒有制定這一條款,根據防衛限度的一般判斷標準,也完全可以推導出與該款內容完全相同的結論。第二,正因為本條款只是提示性的規定,故不能認為只要侵害行為不屬于嚴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就導致侵害人死傷的防衛行為一概成立防衛過當。即便防衛人面對的只是非暴力的不法侵害,只要防衛行為滿足了有效性、安全性和最低性的要求,則無論它是否造成侵害人重傷死亡,原則上均應認定該行為未逾越防衛限度。而基本相適應的標準原本應適用于防御性的緊急避險,那么該條文的內容似乎就可以作為確定防御性緊急避險致人死傷之合法性邊界的立法依據。從該條文可以看出,在立法者眼中,受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行為威脅的重大人身安全,與生命法益相比是大致平衡的。因此,不得已導致危險來源者死亡的避險行為要得到合法化,必須是為了保護重大人身安全。首先,生命自當屬于重大人身安全。其次,由于“行兇”包含了可能造成他人重傷的行為,⑦參見前注⑦,高銘暄主編書,第439頁;前注38○,黎宏書,第144頁。故當他人面臨著遭受身體重傷害的危險時,也可以認為重大人身安全正處于威脅之中。
據此,筆者對前述三個案件展開分析。
從案例1的案情來看,在事發前的數月內,張某某對劉某某的暴力毆打不僅越來越頻繁,而且嚴重程度也在明顯上升,到后來已發展為用鐵鍬和斧頭等殺傷力較大的器械擊打劉某某頭部等要害部位。可以預見,如此以往,劉某某將隨時遭受丈夫手段更殘忍、暴力強度更高的襲擊,故對于被告人而言,身體健康遭受嚴重傷害的危險已迫在眉睫。因此,劉某某將張某某殺死的行為,并未超出防御性緊急避險的限度。
再來看案例2。首先,從目前所知的案情來看,熊某某長期以來對被告人實施的虐待行為并未達到足以導致后者重傷的嚴重程度,也沒有朝造成重傷結果的方向升級的跡象。故不能認為被告人處于重大人身安全即將遭受侵犯的危險之中。其次,吳某通過氰化鉀的出現、熊某某的異常表現等一系列事實,預感到丈夫即將害死自己和兒子,能否據此認為被告人的生命正面臨著急迫的危險呢?由于法院判決并未對這一關鍵性問題給出回答,故在此需要區分情況來討論:(1)若查明熊某某確實有殺害兩名被告人的打算,則吳某與其子殺死熊某某的行為可以成立防御性緊急避險;(2)若確定熊某某當時并無殺人的意圖,吳某的推測與事實不符,則由于客觀上只存在遭受一般虐待的危險,故受到威脅的法益與行為人損害的法益之間相差明顯,被告人的避險行為超出了必要限度,不能成立正當化的緊急避險。在這種情況下,需要進一步根據被告人的錯誤認識是否具有避免可能性做出不同的處理。其一,若被告人在長期肉體和精神遭受折磨的過程中,形成了極度擔憂自己和兒子的安全會受到侵害的敏感心理,從而對施虐者的一切反常舉動都具有超乎一般的恐懼感和警惕性,那就可以認為,她已經喪失了冷靜、準確判斷事態的能力。同時,被告人的認識能力之所以下降,并非是因為自身的過錯,而是被害人長期虐待行為造成的結果。因此,應當根據我國《刑法》第16條關于意外事件的規定,認定避險行為超過限度是“由于……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被告人無罪。其二,若被告人有充分的能力和時間查明是否確實存在死亡的危險,則應根據我國《刑法》第21條第2款的規定,認定其行為屬于避險過當,“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在關于行為人的錯誤認識是否具有可避免性的判斷中,前述“受虐婦女綜合癥”理論的研究成果無疑可以作為一個重要參考。
對于案例3,許多德國學者以被告人本可通過求助公權力擺脫險境為由,否定了其殺人行為成立緊急避險的可能。在此,暫且假定“不得已”的要件已得到滿足,A的行為能否成立防御性緊急避險,就取決于其子R的生命在行為當時是否確已岌岌可危。羅克辛(Roxin)對此給出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是:“那位父親在兒子歸來之時究竟會干些什么,他的怒氣是不是也許會歸于平息或者至少得到壓抑,這誰也不知道。那位母親所允許做的,是準備好武器,等到正當防衛的條件出現時才將其丈夫殺死。”①Roxin,Der durch Menschen ausgel?ste Defensivnotstand,FS-Jescheck,1985,S.483.但這種看法或許將問題過于簡單化了。可以確定的是,僅憑E曾經聲稱要奪R之性命的一句話還不足以肯定這種危險的存在。對此,需要結合更多的案件細節區分情況來處理。其一,如果E在平時已經表露出了對繼子R非同尋常的憎惡,并且在此前的長期虐待過程中經常對其使用較為嚴重的暴力,那么R這一次擅自出逃的行為就很可能成為激發E將其打成重傷甚至置其于死地的導火索。于是,E的那句話恐怕并非戲言,針對R的生命或者重大身體健康的急迫危險已現實存在。不錯,直到E見到R之前,誰也不能百分之百地確定E的真實反應究竟是怎樣。然而,作為緊急避險的前提條件,所謂“正在發生的危險”本來就是站在事前對事態發展所作的一種預測;緊急避險也正是在結果的發生雖有蓋然性但尚不能完全確定的時刻賦予行為人的緊急行動權。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該案中,一旦確定父親真的想要殺害繼子,暴力行為就已經開始,在體力上處于絕對弱勢的母親即便做好了準備,也沒有充分的把握能保護兒子的安全,甚至連她自己都有可能在防衛過程中付出生命或者重大身體健康的代價。法律有什么理由僅僅為了保護具有實施不法侵害危險之人的安全,就迫使無辜者陷入如此艱難和兇險的境地之中呢?②Vgl.Erb,in:MK-StGB,2003,§34 Rn.162.其二,假如E此前對R所實施的只是一般性的虐待,并沒有表現出與R之間水火不容的矛盾,那么再結合E所具有的情緒激動時言語易夸張的性格,大致可以推斷他說的不過是一句氣話,不能認為R的重大人身安全已處在現實危險中。這時,根據前述對案例2的分析,A殺死其夫的行為要么屬于意外事件,要么成立避險過當。
對于本文觀點可能引發的疑慮和異議,筆者認為有必要在此“預防性地”做出以下回應。
其一,將殺死家暴實施者的行為合法化,是否會鼓勵一些人一受虐待就動起殺人的念頭?這完全是杞人之憂,這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防御性緊急避險是以所有其他求助和回避的可能性都已斷絕為先決條件的。首先,正如案例1和案例2所顯示的那樣,被告人的殺人行為之所以有可能合法化,是因為國家和社會能為其提供的及時有效的保護手段寥寥無幾。因此,建立在最后手段原則上的緊急避險,只會以例外的形式出現在極為特殊的案件中,并不會放縱人們濫殺生命。其次,在我國傳統社會中,家法族規擁有對國法加以補充的地位,丈夫作為一家之長亦對妻子以及子女享有統治權甚至責罰權,①參見張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頁。故對于家庭暴力,國家公權力多以“清官難斷家務事”為由避免介入;只是自現代法制建立之后,國家才逐步加大了保護家庭成員基本權利的力度、完善了解決家庭沖突的介入機制。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公權力救濟途徑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和缺陷,這時,允許家庭成員實行自救就是國家在力有未逮、鞭長莫及之時所采取的權宜之計。可以預料,隨著國家和社會針對家庭暴力的預防措施和救助制度日趨完善和多樣,受到最后手段性要件的制約,公民行使防御性緊急避險權的空間勢必逐漸萎縮。在一個以建成現代法治國為目標的國度里,這恰恰是值得期待的發展方向。第二,只有在為保護生命和重大身體健康這兩種最高價值法益的情況下,殺人行為才可能成立防御性緊急避險。所以,僅遭受輕微虐待的人,無論如何無權殺死施虐者。
其二,運用責任阻卻事由的原理來解決相關案件,是否更為合適?不少德國學者堅持認為,即便是為了抵御生命的危險,行為人殺死家庭暴力實施者的行為也不能成立阻卻違法的緊急避險,至多只能成立德國刑法第35條所規定的以期待可能性理論為基礎的阻卻責任的緊急避險。②Vgl.Roxin,Strafrecht AT,Bd.Ⅰ,4.Aufl.,2006,§16 Rn.87;Zieschang,in:LK-StGB,12.Aufl.,2007,§34 Rn.74a; Lackner/Kühl,StGB,27.Aufl.,2012,§34 Rn.9.該觀點也得到了我國一些學者的支持。③參見屈學武:《死罪、死刑與期待可能性》,《環球法律評論》2005年第1期。從能夠達到否定被告人成立犯罪的效果這一點來看,認定被告人的行為成立責任阻卻事由的做法,④在我國,如果無法得出我國《刑法》第21條的規定包含了阻卻責任之緊急避險的解釋結論,那么至少也可以認為存在成立超法規的責任阻卻事由的余地。似乎與將行為認定為違法阻卻事由的觀點沒有實質差別。但筆者認為,責任阻卻說存在以下問題。首先,行為人是否有權損害某一法益,并非取決于該法益的抽象位階,而是取決于它在具體的法益沖突中值得保護性的強弱。生命的最高性和不可比較性是支配責任阻卻說的核心思想。⑤Vgl.Zieschang,in:LK-StGB,12.Aufl.,2007,§34 Rn.74.但是,任何法益都不可能拋開具體的情形無條件地享有絕對保護的地位,生命法益也不例外。如前所述,在攻擊性的緊急避險中,之所以排除了犧牲他人生命的避險行為成立違法阻卻事由的余地,是因為無辜第三人的值得保護性并無明顯下降,故任何法益都不可能比他的生命更為優越。既然在本文所探討的案件中,避險行為的對象就是危險的制造者本人,那么其生命就不可能像無辜第三人那樣仍然值得法律給予完整的守護。在這種情況下,利益衡量的天平完全有可能向行為人的重大法益一方傾斜,避險行為也就存在獲得法律肯定的空間。其次,責任阻卻說也存在前后矛盾之處。按照德國刑法學的通說,一旦出現分娩陣痛,胎兒即成為有生命的人。⑥Vgl.Sch?nke/Schr?der/Eser,StGB,28.Aufl.,2010,vor§211 Rn.13.所以,在此之后的生產過程中,若出現緊急情況,醫生為了避免母親喪生或者健康受到嚴重損害,不得已導致嬰兒死亡,則該行為無疑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包括責任阻卻說的支持者在內的絕大多數德國學者都認為,該行為成立阻卻違法的防御性緊急避險。①Vgl.Roxin,Der durch Menschen ausgel?ste Defensivnotstand,FS-Jescheck,1985,S.476f.;Lackner/Kühl,StGB,27.Aufl., 2012,§34 Rn.9.在此,嬰兒并沒有實施任何行為,他之所以成了威脅其母親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危險源,完全是因為自然的分娩過程所致。既然在這種情形中,殺死無辜的危險來源者的行為都可以合法化,那么在家庭暴力的案件中,危險來源者對于危險的產生具有嚴重的過錯,為何不得已將其殺害的行為反而絕對為法律所不容呢?最后,如果認為殺害家庭暴力實施者的避險行為只能成立責任阻卻事由,那就意味著該行為依然屬于一種不法侵害。于是,施暴者或者第三人就可以針對避險人采取正當防衛,甚至可以行使直接致其死亡的特殊防衛權。這樣的結論恐怕難以為人們所接受。
四、結語
關于為擺脫家庭暴力而殺害施暴者之案件的思考,或許可以為人們帶來以下兩點啟示。
其一,“法律總是要給人一條路走的,而且給的必須是一條屬于人走的路”。②黃榮堅:《刑罰的極限》,臺北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84頁。法律不能只告訴被告人“你不能這么干”、“你那樣做不對”,但在面對被告人“那我究竟該怎么辦”的追問時,卻只回答“那可不歸我管”或者“誰攤上誰倒霉吧”。在刑法教義學領域內能夠體察和吸納常理、人情的所有途徑尚未窮盡之前,不應隨意將被告人的行為劃入違法圈;在排除犯罪性事由得到充分考慮之前,法官也不宜匆忙地給被告人貼上犯罪人的標簽。
其二,關于緊急權的法教義學研究,應當更加自覺地朝體系化的方向邁進。正是通過對緊急權體系的全面把握,防御性緊急避險的形象才更為清晰地展現,由此既避免了正當防衛因承受過多壓力而無限擴張的危險,也為以危險來源者為對象,但不符合正當防衛要件的緊急行為找到了一條合理的正當化路徑。可見,正如對刑法具體條文的把握離不開對刑法整體的理解,對刑法分則具體犯罪的解釋離不開對各罪在整個分則體系中所處地位的考量一樣,對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具體問題的探討,也不能停留在零敲碎打、就事論事的層次上,而有必要將其置于緊急權的體系框架內,在厘清具體緊急權之間的邏輯關聯和位階關系的基礎上去展開。
(責任編輯:杜小麗)
D F611
A
1005-9512(2015)09-0013-14
陳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刑法中緊急權的體系與解釋研究”(項目批準號:15CFX 036)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儲陳城,東南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早稻田大學法務研究科訪問研究員。
*本文為江蘇省第四期“333工程”培養資金資助項目階段性成果,同時受2013年度江蘇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創新計劃省立省助項目”(項目編號:CX ZZ13_0077)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