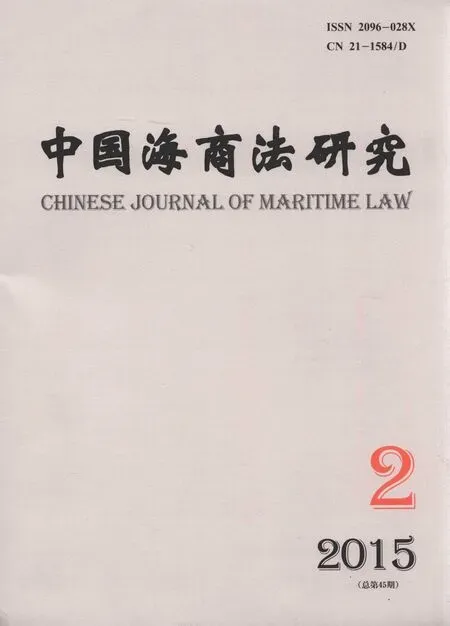中國海事仲裁模式創新路徑探索——臨時仲裁在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的引入
賴震平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029)
中國海事仲裁模式創新路徑探索
——臨時仲裁在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的引入
賴震平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北京100029)
摘要:中國海事仲裁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雖然歷經近60年的發展成績斐然,但是中國海事仲裁依然沒有引入在海事仲裁領域普遍流行的臨時仲裁。臨時仲裁在中國海事仲裁的缺失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的制約。盡管如此,以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為代表的中國海事仲裁機構存在引入臨時仲裁的可能。通過對臨時仲裁的本質研究,試圖在現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的制約下,分析論證通過中國海事仲裁機構的變革以引入臨時仲裁的可能性,實現中國海事仲裁模式的創新。
關鍵詞:臨時仲裁;意思自治;海事仲裁機構
一、中國海事仲裁的發展現狀與缺失
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China Maritime Arbitration Commission,簡稱CMAC)是國內唯一受理海事爭議案件的專業仲裁機構。可以說,CMAC的發展代表了中國海事仲裁的發展。[1]該海事仲裁機構成立于1959年,由中國國際商會組織設立。設立之初名為“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海事仲裁委員會”,于1988年改為現用名稱,該仲裁委員會專門解決海事爭議。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設在北京,在上海、天津、重慶設有分會。仲裁委員會分會可以受理并處理案件。仲裁委員會及其分會設秘書處,秘書處設秘書長,分別領導仲裁委員會秘書處和分會秘書處處理日常事務。
2014年4月28日發布的《關于海仲委第十七屆委員會主要工作和第十八屆委員會工作計劃的報告》指出:
“自2008年至2013年,海仲委共受理案件491件,爭議金額共計人民幣66.9億元。共審結案件343件。2013年,海仲委受理案件137件,爭議金額達15.95億元人民幣。審結案件70件。當事人涉及23個國家和地區。2013年海仲委的受案數量和爭議金額均創歷史新高,案件數量首次突破兩位數。
整體來看,十七屆委員會期間,海仲委受理案件呈現以下突出特點:一是受理案件數量和標的額呈現穩步增長的態勢。2008年至2013年這六年與前六年相比,受案總量增長149%,標的額增長962%;二是大案復雜案件數量增加,案件類型多樣化,除了傳統的租船、碰撞和救助案件外,新類型案件如造船和物流案件增多;三是案件當事人涉及的國家和地區更加廣泛,雙方均為外國當事人的國際案件有所增加。”
盡管中國海事仲裁取得了令人驕傲的成績,但是,在這成績背后,中國海事仲裁仍然存在制度性的缺失,即臨時仲裁的缺失。縱觀世界范圍內的海事仲裁,臨時仲裁是主流形式。然而,中國的海事仲裁卻是以機構仲裁的形式存在。相比較機構仲裁而言,臨時仲裁因其靈活、自主、高效和便捷的特性,能夠快速地解決爭議當事人之間的爭議,尤其適合于海事仲裁。
二、中國海事仲裁缺失臨時仲裁的成因
《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簡稱《仲裁法》)第16條規定:“仲裁協議包括合同中訂立的仲裁條款和以其他書面方式在糾紛發生前或者糾紛發生后達成的請求仲裁的協議。仲裁協議應當具有下列內容:(一)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項;(三)選定的仲裁委員會。”第18條規定:“仲裁協議對仲裁事項或者仲裁委員會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當事人可以補充協議;達不成補充協議的,仲裁協議無效。”依據上述條文規定,《仲裁法》明確規定仲裁協議或條款中必須包含選定的仲裁委員會,否則即視為是無效的仲裁協議或條款。在中國司法實踐中,亦是如此。在1997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僅選擇仲裁地點而對仲裁機構沒有約定的仲裁條款效力問題的函》中認定:“本案合同仲裁條款中雙方當事人僅約定仲裁地點,而對仲裁機構沒有約定。發生糾紛后,雙方當事人就仲裁機構達不成補充協議,應依據《仲裁法》第18條之規定,認定本案所涉仲裁協議無效,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本案。”此外,《仲裁法》規定了裁決書必須要加蓋仲裁委員會的印章。《仲裁法》第54條規定:“裁決書應當寫明仲裁請求、爭議事實、裁決理由、裁決結果、仲裁費用的負擔和裁決日期。當事人協議不愿寫明爭議事實和裁決理由的,可以不寫。裁決書由仲裁員簽名,加蓋仲裁委員會印章。對裁決持不同意見的仲裁員,可以簽名,也可以不簽名。”由于臨時仲裁裁決一般只會有仲裁員的簽名。因此,該條款也對中國海事仲裁引入臨時仲裁造成一定的影響。
一般認為,臨時仲裁基于爭議當事人自主選擇的特性,可以不需要仲裁機構的介入。因此,爭議雙方當事人在約定仲裁協議或條款時,可不必將仲裁機構包含在內。然而,依據上述《仲裁法》條文的規定和司法實踐,一份有效的仲裁協議或條款必須要包含選定的仲裁委員會,否則將視為無效。因此,在中國進行臨時仲裁的仲裁協議或條款,在適用《仲裁法》進行審查時,往往會被認定為無效的仲裁協議或條款。由此,基于無效的仲裁協議或條款做出的臨時仲裁裁決,將無法得到法院的承認與執行。這是中國海事仲裁缺失臨時仲裁的主要原因所在。
三、中國海事仲裁模式的創新
受《仲裁法》的制約,臨時仲裁在中國至今未獲得承認。縱然如此,臨時仲裁在世界范圍內,尤其是在海事仲裁領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是海事航運的大國,臨時仲裁在中國海事仲裁領域的缺失,對中國海事仲裁的發展而言,無疑是不利的。因此,應當引入臨時仲裁,改變中國海事仲裁中只有機構仲裁的單一模式,以完善中國海事仲裁制度。然而,從中國現行的仲裁立法情況來看,在仲裁協議或條款中包含指定的仲裁委員會是仲裁協議或條款有效的前提和基礎。因此,脫離仲裁委員會的臨時仲裁在中國現有立法體制下將無以為繼。
由于臨時仲裁的缺失,在中國提起海事仲裁,爭議當事人往往想到的是機構仲裁以及規范而又嚴謹的中國海事仲裁機構的代表——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臨時仲裁與機構仲裁的最大區別在于臨時仲裁具備自主、靈活、高效和便捷的特性。因此,在一個規范而又嚴謹的中國海事仲裁機構中引入臨時仲裁,似乎是一件很不協調的事情。盡管如此,為彌補中國海事仲裁的這一缺失,完善中國海事仲裁制度,可以依托中國海事仲裁機構,在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引入臨時仲裁。然而,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畢竟是常設仲裁機構,將臨時仲裁引入其中,就需要對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進行變革,從本質上突出臨時仲裁,以區別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中的機構仲裁,從而使臨時仲裁在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的引入成為可能,以實現中國海事仲裁模式的創新。
(一)臨時仲裁的本質
國際社會對于商事仲裁的性質一般可分為司法權理論、契約理論、混合理論和自治理論。司法權理論認為商事仲裁的權限是國家司法權的一種讓與。如果國家法律沒有承認爭議雙方當事人有權將有關爭議提交仲裁解決,并承認該仲裁裁決具有強制力,那么商事仲裁將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更不用說具有任何法律上的效力。此外,司法權論對仲裁員的自主權做出較大限制,強調仲裁必須適用仲裁地國的程序法和沖突規范,且仲裁員的自由裁量權不得大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因此,司法權論容易導致司法權對仲裁的過度干預,對于仲裁的發展是相當不利的。契約理論認為,爭議雙方當事人之間訂立的仲裁協議,是商事仲裁的基礎和來源。著重強調商事仲裁的契約屬性。商事仲裁的契約理論契合了商事仲裁的本質,認為商事仲裁是爭議雙方當事人之間的一種意思自治的產物,是在商事交往中自然形成和發展的一種便捷、高效的爭議解決方式,具有天然的契約性。同時,明確了商事仲裁的爭議雙方當事人對于法律的選擇適用具有很高的自主權力。混合理論是在司法權理論和契約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的。混合理論認為,商事仲裁不僅僅具有司法權性或契約性的單一屬性,而是具有司法權和契約的混合屬性。自治理論是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仲裁的性質,該理論所認為的商事仲裁的性質,完全不同于上述的司法權理論、契約理論和混合理論,自治理論主張商事仲裁的性質,沒有司法權性、契約性和混合性,而是一種完全獨立的性質。雖然對于商事仲裁的性質尚未有最終定論,但除司法權理論外,都認為仲裁是爭議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一般多為法學上的用語,用英語表述為“Private Autonomy”。對于其含義,有學者認為,意思自治“是指民事主體依法享有在法定范圍內的廣泛的行為自由,并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產生、變更、消滅民事法律關系。”;[2]也有學者認為,意思自治是“當事人有權依據自己的意志做出自由選擇,當事人的自我意志是約束其契約關系的準則,當事人應該對依據自己的意志做出的選擇負責。”[3]雖然上述學者對于意思自治的表述不盡相同,但對于意思自治的基本含義并無太多的差異存在。對于意思自治的基本含義主要表現為權利自由,也就是對當事人個人權利和個人意志的尊重。
人類社會發展至今,人類一直在為著自己的自由不懈努力。毋庸置疑,自由是意思自治的重要價值之一。沒有以自由為前提和基礎的意思自治,則無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意思自治。意思自治向來有其特定化的領域,它是私法上的自由。[4]這一說法的目的在于使私法自治獲得不受公權力干預的空間,有利于對私法自治的保障。
意思自治的權利本位價值是由自由價值所決定的,滿足了契約自由的內在要求。契約自由是意思自治的具體表現,它內含權利本位的應有之義,是權利實現的必然邏輯。[5]權利的實現通常是建立在權利交換的基礎上,因此,契約可以被視為是權利交換的一種合意。從實質上講,契約的存在是以權利為基礎,沒有權利為內容的契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契約,也無法體現自由和平等的理念。
臨時仲裁管轄權的確立是來源于爭議雙方當事人的有效仲裁協議,而仲裁協議的達成正是當事人合意的結果,也是爭議雙方當事人意思自治的體現。目前絕大多數國家的仲裁立法和有關國際條約,都承認爭議雙方當事人可以自由約定仲裁協議的內容,比如,爭議雙方當事人可以在不違反仲裁協議準據法規定的前提下自由選擇解決爭議所適用的仲裁程序法和仲裁實體法,仲裁員的選任,仲裁地的確定,自行協商去除仲裁程序中所不必要的環節,僅保留解決爭議所必須的環節,以加快仲裁進程。有鑒于此,臨時仲裁最大限度地尊重了爭議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其自主、靈活、高效和便捷的特點能夠更大程度地滿足當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盡管如此,臨時仲裁所滿足的意思自治不是沒有任何限制的,要受制于公序良俗和法律的制約。但臨時仲裁還是在爭議解決方式上最大限度地滿足和尊重了爭議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自治。
因此,爭議雙方當事人高度的意思自治是臨時仲裁有別于機構仲裁的關鍵,也是臨時仲裁的根本特征和本質。雖然機構仲裁也能體現爭議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但相比較于臨時仲裁而言,則顯得頗為遜色。
(二)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的變革
在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中引入臨時仲裁,需要體現和突出臨時仲裁的本質,以區分在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中的機構仲裁。正如上文所述,臨時仲裁的本質在于意思自治,具體表現在仲裁規則的自主選擇,仲裁員的自主選任以及仲裁員報酬的自行協商確定等。盡管如此,在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中實現臨時仲裁的意思自治的前提在于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的變革。
1.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的管理模式變革
成立于1959年的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作為一家專門的海事仲裁機構是中國海事仲裁機構的代表,標志著中國海事仲裁的起步,也見證了中國海事仲裁的發展。從現行的管理模式來看,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施行的是單一的管理模式。因此,在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引入臨時仲裁,首先需要就該管理模式做出變革。改變單一的管理模式,在保留對仲裁管理的模式下,創設一種新型的監督模式,以適用于臨時仲裁,從而對臨時仲裁形成有效的監督,而不是直接介入管理。通過對仲裁員和仲裁裁決的監督,在充分尊重爭議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保證臨時仲裁的質量。有鑒于此,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可以設立專門的委員會對臨時仲裁進行監督。該監督一般采用被動的方式,在當事人向委員會提起請求時,行使監督權力,以最大限度地保證不主動介入干預。
2.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適用的變革
臨時仲裁中的仲裁規則是臨時仲裁程序所應遵循和使用的規范。與機構仲裁不同,臨時仲裁的爭議當事人可以自主選擇仲裁規則,既可以自行設計仲裁規則也可以在現有的仲裁規則中選擇適用。仲裁規則的繁簡將決定臨時仲裁程序的快慢。因此,仲裁規則的自主選擇可以很好地體現臨時仲裁意思自治的本質。目前,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已經具備讓爭議當事人自主選擇仲裁規則的條件。依據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2015年1月1日起實施的最新《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4條第3款規定,當事人約定將爭議提交仲裁委員會仲裁但對本規則有關內容進行變更或約定適用其他仲裁規則的,從其約定,但其約定無法實施或與仲裁程序適用法的強制性規定相抵觸者除外。當事人約定適用其他仲裁規則的,由仲裁委員會履行相應的管理職責。有鑒于此,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可以允許爭議當事人自主選擇仲裁規則。盡管如此,爭議雙方當事人雖然可以自主選擇仲裁規則,但是仲裁委員會依舊會履行相應的管理職責。因此,這就需要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在仲裁規則的適用上做出變革。在允許爭議雙方當事人自主選擇仲裁規則的情況下,履行相應地監督職責而不是管理職責。
當然,爭議雙方當事人在自主選擇仲裁規則的同時,應同時考慮擬選任的仲裁員對該仲裁規則的熟悉程度,以避免因仲裁員對該仲裁規則的不熟悉而導致的程序拖延。
3.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仲裁員選任的變革
爭議雙方當事人對仲裁員的自主選任亦是體現臨時仲裁意思自治的本質的重要環節。仲裁員是仲裁程序的主持人和仲裁實體問題的決定者,仲裁質量的高低直接取決于審理案件的仲裁員。然而,仲裁員的自主選任,不得不面對仲裁員的資格問題。仲裁的民間屬性使其不同于法院審理,仲裁的審理通常是由專家負責斷案,仲裁的裁判依據既可以是法律,也可以是行業規則,習慣乃至于仲裁員的個人主觀判斷都可以成為斷案的依據。因此,仲裁員一般都必須具備某一行業領域的專業機能和背景以及優秀的自身素質。有鑒于此,就仲裁員的資格而言,大多數國家只是對仲裁員的資格做出原則性的規定,部分國家,例如英國,對仲裁員的資格僅要求具備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總而言之,許多國家的法律對于仲裁員的資格僅作原則性的規定,并成為評判仲裁員是否具備法定資格的重要標準。從總的趨勢上來看,對仲裁員資格的確定正朝著寬松的方向發展。這種趨勢表現為很多國家對商事仲裁中的仲裁員資格的要求不是從“應當”的角度,而僅僅是從“禁止”的角度加以規定。[6]
反觀中國,《仲裁法》對仲裁員的資格不是從“禁止”的角度加以規定,而是從“應當”的角度對仲裁員的資格做出了既嚴格又詳盡的規定,即所謂的“三八二高”規定。依據《仲裁法》第13條的規定,仲裁委員會應當從公道正派的人員中聘任仲裁員。仲裁員應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一)從事仲裁工作滿八年的;(二)從事律師工作滿八年的;(三)曾任審判員滿八年的;(四)從事法律研究、教學工作并具有高級職稱的;(五)具有法律知識、從事經濟貿易等專業工作并具有高級職稱或者具有同等專業水平的。面對這樣嚴格的要求,部分深受爭議雙方當事人所信任并具備優秀素質的專業人士,極有可能因為不符合《仲裁法》所規定的資格條件,從而不無可惜地無法成為仲裁員隊伍的一員。不僅如此,這同樣對爭議雙方當事人自由選定仲裁員的權利進行了限制。盡管如此,假設《仲裁法》對仲裁員的資格條件予以較低門檻的規定,在現階段,則很有可能無法保證仲裁員隊伍的水準。
通常情況下,常設仲裁機構都設有專門的《仲裁員名冊》,以供爭議雙方當事人選定仲裁員。《仲裁員名冊》一般不具有強制性,多為推薦性質。其設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引導和幫助爭議雙方當事人有針對性地、簡便和快速地選任仲裁員。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同樣設有《仲裁員名冊》。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2015年1月1日起實施的最新《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30條仲裁員的選定或指定規定:“(一)仲裁委員會制定統一適用于仲裁委員會及其分會/仲裁中心的仲裁員名冊;當事人從仲裁委員會制定的仲裁員名冊中選定仲裁員。(二)當事人約定在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名冊之外選定仲裁員的,當事人選定的或根據當事人約定指定的人士經仲裁委員會主任確認后可以擔任仲裁員。”從該規定來看,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是允許爭議雙方當事人在《仲裁員名冊》外選定仲裁員,但需經仲裁委員會主任的確認。
雖然現行《仲裁法》對于爭議雙方當事人是否可以在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名冊》外選定仲裁員沒有做出很明確的規定,但是,從長久以來的實踐來看,中國的仲裁委員會一般多是讓爭議雙方當事人從該仲裁委員會設置的《仲裁員名冊》中選定仲裁員的。盡管如此,北京仲裁委員會秘書長王紅松女士在2005年被問及“當事人能否從名冊之外選定仲裁員”的問題時,曾作出明確表態:“在實踐中,如果爭議雙方當事人在仲裁協議當中約定了雙方可以從名冊之外選擇仲裁員,本會通常會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但其選擇的仲裁員須符合仲裁法的相關規定并遵守本會仲裁員道德準則。”[7]有鑒于此,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可以對仲裁員的選任做出變革,即爭議雙方當事人可以在《仲裁員名冊》外,根據所涉爭議的性質和具體情況,自行選定具備法定資格的仲裁員,而無須經過仲裁委員會主任的確認。仲裁員的選任方式包括首席仲裁員的選任由當事人自行協商確定,一般可以由雙方當事人共同選任一名首席仲裁員,也可以由雙方當事人各自選任的仲裁員共同選任一名首席仲裁員。辦案秘書由首席仲裁員自行配備,負責仲裁庭與當事人之間的材料遞送和送達。
當然,臨時仲裁中,如果爭議雙方當事人不配合,也有可能無法就仲裁員的人選達成一致。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可以經爭議雙方當事人的授權,為爭議雙方當事人代為指定仲裁員,以避免僵局的產生。
4.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仲裁費的變革
臨時仲裁中,由于沒有常設仲裁機構的管理,仲裁費用一般僅包括仲裁員的報酬。仲裁員的費用及支付方式通常也是由爭議雙方當事人與仲裁員自行協商確定。[8]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2015年1月1日起實施的最新《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79條規定了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現行的仲裁費機制。根據該條的規定,仲裁委員會除按照制定的仲裁費用表向當事人收取仲裁費外,還可以向雙方當事人收取其他額外的、合理的實際費用,包括仲裁員辦理案件的特殊報酬、差旅費、食宿費、聘請速錄員速錄費,以及仲裁庭聘請專家、鑒定人和翻譯等費用。根據該條的規定,首先,仲裁費用包括仲裁機構的管理費和仲裁員的報酬,其次,仲裁費采用預繳的形式。有鑒于此,就需要對現行的仲裁費收費機制進行變革,以適應臨時仲裁的需要。
第一,設立專門針對臨時仲裁的收費機制。由于現行的收費機制并不區分仲裁機構的管理費和仲裁員的報酬,而臨時仲裁不受仲裁機構的管理,因此并不需要支付仲裁機構的管理費用。盡管如此,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在整個臨時仲裁過程中,會因爭議當事人的請求而提供協助服務,例如仲裁員的代為指定,庭審場地的提供等。因此,對于這類服務的提供,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可以向爭議當事人收取一定的費用。
第二,設立仲裁員報酬的支付標準。通常情況下,臨時仲裁中,仲裁員的報酬和支付方式是由爭議雙方當事人與仲裁員自行協商確定。但有時也會存在爭議當事人與仲裁員無法就報酬達成一致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仲裁員報酬的支付標準的設立可以就仲裁員的報酬形成參考,便于爭議雙方當事人與仲裁員之間就報酬達成一致。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中國現階段,在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做出變革的基礎上,還是具備在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引入臨時仲裁的可能性,以彌補中國海事仲裁只有機構仲裁沒有臨時仲裁的缺失。
第一,在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引入臨時仲裁,形式上符合現行《仲裁法》要求仲裁協議或條款必須包含指定的仲裁委員會的規定,不至于與現行的《仲裁法》起明顯沖突。
第二,雖然《仲裁法》沒有明確臨時仲裁的效力,但是,《仲裁法》對于臨時仲裁也沒有明確禁止,只是規定中國仲裁必須在仲裁委員會進行。在“法無禁止即可為”的法理下,臨時仲裁可以在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的依托下進行。因此,只要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充分尊重爭議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不主動干預仲裁進程,從本質上可以認定是臨時仲裁。關鍵在于尊重爭議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自治,這也是臨時仲裁的本質所在。不僅如此,在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引入臨時仲裁,雖然對臨時仲裁不行使管理職責,但還是可以起到監督作用。
第三,在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引入臨時仲裁,可以有效破解臨時仲裁在仲裁庭組成時的僵局,以避免臨時仲裁程序的拖延。
第四,在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引入臨時仲裁,可以將臨時仲裁和機構仲裁中的各自優點集于一身。
此外,雖然《仲裁法》第54條規定:裁決書由仲裁員簽名,加蓋仲裁委員會印章,但是,為盡可能避免與中國現階段的立法產生沖突,筆者認為臨時仲裁裁決可以出現仲裁委員會的蓋章。因為,在整個臨時仲裁程序中,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可以做到沒有實質性的管理介入。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可以只是依據爭議雙方當事人的請求起協助作用,以協助臨時仲裁程序的順利進行。同時,亦能取得法院的信任,便于日后裁決的順利執行。而且,在香港的臨時仲裁實踐中,亦有仲裁裁決的認證服務,爭議雙方當事人可以請求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對其臨時仲裁裁決進行認證并加蓋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印章。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顧國偉.中國海事仲裁發展初探[J].中國海商法年刊,2009(3):98.
GU Guo-wei.Development of maritime arbitration in China[J].Annual of China Maritime Law,2009(3):98.(in Chinese)
[2]王利明.民法總則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09-110.
WANG Li-ming.The general civil law research[M].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3:109-110.(in Chinese)
[3]趙萬一.對民法意思自治原則的倫理分析[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3(5):15-23.
ZHAO Wan-yi.Ethical analysis of 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 of civil law[J].Journal of Henan Province Management Cadre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Law,2003(5):15-23.(in Chinese)
[4]李軍.私法自治的基本內涵[J].法學論壇,2004(6):76-78.
LI Jun.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private law autonomy[J].Legal Forum,2004(6):76-78.(in Chinese)
[5]胡偉.意思自治的法哲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199.
HU Wei.The autonomy of the legal philosophy research[M].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2:199.(in Chinese)
[6]喬欣.比較商事仲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89.
QIAO Xin.Comparison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M].Beijing:Law Press,2003:89.(in Chinese)
[7]當事人可以在仲裁員名冊外選擇仲裁員[EB/OL].(2005-05-08)[2014-09-29].http://www.bjac.org.cn/news/view?id=841.
The parties may choose the arbitrator outside the list of arbitrators[EB/OL].(2005-05-08)[2014-09-29].http://www.bjac.org.cn/news/view?id=841.(in Chinese)
[8]馬占軍.我國內地與澳門地區仲裁法律制度比較研究[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23.
MA Zhan-ju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legal system of arbitration in mainland of China and Macao[M].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23.(in Chinese)
Exploration of the innovation path of China maritime arbitration—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d hoc arbitration into the CMAC
LAI Zhen-ping
(Law School,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China maritime arbitration started in the 1950s. However, after nearly 60 years of development, China has not yet introduced the widely accepted ad hoc arbitration in the field of maritime arbitration. The lack of ad hoc arbitration in China maritime arbitration is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f theArbitration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Nevertheless, represented by the China Maritim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China maritime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would introduce the ad hoc arbitration. 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nature of the ad hoc arbitration and reform of the China maritim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the paper tried to analyz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d hoc arbitration into the China Maritim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theArbitration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so as to achieve the innovation of the China maritime arbitration.
Key words:ad hoc arbitration; autonomy; maritime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中圖分類號:DF961.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6-028X(2015)02-0040-06
作者簡介:賴震平(1982-),男,上海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國際法專業博士研究生,E-mail:laizhenping1982@163.com。
收稿日期:2015-04-13
賴震平.中國海事仲裁模式創新路徑探索——臨時仲裁在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的引入[J].中國海商法研究,2015,26(2):4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