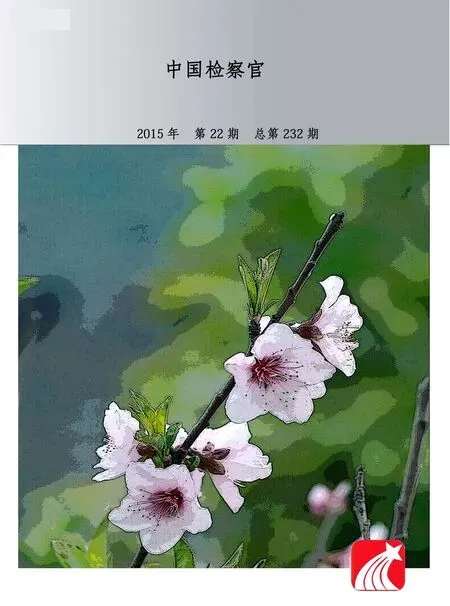網絡尋釁滋事罪中“公共秩序嚴重混亂”的認定
文◎高哲遠
網絡尋釁滋事罪中“公共秩序嚴重混亂”的認定
文◎高哲遠*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100026]
一、基本案情
被不起訴人董某某于2012年5月17日9時23分,使用昵稱為“環保董良杰”的新浪微博賬戶,編造虛假信息——“自來水里的避孕藥”,(內容為:“中國是避孕藥消費第一大國,不僅人吃,且發明了水產養殖等新用途。避孕藥環境污染可導致野生動物不育或降低再生能力。學者對飲水里雌激素干擾物研究發現,23個水源都有,長三角最高。另外,它們作為持久污染物,一般水處理技術去不掉;人體積累,后果難料。各國比比,嚇一跳。”)在我國信息網絡上散布,導致該虛假信息被大量轉發、評論,誤導社會公眾產生錯誤認知,引發對公共服務安全性的憂慮和質疑。
經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審查后認為,被不起訴人董某某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93條第1款第(4)項規定的行為,但犯罪情節輕微,認罪態度較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7條的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73條第2款的規定,于2014年6月6日決定對董良杰不起訴。
二、分歧意見
本案中主要涉及兩個問題:(1)網絡空間秩序是否屬于尋釁滋事罪中的“公共場所秩序”?(2)如何認定網絡尋釁滋事罪中的“公共秩序嚴重混亂”?對此,有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網絡空間目前具有很強的公共屬性,故網絡空間秩序屬于尋釁滋事罪中的“公共場所秩序”。如果造成網絡空間秩序的嚴重混亂,應認定為“公共秩序嚴重混亂”,構成尋釁滋事罪。如本案中,被不起訴人董某某在網絡上散布虛假信息,在網絡上引發大量關注和負面評論,使社會公眾產生恐慌心理,構成尋釁滋事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網絡空間屬于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不能等同,故網絡空間秩序不屬于尋釁滋事罪中“公共場所秩序”。在網絡上實施辱罵、恐嚇他人,情節惡劣,破壞社會秩序的,或者編造虛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虛假信息,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或者組織、指使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起哄鬧事等行為,必須造成現實社會公共秩序的嚴重混亂,才能認定行為人構成尋釁滋事罪。本案中,董某某在網絡上散布虛假信息的行為,并無證據證實造成現實社會公共秩序的嚴重混亂,故不能認定其構成尋釁滋事罪。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一種意見,具體理由如下:
(一)網絡空間具有公共屬性,網絡空間秩序屬于公共社會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網絡空間具有公共屬性。網絡空間是伴隨互聯網技術發展所產生的,其本質是信息交換的媒介。網絡空間的特殊性在于,信息交換和行為多依賴于電子數據和信號的傳輸。互聯網空間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并不是計算機、服務器和數據線等物理客體,而是使用互聯網的使用者。特別是在web3.0時代[1],網絡使用者更加深入地參與到信息發布、交換和接收的過程中。據《2014年第1季度中國移動互聯網市場季度監測報告》數據顯示,2014年1季度中國移動互聯網用戶數達到6.71億人。社會公眾通過互聯網進行信息交換、商品買賣、休閑娛樂,已經形成了一個具有公共屬性的空間,雖與現實社會中的“公路、商城、碼頭”等公共場所在物質組成形式上具有一定區別,但究其本質,均屬于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空間,其公共屬性并無本質差異。
其次,網絡空間本身具有秩序。網絡空間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高速發展,已形成了網絡空間秩序。廣義的網絡空間秩序既包括網絡使用者之間的秩序,也包括物理屬性的互聯網本身的秩序。從刑法罪名分布看,由《刑法》第285條、第286條所規定的非法侵入、破壞計算
機系統罪,屬于《刑法》第六章第一節“擾亂公共秩序罪”之內,可見這兩項罪名的保護客體為物理屬性的互聯網公共秩序。而關于網絡尋釁滋事罪的司法解釋則是對互聯網使用者之間公共秩序的保護。網絡空間秩序具體內容雖無明文規定,但與現實生活秩序一樣,穩定、有序、合理等現實生活公共秩序的要求,也是網絡空間秩序的要求。
最后,網絡公共秩序是公共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學者認為,“不能因為網絡空間秩序具有公共性就將其等同于公共秩序”。[2]筆者認為,正如前文所述,網絡已不僅僅是單純的信息交換的媒體,隨著網絡的發展,網絡空間與公眾的現實生活早已密切相關。苛求“公共秩序”必須具有徹底脫離網絡,完全基于“現實”,這本身既不妥當,也不現實。網絡是“現實”的組成部分,網絡公共秩序是社會公共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能因為網絡的特殊性而不以刑事法律規范保護網絡空間的正常秩序。
(二)在網絡空間編造散布虛假信息等行為,如達到一定程度,則可以認定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的后果
尋釁滋事罪屬于結果犯,在認定網絡尋釁滋事罪過程中,如何判斷其“破壞社會秩序”危害后果的現實性和嚴重性是處理本罪的關鍵。在危害后果的現實性方面,前文已論述網絡空間秩序作為社會公共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網絡空間秩序的損害必然屬于“破壞社會秩序”的危害后果。在對網絡尋釁滋事行為危害后果嚴重性的判斷上,目前在理論界尚存在爭議,在司法實務過程中仍處于探索階段。有學者認為,網絡空間的行為只有對現實生活產生了與對應罪名實質相一致的影響的才能作為法律調整的對象,例如對于盜竊QQ幣等網絡虛擬財產的行為在客觀上導致了與盜竊罪一致的被害人財產損失。[3]筆者認為,認定網絡尋釁滋事罪,并不必然需要造成與現實生活相對應的直接危害。首先,基于網絡空間與現實生活的密切相關性,網絡秩序的混亂對現實生活的影響是必然的。例如,在網絡上傳播“微波爐致癌”的虛假信息,如果該虛假信息得以廣泛傳播并被眾多網絡使用者內心確信,那么必然會造成民眾不愿意使用微波爐,微波爐銷售和生產陷入低谷,廠家和商家利益受損等一系列危害后果。其次,現實生活的直接危害后果并不是認定尋釁滋事罪的必要條件。如果行為人散布虛假信息、辱罵、恐嚇他人等行為已經在網絡上造成了嚴重的秩序混亂,雖然在現實生活中并沒有引發嚴重混亂,但對網絡使用者的危害,所產生的恐懼心理、錯誤認識等危害,并不亞于直接的現實危害后果。
有學者認為,網絡沖擊了傳統的道德觀、法律觀,而適應網絡發展的新道德觀尚未確立,由于缺乏既定的、得到公認的道德規范,故難以形成一部良法調整網絡空間的行為。[4]法律規范具有滯后性,一部法律往往難以預測所有可能遇到的情況,但不能因為社會現實的變化而無視司法實踐對法律規范的需求。對網絡行為的法律規制需要逐步探索和完善,在現有法律框架內,盡可能解決司法實踐中遇到的問題,也是法律解釋所應遵循的原則。
對于網絡尋釁滋事的危害后果認定的證據標準,一般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證實。一是尋釁滋事行為本身是否具有嚴重性,例如散布涉及民生、安全等領域的尋釁滋事行為,容易引發網絡輿論的廣泛關注和恐慌心理。二是該尋釁滋事行為在網絡上的傳播和影響程度,可以由涉案網站出具的書證說明評論數量和內容加以證實。三是對涉案相對人的影響,如辱罵行為對被辱罵人的心理傷害,散布虛假信息行為使信息接受者產生恐慌性心理等。
具體到本案,被不起訴人董某某在網絡上編造散布虛假信息,造成了大量的負面評論,使社會公眾對自來水質量產生了大量負面心理,引發了網絡公共秩序的嚴重混亂,已構成尋釁滋事罪。考慮到董某某在歸案后如實供述,認罪態度較好,犯罪情節輕微,故對其作出不起訴決定。
注釋:
[1]web3.0是新一代網絡技術,是指網站內的信息可以直接和其他網站相關信息進行交換,能通過第三方信息平臺同時對多家網站的信息進行整合使用;用戶在互聯網上擁有自己的數據,并能在不同網站上使用。
[2]孫萬懷、盧恒飛:《刑法應當理性應對網絡謠言》,載《法學》2013年第11期,第15頁。
[3]同[2],第16頁。
[4]劉守芬、孫曉芳:《論網絡犯罪》,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