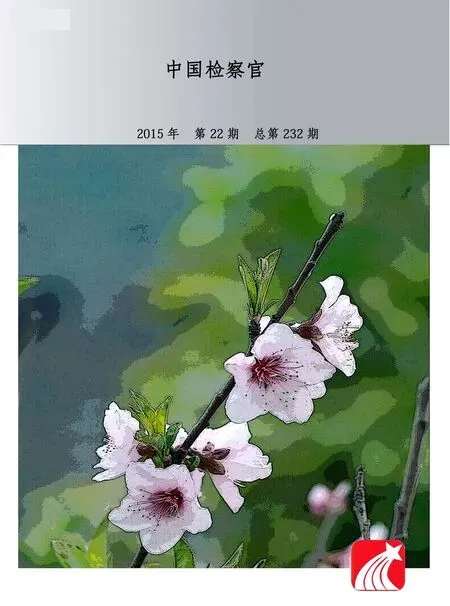善意取得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正確把握
文◎安仲偉
善意取得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正確把握
文◎安仲偉*天津市河北區人民檢察院[300141]
一、基本案情
王甲對坐落于濱海大道的一處別墅享有所有權,產權證上記載權利人為王甲。后王甲出差外地,王甲的兒子王小甲在尚未取得父親授權的情況下,私自對外出售該房屋。買受人崔某在查看了王小甲的身份證明、王甲的身份證明、房產證后,與王小甲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并交付了全部房屋價款共計300萬元。之后,雙方向不動產所在地登記機關提交了相關材料申請辦理房地產權籍過戶登記手續,在王小甲協助下,崔某順利完成變更登記手續,取得該房屋產權證。經查,房屋產權變更登記及房屋買賣協議中的簽字均顯示王小甲代王甲簽。后王甲出差回來,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要求撤銷崔某的產權證。人民法院以辦理變更登記時依據的材料存在虛假內容和原權利人未親自到場為據,判決撤銷崔某的所有權證。崔某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確認其為善意取得人,對訴爭房屋享有所有權。[1]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觀點認為,崔某構成善意取得,房屋買賣合同無效。該觀點認為,崔某購買該房屋時不知該房屋為王甲、王乙、王丙三人共有,且王小甲與王甲存在特殊關系,崔某有理由相信王小甲有代理權限,應當認定崔某主觀善意,構成善意取得。但買賣合同有效與善意取得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邏輯關系,根據《合同法》第51條之規定,無權處分人處分他人財產,未經權利人追認,亦未取得處分權,買賣合同無效。因此應當認定崔某與王小甲之間的房屋買賣合同無效。
第二種觀點認為,崔某構成善意取得,房屋買賣合同有效。根據《物權法》第106條之規定,崔某符合善意取得的構成要件,構成善意取得。同時,為了解釋崔某對訴爭標的房屋合法權利的來源,做好債法與物權法制度銜接,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3條之規定,[2]應當認定崔某與王小甲之間的房屋買賣合同有效。
第三種觀點認為,崔某不構成善意取得,房屋買賣合同無效。該案中,房屋實際產權人為王甲、王乙、王丙,房屋產權證登記權利人為王甲,買受人崔某基于王小甲與王甲的特殊關系信賴王小甲的代理行為,簽訂買賣合同。崔某信賴的內容是王小甲得到合法授權,而不是信賴產權登記簿記載的內容,崔某主觀雖存善意,但不符合善意取得中善意標準,不構成善意取得。另,根據《合同法》第51條之規定,應當認定崔某與王小甲之間的房屋買賣合同無效。
第四種觀點認為,崔某不構成善意取得,但房屋買賣合同有效。該觀點認為,崔某是基于對王小甲代理權的信任與其簽訂買賣合同,而非基于房屋產權登記簿上的權利內容,不符合善意取得中善意的標準,不構成善意取得。但崔某有理由相信王小甲具有代理權限,構成表見代理,根據保護交易穩定原則及表見代理相關理論,應當認定崔某與王小甲之間的房屋買賣合同有效。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四種觀點,崔某不構成善意取得,房屋買賣合同有效。
(一)善意取得中無權處分的認定
《物權法》第106條對善意取得制度進行了規定,構成善意取得的首要前提就是無權處分。無權處分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無權處分包括無權代理和狹義的無權處分。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善意取得中的無權處分僅指狹義無權處分,[3]即當公示狀態與實際權屬不一致時,無權處分人以自己名義處分財產的情形,而不包括無權代理。
從制度價值追求而言,無權處分與善意取得的價值追求各有側重。無權處分的規定主要見于《合同法》第51條,側重保護權利人的利益,就不動產交易而言,更加注重靜態安全;善意取得的規定主要見于《物權
法》第106條,側重保護交易過程中的善意第三人,善意取得更加強調交易順利安全進行,是一種動態安全。[4]正是由于無權處分和善意取得在制度價值追求和立法初衷上存在差異,加之善意取得屬于物權領域,應更加謹慎嚴密,故決定了善意取得中“無權處分”的認定標準更加嚴格,只能是狹義無權處分,不包括無權代理的情形。
本案中,王小甲未取得父親王甲的授權,卻私自以父親王甲的名義出售訴爭房屋,并在房屋產權變更登記和房屋買賣協議中代王甲簽字。上述事實應當認定王小甲是以父親王甲的名義進行房屋買賣行為的,屬于以他人名義進行物權處分,是一種無權代理行為,不屬于善意取得中規定的狹義的無權處分,因此不符合善意取得的基本前提。
(二)善意取得中善意標準的認定
作為物權的取得方式之一,善意取得的核心在于對善意的認定,不動產善意取得更是如此。從整個民法體系來看,對善意的評判應屬主觀范疇,但可以通過客觀化的標準衡量這一主觀概念。具體到不動產善意取得,善意的認定標準應當是對于不動產登記簿上記載內容的充分信賴。[5]
不動產登記以國家公權機關信譽為擔保,具有較高的公信力,本質上講,善意第三人指的就是對以國家信譽為基礎的不動產登記的高度信任和充分信賴。因此不動產登記簿上的權利記載應被推定為正確記載,第三人對于不動產登記簿上的善意信賴是一種推定善意,即如果原權利人主張第三人非善意,根據民事訴訟“誰主張誰舉證”的基本原理,應提供證據證明第三人主觀心態、動機非善意。根據上述原理,只要第三人交易時盡到一般注意義務,查看不動產產權登記簿記載的權利內容,確認出賣人和權利人一致,就應當認定為善意第三人。當然,司法實踐千變萬化,僅憑上述標準難以判斷第三人是否為善意時,還應該充分考慮包括出賣人與買受人的關系、交易價格等在內的全案因素,綜合評價。
本案中,買受人崔某查看了王小甲的身份證明、王甲的身份證明以及房產證上記載的權利人,但并未對出賣人王小甲和產權登記人王甲身份不一致提出質疑。崔某之所以與王小甲簽訂房屋買賣合同,是基于對王小甲身份的信賴,是對王小甲代理王甲辦理房屋買賣的信賴。從本質上講,崔某的這種信賴是對王小甲取得代理權的信賴,而不是對房產登記簿上記載的權利內容和真實房屋所屬狀態的信賴。基于此,崔某主觀雖為善意,但不符合善意取得中善意之標準。
(三)善意取得與合同效力的邏輯關系
闡述善意取得和合同效力之間的邏輯關系,實際上是針對物權理論體系和債權理論體系的銜接配合問題,關系到是否承認物權行為的無因性等一系列理論。對于物權行為的立法模式,世界范圍內主要分三種:以法國為代表的意思主義立法模式[6]、以德國為代表的物權形式主義立法模式和以瑞士為代表的債權形式主義立法模式。當前中國對物權行為采何種立法模式未明確表態,從立法理論和司法實踐看更傾向于債權形式主義立法模式,同時完善第三人善意取得制度,側重于對動態交易安全的保護。《物權法》第15條規定,當事人之間訂立有關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不動產物權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合同另有約定外,自合同成立時生效;未辦理物權登記的,不影響合同效力。由此可知,《物權法》已經明確將合同效力和物權變動區分開來,二者之間并無必然邏輯關系,合同有效物權不必然變動。[7]
需要明確的是,當前我們民法理論通說認為善意取得的前提是交易行為合法有效,一旦買賣合同被認定為無效,受讓人亦不能取得標的物所有權。就本案而言,如果崔某的買受行為構成善意取得,則必然要求崔某與王小甲之間的買賣合同有效,這是物權變動有因原則的要求;如果認定崔某的行為不構成善意取得,則崔某與王小甲之間的買賣合同是否有效仍需進一步分析。從這一角度講,觀點二的部分論述還是準確的。
(四)善意取得司法適用的邏輯順序
善意取得制度確立后爭議不斷,司法適用也不盡相同。筆者認為,善意取得的司法適用應遵循以下邏輯順序:
1.判斷出賣人的處分行為屬于真正無權處分亦或是無權代理,判斷標準為“以何人名義從事處分行為”。
2.在無權處分的情況下,無權處分行為并不影響雙方當事人之間簽訂合同之效力。除無權處分外,合同效力還應當綜合考慮是否存在違背公序良俗、惡意串通損害第三者利益等情形:
(1)當合同僅具備無權處分單一因素時,一般應認定合同有效。此時又區分為以下幾種情形:①原權
利人不予追認且無權處分人未取得處分權時,(a)若第三人善意,已支付合理對價,且已辦理房屋產權變更登記,則第三人構成善意取得,獲得標的物所有權,原權利人可向無權處分人追償;(b)若第三人善意,已支付合理對價,但尚未辦理房屋產權變更登記,第三人不得主張依有效合同過戶房屋產權。因原權利人對無權處分行為不予追認,此時合同已經喪失繼續履行的事實基礎,善意第三人只能向無權處分人主張違約責任,而不能要求繼續履行合同;②原權利人對無權處分進行追認或無權處分人取得處分權的,此時無論第三人主觀善惡,第三人均可依有效合同行為主張對標的物的所有權。
(2)若合同違反效力性、管理性強制性規定,[8]則合同無效,第三人不構成善意取得。
3.在無權代理的情況下,以被代理人對代理人的行為是否追認為標準,區分如下情形:
(1)被代理人對代理人的行為予以追認,此時合同有效,雙方辦理過戶手續的,發生物權變動;未辦理過戶手續的,可依有效合同辦理過戶手續。
(2)被代理人對代理人的行為不予追認,此時合同無效,第三人亦不能構成善意取得,此時即使辦理了產權變更登記,也不發生物權變動效力,第三人不能取得物權。
(3)有一種特殊情形需要注意,即“買受人有充分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權”,此時構成表見代理,買賣合同有效:①若此時未辦理房屋產權變更登記,且原權利人拒絕配合進行產權變更登記的,因喪失現實產權變更登記條件,構成履行不能,人民法院對第三人主張依有效合同進行產權變更登記的請求不予支持,第三人可向原權利人主張違約責任;②若已辦理產權變更登記,原權利人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第三人產權證。[9]第三人可向人民法院主張表見代理,向原權利人主張違約責任,原權利人承擔違約責任后可向代理人追償。
本案中,王小甲以父親王甲的名義出售訴爭房屋,且積極協助買受人崔某辦理產權變更登記,綜合全案考慮,崔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王小甲有代理權限,因此王小甲代父親王甲出賣房屋構成表見代理,王小甲與崔某之間的房屋買賣合同有效。王小甲的行為構成表見代理,不屬于狹義無權處分,且崔某是基于對王小甲代理關系之信賴而簽訂買賣合同,并非基于產權證上記載權利內容,不符合善意取得善意認定標準,故崔某不構成善意取得。崔某可另行向人民法院起訴,主張表見代理,向王甲主張違約責任,王甲賠償后可依法向王小甲追償。
注釋:
[1]參見趙蕾:《“善意”,究竟誰說了算》,載《中國審判》2013年第6期。
[2]該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以出賣人在締約時對標的物沒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為由主張合同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賣人因未取得所有權或者處分權致使標的物所有權不能轉移,買受人要求出賣人承擔違約責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張損害賠償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3]無權代理與狹義無權處分重要區別之一在于,無權代理是無權處分人以他人名義處分財產,而狹義無權處分則是無權處分人以自己名義處分財產。參見吳望超:《論無權處分制度與善意取得制度的沖突與協調》,載《近日中國論壇》2013年第11期。
[4]參見吳望超:《論無權處分制度與善意取得制度的沖突與協調》,載《近代中國論壇》2013年第11期。
[5]參見劉貴祥:《論無權處分和善意取得的沖突與協調》,載《法學家》2011年第5期。
[6]在意思主義立法模式中,物權變動憑當事人之間的債權合意即可完成,物權變動是債權合意的直接后果;在物權形式主義立法模式中,物權行為獨立于債權行為,物權行為的效力不受債權行為的影響,所有權的轉移需債權行為、物權行為和交付三個程序;債權形式主義立法模式是上述二者的折中,承認債權意思是物權變動的依據,同時將登記或交付作為物權變動生效要件。
[7]合同是否有效,除涉及無權處分這一因素外,還涉及是否違背公序良俗、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利益等情形,需要綜合考慮。
[8]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合同必然無效,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合同可能無效,二者存在區別。
[9]我國法律規定產權變更登記原權利人須在場,且提供身份證、產權證、戶口本等;若原權利人委托他人辦理的,應當持有經公證的授權委托書。表見代理過戶過程中,往往存在材料虛假、原權利人不在場等情形,人民法院得判決撤銷產權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