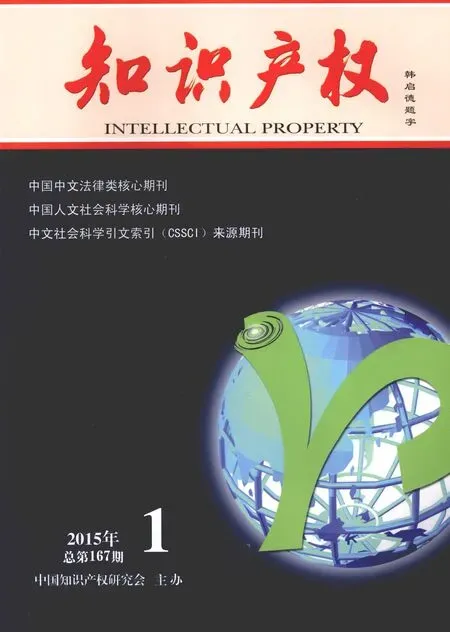論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書修改的最小單元
石必勝
論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書修改的最小單元
石必勝
在無效程序中,修改權利要求書時是否允許修改技術特征,是司法實踐面臨的重要問題。為了保護相關公眾的信賴利益,激勵專利申請人謹慎撰寫權利要求書,不宜允許修改有缺陷的單個技術特征。但是,考慮到權利要求書具有模糊性,我國專利代理水平較低,我國知識產權司法政策的導向,應當允許專利權人修改有缺陷的單個技術特征。為了防止惡意不當得利,不宜允許實用新型專利權人修改有缺陷的技術特征。
專利文件 權利要求書 無效程序 技術特征
《專利審查指南》規定,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書的修改方式一般限于權利要求的刪除、合并和技術方案的刪除三種方式。①2006年《審查指南》第4部分第3章第4.6節及《專利審查指南2010》第4部分第3章第4.6節。在專利審查實踐中,專利復審委員會基本上不允許三種方式之外的修改方式。在司法實踐中,專利復審委員會的做法受到了質疑。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江蘇先聲案即“氨氯地平、厄貝沙坦復方制劑”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中認為,授權公告權利要求書中的數值范圍1:10-30雖然并不對應并列技術方案,但仍然可以修改為1:30。②見最高人民法院(2011)知行字第17號行政裁定書。該案表明,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權利要求的修改不應限于《專利審查指南》規定的三種方式。2014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杜邦案即“氟化烴的恒沸組合物”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中明確表示,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的修改并不僅限于上述三種方式。③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高行終字第1909號行政判決書。在專利無效程序和專利授權行政訴訟程序中,應當對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書的修改確定什么樣的規則,是否允許權利要求書在上述三種方式之外進行修改,圍繞司法實踐中的上述問題,本文擬對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書的修改規則進行研究,以期能為上述問題的解決提供幫助。
一、專利文件修改的基本前提和主要問題
(一)專利文件修改的基本前提
在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書的性質屬于專利文件,因此在研究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書的修改規則時需要首先討論專利文件的修改規則。在討論專利文件的具體修改規則時,首先應當明確專利文件修改的基本前提。在我國,專利文件的修改應當注意以下基本前提。
首先,應當遵守《專利法》和《專利法實施細則》中有關專利文件修改的規定。在我國,專利文件的修改只能在專利無效程序中進行。1984年和1992年《專利法》及相應的《專利法實施細則》均未規定專利權人在專利權無效宣告請求審查過程中有權修改專利文件,但在2000年《專利法》基礎上修訂的2002年《專利法實施細則》第68條規定,“在無效宣告請求的審查過程中,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的專利權人可以修改其權利要求書,但是不得擴大原專利的保護范圍。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的專利權人不得修改專利說明書和附圖,外觀設計專利的專利權人不得修改圖片、照片和簡要說明。”在2008年《專利法》基礎上修訂的2010年《專利法實施細則》,將原來的《專利法實施細則》第68條調整為第69條,但內容沒有變化。由此可見,2001年以來歷次修訂的《專利法實施細則》,均明確賦予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權人在專利權無效宣告請求審查過程中修改專利文件的權利,但是同時對修改專利文件作出了明確限制,即不得修改專利說明書和附圖,且對權利要求書的修改不得擴大原專利的保護范圍。
其次,應當區分專利文件與專利申請文件。專利申請文件與專利文件的法律性質不同,相應的修改規則也不完全相同。在專利授權公告之前,說明書和權利要求書都屬于專利申請文件,而專利授權公告之后,說明書和權利要求書則變成了專利文件。與之對應的是,在專利授權公告之后,專利申請人也變成了專利權人。專利授權公告之前,說明書和權利要求書還處于審查階段,還沒有產生排他性的專利權,權利要求書的修改不會直接損害他人的信賴利益。在授權公告之后,權利要求書具有公示性和排他性,權利要求書的修改可能損害他人的信賴利益。專利文件的修改除了要遵守《專利法》第33條所隱含的先申請原則之外,還要遵守不得擴大原專利保護范圍的限制條件。在專利審查和專利審判實踐中,應當注意區分專利申請文件的修改和專利文件的修改。④石必勝:《技術貢獻視角下的專利申請文件修改》,載《中國知識產權》2014年第8期,第25頁。
再者,應當區分專利文件中的權利要求書與說明書。說明書與權利要求書的法律地位和作用不同,修改規則也不相同。權利要求書與說明書的區別有多個方面,其中以下兩個方面對二者在無效程序中的修改規則有重要影響:第一,權利要求書與說明書的任務不相同。說明書的主要任務是對發明創造作出清楚、完整的說明,權利要求書的主要任務是界定專利權保護范圍。第二,權利要求書與說明書的內容不相同。發明人公開在原始申請文件中的技術貢獻并不一定都體現在權利要求書中,權利要求書要求保護的技術方案并不一定都能夠體現發明人的技術貢獻。正如瑞奇(Rich)法官所說,“不要再說權利要求定義了發明創造。”⑤Janice M. Mueller, A Rich Legacy, 81 J. Pat. & Trademark Off. Soc’y 755, 758-759(1999).由于權利要求書與說明書的上述區別,二者修改產生的法律后果也不完全相同,因此二者在無效程序中的修改規則也不相同。2002年修訂的《專利法實施細則》第68條和2010年修訂的《專利法實施細則》第69條第1款規定,在無效宣告請求的審查過程中不得修改專利說明書,因此,專利文件的修改在我國只涉及到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書的修改,不涉及說明書的修改。
(二)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書修改的主要問題
在司法實踐中,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書的修改涉及的主要問題是,《專利審查指南》規定權利要求書修改限于權利要求的刪除、合并和技術方案的刪除,除了這三種修改方式外,是否還有其他修改方式。目前專利復審委員會和法院對此問題的意見并不相同。為了討論這個問題,可以對權利要求書的結構進行分析。根據范圍大小,權利要求書的組成單元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權利要求、技術方案、技術特征。權利要求書可能由一個或多個權利要求組成,權利要求可能由一個或多個技術方案組成,技術方案由多個技術特征組成,因此,技術特征是權利要求書中的最小單元。《專利審查指南》規定權利要求書修改只能有三種方式,權利要求的刪除和技術方案的刪除只涉及到技術方案的減少,不涉及技術特征的修改。權利要求的合并是指兩項或者兩項以上相互無從屬關系但在授權公告文本中從屬于同一獨立權利要求的權利要求的合并。⑥《專利審查指南》第4部分第3章第4.6.2節。在此情況下,所合并的從屬權利要求的技術特征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權利要求。該新的權利要求應當包含被合并的從屬權利要求中的全部技術特征。權利要求的合并也不涉及單個技術特征的修改,只涉及技術方案的修改。因此,《專利審查指南》實質上是將權利要求修改的最小單元限定為技術方案,即雖然可以修改技術方案,但不能修改其中的單個技術特征。
根據修改的最小單元不同,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書的修改在邏輯上可能有兩種方案:方案一,最小修改單元為技術方案,但不能修改其中的單個技術特征。如果技術方案有缺陷,可以通過技術方案的刪除、合并來克服相應缺陷,但不能修改技術方案中的單個技術特征來克服缺陷。如果技術方案中的單個技術特征有瑕疵,不能修改該技術特征,技術方案在整體上應當被宣告無效。《專利審查指南》基本上采用了此方案。方案二,最小修改單元為技術特征。如果技術方案中的單個技術特征有缺陷,可以通過修改該技術特征來克服相應缺陷。哪一種方案才是符合專利法立法目的和價值取向的合理方案,正是我國專利確權司法實踐中面臨的主要問題。
二、信賴利益保護視角下的最小修改單元
(一)信賴利益保護原則
為了深入分析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書修改的最小單元這個司法實踐中的重要問題,應當考慮專利文件修改的基本原則。專利文件的修改應當遵守先申請原則、技術貢獻匹配原則、信賴利益保護原則和利益平衡原則,其中,信賴利益保護原則對權利要求最小修改單元有重要影響。自授權公告之日起,發明和實用新型的權利要求書所確定的保護范圍就正式地產生了排除他人進入的法律效果。與已經授權的專利利益相關的公眾,不得不信賴已經授權公告的權利要求是有效的,因此對于授權公告之后的權利要求書進行修改時,不能損害相關公眾的信賴利益。對相關公眾信賴利益的保護,主要著落在對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書修改的限制上,即對權利要求書的修改不得擴大原專利權的保護范圍。從邏輯上來講,相關公眾對授權公告權利要求書的以下兩個方面的信賴利益應當受到保護:
第一,不侵權的信賴利益,即不進入專利權保護范圍、不構成侵權的安全性。權利要求書沒有要求保護的范圍是可以隨意進入的,因此不允許專利權人修改權利要求時擴大保護范圍又將其納入保護范圍,避免信賴授權公告權利要求的相關公眾由不侵權變成了侵權。歐洲專利局明確闡述了為什么不允許在專利授權之后擴大權利要求的保護范圍。《歐洲專利公約》第123條第3項規定,“歐洲專利不能通過修改來擴大保護范圍。”歐洲專利局在其《專利審查指南》中認為,此項規定的目的在于,防止擴大已經授權的專利權保護范圍,從而將原本不屬于侵權的行為變成侵權行為。即使這樣,擴大范圍的修改能夠得到原專利申請文件的支持。⑦2013年歐洲專利局申訴委員會《案例法(第七版)》第II部分第E章第2節。歐洲專利局認為,《歐洲專利公約》第123條第3項所述的不得擴大保護范圍,是指修改后的保護范圍在整體上與修改前的保護范圍相比較,只要沒有擴大即可。只要修改之后的所有權利要求的保護范圍沒有超出修改前的所有權利要求的保護范圍就是允許的。⑧同注釋⑦ 。
第二,不走彎路的信賴利益,即不因為專利權人的“不當得利”而繞彎路的信賴利益。相關公眾相信,授權公告的權利要求書是有效的,是與專利權人的技術貢獻相匹配的。但專利權人之所以要修改權利要求書,縮小專利權保護范圍,原因就是無效程序中發現授權公告權利要求要求保護的全部或部分范圍不應當得到保護。在上述情形下,專利權人實際上獲得了“不當得利”。允許專利權人縮小保護范圍,實質上就是允許專利權人將“不當得利”排除在專利權外,回到合理的保護范圍之中。那么,信賴專利權的保護范圍進而繞路行走的相關公眾,因為“不當得利”走了冤枉路,由此承擔走彎路的機會成本,實質上也是信賴利益受到了損害。換一個角度來看,允許專利權人縮小專利權保護范圍,實質上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允許其“不當得利”,并損害相關公眾不走彎路的信賴利益。
(二)信賴利益保護原則對最小修改單元的影響
無論最小修改單元為技術方案還是技術特征,在不得擴大保護范圍的前提下,都不會損害不侵權的信賴利益,但最小修改單元的選擇可能會對不走彎路的信賴利益產生不同的影響。如果最小修改單元是技術方案,意味著一旦技術方案中的單個技術特征有缺陷,專利權人無法通過修改該技術特征來克服該缺陷,只能放棄包含該技術特征的整個技術方案。這樣的修改規則將會激勵專利申請人更加謹慎地選擇合適的技術特征,盡量使技術特征與其公開在原始申請文件中的技術貢獻相匹配。這樣一來,能夠有效避免因為單個技術特征與技術貢獻不匹配而產生的“不當得利”,也能夠有效地保護相關公眾不走彎路的信賴利益。如果最小修改單元是技術特征,意味著雖然技術方案中包含了有缺陷的單個技術特征,專利權人也有機會在無效程序中通過修改該技術特征來克服相應缺陷。這樣的修改規則相對于前述的修改規則不利于激勵專利申請人謹慎、合理地確定技術特征的保護范圍。相對于最小修改單元為技術特征的規則,最小修改單元為技術方案的規則更有利于保護相關公眾不走彎路的信賴利益。從這個角度來看,《專利審查指南》規定最小修改單元為技術方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撰寫激勵視角下的最小修改單元
(一)激勵分析方法的必要性
司法裁判的激勵分析方法是建立在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之上的案件裁判方法,可以普遍適用于知識產權案件的審判實踐。⑨石必勝:《網絡不正當競爭糾紛裁判規則的激勵分析》,載《電子知識產權》2014年第11期,第51頁。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之一是,由于人們通過比較成本與利益作出決策,所以,當成本或利益變動時,人們的行為也會改變。這就是說,人們會對激勵作出反應。經濟學提供了一個科學的理論來預測法律規則對行為的效應。對經濟學家來說,法律規則就像是價格,人們對法律規則的反應就像是對價格的反應一樣。在前述理論基礎上,經濟學家可能用數學化的精確理論(價格理論和博弈論)和經驗式的可靠方法(統計學和數量經濟學)來分析法律規則對行為的效應。⑩[美]羅伯特·D·考特、托羅斯·S·尤倫著:《法和經濟學(第三版)》,施少華、姜建強等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由于法律規則包括的裁判規則可能會改變人們面臨的成本或利益,從而改變人們的行為,因此經濟學提供了預測人們如何對裁判規則作出反應的理論基礎。法律經濟學家據此提出了事前分析研究方法,或者說激勵分析研究方法。相對于傳統法學研究側重于對案例的事后研究,激勵分析方法側重于對行為的預測研究。
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書的修改規則,必然會對專利申請人撰寫權利要求書產生引導和激勵,因此確定授權后權利要求書的修改規則時,不僅僅要考察個案中當事人之間的利益之間是否平衡,個案正義是否得到申張,更要注意在個案中確定的裁判規則將會對其他潛在當事人產生什么樣的激勵作用。①石必勝:《隱含特征在權利要求解釋中的作用》,載《中國知識產權》2013年第12期,第25頁。如果在個案中只是關注裁判結果對個案的影響,而忽略相應裁判規則對其他人的激勵作用,則可能會產生不好的法律和社會效果。例如,在個案中如果僅僅依據行為人扶起了摔倒在地的老人,就初步推定行為人將老人撞倒,將會導致其他人不去扶起摔倒的老人。在討論授權后權利要求書的修改規則是否合理時,有必要從激勵權利要求書撰寫的視角來分析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書修改的最小單元。
(二)最小修改單元對權利要求書撰寫的激勵后果
最小修改單元為技術特征,將會對權利要求書的撰寫產生消極激勵后果。專利申請人將可能在撰寫時選用外延大于其技術貢獻的技術特征,因為這樣做可能收益大于成本。首先,實用新型專利不需要經過實質審查,這樣做不容易被發現。其次,即使對發明專利,這樣做也不容易導致包含該技術特征的技術方案被宣告無效。因為如果有人針對該技術特征存在的缺陷提出無效宣告請求,專利權人有機會修改該技術特征,使其與技術貢獻相匹配從而克服相應缺陷。例如,專利申請人雖然明知與其技術貢獻匹配的技術特征是1-10,但可能會故意撰寫成1-20。一旦有人提出無效宣告請求,專利權人還可以通過修改該技術特征將其縮寫成1-10。最小修改單元為技術特征,可能會激勵專利申請人選擇外延大于其技術貢獻的技術特征,使其獲得與技術貢獻不匹配的“不當得利”,因此最小修改單元為技術特征會對權利要求書的撰寫產生消極激勵后果。
相對而言,最小修改單元為技術方案,將會對權利要求書的撰寫產生積極激勵后果。最小修改單元為技術方案意味著,如果技術特征中包含了壞點,技術方案整體上就應當被宣告無效,這樣有利于激勵專利申請人更加謹慎地選擇與其技術貢獻相匹配的技術特征,避免因為某個技術特征與技術貢獻不匹配而導致整體技術方案被宣告無效。前面的分析表明,最小修改單元為技術方案更有利于激勵專利申請人更加謹慎地選擇與其技術貢獻相匹配的技術特征,更加合理地確定保護范圍,更有利于避免損害相關公眾的合法權益,提高專利撰寫質量。因此,從有利于激勵專利申請人撰寫的角度來看,應當不允許專利權人在無效程序中修改有缺陷的單個技術特征。從這個角度來看,《專利審查指南》的現有規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四、權利要求書不準確性視角下的最小修改單元
(一)權利要求書的不準確性
在確定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書修改規則的時候,必須考慮權利要求書天然具有的不準確性。權利要求書的不準確性是指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權利要求所要求保護的專利權范圍具有不確定性和模糊性。權利要求書不準確性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專利申請人難以準確認識到其作出的技術貢獻。很多發明創造與現有技術的差異是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定性的差異使得專利申請人在主觀上很難準確界定要求保護的范圍。第二,文字與物的不完全對應性。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語言與客觀事物的準確對應是一個永恒的難題。而且,技術方案可能涉及到很多二維、三維的技術信息,而文字更多地適合描述一維的信息,因此,文字對技術信息的描述具有天然的局限性。第三,漢字的模糊性。自然語言具有精確性和模糊性的雙重屬性。從字的生成和構造來看,漢語的語義不準確性更容易產生,因此,使用合適的漢字來準確表述技術信息難度更大。第四,撰寫能力的局限性和差異性。專利代理人撰寫能力的局限性和差異性容易導致權利要求的文字表達不能夠準確表述專利申請人意圖要求保護的范圍。
(二)權利要求書不準確性的考量
權利要求書的不準確性是權利要求書自身性質決定的,是客觀難題,難以避免。權利要求書的不準確性對專利授權確權審判實踐和專利侵權審判實踐判均具有重要的影響。例如,專利侵權判定規則中的等同侵權就是基于權利要求書不準確性產生的。雖然理論上來說應當嚴格按照權利要求的內容來確定專利權保護范圍,但是各國的司法實踐都表明,如果過分拘泥于權利要求的文字,則不能為專利權人提供有效的專利保護。②尹新天:《專利權的保護(第2版)》,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頁。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01年以來討論《專利法實體條約》的過程中,各國基本上同意在條約中采納等同侵權規則,表明多數國家都承認權利要求書不準確性這一客觀事實。
如果說只要專利申請人在主觀上愿意準確表述保護范圍,在客觀上就能夠實現該目的,那么對權利要求書的撰寫應當確立比較嚴格的評價標準,一旦發現權利要求中存在有缺陷的技術特征,就可以否定其有效性。這樣的評價規則不會損害善意專利申請人的合法權益,也有利于保護相關公眾的利益。但在前面所述的權利要求書撰寫的多種難題及多種不確定因素下,考慮到專利申請人很難一次性準確確定合適的技術特征,不僅僅應當允許專利申請人在專利申請程序中對有缺陷的技術特征進行糾錯,也應當允許專利權人在專利無效程序中對有缺陷的技術特征進行糾錯。各國專利制度一般都允許專利申請人和專利權人在專利授權前后對專利權保護范圍進行調整,給予專利申請人和專利權人對技術特征和技術方案進行糾錯的機會。技術方案和技術特征的準確性在專利審查程序和專利無效程序中不斷被檢視和糾正,技術方案和技術特征的修改和完善是一個過程。綜上,權利要求書的不準確性是允許專利權人修改有缺陷的單個技術特征的重要理由。從權利要求書不準確性的視角來看,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修改的最小單元更宜確定為技術特征而非技術方案。
五、司法政策視角下的最小修改單元
(一)專利代理實際情況的考量
“法律是實踐的,是要解決問題的,是要解決我們的問題的,是要解決我們眼下的問題的。”③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頁。在當前討論我國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書的修改規則,不能不考慮當前我國專利代理行業的現實情況。我國專利制度建立時間不長,專利代理行業的發展時間較短。雖然在近年來發展迅速,但我國專利代理從業人員數量與服務質量存在雙重匱乏的問題。④林小愛、朱宇:《專利代理機制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載《知識產權》2011年第5期,第 48 頁。在當前,專利申請人普遍舍不得在專利申請階段花錢,大量專利申請文件由沒有專利代理人資格的人撰寫。如果對專利撰寫水平要求過高,客觀上會影響確實有技術貢獻但撰寫有瑕疵的發明創造的有效性。⑤孔祥俊:《知識產權保護的新思維——知識產權司法前沿問題》,中國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頁。因此,在現實情況下似乎應當考慮適用對專利權人相對寬松的權利要求書修改規則,允許對單個技術特征進行修改。
有些司法判例也表明,法院在評價專利權有效性時考慮了專利代理人的實際撰寫能力。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第一三共株式會社案,即“用于治療或預防高血壓癥的藥物組合物的制備方法”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中認為,“眾所周知,在專利文件撰寫及專利審查過程中,無論專利申請人還是審查員,只能在特定范圍內檢索現有技術的內容。由于現有技術范圍廣泛,任何人均不可能檢索到所有的現有技術。如果將授權后的馬庫什權利要求視為一個整體技術方案而不允許刪除任一變量的任一選擇項,那么專利權人獲得的專利權勢必難以抵擋他人提出的無效請求。”⑥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高行終字第833號行政判決書。在該案中,法院認為,在無效程序中應當對專利權人修改權利要求給予適度的寬容。本文不探討該案涉及的具體規則是否合理,但該案中法院基于撰寫的客觀局限性給予專利權人修改權利要求更寬松的條件是符合我國當前實際情況的。
(二)司法政策的考量
僅僅立足于固定的概念或者法律標準,那是一種技術性思維,在法律適用中是不夠的。只有植入價值和政策,用價值和政策指導法律的適用,法律適用才不是僵硬的和冷冰冰的,才能充滿活力。⑦孔祥俊:《商標法適用的基本問題》,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頁。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修改應當確定什么樣的具體規則,最終取決于價值選擇和政策考量。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的具體修改規則是如何涉及到利益平衡,從而涉及到價值選擇和政策考量的呢?雖然對有缺陷的技術特征的修改是以縮小專利權保護范圍為前提,但是,在專利授權之日至專利權人通過修改限縮保護范圍之日,相關公眾不能進入通過修改而排除在外的那一部分保護范圍。通過修改而排除在外的保護范圍實際上是專利權人本來就不應當獲得的保護范圍,但在專利授權公告之日至修改被接受之日,事實上起到了排除相關公眾進入的效果。被排除在外的保護范圍相對于專利權人而言,是“不當得利”。專利權人通過修改限縮保護范圍,就是將“不當得利”返還給相關公眾。在最小修改單元為技術方案的規則之下,專利權人要對“不當得利”付出代價,即放棄部分技術方案,但在最小修改單元為技術特征的規則之下,專利權人不會對“不當得利”付出代價,因為有缺陷的技術方案可以通過單個技術特征的修改繼續有效。因此,相對于最小修改單元為技術方案的規則,最小修改單元為技術特征的規則,雖然會最大限度地保護專利權人的利益,但卻會損害相關公眾的利益。而最小修改單元為技術方案的規則,雖然會更有效防止損害相關公眾的利益,但卻對專利申請人的撰寫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專利權人與相關公眾的利益沖突之間選擇,是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具體修改規則的核心問題。
我國當前的知識產權基本司法政策對于這個核心問題的處理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為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和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見》中,最高人民法院表示,“充分考慮專利文件撰寫的客觀局限,在專利申請文件公開的范圍內,盡可能保證確有創造性的發明創造取得專利權,實現專利申請人所獲得的權利與其技術貢獻相匹配,最大限度地提升科技支撐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該意見可以解讀為,對于確實有技術貢獻的發明創造,應適度容忍其撰寫上的瑕疵。基于這樣的司法政策,似乎應當允許專利權人在無效程序中修改有缺陷的技術特征。
最高人民法院在相關判例中也體現出類似的政策傾向。在“氨氯地平、厄貝沙坦復方制劑”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中,專利權人在無效程序中將權利要求1中的某藥物成分的比例“1:10-30”修改為“1:30”。專利權人在無效程序中的上述修改實際上就是對有缺陷的單個技術特征的修改。專利復審委員會認為,無效程序中修改權利要求書時不能修改有缺陷的單個技術特征,依據《審查指南2006》第4部分第3章第4.6.2節的規定,認為該修改不應接受。最高人民法院在該案中認為,專利權人對權利要求1的修改應當予以允許,《審查指南》的相關規定過于機械。最高人民法院在該案中的意見似乎更傾向于保護專利權人通過修改有缺陷的單個技術特征而挽救專利權的機會。因此,按照當前的司法政策,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修改的最小單元應當確定為技術特征而非技術方案,即在不擴大原專利權保護范圍的前提下,應當允許專利權人在無效程序中修改有缺陷的技術特征。
六、發明與實用新型區分視角下的最小單元修改
(一)發明與實用新型的區分
值得討論的是,發明與實用新型的授權程序并不相同,為了更有效保護相關公眾不走彎路的信賴利益,發明與實用新型的權利要求書在無效程序中的修改規則是否應當有所區別。發明專利經過了實質審查,即使發明人意圖使用大于其技術貢獻的技術特征,理論上講專利審查員也會予以限制。因此,經過專利審查員在實質審查后的專利權保護范圍,即使有“不當得利”,也必然是不明顯的,而且也不能認為是專利申請人惡意獲得的。從這個角度來講,發明專利權人即使在授權公告的權利要求中獲得了“不當得利”,也屬于“善意不當得利”。但是,實用新型專利不同于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申請不需要經過實質審查,專利權保護范圍沒有經過專利審查員的確認,專利申請人在提出申請時故意要求保護與其技術貢獻不匹配的“不當得利”,不會受到專利審查程序的限制,因此,實用新型專利權人有機會獲得“惡意不當得利”。實用新型專利權自授權公告之日起生效,一旦生效,就產生了排除他人進入保護范圍的效力。除非通過較為復雜和漫長的專利無效程序,實用新型專利申請人的“惡意不當得利”難以消除。因此,對于實用新型專利,如果在無效程序中的最小修改單元是技術特征,專利權人可以通過修改單個技術特征放棄“不當得利”,后退到與其實際技術貢獻相匹配的技術特征,專利權人損害相關公眾不走彎路的信賴利益只需要承擔較小的代價。相反,如果實用新型專利的權利要求書在無效程序中最小修改單元是技術方案,意味著一旦某個技術特征與技術貢獻不匹配,整個技術方案就會被宣告無效,實用新型專利申請人在撰寫時就會盡量避免“惡意不當得利”。
理想的無效程序權利要求書修改規則應當允許 “善意不當得利”,防止“惡意不當得利”。鑒于發明專利與實用新型專利在審查程序上的區別,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修改的理想方案是,發明專利權人在無效程序中可以修改有缺陷的單個技術特征,而實用新型專利權在無效程序中不能修改有缺陷的單個技術特征。但從宏觀上來看,是避免實用新型專利申請人可能的“惡意不當得利”,保護相關公眾的利益更為迫切和重要,還是保護實用新型專利權人通過修改克服單個技術特征的缺陷從而挽救專利權人的利益更為迫切和重要,還需要更進一步討論。
(二)比較法的考察
在無效程序中允許專利權人修改權利要求時修改有缺陷的單個技術特征也能夠得到比較法的支持。歐洲專利局在《專利審查指南》中表示,《歐洲專利公約》第123條第3項的規定表明,修改授權后的權利要求書時,可以重寫、修正或刪除部分或全部權利要求中的技術特征,并不受到授權公告的權利要求書中的具體技術特征的限制,只要修改后的權利要求書符合《歐洲專利公約》第123條第2項的規定即沒有超出原申請文件的范圍,并且沒有超出授權的權利要求書所確定的保護范圍。⑧同注釋⑦ 。上述規定中所說的對技術特征的重寫、修改或刪除實質上就是允許修改有缺陷的單個技術特征。美國有再頒(reissue)程序,在再頒程序中允許專利權人修改單個技術特征。美國和歐洲專利局對于專利授權之后權利要求書的修改都允許對單個技術特征的修改,因此從比較法的角度來看,應當允許專利授權之后修改單個技術特征。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和歐洲專利局并不授予實用新型專利,在發明專利授權之前都要進行實質審查,因此不用擔心專利申請人在不承擔風險的情況下故意使用大于技術貢獻的技術特征以獲取“不當得利”。比較法只是支持在發明專利無效程序中允許修改有缺陷的單個技術特征,并不支持實用新型專利無效程序中允許修改有缺陷的單個技術特征。
結 語
即使要采用最小修改單元為技術特征的無效程序權利要求修改規則,也不意味著所有有缺陷的單個技術特征都可以進行任意修改。單個技術特征的修改將會涉及到很多問題,也需要設定一些限制條件,例如,技術特征的修改是否必須以限縮該技術特征的方式進行,技術特征的修改是否必須以實施例為依據,是否可以在權利要求中增加技術特征。對最小修改單元為技術特征的修改規則設定哪些具體限定條件,還需要結合法律規定和專利法基本原理進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的分析表明,在確定專利文件修改規則時,首先要區分專利申請文件與專利文件,要區分說明書與權利要求書。為了深入分析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書修改的最小單元這個司法實踐中的重要問題,應當考慮專利文件修改的基本原則,包括先申請原則、技術貢獻匹配原則、信賴利益保護原則和利益平衡原則,其中,信賴利益保護原則對無效程序中權利要求的修改規則有重要影響。為了有效保護相關公眾的信賴利益,激勵專利申請人合理確定保護范圍,不宜允許專利權人修改有缺陷的單個技術特征。但是,考慮到權利要求書的不準確性,應當給予專利權人更為寬松的修改規則。考慮到我國專利代理行業的實際情況以及我國當前的知識產權基本司法政策,對專利權人在無效程序中修改有缺陷的技術特征應當較為寬容。但是,實用新型專利不需要經過實質審查,允許專利權人在無效程序中修改有缺陷的單個技術特征可能弊大于利,因此可以考慮對發明和實用新型分別適用不同的修改規則,不允許實用新型專利權人在無效程序中修改有缺陷的單個技術特征。
There exists an important question whether patentee can be allowed to modify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when amending claims in patent invalidation procedure. In order to protect reliance interest of relevant public and motivate patent applicants to write claims carefully, it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modify single technical feature which is defective. However,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vagueness of claims and the low level of patent agent, it is advised to allow patentee to to modify single technical feature which is defective through intellectual property judicial policy. However, utility model is the exception, in order to avoid illegal profi t.
patent documents; claims; invalidation procedur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石必勝,華東政法大學博士后研究人員,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