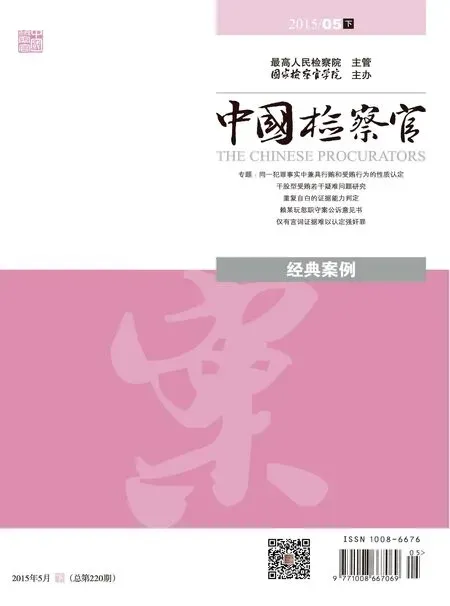呼格吉勒圖案的反思
文◎戴哲宇
呼格吉勒圖案的反思
文◎戴哲宇*
2014年12月15日,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對呼格吉勒圖故意殺人、流氓罪作出再審判決,撤銷原判,宣告呼格吉勒圖無罪。一起塵封了18年的冤案,總算迎來了遲到的正義;那個屈打成招的冤屈者,總算迎來了昭雪的這一天。如今,正義雖然來臨,卻無法讓逝者復生;無罪判決雖下,卻無法讓逝者明鑒。遲來的正義背后,下一步,便是對造冤者的責任追究,以及對冤案生成機制的反思、對冤屈者的賠償。
蹊蹺案情少年命殞,家人痛苦無望等待
1996年4月9日,位于呼和浩特市賽罕區的呼和浩特第一毛紡廠家屬區公共廁所內,一年輕女子遭到強奸并殺害。當晚,呼和浩特卷煙廠男職工呼格吉勒圖聽見廁所傳來女子喊叫聲,找來同事閆峰一起進入女廁內,發現一個女子裸露著下身仰躺在廁所的矮墻上。在發現案情后,呼格吉勒圖讓閆峰回煙廠幫他請假,自己則主動找到轄區治安崗亭報案。當晚,警察把他倆一起送到新城區分局,分開詢問口供。事后,呼格吉勒圖被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分局特警認為有作案嫌疑并實施拘捕,在調查過程中疑似存在刑訊逼供的行為。1996年4月20日,呼和浩特晚報報道了4.9女尸案,報道稱兇手為呼格吉勒圖。在案件仍有疑點的情況下,檢方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流氓罪”和“故意殺人罪”兩項罪名對呼格吉勒圖提起公訴,提交的證據包括“證人證言、公安機關刑事科學技術鑒定書、尸體檢驗報告以及現場勘查筆錄”。呼格吉勒圖一審開庭是1996年5月23日,庭審時間并不長,檢方宣讀公訴意見,律師張娣起初為呼格吉勒圖做的是無罪辯護,最后卻以他“認罪態度好,是少數民族,年輕”為由,在法庭上做出求情陳述。短暫的休庭合議之后,法官當庭宣判,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呼格吉勒圖死刑。6月5日內蒙古高院二審裁定“維持原判”,而這意味著終審死刑核準裁定。二審裁定出來的第5天,1996年6月10日,呼格吉勒圖被押往刑場。從案發到執行死刑,只隔了62天。
過去的18年間,這個呼和浩特市普通職工家庭的命運,因為一起殺人案數度起伏。
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紡廠在當地簡稱“一毛”,曾經是呼市有名的國企。李三仁和妻子尚愛云都是“一毛”的職工,他們的三個兒子都出生在牧區,都取了蒙古名字。在毛紡廠,李三仁家境能算中上,尤其是老大昭格力圖和老二呼格吉勒圖先后參加工作后,這個五口之家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能看見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過”,尚愛云記得從前的簡單和幸福。
好光景隨著呼格吉勒圖被帶進公安局戛然而止。在一個到處都是熟人的小區里,“流氓罪和故意殺人罪”這兩個字眼,抵消了幾乎所有人對這個家庭的好感,“抬不起頭來,感覺到處都有人戳脊梁骨,”尚愛云說。這個之前下班后還會擺攤的開朗女主人,從此變得沉默。兒子被執行死刑是在6月,大熱的天,尚愛云常常一人站在馬路上,神情恍惚。李三仁內向口拙,他情愿把自己鎖在家,郁悶難解時,做得最多的是一拳拳地捶向沙發和墻壁。
2006年年初,正在住院的李三仁聽說趙志紅來他們小區指認兇案現場后,他和老伴走上了上訪之路,奔波于家和內蒙古高院,奔波于呼和浩特和北京之間。他們至今還保留著的一沓厚厚的火車票、上百張快遞回執單和數百張信訪處理單。
李三仁說,從1996年呼格吉勒圖出事至今,他一直堅信兒子是冤枉的。在這個沒有希望的9年里,李三仁先后戒煙、戒酒、也戒了象棋,變得沉默寡言,親戚之間他也不再走動。身邊人的指指點點讓他如芒在背,在呼格吉勒圖被執行死刑后的幾天里他就愁白了頭發,一家人過起了“半隱居”的生活。慶格勒圖是呼格吉勒圖的弟弟,在二哥被定為奸殺案的兇手時,正在上初中的他突然發現同學和小區里的小伙伴們都不跟他玩了。他說,老師告訴同學們,他是強奸殺人犯的弟弟,讓離他遠一點,別學壞了。隨后的幾個月里。慶格勒圖變得越來越不合群,學習成績逐漸下降,當時不到14歲的他一個多月就掉光了頭頂的頭發。呼格吉勒圖案發不到半年,慶格勒圖就輟學了。如今,內向的慶格勒圖以給別人開車為生。
2005年趙志紅的落網讓一家人燃起了希望。在隨后的9年里,李三仁每天晚上19時,雷打不動地看新聞聯播,每天要買一份刊登有法制新聞的報紙,了解國家法規政策。他說,“要有理有據地上訪”。在呼和浩特賽罕區山丹小區那個簡陋的兩居室里,李三仁床頭一直放著一本由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的《刑事錯案與七種證據》,這本書有的地方已經被翻得起了毛邊,很多地方用筆勾勾劃劃過,在一些地方,他還專門用白紙寫下了自己的理解,并讀給文化程度不高的老伴聽,老兩口互相鼓勁“要堅持下去”。
真兇現身重啟舊案,五篇內參推動重審
2005年初,內蒙古烏蘭察布市接連發生數起奸殺慘案。警方鑒定確認,案件系同一人所為。2005年10月23日,系列強奸,搶劫,殺人案的犯罪嫌疑人趙志紅落網。落網后,趙志紅主動交代了其1996年犯下的第一起強奸殺人案,就在呼和浩特賽罕區臨近卷煙廠的公廁里,并準確指認了早就被拆除重新建設的案發地點。趙志紅甚至說出了諸如“南北朝向,女廁在南”的廁所方位,內部結構,被害人身高,年齡,當時扼頸殺死被害人的方式,尸體擺放位置等其他作案細節,都有清晰,肯定的記憶。趙志紅對案件表述的準確程度遠遠超過了1996年就已經被執行槍決的呼格吉勒圖。
當趙志紅供述自己是“四九”案真兇時,專案組成員大吃一驚。為確認趙志紅所供述的真實性,專案組先后安排四組經驗豐富的干警訊問趙志紅。這四份口供相互印證,沒有漏洞。這一情況立刻在全國引起震動。盡管當時呼和浩特市警方有意見認為,趙志紅的一面之詞缺乏有力的證據支持,但10年前的案件尋求證據已無可能,并且有法律界及社會各界人士同樣對當年呼格吉勒圖被判死刑的證據支持和提出質疑,對趙志紅的供認如果不能認定,對于呼格的指控和審判同樣存在嚴重的問題。呼格吉勒圖冤案由此而來。而對這起冤案的調查認定和重審程序的啟動卻走上了漫漫之路。
誰也不會想到,十年后,這個倉促的句號,卻因一起特大系列強奸搶劫殺人案件的艱難告破,被猛然拉成巨大的問號與嘆號。在趙志紅供出“四九”命案后,內蒙古自治區政法委也組成了以時任政法委副書記宋喜德為組長的四九案件核查組,對案件進行復查。但四九命案始終沒有開啟重審。
最先將此事報道出去的是新華社內蒙古分社政文采訪部主任、高級記者湯計。
湯計說,他的第一篇內參寫于2005年11月23日,距離趙志紅落網剛好一個月,多年在內蒙古政法系統的良好人脈讓他獲悉這起存在巨大疑點的冤殺案,并在獲知消息的第一時間將情況形成文字,以內參的形式發往北京,“發給誰?”對于記者的提問,湯計保持緘默,“這是機密,不能說。”但他表示當時的多位政治局委員是看到了這篇內參的。
于是2006年的3月,內蒙古自治區政法委組成了案件復核組對案件進行調查。同年的8月,復核得出結論,“呼格案”確為冤案。
就在湯計等待有關部門對結論明確表態的時候,2006年11月28日,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趙志紅案進行了不公開審理。庭上,公訴機關對趙志紅招認的10起強奸殺人案的9起提起公訴,唯獨漏掉了1996年4月9日的那起案件。趙志紅當庭指出了這一問題,法庭審理因此中斷。
“我在得知這一消息后,覺察到問題的嚴重性,就立即寫了第二篇內參。”湯計說,2006年12月8日,他在對案件復核情況進行了詳細了解后形成文字,并于同日將內參發出。
2006年12月20日,湯計寫下第三篇內參。“在我寫完上一篇內參的第8天,有一個警察交給我一封趙志紅寫的償命申請書,我原文不動的發到北京,趙志紅當時可能已經認識到“4.09”案件對他是很關鍵的。湯計說,這篇內參很快就被批示下來了,引起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
為了擴大影響,2007年湯計寫了關于該案件的上下篇,形成大內參,在全國黨政系統發行,在更大范圍內通過客觀地報道擴大了事件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的推動了呼格案的重新調查。隨后,《瞭望》雜志根據湯計的內參形成報道公開報道。“呼格案”在全國范圍內引起關注。
2007年11月28日,湯計完成了第五篇內參,根據法律界人士的意見,直接呼吁案件跨省區異地審理“呼格案”。這篇內參發出后,同樣引起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視,最高法從內蒙古調閱了“呼格案”的案卷,對案件直接予以關注。
案件重審國家賠償
“正義從來不會缺席,只會遲到”。重審開啟近十年之后,休尼特法官這句名言,終于得以應驗——盡管,呼格吉勒圖已長眠18年。此時此刻,沒有什么能夠足夠表達這一紙無罪宣判來臨時的意味深長。死者已逝,終得昭雪,對于呼格吉勒圖的家人而言,一紙無罪宣判,意味著多年來的爭議奔呼暫時換來結果,但之于司法公正而言,醞釀呼格吉勒圖的司法機制的修復之路,仍舊道阻且長。
2014年,內蒙古自治區政法委組織公檢法等多部門商議決定開始啟動針對呼格吉勒圖的法律重審程序。2014年11月20日,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暴巴圖代表高院向呼格吉勒圖父母送達立案再審通知書,備受關注的呼格吉勒圖案進入再審程序。2004年12月15日,內蒙古自治區高院對呼格吉勒圖故意殺人、流氓罪一案作出再審判決,撤銷內蒙古高院1996年作出再審判決,撤銷內蒙古高院1996年作出的關于呼格吉勒圖的二審刑事裁定和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1996年對呼格吉勒圖案作出的一審刑事判決,宣告原審被告人呼格吉勒圖無罪,并向其父母送達了再審判決書。
呼格吉勒圖再審改判無罪案,呼格吉勒圖父母李三仁、尚愛云于2014年12月25日向內蒙古高院提出了國家賠償申請,內蒙古高院于同日立案,并于12月30日依法作出國家賠償決定,決定支付李三仁、尚愛云國家賠償金共計2059621.40元。該決定已于12月31日送達。一、向賠償請求人李三仁、尚愛云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共計1047580元;二、向賠償請求人李三仁、尚愛云支付呼格吉勒圖生前被羈押60日的限制人身自由賠償金12041.40元;三、向賠償請求人李三仁、尚愛云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100萬元。以上各項合計2059621.40元。
2015年2月3日,呼格吉勒圖父母領取到國家賠償金205萬余元。呼格父母表示,這筆錢會首先用來為呼格購買一處新墓地。
糾正錯案意義深遠
呼格吉勒圖案之所以引發輿論關注,與“一案兩兇”的懸疑有關,更與疑案持續8年得不到重審密不可分。媒體和公眾所期望看到的,是案件真相的還原,是重審程序一拖再拖的因由調查。期待通過這一案件,向公眾彰顯法律的公道正義。
無論是糾正錯案,還是推動制度建設,無疑都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決心。雖然過程一波三折,也離不開外界推動,但畢竟是法院系統在法律框架內部通過正常法律程序完成,這與具有人治色彩的“平反”相比,法治是最終的贏家。
反思這起錯案的形成以及依法糾正的過程和結果,對于推動法制建設的意義非常重大,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案例。呼格吉勒圖案室在用其血淚昭示:如何啟動制度化的反思,從根源之上避免冤案;如何打破司法制度的某些堅冰,讓錯案重審來得不再艱難,正義不再姍姍來遲。逝者已矣,呼格吉勒圖案也已平反,然而在某種程度上,仍遠遠沒有結束。讓辦冤案者得到應有的懲戒,讓呼格吉勒圖父母得到應有的撫慰,這自然是首先要做的。而在此之后,如何用制度革新或者重建,激活司法的良心,讓司法人員不至于在案件中,極易丟失獨立的法律人格,這更是至關重要的。只有鏟除了冤案產生的土壤,才會避免下一個呼格吉勒圖;只有重新設計再審程序,才會避免下一個長達九年的泣血申訴。也只有這樣,正義才最終抵達了終點。
每一個判例,都可能為法律信仰加一塊基石;每一次失誤,都可能成為信仰崩塌的鏈條。人們不僅要求實體公正,也要求程序公正;不僅要求公正,更要求及時的正義。盡管遲來的正義也是正義,但如若始終姍姍來遲,有時就是非正義,因為生命耗不起,公理等不起,世道人心傷不起。期待呼格吉勒圖早日等到正義,期待呼格吉勒圖早日等到正義,期待有錯必糾與有錯必糾同時進行,更期待冤假錯案不再出現。
一次不公的裁判要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猶烈。要防止司法異化,實現司法公正,就必須首先重鑄程序法和程序的尊嚴。具體說來,應當要實現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則和要求:一、以無罪推定的原則代替“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的規定,實行疑罪從無、維護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權;二、建立沉默權規則,通過賦予犯罪嫌疑人面對警察訊問保持沉默的權利,使刑事案件的偵破由依賴口供轉向依賴物證和其他證據,以杜絕現實司法實踐當中大量存在的刑訊逼供現象;三、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構造,對涉及公民重大權益的偵查措施和強制措施,必須獲得法院的司法授權方能進行,對違法的偵查和強制行為,法院有權予以審查和撤銷,從而能夠對刑事追訴活動起到反向的制約作用;四、改革發揮重審制度,將發回重審的范圍限定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對于證據明顯不足、存在合理懷疑的案件,上級法院應從及時終結訴訟、維護被告人權利角度考慮,應當直接做出判決,而不得發回重審以滯延訴訟;五、從根本上來說,最重要的是建立能夠保障司法權獨立行使的一套制度設計,也就是實現法院和法官的獨立。
*西城區檢察院[10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