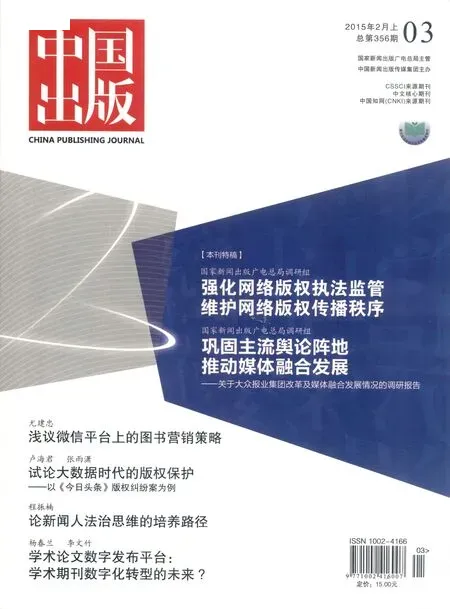數字時代時事新聞的界定與版權保護
□文│劉 慶 曾夢倩
數字時代時事新聞的界定與版權保護
□文│劉 慶 曾夢倩
數字時代,新聞的內容和形式極大豐富,現行《著作權法》關于時事新聞的模糊界定已無法很好應對實踐需求,導致實踐中對時事新聞的認定標準不一、爭議不斷。時事新聞的核心屬性是非獨創性的單純事實陳述,且僅限于文字形式,除此以外,任何具有獨創性的時事新聞作品均應當排除于時事新聞的認定范疇之外,從而獲得《著作權法》的保護。
時事新聞 獨創性 數字新聞 法律界定
時事新聞是對社會事件的單純事實型報道,不具有獨創性,同時,其也是公眾知悉社會事件的重要途徑,具有公共性,因此,長期以來,時事新聞被劃入事實作品(WorksofFact)的范疇,未納入著作權法的保護,我國《著作權法》第五條也規定:“本法不適用于時事新聞”,但法律對時事新聞這一概念內涵外延的界定并不清晰,司法實踐對“時事新聞”的理解也不統一,認定標準模糊,侵害新聞作品版權的現象屢有發生。當前,新聞正經歷著從傳統新聞向數字新聞的轉型與融合,數字新聞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傳統新聞的制作、傳播與呈現過程,其表現手法豐富、呈現方式多樣,更給時事新聞的認定帶來了新的挑戰。同時,交互式、便捷化的傳播特征也使得因侵犯新聞作品版權所產生的危害成倍放大,因此,合理界定時事新聞,明確新聞版權保護邊界,對保障相關新聞創作人的合法權益乃至對整個數字新聞產業的健康良性發展意義重大。
一、問題的提出——以一則案例展開
2011年6月23日,北京城區遭遇了一場十分罕見的降雨,降雨導致市內多條交通要道嚴重積水,部分地鐵線路因此停運。因雨勢過大,大雨積水很快漫過地鐵站入口,順勢而下,形成了壯觀的地鐵瀑布景象,這一場景恰好被路過地鐵的楊某遇見,楊某用手機將此景象拍下并上傳到微博,短短幾分鐘時間,該圖片的轉發就達上千條,與此同時,此圖片還被新華網等多家網站轉載,一時間,該圖片迅速登上各大網站主頁,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媒體在使用該照片時并未征得楊某的同意。[1]事后,該事件的討論焦點很快轉移到對網站未經楊某同意而使用照片的行為性質的認定上,并形成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地鐵瀑布的照片屬于楊某拍攝的作品,自其拍攝之時起,楊某便當然取得作品的著作權,未經楊某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該照片,否則即構成對楊某作品著作權的侵害;另一種觀點認為,楊某拍攝的照片屬于客觀反映北京大雨這一事件的時事新聞,不受我國著作權法的保護,任何報刊媒體均可使用,無需征得楊某的同意。
可以看出,對網站擅自使用地鐵瀑布照片行為的認定,涉及我國《著作權法》對時事新聞的界定,而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恰巧反映出現行《著作權法》在時事新聞概念界定上的模糊,隨著數字新聞時代的到來,新聞作品的表現手法和傳播方式更加豐富多樣,使得現有法律關于時事新聞概念的模糊界定在應對此類問題時更顯捉襟見肘,概念不清晰的問題在數字新聞背景下也將暴露得更為徹底,因此,我們有必要從法律上進一步明晰時事新聞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
二、“時事新聞”內涵探究
時事新聞一詞具有新聞學和法學雙重屬性。一般而言,時事新聞包括時事和新聞兩個方面內容,《現代漢語詞典》 (第6版)中將“時事”一詞定義為:“最近一段時間的國內外大事”,“新聞”則指:“報社、通訊社、廣播電臺、電視臺等新聞機構對當前政治事件或社會事件所作的報道。”因此,通常意義上的時事新聞可以理解為報社、通訊社、廣播電臺、電視臺等新聞機構對當前政治事件或社會事件等國內外大事所作的報道。顯然,這一定義所涵蓋的內容十分寬泛,既包括對事件的單純客觀敘述,也包括對事件進行的獨創性分析與評論,形式上既包括文字形式,也包括圖片、錄音、錄像等多媒體形式。若將這一定義作為我國《著作權法》對“時事新聞”的界定,則必然導致很多本應受《著作權法》調整的時事新聞作品無法得到應有保護,從而挫傷廣大新聞工作者進行高水平新聞創作的積極性,甚至對整個新聞業的健康持續發展也會造成負面影響,《著作權法》中的時事新聞顯然與我們通常理解的時事新聞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必須對通常意義的時事新聞概念作適當調整。
關于時事新聞概念范圍,根據我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規定:“時事新聞是通過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報道的單純事實消息”,時事新聞的內涵應當由兩部分構成:①時事新聞必須由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報道;②時事新聞屬于單純事實消息。因此,不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時事新聞當指由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報道的單純事實消息,《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對單純事實消息作前置性限定,將通過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傳播的單純事實消息與其他形式的事實消息報道區分開來的做法并無太多實際意義。實際上,此種限定在數字時代受到了挑戰,由于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革新為數字新聞提供新的傳播模式與利潤增長點,新聞業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對傳統媒體形式的依賴,微博、微信、移動數據終端等新興傳播介質發展之迅速,難以想象,同樣由新聞單位發布的時事新聞,會因傳播媒介不同而導致著作權法對其完全迥異的保護效果。同時,著作權法保護的僅是思想表達形式,任何單純事實描述均不受保護,而不論其以何種媒介傳播,因此,在數字時代背景下作此種限定已略顯多余。
就時事新聞的單純事實消息這一性質而言,曾參與《著作權法》立法的劉春田教授認為:“單純事實消息是全部內容都由硬件信息(包括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等客觀事實)組成的新聞,是簡單的文字和機械的記錄方式對客觀事實的再呈現”,[2]也即,單純事實消息是以新聞內容限制在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原因五個要素之內的簡單報道,僅單純機械陳述何時、何地、何人、發生何事以及發生此類事件的緣由,實際上,將單純事實消息限定為5W的簡單報道,具有其合理性。
首先,單純事實消息不具有獨創性,無法滿足作為作品所需的獨創性要求。具有獨創性是作品獲得《著作權法》保護的前提,雖然各國著作權法對作品獨創性的判斷標準不同,但均規定了以獨創性作為判斷作品能否受到法律保護的標準,我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二條明確規定:著作權法所稱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成果,這是對作品獨創性要求的法律依據,理論上,作品的獨創性必須包含以下兩個基本要素:①獨立創作完成;②作品的誕生是作者創造性智力勞動的結果,顯示了作者創作過程中的個性特征。而新聞工作人員在進行時事新聞的撰寫時,盡管也付出了一定的勞動,但此種勞動僅是單純事實消息的直接反映,是語言文字對社會事件的機械反映,不具有創造性智力勞動的特征。
其次,單純事實消息對社會事件的反映具有唯一性。單純事實消息對事件的時間、地點、人物、事由等要素的簡單組合,具有唯一性,若對唯一的表達形式賦予著作權,無疑會造成少數人對該內容的合法壟斷,不利于文化和科學的發展與進步。
最后,排除對單純事實消息的著作權保護可以有效保障公眾對社會事件的知情權。時事新聞傳播的都是國內外的最新消息、國家的大政方針以及社會重大事件,這些資訊與大眾生活決策密切相關,是公民參與社會治理、實現民主權利的重要保障,因此,必須通過多種途徑保障時事新聞便捷有效的傳播。倘若賦予單純事實消息以著作權保護,無疑是對信息自由流通的公然遏制。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在內涵上,時事新聞應當以不具有獨創性的單純事實消息描述為其本質特征。具體而言,以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和原因五要素之全部或部分的簡單組合作為判斷標準,而新聞工作者在新聞媒體上發表的調查報告、帶有研究思考性的分析性或解釋性新聞等,由于加入個人獨創性元素,具有一定的文學或科研價值,體現了作者的創造性智力勞動,可以稱之為新聞作品,不屬于時事新聞,應當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
三、時事新聞的外延探究
我國《著作權法》和《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將單純事實消息作為認定時事新聞的核心特征,但未對單純事實消息的表現形式作進一步的界定,對于以何種形式表現出來的單純事實消息才能被認定為時事新聞這一問題,筆者認為,只有以文字形式表現的單純事實消息才有被認定為時事新聞的可能,對于照片、圖片、視聽作品,一般都應當獲得著作權的保護。
首先,以文字形式展現的單純事實消息,其表述形式具有唯一性,基本遵循了5W表達結構,對此種表達形式無法賦予獨占性保護,否則必然成為變相的文字表述壟斷。反映新聞事件的照片或攝影作品則不同,即使拍攝對象一樣,也不可能存在完全相同的兩張照片或攝影作品。拍攝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充分展示拍攝者個性空間的過程,任意兩個拍攝作品都不可能做到在拍攝角度、拍攝光線、拍攝距離等方面上的完全相同,因此,拍攝過程的此種特質為賦予其著作權保護留下了制度空間。
其次,就拍攝作品而言,我國與英美法系國家極為相似,均采取了較低的獨創性標準,如前所述,拍攝行為本身就是一個充分施展拍攝者個性空間的過程,“任何照片,無論多么簡單都不可能不受到拍攝者個性的影響”,[3]拍攝行為本身具有的個性化特征不會因其拍攝內容是否為時事性事件而有所改變,因此,賦予以時事性事件為拍攝對象的拍攝作品以著作權法保護也便順理成章。
最后,賦予新聞圖片、新聞視頻以著作權保護,在新聞實踐中也極具積極意義。賦予這些成果以著作權保護,可以有效激發新聞工作者的工作熱情,鼓勵新聞工作者多開展實地采訪采編,多采用新聞圖片、新聞視頻等形式,充分運用現代技術,使新聞報道更加生動形象。
比較法上,日本也承認以攝影方式報道的時事性事件的版權地位,《日本著作權法》第41條規定:“通過攝影、電影、播放或者其他方法報道時事事件時,構成該事件的作品,或者在該事件中看到或聽到的作品,在報道目的的正當范圍內,可以進行復制并在報道該事件時進行使用。”[4]因此,不適用《著作權法》的單純事實消息在形式上僅限于文字新聞,新聞圖片、新聞視頻可以構成攝影作品或視聽作品并應得到《著作權法》的相應保護。
四、結語
時事新聞猶如阻隔在單純事實消息與新聞作品之間的一堵高墻。合理界定時事新聞的界限可以充分激發新聞工作人員創作高水準新聞作品的工作熱情,推動傳統新聞產業與數字新聞模式的進一步融合,同時,也能兼顧民眾及時獲取時事新聞信息的權利。我國現行《著作權法》和《著作權法實施條例》關于時事新聞的界定過于模糊,不利于各方主體權利義務的明晰。未來,我們應當明晰時事新聞的判定標準,一方面,通過“單純事實消息”特有的5W表述結構認定是否具有獨創性的問題,排除一切具有獨創性的新聞作品,另一方面,確立起“時事新聞”的描述形式標準,排除一切以非文字形式表現的時事新聞,從內涵與形式兩個方面樹立起較為明晰的判定標準,并落實到制度層面,從而為新聞事業健康發展提供科學的法制保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
[1]馮曉青.著作權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馬曉靜.我國數字出版版權問題探析[J].中國出版,2014(15)
[3]袁博.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對“時事新聞”的新立場[N].中國知識產權報,2012-07-11
[4]曹新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5條第2項之修改[J].法商研究,2012(4)
[5]吳偉光.數字技術環境下的版權法危機與對策[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
[6][德]M·雷炳德.著作權法[M].張恩民,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注釋:
[1]中國網,“北京地鐵瀑布”照片引發網絡圖片版權討論[EB/OL].http://www.china.com.cn/photochina/2011-06/27/ content_22863687.htm,2014-10-26
[2]劉春田.著作權法講話[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66
[3]JEWELERS'CIRCULARPUB.CO.V.KEYSTONEPUB. CO.274F.932,AT934(1921).
[4]十二國著作權法翻譯組.十二國著作權法[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