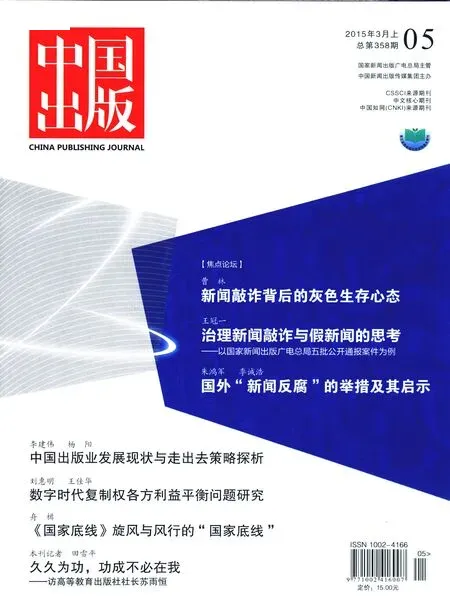新聞敲詐背后的灰色生存心態(tài)
□文│曹 林
新聞敲詐背后的灰色生存心態(tài)
□文│曹 林
分析幾起新聞敲詐的典型案件,暴露的不僅僅是某些媒體的道德缺失和記者的職業(yè)迷失,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多重的灰色生存心態(tài)和狀態(tài)。其一是少數(shù)媒體人的灰色生存心態(tài),在“社會(huì)公器”和“商業(yè)機(jī)器”間的精神分裂;其二是監(jiān)督缺失的灰色區(qū)域,“同行不互相批評(píng)”的潛規(guī)則使某些媒體人成為監(jiān)督盲區(qū),對(duì)新聞管制的反彈力使中國(guó)媒體人骨子里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受害情結(jié)和烈士般的悲壯感,這種悲壯感更容易掩飾媒體本身的問題;其三是被敲詐者的灰色心態(tài),政府和企業(yè)怕記者怕媒體怕惹事,見不得陽光的灰色心態(tài)縱容著敲詐行為。
灰色生存 商業(yè)機(jī)器 不批評(píng)同行
編者按
2015年2月5日,國(guó)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通報(bào)了4起新聞報(bào)刊領(lǐng)域違法違規(guī)典型案件的查辦情況。其中,《中國(guó)產(chǎn)經(jīng)新聞》在江西組織有償新聞,給予報(bào)社警告、罰款和退回違法收入的處罰,同時(shí)撤銷江西記者站;涉案記者余樟樹5年內(nèi)禁止從事新聞采編工作,并移送司法機(jī)關(guān)處理。新華社編輯張小俊利用職務(wù)便利,多次收受北京迪思公關(guān)顧問有限公司給予的錢款共計(jì)50935元。張小俊被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終身禁止從事新聞采編工作。
這是自中宣部、國(guó)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中國(guó)記協(xié)等9部門于2014年3月部署開展打擊新聞敲詐和假新聞專項(xiàng)行動(dòng)以來,國(guó)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第五次公開通報(bào)違法違規(guī)案件的查處情況。新聞敲詐和假新聞為何屢禁不止,其背后有何深層原因?如何治理新聞敲詐和假新聞?國(guó)外有哪些經(jīng)驗(yàn)值得借鑒?本期焦點(diǎn)論壇就此展開討論。
2015年2月5日,國(guó)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通報(bào)了4起新聞報(bào)刊領(lǐng)域違法違規(guī)案件,又是涉及新華社記者,又是終身禁止從事新聞采編工作,又是在整體反腐的大背景下,因此引發(fā)了輿論極大關(guān)注。由于媒體整天鞭撻丑惡、監(jiān)督別人、曝光其他群體的問題,當(dāng)媒體自身腐敗問題被曝光時(shí),自然會(huì)受到輿論的報(bào)復(fù)性關(guān)注和批評(píng)。在網(wǎng)絡(luò)上,媒體和記者經(jīng)常被網(wǎng)友稱為“霉體”,可見公眾對(duì)媒體腐敗問題也已深惡痛絕。
分析這幾起新聞敲詐的典型案件,暴露的不僅僅是某些媒體的道德缺失和記者的職業(yè)迷失,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多重的灰色生存心態(tài)和狀態(tài)。
一、媒體人的灰色生存心態(tài)
“新聞理想”是媒體人常用來激勵(lì)自身和尋找職業(yè)榮譽(yù)感的職業(yè)信條。人們常把媒體稱為“社會(huì)公器”,對(duì)媒體和記者有諸多的職業(yè)期待,希望媒體站在時(shí)代的船頭瞭望,扮演公權(quán)力的監(jiān)督者、真相的挖掘者、公益的代言者和公正的捍衛(wèi)者,用負(fù)責(zé)任的報(bào)道滿足大眾對(duì)公共事務(wù)的知情需求。這是公眾所期待的理想媒體,也是記者的新聞理想,可媒體王國(guó)里一個(gè)個(gè)媒體人并非不食人間煙火,這種理想一觸碰骨感的現(xiàn)實(shí),就變得很無力。媒體人很容易生存在“社會(huì)公器”和“商業(yè)機(jī)器”的夾縫中,在精神分裂的灰色生存中做新聞。
在當(dāng)下的市場(chǎng)壓力和商業(yè)誘惑下,媒體很容易從“社會(huì)公器”滑向“商業(yè)機(jī)器”,從“利益集團(tuán)的監(jiān)督者”變成“獨(dú)立的利益集團(tuán)”。這種利益機(jī)制下的媒體人,在不擇手段追逐市場(chǎng)利潤(rùn)時(shí),也很容易滑向新聞敲詐,在輿論監(jiān)督的幌子下進(jìn)行敲詐勒索,大搞有償新聞,玩有償不新聞,收保護(hù)費(fèi)當(dāng)保護(hù)傘。當(dāng)淪為商業(yè)機(jī)器后,一些媒體的地方記者站記者完全不像記者,而成了強(qiáng)盜,炮制負(fù)面報(bào)道,拿著單位蓋的公章公開向企業(yè)要錢。一家被曝光的媒體,甚至公開將新聞敲詐當(dāng)成了單位生意,不僅不向記者發(fā)工資,還向記者收提成,縱容記者在地方敲詐勒索。
市場(chǎng)化改革是中國(guó)新聞改革的一大動(dòng)力,改變了中國(guó)媒體業(yè)的格局和語態(tài),帶來了輿論監(jiān)督的春天,催生了一大批優(yōu)秀媒體和媒體人,中國(guó)媒體至今仍享受著市場(chǎng)化的改革紅利。可由于媒體自身管理體制的改革沒有跟上,部分媒體在改制的過程中缺乏法律的約束,與財(cái)政脫離后同時(shí)出現(xiàn)管理真空,廣告經(jīng)營(yíng)與采編未能分開,在體制的根子上留下了新聞敲詐的巨大漏洞。一方面監(jiān)督權(quán)力很容易異化為敲詐權(quán),另一方面,經(jīng)營(yíng)壓力又使這種權(quán)力尋租找到了貌似堂皇的借口,某些媒體便出現(xiàn)了塌方式腐敗,地方記者站更成為腐敗重災(zāi)區(qū)。
“社會(huì)公器”賦予了冠冕堂皇的神圣光環(huán),“商業(yè)機(jī)器”是現(xiàn)實(shí)的利益驅(qū)使,在“社會(huì)公器”和“商業(yè)機(jī)器”的灰色地帶,某些記者一手握著輿論監(jiān)督的社會(huì)公器,一手拿著廣告經(jīng)營(yíng)的商業(yè)機(jī)器,給錢就“塑造形象”,不給錢就“披露丑聞”,使媒體業(yè)這個(gè)過去曾備受尊敬的行業(yè)被貶低為受到唾棄的“霉體”。
二、缺乏監(jiān)督的灰色區(qū)域
媒體整天曝光各行各業(yè)的問題,常被人追問:你們整天盯著別人監(jiān)督別人,誰來監(jiān)督你們媒體呢?
在一般情況下,這純粹是一個(gè)偽問題。監(jiān)督別人的媒體,會(huì)在一種開放的體制下受到同行和大眾的監(jiān)督。媒體行使的是輿論監(jiān)督權(quán),而這種輿論監(jiān)督有一種“自我監(jiān)督”的天然機(jī)制。不像一個(gè)普通人或一個(gè)普通的單位,無法實(shí)現(xiàn)“自我監(jiān)督”,而輿論是由無數(shù)個(gè)媒體和個(gè)人組成,它們之間是能夠?qū)崿F(xiàn)互相監(jiān)督的,存在一種天然的倫理自治和自我凈化功能。比如,這家媒體到太平間偷拍去世明星的尸體,那家媒體不顧別人感受強(qiáng)迫采訪死者家屬,就會(huì)受到大眾和同行的激烈批評(píng)。
但在潛規(guī)則的約束下,這種“自我監(jiān)督”的機(jī)制常受到干擾,使媒體間的同行監(jiān)督無法運(yùn)行起來,使媒體腐敗成為缺乏監(jiān)督的灰色區(qū)域。
中國(guó)媒體業(yè)有一個(gè)不成文的規(guī)定,就是同行之間盡可能地避免相互批評(píng)。媒體在批評(píng)其他行業(yè)丑惡的時(shí)候,總是掄圓了去狠批,可批評(píng)本行業(yè)問題的時(shí)候,就會(huì)受到很多看不見的約束,會(huì)被戴上“同行相輕”的帽子,會(huì)被指責(zé)“借貶低和抹黑同行抬高自己”,會(huì)被威脅“等你出問題時(shí)也來狠批你”,會(huì)被警告“壞了行業(yè)的規(guī)矩”。
不知道這種“同行不互相批評(píng)”的潛規(guī)則是何時(shí)形成的,總之在這個(gè)行業(yè)客觀存在。也許是擔(dān)心媒體掌握著話語權(quán),互相批評(píng)很容易變成意氣之爭(zhēng),使“社會(huì)公器”淪為互相泄私憤、惡意攻擊對(duì)方的混戰(zhàn)——更重要的是一種行業(yè)性的護(hù)短。有的記者在拿紅包,有的媒體在搞有償新聞、有償不新聞,當(dāng)這種媒體腐敗成為一種見慣不怪的行為時(shí),就成為一種行業(yè)默契:誰也不比誰高尚,誰也沒資格揭露誰,批評(píng)了對(duì)大家都不好,批評(píng)了就會(huì)讓很多人失去這種行業(yè)性的腐敗紅利。于是就形成了“同行不批評(píng)”的陋俗。
再加上媒體有著“社會(huì)公器”的正義外衣,輿論監(jiān)督有著一種天然的正當(dāng)性,記者又有著“觸碰了利益集團(tuán)會(huì)受到報(bào)復(fù)”的受迫害意識(shí)——這種輿論監(jiān)督環(huán)境所賦予記者的正義光環(huán)弱者形象、悲情的受迫害形象,也成為某些記者逃避監(jiān)督的一層外衣。這些因素,都使媒體業(yè)成為這個(gè)社會(huì)的一個(gè)監(jiān)督盲區(qū)和腐敗特區(qū)。正因?yàn)榇耍?dāng)幾年前《中國(guó)青年報(bào)》記者在一次礦難中曝光了同行收礦主金元寶的行業(yè)丑聞后,贏得了公眾的尊敬。敢曝光同行,一方面是自己足夠硬,另一方面有一種“清理門戶自我凈化”的真正共同體榮辱感。
中國(guó)少數(shù)媒體人骨子里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悲壯感,這種悲壯感更容易掩飾媒體本身的問題。典型表現(xiàn)在《新快報(bào)》記者陳永洲被抓引發(fā)的輿論反應(yīng)上。陳永洲被“跨省刑拘”的描述,使這個(gè)群體陷入了一種“被迫害”的悲壯意識(shí),本能地站到陳永洲一方譴責(zé)公權(quán)力對(duì)記者的“打壓”,而沒有追問記者是不是真的收了錢違了法。陳永洲承認(rèn)收錢黑企業(yè)后,不少企業(yè)都在微博上抱怨被記者敲詐的經(jīng)歷,一些業(yè)內(nèi)人也曝光了不少企業(yè)借記者打擊對(duì)手的黑幕,甚至已經(jīng)成為一種業(yè)內(nèi)人皆知的潛規(guī)則。可是,這個(gè)丑陋的潛規(guī)則,為什么這個(gè)“媒體共同體”沒有自身戳破它?行業(yè)自身的那些敗類,為什么不是媒體同業(yè)去揭露和曝光,而都要借助警方和司法的力量?
“媒體共同體”是一個(gè)神圣的概念,是一種訴諸于共同的利益感覺、職業(yè)理想、專業(yè)情懷和公共精神而形成的共同體意識(shí),有著共同價(jià)值取向和專業(yè)追求的人凝聚在一種共同的職業(yè)身份中,捍衛(wèi)共同的權(quán)益,分享共同的職業(yè)榮譽(yù),強(qiáng)化共同的理念。當(dāng)年馬克斯·韋伯一篇“以政治為業(yè)”的演說提起了政治人的職業(yè)主義精神,隨著中國(guó)社會(huì)的發(fā)展和媒體人權(quán)利意識(shí)的激發(fā),與律師、環(huán)保人、公共知識(shí)分子一道,成為中國(guó)最先具備“職業(yè)共同體意識(shí)”的一群人。他們以集體的身份在公共事件中扮演推動(dòng)社會(huì)進(jìn)步的角色,有鮮明的共同訴求,能夠合作與抱團(tuán)。可讓人遺憾的是,這個(gè)被浮躁的輿論場(chǎng)所裹挾的媒體共同體有時(shí)會(huì)陷入烏合之眾的正義幻覺中,在自閉和自負(fù)中失去判斷力,將“共同體”當(dāng)成一種討伐的武器,徒有一腔空洞的道德激情,而缺乏對(duì)共同體進(jìn)行自我凈化的能力。
三、被敲詐者的灰色心態(tài)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不得不說到那些被記者敲詐的對(duì)象,他們與某些記者一樣,同樣有某種不健康的灰色生存心態(tài)。他們被敲詐,屬于受害者,但他們?cè)诤芏鄷r(shí)候的不健康心態(tài),助長(zhǎng)著一些媒體和記者的囂張。
與某地官員交流時(shí)談到過新聞敲詐的問題,他們也深受敲詐之苦,常花錢買清凈。筆者問他們?yōu)楹稳淌芮迷p而不舉報(bào)那些記者而將其繩之以法,他說有難言之隱:遭遇過某媒體地方頻道的敲詐,不過不知道如何處理,雖然記者拿來敲詐的事實(shí)并不存在,或嚴(yán)重扭曲并被夸大,但當(dāng)?shù)卮_實(shí)有一些其他小問題,記者也清楚地掌握著。他擔(dān)心舉報(bào)了記者后,把本地其他問題牽出來。他不知道如何對(duì)付,如果認(rèn)了,給了記者錢,覺得冤枉,而且這種敲詐會(huì)成為一個(gè)無底洞。如果不給錢,又怕投鼠忌器被報(bào)復(fù)性曝光,畢竟把勒索當(dāng)生意做的記者已成地頭蛇,結(jié)成了利益同盟,一嗅到“問題”便結(jié)伴去敲詐,得罪了一個(gè)就得罪了一幫。
顯然,正是政府和企業(yè)這種投鼠忌器的灰色生存心態(tài),助長(zhǎng)了一些記者的肆無忌憚。無論如何,政府或企業(yè)總有些“把柄”掌握在記者手上,這些單位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tài)面對(duì)這些問題,想捂著瞞著問題,怕被曝光和糾纏,怕“得罪”記者,看到負(fù)面輿情就恐慌。即使一些沒什么問題的單位,也覺得媒體惹不起,養(yǎng)成了花錢擺平的習(xí)慣——反正花的也不是自己的錢。這種見不得陽光的駝鳥意識(shí)和灰色心態(tài)在地方政府和某些企業(yè)中普遍存在。受害者忍氣吞聲,施害者自然變本加厲。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與少數(shù)媒體結(jié)成了某種穩(wěn)定的利益同盟,政府部門明知道那屬于敲詐,但已經(jīng)形成了利益默契,以接受敲詐、與媒體合作的方式去向記者“行賄”,花錢買媒體版面,以各種方式向記者輸送利益,讓記者幫著吹捧、幫著掩蓋問題、幫著控制負(fù)面輿情。這種新聞敲詐,屬于利益勾結(jié)和交易性的新聞敲詐。
如果政府和企業(yè)心態(tài)健康,一遇到敲詐就能夠站出來舉報(bào),新聞敲詐行為就會(huì)受到大大的遏制。其實(shí),新聞敲詐本身是見不得陽光的行為,敲詐者本來是很心虛的,但如果被敲詐者比敲詐者還心虛,就失去了對(duì)敲詐天然的制衡和約束力量。如果政府和企業(yè)充分的透明和公開,不諱疾忌醫(yī),不遮不掩,以“身正不怕影子歪”的正派心態(tài)對(duì)待輿論監(jiān)督,面對(duì)新聞敲詐,每個(gè)受害者能勇敢地站出來依法維權(quán),敲詐行為就失去了滋生的土壤。
另一方面,如今依法受到處理的都是那些主動(dòng)的新聞敲詐,而那種和媒體默契合作的變相敲詐行為并未受到影響,如果這種深層次的媒體腐敗不被追究,新聞敲詐很難根治。
最后還有管理層面的灰色區(qū)域,哪些行為屬于新聞敲詐,哪些交往不屬于,缺乏一個(gè)清晰的界限和法律定性。比如,某企業(yè)有了丑聞,某媒體采訪了沒有報(bào)道,后來該企業(yè)在這家媒體投放了廣告,這是否屬于敲詐行為?某企業(yè)出現(xiàn)丑聞,某媒體作了報(bào)道,后來該企業(yè)在這家媒體投放了廣告,這涉及敲詐嗎?還有,編輯稱政府不給錢,就不發(fā)政府的宣傳稿,這是否又屬于新聞敲詐?長(zhǎng)期以來,媒體在與被采訪對(duì)象的交往中形成了一些默契性的利益交換,合法與非法之間有巨大的灰色空間。這些都需要通過清晰的立法進(jìn)行界定。
(作者單位:中國(guó)青年報(b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