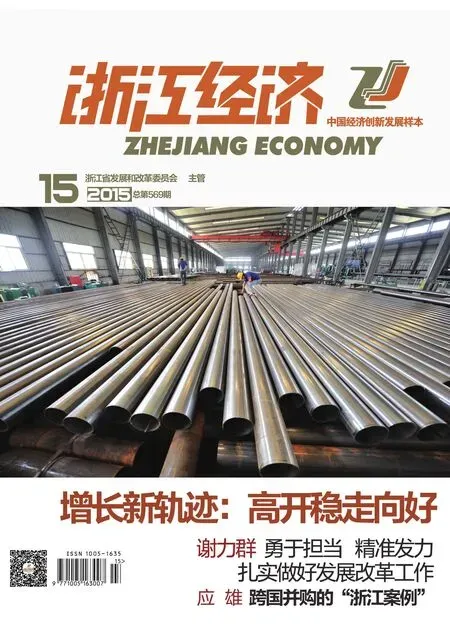“三十而立”與“四十不惑”之間
董波
“三十而立”與“四十不惑”之間
董波
孔夫子曾經對自己的人生,編制了一個清晰的規劃——“十五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
竊以為,在他所規劃的不同人生階段中,“三十而立”和“四十不惑”是最為關鍵的轉折點。前者是從“未立”轉為“已立”,后者是從“有惑”變為“不惑”,都是人生境界的質變和飛躍。至于后來的“知天命”、“耳順”及“從心所欲”,應該是一把年紀活下來后,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六十已退休,子女亦成家立業,若不“耳順”點,豈不白白給自己添堵?)
而在“三十而立”與“四十不惑”之間的十年,我認為是人一生中最為關鍵的時期。這段歲月的積淀和打磨,這個時期的選擇和付出,將決定一個人最終的成色,以及生命的厚度和寬度。
十年的起點,是“三十而立”。我至今清晰記得,自己臨近三十歲時的苦逼光景和焦慮心情。那時候工作已有五六年,仍是部門里跑腿打雜的小年輕,房子買不起,車子養不起,孩子也未出生。參加次同學會,回來得郁悶好幾天。當初成績不如自己的同學,已或是董秘或是部門經理,開著大奔款款而來,席間“輕描淡寫”地談起公司給了多少多少的干股。回家后輾轉床上,想到孔夫子“三十而立”之說,心頭就會串起一股無名的焦灼之火。
持續的焦慮中,有一天我幡然醒悟,孔夫子混了一輩子,在世時依然是個“擼瑟”,他不會打自己臉呀。“三十而立”應該不是指有房有車、在機關里混到了處長,或在公司里當上了部門經理;更可能的是指內心一套基本體系的建立,形成自己穩定的價值取向和評判標準。或簡而言之,是自己的“三觀”立了起來。
所以那段時間,焦慮中的我一頭扎到書堆里尋求慰藉。每月十本書,一年看百本,不求甚解。從文字中窺視世界的本質及他人的經歷,反復咀嚼后形成構建成自己內心世界的絲絲縷縷。那個時期,似乎能夠感覺到自己的獨立人格和思維方式正逐步形成,自信心由此慢慢恢復乃至膨脹。這才覺得自己算是真正“立”了起來,精神上終于成年,手握理論思維的小刀,躍躍欲試著想剖析和應對這個世界了。
“三十而立”,主要是關于自己的內在建設。但隨后的人生中,依然避免不了內在與外在沖突的矛盾和困惑。在心境上,焦慮可能逐步減緩,糾結卻還時常發生。“而立”之后為何依然“有惑”?我想,主要由于人是群體性生物,再堅定的自我價值,也離不開社會的認同。當整個社會被商品經濟及相應的功利主義所挾裹的時候,個體內在中任何一點與主流社會價值格格不入的東西,都會硌得讓自己難受,乃至隱隱作痛。現實來看,你的自身自由意志,還常常與家庭期待、單位賦予的角色相沖突呢,家庭問題和同事關系的處理就足夠喝一壺了,哪還自信能以澄明的眼神說:“我對這個世界已經沒有疑問了”呢?
但類似的困惑和糾結多了,就會發現所有的問題,其實無非就一個問題:“To be,or not to be?”,翻譯成白話,就是“從,還是不從?”這是真正考驗自我價值體系的時候,也是檢驗知行能否合一的時刻。而在十年中,經歷一次次“從,還是不從”的選擇后,我想到了四十歲以后大約就能固化下來,形成明確的自我認知了,下一次面臨選擇時再也不會困惑和糾結。所以十年的終點,才是“四十不惑”。
就我個人而言,現在正處于這十年的后半程。遇到重要選擇或人生波折時,雖自詡灑脫,但往往還會影響到自己的睡眠。這種“患得患失、榮辱皆驚”的反應,想必是老子最為鄙夷的狀態。所以,也明了自己遠沒有達到“不惑”的境界,也經常為自己膚淺的困惑與糾結感到羞愧。所幸,這樣的困惑和糾結,近年來已越來越少。更要感謝命運的垂青,領導同事的厚愛,讓我在人生的關鍵時期到地方掛職,當了兩年的“縣太爺”。進入體制內的切身感受,體驗權力的責任和“快感”,使我懂得不同人生選擇所面臨的處境。也讓我在后續的選擇中,更加堅定了初心,懂得何是我欲,我欲成何。
信筆寫下“三十而立”與“四十不惑”之間,是因為這是自己正在經歷的一段路程,也正是周邊很多青年面臨的階段。世界衛生組織于2013年將青年的年齡上限提高到了44歲,那么30-40歲之間,正是青年群體的中位區間。在此與諸君共勉,望共同到達“四十不惑”的彼岸,早日養成堅如磐石的信念,豁達寬敞的胸懷,從容澄明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