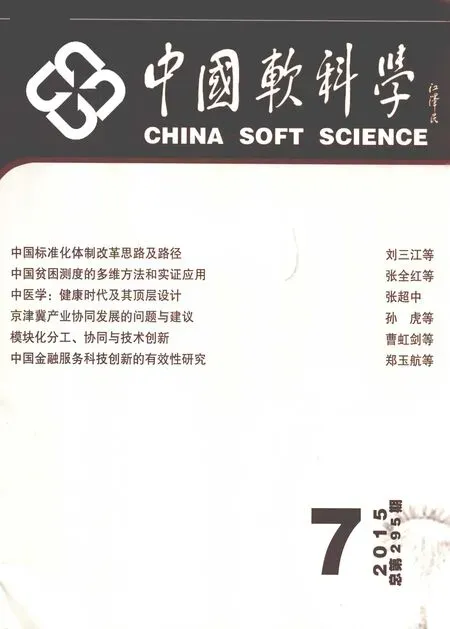中醫學:健康時代及其頂層設計
張超中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
?
中醫學:健康時代及其頂層設計
張超中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北京100038)

摘要:從詮釋學的角度看,王冰對《黃帝內經素問》的“重廣補注”堪稱典范,為當代中醫的原創性發展提供了關鍵性的啟示。從中可見,作為上古文化理想的“健康時代”是開啟未來“健康時代”的歷史資源,而開啟的關鍵是“知道者”的教化和實踐。更進一步說,中醫學的思想方法注重健康之道的整體性和“自足性”,通過闡釋創新,能夠直接服務于“全球健康高速公路計劃”。對這一計劃的頂層設計和實施,將促進中醫學新形象的建立和中國文化的新發展。
關鍵詞:中醫學;黃帝內經;健康時代;頂層設計;全球健康高速公路

在研究中醫原創思維的過程中,借助于詮釋學(亦稱“解釋學”)研究中醫經典的思想方法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承認,“闡釋創新”逐漸成為促進中醫藥現代發展的另一種理論創新方式。在這種視域下,王冰對《黃帝內經素問》的整理和注釋獲得了新的意義,為中醫學的未來發展提供了關鍵性的思想和理論基礎。
大唐寶應元年,當王冰經過十二年的重新編次和精心校注之后,《黃帝內經素問》以新貌面世,流傳影響至今。在正文之前,王冰撰寫的《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序》可謂是全書的導讀。他認為,伏羲、神農、黃帝之書是“言大道”的“三墳”,具有“釋縛脫艱,全眞導氣,拯黎元於仁壽,濟贏劣以獲安”的現實功能。他自己“弱齡慕道,夙好養生”,認為《素問》是“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的“真經”,把它“式為龜鏡”。為了“昭彰圣旨,敷暢玄言”,他“精勤博訪”、“因而撰注”,“宣揚至理”,相信一旦“學者惟明,至道流行”,則“千載之后,方知大圣之慈惠無窮”[1]。
從寶應元年至今,一千多年過去了。在經過近代以來外來文化的強力沖擊之后,“三墳”典籍雖“授學猶存”,但已“散于末學”,其應用發展的黃金時代成為歷史記憶。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方知大圣之慈惠無窮”,《黃帝內經》重新受到廣泛關注。2011年,《黃帝內經》和《本草綱目》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昭示著其中蘊涵的獨特文化價值具有了新的時代意義,亟待“宣揚”。不過總的來看,眼下的重興之勢僅是開端,社會各界尚需要從理論上認識和把握這種情勢的深遠意義,而對《黃帝內經》的闡釋性研究有助于繼往開來,在“通古今之變”的基礎上理解中醫學的時代使命。我們看到,盡管世界衛生組織早已提出“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目標,健康也正在成為每個人的自覺追求和行動,但是在全球范圍內仍然缺乏理論明確、路徑清晰的健康計劃,而基于中醫學的思想理論能夠發展出普世性的健康服務新模式。當然,普及推廣這樣的新模式需要“健康時代”的建設和支撐。可以想象,一旦“健康時代”真正來臨的時候,《黃帝內經》將作為“健康圣經”受到全球性的尊崇,這也是本文的闡釋與研究所要達到的初步目標。
一、《黃帝內經》的時代性和永恒性
至今為止,學術界仍然對《黃帝內經》的作者身份問題沒有達成共識,其說有肇始于黃帝者,也有集成于漢代者,難有定論,尚待深析。在“兩重證據法”不足以解決問題的前提下,哲學詮釋學的建立為《黃帝內經》的當代研究提供了一條新路,即通過詮釋,使經典文本獲得了“學理上的真實”。事實上,王冰對《黃帝內經素問》的“重廣補注”即是應用詮釋方法的典范,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其所取得的新成就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王冰通過對《素問》的重新編次,恢復了原本存在的道家思想風貌。例如,在全元起注本中,《上古天真論》原在第九卷,但王冰使之“移冠篇首”后,原始道家思想與《黃帝內經》之間的天然聯系便凸顯出來。這種聯系的思想意義在于,應當進一步看到中醫思想與技術之間的相輔相成關系,即從道家思想的設定或“古之道術”的本來意義來看,技術的進步發展實際上是以思想境界的降低為前提和代價的,當代單純從技術的角度考察中醫則顯然有失偏頗。《老子三十八章》說:“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這種從“失”出發看待發展的標準不僅更能夠直指進步的本質,而且有利于復活中醫以“道”為本的自身標準,從而有助于認識和把握中醫的自身發展規律。與之相比,當代中國受社會進化論的影響,大部分人仍然相信技術進步能夠促進社會進化。實際上科學技術與社會道德分屬不同的領域,科技進步與社會的和諧穩定之間存在復雜的關系,不是單向促進那么簡單。從這層意義上說,《黃帝內經》的“道術”演變規律及其核心思想反而能夠對當代社會發展具有指導價值。我們看到,《黃帝內經》所記載的“道術”演變是由“精神內守”、“移精變氣”、“湯液醪醴”、“按摩導引”而至于“砭石灸刺”,“技術”的發展是一個從“無形”到“有形”的過程,其演變歷程伴隨著“道”之虧衰,而“技術”的發明及其作用則在于彌補“道”之缺損,其性質與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相同,具有整體論性質的“以術達道,道術合一”的鮮明特征,這也是中國傳統“道術”的基本特色。由上來看,我們分析中醫學術的思想內涵,就可看到古之“圣人”能夠見微知著,明了“道”的虧損原是由于“心”地不純,致使“心主神明”的功能受到損害。為了進一步鞏固作為“道基”的“心”,其首要的方法手段是通過教化使人免遭不良社會文化的影響,使之重新“合于道”。從學理上來分析,這種“心術合一”的風格是在對“道”之精神實在虛心體認的基礎上形成的,故而中醫學的文化性質不言而喻。以“心”攝“術”而歸本于“精神”與“道”的整體性,這既是中醫學的特色,也是它不同于科學的特點[2]。這種特點是以“道”的永恒性來駕馭主宰“術”的時代性,實現了“變”與“不變”的統一。相比之下,當代社會的最大缺失并不是技術,而恰恰是指導其可持續發展的永恒之道。因此,《黃帝內經》將對解決如何以倫理教化平衡科技發展,從而促進社會的平穩演化提供了關鍵性的啟示。
其次,王冰把“舊藏之卷”補入《素問》的做法雖然受到批評,如林億說:“是《素問》與《陰陽大論》兩書甚明,乃王氏并《陰陽大論》于《素問》中也。要之,《陰陽大論》亦古醫經,終非《素問》第七矣。”[1]但是王冰的出發點是“先師張公秘本,文字昭晰,義理環周,一以參詳,群疑冰釋。”也就是說,從學理的層面看,把七篇大論補入《素問》不僅沒有降低《素問》的價值,反而更加凸顯了《黃帝內經》的理論特色。《氣交變大論》曰:“善言天者,必應于人,善言古者,必驗于今,善言氣者,必彰于物,善言應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變者,通神明之理。”上述五個“善言”,可以說是中醫詮釋學的基本原則,王冰不僅在具體的注釋中反復提及,他在《序》中對原存“八卷”的評價也符合上述原則:“其文簡,其意博,其理奧,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陰陽之候列,變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謀而遐邇自同,勿約而幽明斯契,稽其言有徴,驗之事不忒。”更進一步說,“一以參詳”之“一”在理論上指的是“神明之理”,所謂“通其一,萬事畢”。從此出發,不僅能夠打開《黃帝內經》的理論之門,而且也能夠開啟通過中醫學詮釋儒釋道等中國傳統文化的新路徑,在重新昌明“三墳”“大道”的基礎上,開創具有時代精神的中國文化發展的新階段。
最后,通過詮釋,上述“學理上的真實”理事俱在,將其推而廣之,我們可以對上古文明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在《上古天真論》中,黃帝雖然是“生而神靈”的,但是他并沒有生活在“上古”時代,關于“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的說法也是他聽來的。按照現代的思維習慣和行為方式,凡是聽來的皆未必可靠和可信,但是黃帝顯然沒有表示出任何懷疑,并且非常向往,故而求教于“天師”如何才能做到,即重現“上古盛世”,實現文明的復興。因此從這層意義上說,《黃帝內經》既是“上古文明”的產物,又是實現文明復興的基礎,其中包涵著尚待重新認識和評價的基礎準則。在《列子·黃帝篇》中,黃帝曾經“晝寢而夢,游于華胥氏之國”,其所謂“游”,“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也就是說,在精神世界中,所謂常人看起來的“夢”也都是真實不虛的。事實上,在我們上面的討論中,“神明之理”既然“驗之事不忒”,那么此“事”就應當可從“小事”推而至于“大事”,甚至成為“大勢”。及至“大勢”已成,那么“文明”即興。用現代的眼光來看,“上古文明”實際上屬于一個“健康時代”,或者說屬于一個文化理想中的“健康時代”。在這個時代中,“百歲”之人隨處可見,人的平均壽命遠遠超出當代社會,因此又可以說,這個時代的社會就是“健康社會”。就目前的現實來說,“健康社會”似乎是當代人的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不過《黃帝內經》在“學理上的真實”又確實能夠使“夢想”變成“理想”,通過“信而奉行”的實踐,從而實現上古文明的復興。因此,在理論詮釋之后,行動詮釋或體驗參與性詮釋就必然成為研究上古文明的新方法。這樣一來,《黃帝內經》的教育和實踐將與儒釋道等中國傳統文化的“修身”傳統相得益彰,殊途同歸。
二、人的健康自覺是健康時代的基本特征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修身”、“修心”和“煉養”等關乎“形神俱妙”的學問淵源有自,并一直是以文化生活化的方式成為代代相傳的“傳統”。近年來,我國中醫藥管理部門大力提倡和推廣中醫藥的“治未病”,許多中醫藥適宜技術重新得到普及,雖然其在形式上不無技術化的傾向,但是用力用心之久之后,單純技術化的不足一定需要用文化的功用將其彌補和提升,而提升的路徑及其標準就是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覺”。本質上看,中醫學的“文化自覺”一定要落實到“健康自覺”上面,而這樣的轉化則意味著一個中國文化醫學時代的開創和來臨,故而這樣的醫學時代也可稱其為健康時代。可以想見,在健康時代里,中國文化的上述“傳統”皆能成為生活化的“時尚”,而在活態“時尚”的流行過程中,文明的復興和社會的新發展皆可逐步得以實現。
當然,從當今世界性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趨勢及其規律來看,“傳統”的“時尚化”以及“健康”的“中醫化”都是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更進一步說,在未來的社會發展中,中國傳統文化的創新將在健康需求的強大驅動下呈現出“中醫協同效應”。因此,從理論上洞察和把握這種“協同創新”的特征,勢必有助于促進當代社會的轉型發展。我國當代科學史家董光璧先生曾經提出過啟發性的“社會中軸轉換原理”,認為在人類社會中,可以設想道德、權勢、經濟、智力和情感是維系人類社會的5種抽象的基本力,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使其中的某一要素成為社會結構的中軸,也就是說,社會形態取決于社會的中軸結構。他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已經經歷了原始時代的道德社會、農業文明時代的權勢社會和工業文明時代的經濟社會。現在,當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正在走向科業文明時代的智力社會,或許今后將最終進入人類的理想社會——情感社會。他認為,“社會中軸轉換原理”是一個啟發性的原理,可以想象歷史的車輪在換軸,通過一個社會圍繞哪個基本力在轉,就可以基本判定我們處在什么樣的時代[3]。
通過上述啟發性的“社會中軸轉換原理”,我們看到眼下全球性的信息社會并不是社會發展的終點。按照董先生的設想,這僅僅是智力社會發展中的一個片段,雖然信息科技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行為方式,但是我們從喬布斯的遺憾和比爾·蓋茨的轉型中看到,在創新之道和財富之道的背后則是對健康之道的潛在需求。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健康的涵義是多方面的,其中也蘊涵著董先生所說“情感社會”的內在要求。而按照李澤厚先生的研究,“情本體”的中國哲學應該登場了,其核心思想即在于承認人之為人的“感應”的能力及其正當性。在文化傳統上,上述問題仍然是“天人相應”和“天人合一”所涉及的核心議題,并使人進一步認識到,在闡釋學的意義上,上述種種看起來殊不相關的領域和問題皆可轉義而能通,并共同指向意義豐富的“健康時代”。世界衛生組織曾經指出,要應對21世紀的挑戰,必須轉變醫學模式,實現從疾病醫學到健康醫學的轉型。當前,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都面臨著發展方式轉變的時代性問題,而且種種跡象表明,真正能夠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中軸”是對健康之道的“正解”和“正信”。在《黃帝內經》中,“知道者”本來就是“健康自覺”的人,他們提出了若干基本準則,如“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按照這些基本準則,就能夠實現“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的理想。同理,“上古圣人”也是“知道者”,其提出和實行的教育原則也是《黃帝內經》研究者耳所能詳的“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惔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同樣,“道者”、“真人”、“至人”和“賢人”的所作所為也成為那個時代的典范。總而言之,“健康自覺者”即“知道者”的普遍涌現和存在,成為上古社會“健康時代”的基本標志。
按照“道”的永恒性原理,我們亦能夠推定,未來的健康時代和健康社會建設同樣需要遵循“天人合一”的基本準則,而作為未來時代的基本特征,則必然是“知道者”的普遍存在,或人人皆成為“知道者”,也就是說,“健康自覺”成為每個人的基本追求。世界衛生組織曾經提出的“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戰略目標,按照中國文化的傳統,其所能夠實現的路徑必然是人人皆成為“知道者”,即只有通過健康自覺才能真正“享有”,外在的健康服務只能起到輔助性的功能。從《黃帝內經》的文本來看,中醫學當從“知道者”而來,后人能夠通過學習和實踐而成為新的“知道者”,所謂代有傳人,發揚光大。因此,在未來的健康時代里要成為“知道者”,促進健康自覺的實現,《黃帝內經》將是一部人人必讀的基本經典,并將由此而成為“健康圣經”,中醫學也將成為“健康醫學”。國醫大師陸廣莘先生在其晚年提倡發展“健康醫學”,并把中醫學的理論闡釋為“生生之道”,開啟了以中國文化闡釋中醫學的新路。雖然很多人仍然囿于科學思維,不能真正理解他一生學術思想的精華之所在,但是思想的光芒一旦透出,籠罩在中醫學之上的霧霾必將逐漸消散。從中可見,長期以來中醫現代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不是科學不科學的問題,而是中國文化的創新問題。以文化視域引領中醫發展,“健康自覺”才可能得到逐步落實。
三、健康時代中醫學發展的文化問題
中國自古就有“上醫治國,中醫治人,下醫治病”的文化傳統,“醫”的普遍性功能已經潛在地表現于中國歷史之中。但是在人們的認知上,中醫學只是以實用的方式存在,并沒有取得文化上的獨立性。進入21世紀之后,中國哲學界已經率先突破舊的哲學范疇,將中醫作為與儒釋道并立而存的獨立體系。如何將認識上的突破轉化為卓越的實踐能力,這將是中國文化的現代創新所要面臨的最基本課題。
在中國哲學界的影響之下,我國中醫藥界已經開始在思考中醫藥發展的文化問題,并成立了相應的文化建設與科普專家委員會。與以往單純地重視科普不同,該專家委員會卻是以文化建設引領和促進科普,凸顯了中醫藥區別于其他科學技術體系的獨特性。一般來說,人們往往從科學內涵上研究中醫藥的獨特性,其實從文化傳統上認識其獨特性,反而能夠順理成章。當然,在近現代西方文明的影響之下,人們多注重借用其科學、哲學等學術體系闡釋中醫的學理,并形成了主流性的當代中醫學術。但是,上述研究因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最終卻無法開顯中醫理論的自明性,而從中國文化自身的傳統來看,“修身”恰恰是達到“神明之境”的切實手段,并促進實現領會“天人合一”之妙用。面對新健康時代的到來,“修身”傳統將能夠充分彰顯中醫藥的獨特性,而這種獨特性的發揮也將成為引領傳統文化及其養生資源向現實轉換的關鍵。我們看到,盡管在歷史上曾經忽視了“醫”的潛質,在現代也沒有做好促進醫學廣泛傳播的哲學理論準備,但是學術界卻對“道”的普遍性和實在性進行了深入研究,而其理論成果能夠直接應用于中醫學。實際上,在上述有關《黃帝內經》的詮釋學研究中,“道”和“醫”的聯系性和互通性已經具備“學理上的真實”,進一步體認這種真實性,那么面向健康時代的新的“醫”“道”關系將能夠得到學理上的確認和建立,為開啟中國文化應用和發展的新視域奠定了源于歷史事實的基礎。
概括來說,這種新視域就是以醫為體,以道為用,通過中醫學的全面系統應用促進道學及其他中國文化體系的創新。在這種意義上,以往采取批判或回避的方式所觸及到的宗教、信仰等與精神生活相關聯的領域,也許其在健康時代恰恰是最需要直面的領域。我們看到,道教是全球宗教中最具養生特色的宗教,雖然在道教內部對各種養生方術有自己的評價方式,但是道教的方術體系在整體上都具有促進健康的作用。通過系統研究中醫學和道家關系的邏輯起點和原點,學術界發現中醫中蘊藏著道教發展的所有關鍵,而且從“道”的角度來看“醫”即“道”,從“醫”的角度來看“道”即“醫”,二者互為體用,難有分別。從此出發,我們應當承認,盡管《黃帝內經》被收入《道藏》,但是近現代的道教學術界并沒有特別看重它在道教中的價值和地位。事實上,《黃帝內經》對道教發展的貢獻可以與《道德經》相提并論,后世關于養生方術的道經,其理論往往從《黃帝內經》中來,或與《黃帝內經》相融通。因此可以說,應當重新確立《黃帝內經》在道教中的經典地位。確立其經典地位的意義還在于,當代道教發展將進入“健康道教”發展的新階段,從而開辟了新的“健康醫學”發展的新模式。
另一方面,在國家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過程中,《中華醫藏》的編纂工程也已經啟動,《黃帝內經》自然被中醫界認為是醫經和醫學之最重要的經典。但是遺憾的是,《道德經》并沒有被編入,這既反映出當今醫學視域的偏狹,也反映出長期以來對醫道關系的忽視。由此可見,通過系統疏理和深入研究,重現中國歷史上的醫道關系,應當成為面向新健康時代的重大課題。而從歷史上看,葛洪、陶弘景、孫思邈等道醫成為連接道教和醫學的最佳中介。一方面,人們用“十道九醫”來表述道士對醫術的精通,醫術成為道教為社會服務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人們又用“不懂醫不懂道”來總結醫理對養生修煉的重要性。可是當代社會特別是醫學界不僅沒有開啟修道作為中醫成才的基礎路徑,而且道醫也沒有合法行醫的政策基礎,這就使得道醫既被社會和醫學界邊緣化,也同時在道教界內部被邊緣化,由此大大削弱了道教和中醫服務當代社會的能力。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自然是評價標準的“非原創化”。作為“本土”的宗教和醫學,道教和中醫處處受到“現代”的質疑和排斥,致使其自主性的原創發展受到時代性制約。但是在健康時代,道教和中醫的原創潛力將得到充分發揮,其自主發展不僅不再會受到制約,而且其本身就是時代的鮮明標志。為了促進健康時代的到來,目前首當其沖的是應當重新認識和評價道教和中醫,使得二者共同突破舊時代加于其身的枷鎖,同時煥發新的生機。我們看到,“知道者”的健康自覺是健康時代的標志。從此出發,那么未來對醫學和醫生的評價標準就應當從一般的“科學”轉換為原創性的“道”。這種轉換將是一種整體性的文化和社會轉型,而如何促進這種轉型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重大課題。
2010年,作為哲學性的中醫原創思維研究得到國家基礎科學研究重大計劃的支持,這本身就是一個標志性的突破。在進入研究之初,有關專家和學者尚是非常關切中醫原創思維的“象思維”特征,注意到作為整體性的“象思維”與一般科學思維的不同之處。及至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一個意想不到的現象隱然出現,即研究原創思維的思維不是原創的,從而彰顯出具有時代特征的“悖論”。為了消解這個“悖論”,必須把“中醫原創思維”從一個單純的科學哲學問題還原為歷史文化命題,而且如果再一味構建其作為科學思維的體系與邏輯,那么就有可能離研究初衷越來越遠。在這種情勢下,應當而且必須放棄從“科學”進入的既定路徑,轉而尋找與中醫原創思維能夠相應的新路徑。可以說,這個新路徑就是“人文思維”。北京大學的樓宇烈教授曾經論述過“人文思維”與“科學思維”的不同,認為二者之間的最大區別是出發點不一樣:“人文的思維方式跟科學的思維方式有很大不同,它們從出發點上就不一樣。科學思維是從靜態出發的,或者是從具體的物出發的,而中國的人文思維,則是從人出發的,或者是從人事出發的,是動態的。”[4]如同“飛矢不動”的悖論一樣,發生在中醫身上的“原創悖論”也是以靜止的“科學思維”看待和規范動態的“人文思維”的結果。學理雖然清楚,但是根本的問題卻在于為什么這樣的思維方式一直被認為是正確的,以至于絕大多數研究者已經被養成只習慣于科學思維,而對人文思維則無比陌生,甚至斥之為謬。從此來看,對中醫原創思維的研究需要從一般的專業領域向更深更廣的歷史文化領域拓展,而其核心命題則是時代的轉型問題。因此,如果以“科學”的態度闡釋中醫原創思維的“科學意義”,答案可能是建設性的“否定”,即不能一味堅持靜止的科學思維,動態的人文思維不僅能夠使中醫變得更美好,而且能夠促進整體性的文化和社會轉型,并一起走進新的“健康時代”。
四、全球化時代下的健康之道及其頂層設計
有關人文思維的研究是一個關乎未來發展的大課題,尚需系統性的深入開展,但對頂層設計來說,這是一項涉及到發展方向的基礎性課題。實際上,要做好頂層設計并非易事,其中存在“權力失靈”的關鍵機制,若要保障其有效性,其中的關鍵就是要保持人文思維對科學思維的主導性。我們看到,在由政府主導制定的有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中,人文思維的影響并不明顯。在有關中醫藥的發展規劃中,科學思維甚至主導和抑制了人文思維,從而導致“原創悖論”多領域、多層次、多方位的反復出現。可以形象地說,“原創悖論”的出現是“西學東漸”的結果,而要消除“原創悖論”,應當以“東學西漸”為目標,反其道而行之。
近代以來,中國被迫參與由西方文明發起和推動的全球化進程,中國社會亦發生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今,全球化進程中的新動向表明,中華文明迎來了主動推動全球化的重大歷史機遇,而其基礎性平臺就是健康的全球化發展。我們看到,要實現健康的全球化,必須在全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新規則中融入“健康之道”,以促進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這也是健康時代的內在要求。從歷史來看,中華文明長于“健康之道”,發揮這種特長和優勢,也是中華民族面向未來向全球貢獻和負責任的最佳方式。為此,中國政府和社會應當轉變既往的思維方式,以人文思維為依托,做好面向未來的以原創為基礎的頂層設計。
與美國政府提出的戰略性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相比,我國政府應當從頂層設計的高度提出“全球健康高速公路計劃”,這是從中醫學的思想理論出發,面向健康時代的關鍵選擇和決策。盡管該計劃的具體制定和實施尚需時日,但其核心思想及其理論方法一應俱在,應當基于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凝聚共識,盡快啟動。當然,凝聚共識也是一個歷史文化進程,也正因為有此進程,中醫學思想的原創潛力才能充分顯現。也可以這樣說,中醫學的思想、理論和方法已經包含有“全球健康高速公路”的雛形,通過闡釋創新,古為今用,人們大致能夠在如下幾個方面達成基礎性的共識:
1.健康是人類的永恒和終極性追求,但只有按照整體與生成的方式才能最終實現。這種方式的本質是健康自覺,而只有“知道者”才能實現健康自覺。近代以來科學方法所擅長的還原論方式存在“原創悖論”,不能夠直接通達整體,因此難以解決健康的“最后一公里”問題。如果能夠因勢利導,“轉識成智”,在人文思維的主導下,科學也能夠成為促進健康的有效方式。
2.人人皆具有自我實現健康的天然潛力,此即“何期自性,本自具足”理論在健康領域的基礎性闡釋,這一理論也是建設健康高速公路的前提和基礎。對這個理論的認知需要個體的學習和實踐參證,通過社會化和工程化的方式將其曉之天下,人人共享,做到“不疾而速”,實即“高速”。《易傳》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全球健康高速公路計劃”之所以能夠反其道而行之,端的在于“學以為己”、“內定而外附”的中國教育的基本原則。
3.相比較而言,以中醫學為代表的傳統醫學直接從個性化出發,以人為中心建立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這種體系鼓勵人的自主和自由發展,因此注重和擅長于充分發揮人本來的原創潛力。只有人自身天然潛力的發揮,才能引領和促進世界范圍內傳統醫學原創潛力的發揮,傳統醫學的現代化和中醫藥的全球化皆是這一潛力發揮的自然成果。如果離開了這個基礎而走入他途,雖看似捷徑,但實為彎路和歧路,所謂“欲速則不達”。
4.當代世界的醫學模式需要根本性轉變,但其轉型過程極其漫長。對我國來說,上述轉型則是回歸,而回歸的關鍵是以人文思維為主導。因此,全球健康高速公路計劃應當自始至終貫徹人文原則,在利用全球科技、醫療和文化資源,著力研究新醫學模式的示范性、可復制性、可及性和可負擔性的進程中,提倡本土文化,注重包容并蓄,使多樣性成為促進醫學模式轉變的基本原則。中國的歷史文化本即“多元一體”,將之服務于健康時代,必將促進中國文化的自主創新。
綜合來看,從《黃帝內經》到“全球健康高速公路計劃”,其路并不遙遠,關鍵在于是否能夠領會闡釋創新的“心心相印”。可以預見,健康時代的“健康自覺者”能夠克服語言障礙,將以中醫為引領的中國文化的新教化惠及于天下。
參考文獻:
[1]黃帝內經素問[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
[2]張超中.《黃帝內經》的原創之思[M].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3.
[3]董光璧.傳統與后現代——科學與中國文化[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
[4]樓宇烈.中國的品格:樓宇烈講中國文化[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
(本文責編:王延芳)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Era and Its Top-Level Design
ZHANG Chao-zhong
(InstituteofScientificandTechnicalInformationofChina,Beijing100038,China)
Abstract:From the viewpoint of Hermeneutik, Wangbing had done a paradigm work on Huangdi Ningjing Suwen by reediting and annotating, and left us a key enlightenment on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in originate form. It tells us that the ancient society had its cultural idea about health times, and the idea is just the historical resour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uture health times in which the Tao-knower is the key factor. Furthermore,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TCM emphasize on that health principle has its unique character of holism and self-sufficient, and can be used to give birth to the Global Health Highway Project. As long as the Project having its top-design and being carried out in future, both TCM and Chinese culture will have their new development.
Key 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Huangdi Ningjing; health times; top-design; Global Health Highway
中圖分類號:R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9753(2015)07-0052-07
作者簡介:張超中(1965-),男,河南柘城人,哲學博士,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研究員,碩士生導師,(全國)老子道學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研究方向:中醫藥發展戰略、中醫哲學、道家與道教文化。
基金項目:本文由國家重點基礎科學研究計劃(973計劃)項目《中醫原創思維與健康狀態辨識方法體系研究》(編號:2011CB505400)資助。
收稿日期:2015-01-06修回日期:2015-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