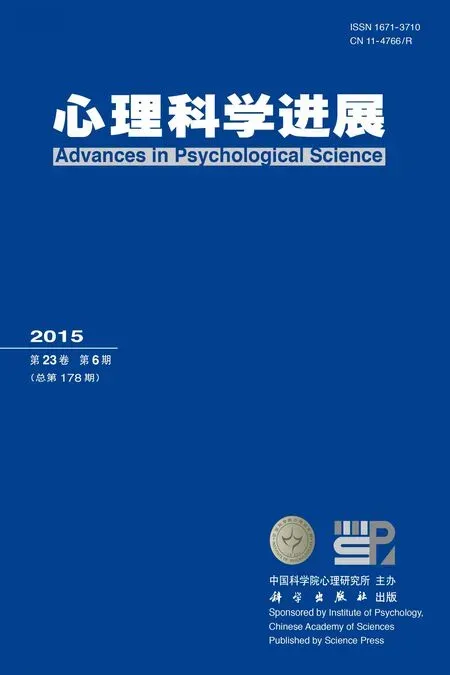倫理型領導對員工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機制:多層次視角*
張永軍 趙國祥
(1河南大學教育科學學院;2河南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開封 475004)
1 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隨著安然、三鹿奶粉等國內外公司丑聞的頻繁爆發,組織中非倫理行為成為大眾傳媒報道和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之一。人們在斥責這些公司無視他人利益、挑戰人類道德底線的同時,也在思考為何非倫理行為在有些組織中能夠大行其道,而在其他組織中卻無處藏身。在這一過程中,大家逐漸認識到領導的道德特質與倫理行為可能對員工的(非)倫理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并由此產生了一種新的領導行為——倫理型領導(Ethical Leadership;莫申江,王重鳴,2010)。
中國有句古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意思是說若領導道德低下,是非倫理型領導,下屬就會跟著學壞。那么,是不是可以說若領導道德高尚,是倫理型領導,下屬就會跟著學好,從而減少自己的反生產行為(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呢?(上梁正下梁就不歪?)文獻回顧發現,以往有關倫理型領導與員工反生產行為關系的研究并不多見(Deter,Trevino,Burris,&Andiappan,2007;Mayer,Kuenzi,Greenbaum,Bardes,&Salvador,2009),而由于缺乏從多層次視角揭示倫理型領導的作用機制(莫申江,王重鳴,2010;Brown&Mitchell,2010;蘆青,宋繼文,夏長虹,2011;洪雁,王端旭,2011),導致我們很難對上述問題做出回答。事實上,組織中倫理型領導根據層級高低可以分為高層倫理型領導(executive/top management ethical leadership)和基層倫理型領導(supervisory ethical leadership)(Brown,Trevino,&Harrison,2005)。由于所處的位置、關注的事物以及與員工互動的頻率不同,高層倫理型領導和基層倫理型領導對員工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機制可能存在一定的差異(Brown&Trevino,2006)。然而,以往僅有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基層倫理型領導層面(Mayer,Kuenzi,&Greenbaum,2011;張永軍,2012),很少有研究從多層次視角系統探討高層倫理型領導是如何對員工反生產行為產生影響的,以及高層倫理型領導和基層倫理型領導在影響員工反生產行為過程中的關系等問題。也正因為如此,現有研究不僅難以厘清倫理型領導與員工反生產行為的關系,也無法全面揭示倫理型領導的效能。
中國自古以來就強調領導的道德特質和倫理行為。然而,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不僅對人們的權力距離等觀念產生較大沖擊(廖建橋,趙君,張永軍,2010),還導致人們的倫理意識、道德素質產生了極為嚴重的下滑。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注重倫理道德,也不再對正人君子、道德楷模如此頂禮膜拜。那么,在當前社會轉型大背景下,倫理型領導還能否對員工產生影響?如果能,這其中的作用機制又是什么呢?鑒于上述理論現狀和社會現實,本研究擬對“倫理型領導對員工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機制:多層次視角”這個主題進行深入探討,重點解決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高層倫理型領導是如何對群體反生產行為產生影響的?哪些因素會產生調節作用?本項研究著重探討倫理文化在高層倫理型領導與群體反生產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以及不同組織結構對兩者關系的調節效應。倫理文化(ethical culture)是指影響和控制員工(非)倫理行為的行為規范(Trevino&Youngblood,1990)。研究發現,高層倫理型領導對構建和維系組織的倫理文化至關重要(Trevino,Weaver,&Reynolds,2006),而倫理文化往往決定著反生產行為是否會以群體形式爆發(Robinson&O’Leary-Kelly,1998)。因此, 高層倫理型領導可能是通過營造積極的倫理文化進而對群體反生產行為產生影響的。組織結構主要指機械式組織和有機式組織。由于倫理型領導在規則模糊、管理層級較少的組織中更能發揮作用(Brown&Trevino,2006),而機械式組織和有機式組織在規則、制度等方面存在較大不同。因此,在不同的組織中高層倫理型領導對群體反生產行為的影響可能不同。
第二,高層倫理型領導影響員工反生產行為是否具有“瀑布效應”(cascading effect)?哪些因素可以產生調節作用?本項研究主要檢驗高層倫理型領導影響員工反生產行為的“瀑布效應”在中國是否成立,以及權力距離導向的調節作用。領導力“瀑布效應”是指高層領導的影響通過其他較低層級領導,由上至下、層層傳遞,并最終對員工產生作用(Bass,1990)。雖然以往研究已經證實倫理型領導的影響具有“瀑布效應”(Brown et al.,2005),但這些研究均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進行的,缺乏中國情境下的檢驗。權力距離導向(power distance orientation)是權力距離在個體層面上的體現,指個體對上下級權力差異的看法或價值觀念(Dorfman&Howell,1988)。由于“瀑布效應”可視為一個社會學習過程,而不同權力距離導向個體對領導權力的接受和認同不同,這可能會影響其學習領導的意愿。因此,在中國高層倫理型領導影響員工反生產行為的“瀑布效應”是否成立,這一過程是否會受個體權力距離導向的影響值得進一步檢驗。
第三,基層倫理型領導是如何對員工反生產行為產生影響的?兩者關系的邊界條件有哪些?本項研究主要檢驗領導信任和領導認同在基層倫理型領導與員工反生產行為之間的中介作用,以及傳統性和道德同一性對上述關系的調節效應。領導信任的中介作用主要在于探討倫理型領導與員工之間是否存在社會交換關系,領導認同的中介作用在于探討員工是否根據倫理型領導進行自我定義。傳統性(traditionality)是指個體遵守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程度,主要表現為遵從權威、敬祖孝親、安分守成等(Farh,Earley,&Lin,1997)。道德同一性(moral identity)是指個體圍繞一系列道德特質進行的自我概化(Aquino&Reed,2002)。由于不同傳統性個體對“上尊下卑”、服從領導的觀念不同,不同道德同一性維度對外界信息的接受和處理方式也不盡相同(Skarlicki,Van Jaarsveld,&Walker,2008),這都可能進一步影響員工對倫理型領導的接受,進而表現出不同水平的領導信任和領導認同。
總之,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和檢驗不僅在理論上可以多層面、多角度、立體化地展現倫理型領導對員工反生產行為的影響,進一步打開倫理型領導影響效能的“黑箱”,從而豐富和發展倫理型領導與反生產行為的理論體系;在實踐方面對指導組織如何加強倫理型領導的選拔和培養、倫理型領導自身如何開展工作,以及在中國各級倫理型領導如何發揮影響力也有一定的管理啟示。
2 國內外研究現狀
2.1 倫理型領導的相關研究
2.1.1 倫理型領導的概念內涵與結構維度
雖然大家對領導的倫理和道德特質探討由來已久,但倫理型領導概念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被真正提出來。Enderle(1987)認為倫理型領導是一種思維方式,旨在明確描述管理決策中的倫理問題,并對決策過程所參照的倫理原則加以規范。Trevino,Hartman和Brown(2000)認為倫理型領導不僅是具有正直、公平、言行一致等個體特征的合乎倫理的人,也是經常與下級溝通、設定明確倫理準則,并利用獎罰來監督下級對這些標準遵守情況的合乎倫理的管理者;管理者所樹立的倫理榜樣對直接下屬產生影響,而高層倫理型領導對組織的整體倫理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基于社會學習理論,Brown等人(2005)提出了一個比較系統的倫理型領導概念。他們認為倫理型領導是指領導者通過個體行為與人際關系,向員工表明什么是規范的、恰當的行為,并通過雙向溝通和強制等方式促使他們遵照執行。研究發現,倫理型領導與變革型領導、真實型領導等存在許多類似或重疊之處,但倫理型領導更加強調倫理準則和道德管理(Brown&Trevino,2006)。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倫理型領導同時具備變革型領導和交易型領導的部分特征(Trevino,Brown,&Hartman,2003)。
學者們分別對高層倫理型領導和基層倫理型領導的結構維度進行了研究。Trevino等人(2003)通過對美國多家大中型企業的20位高管及20位倫理專員進行半結構化訪談發現,高層倫理型領導包括堅持以人為本、采取倫理行動、設置倫理標準、拓展倫理意識和執行倫理決策五個維度。Khuntia和Suar(2004)通過對印度兩家私營和兩家公有制企業的340位中層管理者研究發現,授權(empowerment)、動機和性格(motive and character)是高層倫理型領導的兩個主要維度。De Hoogh和Den Hartog(2008)在新西蘭通過對73家中小型企業的73位CEO研究發現,高層倫理型領導包括道德與公平、角色澄清和權力分享三個維度。Brown等人(2005)研究發現基層倫理型領導是單維結構,并開發了一個包含10個條目的測量工具。Resick,Hanges,Dickson和Mitchelson(2006)通過對62個國家和地區的跨文化樣本研究發現,誠信、利他主義、集體動機和激勵是構成倫理型領導的四個維度,這一結論被后續的研究再次證實(Martin,Resick,Keating,&Dickson,2009)。Kalshoven,Den Hartog和 De Hoogh(2011)對荷蘭的樣本研究發現,倫理型領導是包含公平、誠信、倫理指導、人際導向、權力分享、角色澄清和關心可持續性的七維結構,并開發了相應的測量工具。Eisenbeiss(2012)通過綜合中西方道德哲學和世界宗教的倫理法則,認為倫理型領導應該包括人道導向(humane orientation)、公正導向(justice orientation)、責任和可持續導向(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rientation)和節制導向(moderation orientation)四個維度。
文獻回顧發現,雖然學者們認為高層和基層倫理型領導的結構維度不同,但在探討多層次倫理型領導影響效能時基本上都采用Brown等人(2005)所開發的單維結構(Mayer et al.,2009;Ruiz,Ruiz,&Martinez,2011)。對此,Brown和Trevino(2006)分析認為無論是高層倫理型領導還是基層倫理型領導,都包含“合乎倫理的人”和“合乎倫理的管理者”這兩個核心元素,可以用相同的方法進行測量。
2.1.2 不同層次倫理型領導的影響后果
現有研究對高層倫理型領導影響后果探討的不多,且主要集中在“瀑布效應”方面。比如,De Hoogh和Den Hartog(2008)研究發現高層倫理型領導有助于提升組織高管團隊效能(整體合作水平和決策效能),并促使員工對組織的未來發展形成積極樂觀的態度。Mayer等人(2009)對倫理型領導影響的“瀑布效應”進行了檢驗,結果發現高層倫理型領導可以對群體反生產行為、群體組織公民行為產生影響,中層倫理型領導具有完全中介作用。Ruiz等人(2011)也證實了倫理型領導的影響具有“瀑布效應”,并發現高層倫理型領導對員工的組織承諾、離職意愿和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比基層倫理型領導更明顯。Schaubroeck等人(2012)對部隊中倫理型領導、倫理文化和軍人的倫理和非倫理行為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層級(連、排、班)的倫理型領導和倫理文化對軍人的倫理和非倫理行為呈現出一定嵌套影響效果。
對基層倫理型領導的研究可以分為團隊和個體兩個層面,影響結果主要包括員工的工作態度、行為和績效等。團隊層面的研究相對較少。Brown等人(2005)研究發現倫理型領導能夠強化自身的關懷行為、互動公平和領導誠信,并在團隊層面對員工的效能感、滿意度、額外工作努力和主動報告問題等產生積極影響。Walumbwa和Schaubroeck(2009)發現倫理型領導能夠通過團隊心理安全對員工建言行為產生積極影響。Walumbwa,Morrison和Christensen(2012)研究發現倫理型領導通過群體責任心和群體建言對群體的角色內績效產生積極影響。
在個體層面,Den Hartog和De Hoogh(2009)研究實證倫理型領導的誠實、公正和授權行為能積極影響員工對管理者、同事的信任和對組織的情感承諾、規范承諾,而對持續承諾產生消極影響。Piccolo,Greenbaum,Den Hartog和Folger(2010)發現倫理型領導通過工作特征模型中的任務重要性和工作自主性進而對員工的努力產生積極影響,并最終增加員工的任務績效和組織公民行為。Mayer等人(2011)發現倫理型領導通過倫理氛圍對員工的反社會行為產生負面影響。Avey,Palanski和Walumbwa(2011)發現倫理型領導與員工自尊心對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存在交互影響,即當領導是倫理型領導,員工又是高自尊心個體時,員工表出現的組織公民行為更多、反生產行為更少。Walumbwa等(2011)研究發現倫理型領導對員工的任務績效具有積極影響,領導成員交換關系、自我效能感和組織認同分別在兩者關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Kacmar,Bachrach,Harris和Zivnuska(2011)發現組織政治知覺和性別可以調節倫理型領導與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關系,在低組織政治知覺條件下,倫理型領導對女性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正向影響更強烈,而在高組織政治知覺條件下,倫理型領導對男性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正向影響更強烈。蘆青等人(2011)從社會交換視角發現倫理型領導部分通過領導成員交換關系對員工的任務績效、組織公民行為、工作滿意度、組織承諾產生正向影響,組織公平對倫理型領導與員工組織公民行為、工作滿意度和組織承諾的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張永軍(2012)從社會學習和社會交換雙重視角研究發現,領導公平、程序公平在倫理型領導與員工反生產行為關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應。Avey,Wernsing和Palanski(2012)發現倫理型領導通過建言與員工的心理幸福感正相關,通過心理所有權與工作滿意度正相關。
2.2 反生產行為的相關研究
2.2.1 反生產行為的概念內涵與結構維度
反生產行為指員工故意實施的傷害組織和/或組織利益相關者的行為,其中利益相關者包括投資者、顧客和員工等(Spector&Fox,2005)。反生產行為具有三個典型特征:第一,這些行為是有意的,并非偶然的;第二,這些行為違反了組織重要的管理規則;第三,這些行為是有害的,有的指向組織,有的指向員工(張永軍,廖建橋,趙君,2012)。與反生產行為類似的概念很多,包括攻擊行為、反社會行為、組織偏差行為以及報復行為等。Spector和Fox(2005)指出雖然這些概念提出的視角不同,但在測量內容以及所反映的行為本質上具有很大的重疊之處。隨著研究的深入,反生產行為逐漸成為學者們研究員工消極行為所普遍采用的概念之一。
反生產行為包括單維、二維、三維、四維、五維和六維等眾多維度模型(張永軍等,2012)。其中,Bennett和Robinson(2000)根據行為指向所提出的組織指向反生產行為和人際指向反生產行為二維模型最受學者們認可。實證研究中,自我報告法、他人報告法、試驗法、客觀數據法是反生產行為常用的測量方法,但都存在明顯的優缺點。相對而言,采用問卷要求被試報告自己在一定時間內所實施的反生產行為次數是目前最常用、最有效的方法。在中國,也有一些學者指出可以采用投射法要求被試回答身邊同事反生產行為的情況來間接反映焦點個體的反生產行為,實證結果表明測試效果更好(張永軍,2012;張燕,陳維政,2012)。
2.2.2 反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
反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分為個體因素和情境因素兩大類(張永軍等,2012)。個體因素主要包括大五模型、消極情感特質、誠實性、自尊、控制點、自我控制以及馬基雅維利主義等。研究發現,大五模型中的責任心、宜人性和情緒穩定性,以及誠實性和自我控制與反生產行為負相關,消極情感特質、馬基雅維利主義與反生產行為正相關。自尊與反生產行為負相關,兩者關系受自尊類型的正向調節作用;相對于內控制點個體,外控制點個體更容易實施反生產行為。情境因素主要包括工作壓力、組織因素、領導因素和員工認知因素四大類。工作壓力通過負面情緒進而對反生產行為產生積極影響得到很多研究的證實。組織因素主要包括反生產行為的懲罰措施、組織的倫理氛圍(文化)以及績效考核和薪酬制度等。研究發現,組織對反生產行為的懲罰越嚴厲,員工實施反生產行為的可能性越低;不良的倫理氛圍(文化)可以對反生產行為產生刺激作用;不合理的考核指標、結果導向的考核體系、消極的績效反饋以及個體薪酬、傭金制都可能對反生產行為產生積極的影響。領導因素主要包括領導的辱虐管理和倫理型領導,其中辱虐管理被證實與員工反生產行為呈正相關關系。員工認知因素主要包括工作滿意度、組織公平感、組織承諾、信任、組織支持感以及心理契約破裂等。研究發現工作滿意度、情感承諾、組織公平感、信任、組織支持感與反生產行為負相關,心理契約破裂與反生產行為正相關。
2.3 現有研究述評
通過總結以往研究可以發現,雖然學者們分別對倫理型領導和反生產行為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討,但將兩者聯系起來,并從多層次視角系統探討倫理型領導對員工反生產行為影響機制的研究依然比較匱乏。具體而言,我們認為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第一,高層倫理型領導對群體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機制。研究發現,反生產行為可以通過傳染和擴散,最終以群體形式出現(Robinson&O’Leary-Kelly,1998),而這往往和組織的文化氛圍以及高層領導的言行舉止有很大關系(Trevino et al.,2006)。在組織中,高層倫理型領導對構建、推廣和維系組織的文化氛圍具有決定性作用;同時,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高層倫理型領導的一言一行不僅影響范圍廣,而且示范作用大,因此更容易對群體行為產生影響(Mayer et al.,2009)。那么,高層倫理型領導究竟是通過什么機制對群體反生產行為產生影響呢?又存在哪些邊界條件呢?以往研究缺乏對上述問題的探討。
第二,高層倫理型領導影響員工反生產行為的“瀑布效應”。高層倫理型領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與員工的社會距離較遠,缺乏高頻率的社會互動,高層倫理型領導是如何對一般員工產生影響的并不清楚(Brown&Trevino,2006)。近年來,有少數研究發現倫理型領導的影響具有“瀑布效應”,即高層倫理型領導可以通過基層倫理型領導由上至下、層層傳遞,并最終對員工反生產行為(非倫理行為)產生影響(Mayer et al.,2009;Schaubroeck et al.,2012)。然而,這些研究均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進行的,個別研究樣本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軍人)。因此,中國文化背景下高層倫理型領導影響員工反生產行為的“瀑布效應”是否成立,有哪些邊界條件,仍需進一步檢驗。
第三,基層倫理型領導對個體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機制。基層倫理型領導與員工社會距離較近、社會互動頻率較高,因此對員工的影響更明顯、更直接。然而,以往研究更多采用社會學習理論來解釋倫理型領導的作用機制,缺乏從社會交換等其他理論視角進行的分析(Brown&Trevino,2006)。那么,如何運用社會交換理論來解釋基層倫理型領導對員工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機制?是否還存在其他理論可以解釋兩者之間的影響關系?這其中又有哪些中國文化元素可以發揮作用?以往研究也很少探討這些問題。
3 研究構想
本研究主要包括三個內容:第一,高層倫理型領導對群體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機制研究;第二,高層倫理型領導影響員工反生產行為的“瀑布效應”;第三,基層倫理型領導對員工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機制研究。在本項研究中,基層倫理型領導是指員工的直線領導(部門主管),高層倫理型領導包括兩類人員,一類是組織的最高負責人(CEO),另一類是高管團隊。群體反生產行為是指部門或群體內所有員工表現出來的反生產行為,員工反生產行為是指員工個體所實施的反生產行為(Mayer et al.,2009)。
3.1 研究1:高層倫理型領導對群體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機制研究
(1)倫理文化的中介作用。反生產行為通過傳染、擴散,最終以群體形式爆發,而這一過程與組織的倫理文化有很大關系(Trevino et al.,2006)。倫理文化是組織文化的一部分,指通過相互影響能推動倫理/非倫理行為的各類組織“正式”和“非正式”行為控制系統(Trevino&Youngblood,1990)。根據社會學習理論,在強倫理文化的組織中,員工有清晰的倫理準則可以遵循,知道如何改變和調整行為以符合組織的預期,從而會減少自己的反生產行為;同時,強倫理文化會促使員工彼此間相互學習和觀察,引導成員行為趨于一致,并最終減少群體反生產行為的出現(Trevino et al.,2006)。研究發現,高層倫理型領導對塑造、推廣和維系組織的倫理文化至關重要。通過講述員工積極行為是如何被獎勵的和/或以往員工消極行為是如何被懲罰的故事,高層倫理型領導可以構建強烈的倫理文化(Schein,2010)。“基調在高層”(tone at the top)學派就指出高層倫理型領導可以傳遞組織的倫理價值觀并激發員工遵守(Grojean,Resick,Dickson,&Smith,2004),從而對員工行為產生影響。Schaubroeck等人(2012)也證實倫理型領導(軍官)與部隊的倫理文化正相關,并通過倫理文化對軍人的倫理和非倫理行為產生影響。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由于高層倫理型領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其言行舉止可以營造和強化積極的倫理文化,進而對群體反生產行為產生影響,也即倫理文化在高層倫理型領導與群體反生產行為之間具有中介效應。
(2)組織結構的調節作用。組織結構包括機械式組織和有機式組織(Burns&Stalker,1961)。機械式組織具有正式的職權層級鏈,管理幅度較窄,組織中的規則、標準較多,決策權高度集中;有機式組織管理層級較少,管理幅度較大,各種標準、規定不多,充滿更多的模糊和變化。由于是通過角色典范和人際互動產生影響,因此,倫理型領導在不明確、操作準則不具體的情景中更能發揮作用(Brown&Trevino,2006)。在機械式組織中,由于各種規則、標準非常清楚,高層倫理型領導與員工的社會距離比較遠,溝通、互動的機會少,其角色典范的影響力可能會受到干擾。在有機式組織中,由于存在更多的模糊和變化,員工更在意高層領導的一言一行;同時,高層倫理型領導與員工的層級距離相對較近,溝通、互動的機會也相對較多,因此其角色典范的影響力可能會更強烈(Mayer et al.,2009)。綜上所述,高層倫理型領導對群體反生產行為的影響可能會受到組織結構的調節作用。
我們將采用訪談法、內容分析法和問卷調查法研究上述問題。訪談法和內容分析法主要用于檢驗CEO倫理型領導對群體反生產行為的影響。首先擬選取30名左右的企業CEO,對他們進行個人價值觀、領導行為、倫理文化和員工負面行為深度訪談,然后采用內容分析法對訪談內容進行整理、分析。問卷調查法主要用于檢驗高管團隊倫理型領導對群體反生產行為的影響。首先采集群體中的員工對高層倫理型領導和組織結構的評價數據;3個月以后,采集群體中員工對組織倫理文化的評價數據;再過3個月,采集群體的直線主管對群體反生產行為的評價數據。數據處理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和跨層分析技術(HLM)。
3.2 研究2:高層倫理型領導影響員工反生產行為的“瀑布效應”
(1)“瀑布效應”的直接檢驗。Bass(1990)最早提出領導的影響具有“瀑布效應”,即高層領導者的角色典范可以在組織中由上至下、層層傳遞,并最終對員工產生影響。基于社會學習理論,Brown等人(2005)認為下屬通過模仿和觀察學習,會表現出與他們領導一樣的行為方式,倫理型領導的影響也應該具有“瀑布效應”。Mayer等人(2009)指出追隨者效仿管理者的倫理行為是倫理型領導構念成立的前提條件。在組織中,比高層管理者層次較低的管理者應該對高層管理者負責,他們通過學習和模仿高層管理者,可以促使高層管理者的倫理行為流向基層。基于此,他們首次對倫理型領導的“瀑布效應”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高層倫理型領導可以對群體反生產行為和組織公民行為產生影響,中層倫理型領導具有完全中介作用。Ruiz等人(2011)發現高層倫理型領導可以通過基層倫理型領導對員工的工作滿意度、情感承諾、組織公民行為和離職意愿產生影響。Schaubroeck等人(2012)也以軍人為樣本檢驗了倫理型領導的“瀑布效應”,結果發現高層倫理型領導(連隊)會通過較低層級的倫理型領導(排、班)逐層向下并最終對軍人的倫理和非倫理行為產生影響。這就說明,雖然高層倫理型領導對組織非常重要,但由于與一般員工的社會距離較遠,社會互動機會較少,他們要想對一般員工產生影響,處于中間層級的基層倫理型領導需要承擔非常重要的傳遞作用(莫申江,王重鳴,2010)。如果基層倫理型領導缺乏道德素質,不效仿高層倫理型領導,那么高層倫理型領導的影響很可能成為“空中樓閣”。在中國,2000多年的儒家文化也倡導“由己及人、自上而下”的道德影響過程(蘆青等,2011)。比如,在政治領域,全國對模范人物的學習是由中央到省、市、縣,再到基層的這樣一個過程;在學校,高層領導的道德意識和倫理行為也需要通過院系、職能部門層層學習、逐層傳遞,最終流向一般老師和學生。因此,我們分析認為在中國文化背景下,高層倫理型領導對員工個體反生產行為的影響也應該具有“瀑布效應”。
(2)權力距離導向的調節作用。高層倫理型領導影響員工反生產行為的“瀑布效應”在本質上是一個社會學習過程,因此,下屬愿不愿意學習上級領導的行為方式與其認可、接受上級領導的權威程度有關,也即個體的權力距離導向可能會對倫理型領導的效能產生影響(Loi,Lam,&Chan,2012)。權力距離導向是指組織中個體對上下級權力差異的看法或價值觀念(Dorfman&Howell,1988)。研究發現,權力距離導向會影響個體的角色定位和溝通方式的選擇(Brockner et al.,2001)。高權力距離導向個體不僅認同權力在自身與領導之間的不平等分配,愿意維持自己在權力關系中的從屬地位,還傾向于隱藏自己的觀點而傾聽上級的指導和安排,努力與領導的言行保持一致(Botero&Van Dyne,2009)。Kirkman,Chen,Farh,Chen和Lowe(2009)也證實權力距離導向可以負向調節變革型領導與程序公平感的關系,并最終對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產生積極影響。中國一直被視為高權力距離的國家(Hofstede,1984),這就意味領導的言行舉止對下屬影響很大。然而,改革開放30年,隨著教育水平、信息技術等各方面的發展,人們的權力距離觀念已呈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廖建橋等,2010),這可能會影響下屬對倫理型領導的學習和效仿。相對而言,高權力距離導向的部門主管會更愿意學習和效仿高層倫理型領導,更可能成為基層倫理型領導;高權力距離導向的員工也會積極學習和效仿基層倫理型領導,減少自己反生產行為的可能性也更大。因此,我們分析認為,個體的權力距離導向(包括部門主管和一般員工)會對高層倫理型領導影響員工反生產行為的“瀑布效應”產生調節作用。
為了檢驗倫理型領導影響反生產行為的“瀑布效應”,我們采用問卷調查法首先采集員工對高層倫理型領導(高管團隊)的評價數據;3個月以后,采集員工對基層倫理型領導和部門主管對自己權力距離導向的評價數據;再過3個月,采集部門主管對員工反生產行為和員工對自己權力距離導向的評價數據。數據處理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和跨層分析技術(HLM)。
3.3 研究3:基層倫理型領導對員工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機制研究
(1)領導信任和領導認同的中介作用。本研究認為基層倫理型領導可以通過領導信任和領導認同兩種不同的中介機制對員工反生產行為產生影響。其中,領導信任可以用社會交換理論來解釋,而領導認同可以用社會認同理論來解釋。領導信任(trust in leadership)是一種垂直信任,在本項研究中主要是指員工對其部門主管所表現出的信任程度。研究發現,領導角色和行為是下屬對領導產生信任的重要因素(Dirks&Ferrin,2002)。由于基層倫理型領導公平、正直、誠信,經常與員工溝通、交流,并表現出很多人際關懷行為,因此可以對員工的領導信任產生積極影響(Brown&Trevino,2006;Den Hartog&De Hoogh,2009;Walumbwa et al.,2011)。員工信任領導,就會通過展現積極行為來維系雙方的交換關系(Dirks&Ferrin,2002),反之,則可能誘發員工實施滿足私利的不良行為來保護自己(Thau,Crossley,Bennett,&Sczesny,2007)。根據社會交換理論,倫理型領導正直、誠信,在工作中關心、支持員工,可以激發員工對領導產生較高水平的信任感,進而促使員工愿意與領導進行社會交換,愿意接受領導對自己的影響(韋惠民,龍立榮,2009),從而減少自己的反生產行為。領導認同(leadership identification)是指員工對領導產生的認同感,在本項研究中主要是指員工對其部門主管的認同。研究發現,當員工佩服其主管的某些特質和行為時就會對其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并認為能與這樣的主管共事而感到驕傲和自豪(Becker,1992)。由于倫理型領導言行一致、具有很高的道德品質、注重權力分享并積極傾聽員工的建言,應該可以激發員工形成強烈的領導認同感(Brown&Trevino,2006)。領導認同不僅表現為對領導價值觀、信念的認同,也反映為員工內化領導所倡導的行為規范并時刻嚴格要求自己(Sluss&Ashforth,2007)。當員工領導認同感較高時,就會處處表現出能體現領導信念和要求的行為;反之,員工效仿領導言行舉止的可能性較小,甚至表現出截然相反的行為。根據社會認同理論,由于倫理型領導正直、誠信、注重授權和人際導向,容易激發員工形成強烈的領導認同感,這種認同感進一步促使員工以倫理型領導的價值觀、道德準則和行為方式來定義自己,努力表現出符合倫理型領導特征的行為,從而會減少自己的反生產行為。事實上,一些學者已經指出并呼吁未來應檢驗信任、認同在倫理型領導與員工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Brown&Trevino,2006;Brown&Mitchell,2010;Mayer et al.,2012;Schaubroeck et al.,2012)。
(2)傳統性和道德同一性的調節作用。傳統性是個體遵守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程度,被認為是最能描述中國人性格和價值觀取向的概念之一(Farh et al.,1997)。中國人的傳統性體現在組織中上下級關系中,往往表現為傳統社會所強調的“上尊下卑”的角色關系與義務以及下級應無條件地尊敬和服從上級(吳隆增,劉軍,劉剛,2009)。高傳統性個體更加遵從傳統的社會角色義務,而低傳統性個體則遵從誘因-貢獻平衡原則(Farh,Hackett,&Liang,2007)。因此,面對同樣的倫理型領導,不同傳統性個體所表現出的領導信任和領導認同程度可能不同。道德同一性是指個體圍繞一系列道德特質進行的自我概化,包括象征(symbolization)和內化(internalization)兩個維度(Aquino&Reed,2002)。其中,象征維度是指個體傾向于將道德特質公開表達的程度,而內化維度是指個體將道德特質作為自我概念的程度。研究發現,象征維度和內化維度都與敵對和破壞行為直接相關(Reed&Aquino,2003),但兩者對外界信息的關注和處理方式以及隨后的行為調節方式卻不太相同(Skarlicki et al.,2008)。因此,道德同一性高低不同的員工會對基層倫理型領導的感知不同,進而導致相應的反應也會有所差別(Brown&Mitchell,2010)。綜上分析,我們認為員工的傳統性和道德同一性可能對基層倫理型領導與員工的領導信任和領導認同的關系具有調節效應。
為了檢驗上述研究內容,我們將采用問卷調查法首先采集員工對基層倫理型領導、員工自身的傳統性和道德同一性的評價數據;3個月以后,再采集員工的領導信任和領導認同的數據;再過3個月,采集部門主管對員工反生產行為的評價數;最后運用結構方程模型和跨層分析技術(HLM)對數據進行處理。
4 小結
4.1 研究模型
倫理型領導究竟如何影響員工反生產行為?由于組織中存在高層倫理型領導和基層倫理型領導,反生產行為也包括群體反生產行為和個體反生產行為,因此,弄清不同層面倫理型領導對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機制有何不同,以及不同層面倫理型領導在影響反生產行為過程中是何關系是回答這一問題的關鍵。圖1是根據上述研究內容構建的理論框架,旨在揭示三個子研究的內在機理和邏輯關系。研究1主要探討高層倫理型領導(組織層面)能否通過倫理文化(組織層面)對群體反生產行為(團隊層面)產生跨層影響,以及組織結構(組織層面)在其中是否具有跨層調節效應;研究3主要探討基層倫理型領導(團隊層面)能否通過領導信任(個體層面)、領導認同(個體層面)兩大中介機制對個體反生產行為(個體層面)產生跨層影響,以及傳統性(個體層面)和道德同一性(個體層面)在其中是否存在跨層調節作用;研究2主要將研究1中的高層倫理型領導與研究3中的基層倫理型領導和個體反生產行為串聯起來,檢驗在中國倫理型領導影響員工反生產行為的“瀑布效應”是否成立,以及個體的權力距離導向(部門主管、員工個人)在其中是否具有調節作用。三項研究彼此獨立但又關系密切,組合在一起可以較好地揭示倫理型領導對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機制。

圖1 本研究的理論模型
4.2 創新之處
本研究的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從多層次視角探討了倫理型領導對員工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本研究突破以往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基層倫理型領導層面的局限,基于多層次視角(組織、團隊和個體)不僅對高層(基層)倫理型領導是如何對群體(員工)反生產行為產生影響的進行了研究,還對高層倫理型領導通過基層倫理型領導影響員工反生產行為的“瀑布效應”進行了檢驗。從多層次視角探討倫理型領導與員工反生產行為的關系有利于全方位揭示倫理型領導對員工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機制。
第二,運用了多個理論分析倫理型領導對員工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機制。本研究綜合運用了社會學習理論、社會交換理論和社會認同理論來解釋倫理型領導對員工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機制。其中,社會學習理論主要用于解釋高層倫理型領導對員工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機制(研究1和研究2),社會交換理論和組織認同理論主要用于解釋基層倫理型領導對員工反生產行為的影響機制。基于多個理論進行的分析不僅可以說明不同層面的倫理型領導對員工反生產行為影響過程的差異,還可以揭示倫理型領導影響員工反生產行為的多條路徑。
第三,充分考慮了中國本土文化特征變量的影響。以往有關倫理型領導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進行的,缺乏對跨文化因素的分析。本研究在構建倫理型領導影響員工反生產行為的理論模型時充分考慮了權力距離導向、傳統性等中國本土文化特征變量,研究結論不僅檢驗了倫理型領導影響效能的跨文化效應,還可以充分揭示在中國倫理型領導發揮影響的邊界條件。
洪雁,王端旭.(2011).管理者真能“以德服人”嗎?社會學習和社會交換視角下倫理型領導作用機制研究.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32(7),175–179.
廖建橋,趙君,張永軍.(2010).權力距離對中國領導行為的影響研究.管理學報,7(7),988–992.
蘆青,宋繼文,夏長虹.(2011).道德領導的影響過程分析:一個社會交換的視角.管理學報,8(12),1802–1812.
莫申江,王重鳴.(2010).國外倫理型領導研究前沿探析.
外國經濟與管理,32(2),32–37.
韋惠民,龍立榮.(2009).主管認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對員工行為及績效的影響.心理學報,41(1),86–94.
吳隆增,劉軍,劉剛.(2009).辱虐管理與員工表現:傳統性與信任的作用.心理學報,41(6),510–518.
張燕,陳維政.(2012).工作場所偏離行為研究中自我報告法應用探討.科研管理,33(11),76–83.
張永軍.(2012).倫理型領導對員工反生產行為的影響:基于社會學習與社會交換雙重視角.商業經濟與管理,12,23–32.
張永軍,廖建橋,趙君.(2012).國外反生產行為研究回顧與展望.管理評論,24(7),82–90.
Aquino,K.F.,&Reed,A.(2002).The self-importance of moral identit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86(3),1423–1440.
Avey,J.B.,Palanski,M.E.,&Walumbwa,F.O.(2011).When leadership goes unnoticed:The moderating role of follower self-estee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al leadership and follower behavior.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98(4),573–582.
Avey,J.B.,Wernsing,T.S.,&Palanski,M.E.(2012).Exploring the process of ethical leadership: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loyee voice and psychological ownership.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107(1),21–34.
Bass,B.M.(1990).Bass & Stogdill’s handbook of leadership(3rded,pp.339–362).New York:Free Press.
Becker,T.E.(1992).Foci and bases of commitment:Are they distinctions worth making?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35(1),232–244.
Bennett,R.J.,&Robinson,S.L.(2000).The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of workplace deviance.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85(3),349–360.
Botero,I.C.,&Van Dyne,L.(2009).Employee voice behavior:Interactive effects of LMX and power dist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lombia.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3(1),84–104.
Brockner,J.,Ackerman,G.,Greenberg,J.,Gelfand,M.J.,Francesco,A.M.,Chen,Z.X.,Shapiro,D.(2001).Culture and procedural justice:The influence of power distance on reactions to voice.Journal of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37(4),300–315.
Brown,M.E.,&Mitchell,M.S.(2010).Ethical and unethical leadership:Exploring new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20(4),583–616.
Brown,M.E.,&Trevino,L.K.(2006).Ethical leadership:A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The Leadership Quarterly,17(6),595–616.
Brown,M.E.,Trevino,L.K.,&Harrison,D.A.(2005).Ethicalleadership:A sociallearning perspective for construct development and testing.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97(2),117–134.
Burns,T.,&Stalker,G.M.(1961).The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pp.10–31).London:Tavistock.
De Hoogh,A.H.B.,&Den Hartog,D.N.(2008).Ethical and despotic leadership,relationship with leader’s social responsibility,top management team effectiveness and subordinates’optimism:A multi-method study.The Leadership Quarterly,19(3),297–311.
DenHartog,D.N.,& DeHoogh,A.H.B.(2009).Empowering behavior and leader fairness and integrity:Studying perceptions of ethical leader behavior from a level-of-analysis perspective.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18(2),199–230.
Detert,J.R.,Trevino,L.K.,Burris,E.R.,&Andiappan,M.(2007).Managerial modes of influence and counterproductivity in organizations: A longitudinal business-unit-level investigation.JournalofApplied Psychology,92(4),993–1005.
Dirks,K.T.,&Ferrin,D.L.(2002).Trust in leadership:Meta-analytic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87(4),611–628.
Dorfman,P.W.,&Howell,J.P.(1988).Dimensions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effective leadership patterns:Hofstede revisited.Advance i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Management,10(3),127–150.
Eisenbeiss,S.A.(2012).Re-thinking ethical leadership:A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ve approach.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3(5),791–808.
Enderle,G.(1987).Some perspective of managerial ethical leadership.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6(8),657–663.
Farh,J.L.,Earley,P.C.,&Lin,S.C.(1997).Impetus for actions:A culture analysis of justice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 Chinese society.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42(3),421–444.
Farh,J.L.,Hackett,R.,&Liang,J.(2007).Individual-level culture values as moderators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employee outcomes relationships:Comparing the effects of power distance and traditionality.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0(3),715–729.
Grojean,M.W.,Resick,C.J.,Dickson,M.W.,&Smith,D.B.(2004).Leaders,values,and organizational climate:Examining leadership strategies for establishing an organizational climate regarding ethic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55(3),223–241.
Hofstede,G.H.(1984).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 in work-related values(pp.172–265).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
Kacmar,K.M.,Bachrach,D.G.,Harris,K.J.,&Zivnuska,S. (2011).Fostering good citizenship through ethical leadership:Explor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and organizational politic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96(3),633–642.
Kalshoven,K.,Den Hartog,D.N.,&De Hoogh,A.H.B.(2011).Ethical leadership at work questionnaire(ELW):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2(1),51–69.
Khuntia,R.,&Suar,D.A.(2004).A scale to assess ethical leadership of Indian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 manager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49(1),13–26.
Kirkman,B.L.,Chen,G.,Farh,J.L.,Chen,Z.X.,&Lowe,K.B.(2009).Individual power distance orientation and follower reactions to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A crosslevel,cross-culture examin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2(4),744–764.
Loi,R.,Lam,L.W.,&Chan,K.W.(2012).Coping with job insecurity:The role of procedural justice,ethical leadership and power distance orientation.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108(3),361–372.
Martin,G.S.,Resick,C.J.,Keating,M.A.,&Dickson,M.W.(2009).Ethical leadership across culture: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erman and US perspectives.Business Ethics:A European Review,18(2),127–144.
Mayer,D.M.,Kuenzi,M.,&Greenbaum,R.L.(2011).Examining the link between ethic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misconduct:The mediating role of ethical climate.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95(1),7–16.
Mayer,D.M.,Kuenzi,M.,Greenbaum,R.,Bardes,M.,&Salvador,R.(2009).How low does ethical leadership flow?Test of a trickle-down model.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08(1),1–13.
Piccolo,R.F.,Greenbaum,R.,Den Hartog,D.N.,&Folger,R.(2010).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al leadership and core job characteristics.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31(2-3),259–278.
Reed,A.,&Aquino,K.F.(2003).Moral identity and the expanding circle ofmoralregard toward out-group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84(6),1270–1286.
Resick,C.J.,Hanges,P.J.,Dickson,M.W.,&Mitchelson,J.K.(2006).A cross-culture examination of the endorsement of ethical leadership.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63(4),345–359.
Robinson,S.L.,&O’Leary-Kelly,A.M.(1998).Monkey see,monkey do:The influence of work group on antisocial behavior of employee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1(6),658–671.
Ruiz,P.,Ruiz,C.,&Martinez,R.(2011).Improving the“leader-follower”relationship:Top managers or supervisor?The ethical leadership trickle-down effect on follower job response.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99(4),587–608.
Schaubroeck,J.M.,Hannah,S.T.,Avolio,B.J.,Kozlowski,S.W.J.,Lord,R.G.,Trevino,L.K.,Peng,A.C.(2012).Embedding ethical leadership within and across organization level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5(5),1053–1078.
Schein,E.H.(2010).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4thed,pp.235–237).Hoboken,NJ:Jossey-Bass.
Skarlicki,D.P.,Van Jaarsveld,D.D.,&Walker,D.D.(2008).Getting even for customer mistreatment:The role of moral ident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stomer interpersonal injustice and employee sabotage.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93(6),1335–1347.
Sluss,D.M.,&Ashforth,B.E.(2007).Relational identity and identification:Defining ourselves through work relationship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32(1),9–32.
Spector,P.E.,&Fox,S.(2005).The stressor-emotion model of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In S.Fox&P.E.Spector (Eds.),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Investigations of actors and targets(pp.151–174).Washington,DC:APA.
Thau,S.,Crossley,C.,Bennett,R.J.,&Sczesny,S.(2007).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st,attachment,and antisocial work behaviors.Human Relations,60(8),1155–1179.
Trevino,L.K.,Brown,M.,&Hartman,L.P.(2003).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of perceived executive ethical leadership:Perceptions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the executive suite.Human Relations,56(1),5–37.
Trevino,L.K.,Hartman,L.P.,&Brown,M.(2000).Moral person and moral manager:How executives develop a reputation for ethical leadership.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42(4),128–142.
Trevino,L.K.,Weaver,G.R.,&Reynolds,S.J.(2006).Behavior ethics in organization:A review.Journal of Management,32(6),951-990.
Trevino,L.K.,&Youngblood,S.A.(1990).Bad apples in bad barrels:A causal of ethical decision-making behavior.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75(4),378–385.
Walumbwa,F.O.,Mayer,D.M.,Wang,P.,Wang,H.,Workman,K.,& Christensen,A.L.(2011).Linking ethical leadership to employee performance:The roles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self-efficacy,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15(2),204–213.
Walumbwa,F.O.,Morrison,E.W.,&Christensen,A.L.(2012).Ethical leadership and group in-role performance:The mediating roles of group conscientiousness and group voice.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3(5),953–964.
Walumbwa,F.O.,& Schaubroeck,J.(2009).Leader personality traits and employee voice behavior:Mediating roles of ethical leadership and work group psychology safety.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94(5),1275–1286.